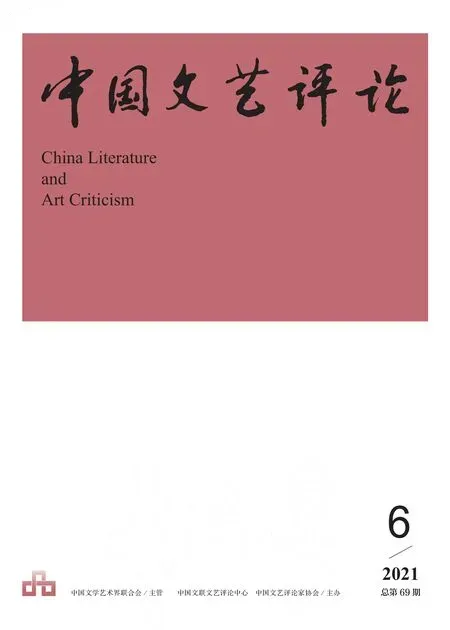戏剧“结构”中人物的立体呈现
——以当代九部历史剧作品为例
于 鹏 郭海瑾
戏剧结构是对舞台时空的组织和安排。戏剧理论家、创作者历来对结构都非常重视。情节通过结构安排展现,观众在不同的结构呈现中发现人物的各种动作。可以说,结构是撑起一部戏剧作品的骨架。
在话剧领域,历史剧指的是取材于辛亥革命之前,以真实的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和可能存在的历史人物与可能发生的历史事件为题材内容的作品。当代历史剧则是指创作于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剧作品。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北京三大剧院(国家大剧院、国家话剧院、首都剧场)复演时间持续较长的历史剧作品,可以发现,知名历史剧作家姚远编剧的《商鞅》自20世纪90年代创作至今,一直活跃在京沪两地剧院;“传神史剧”作家郭启宏笔耕不辍,作品《李白》《天之骄子》《知己》《杜甫》持续上演于首都剧场;知名导演林兆华执导的徐瑛“春秋三部曲”(《门客》《刺客》《说客》)已成为一种历史剧现象;莫言创作的《我们的荆轲》、田沁鑫改编并导演的《北京法源寺》则是近十年来颇具特色的历史剧作品。本文通过对上述作品中的九部作品进行戏剧结构的分析,探究戏剧结构与历史人物呈现的关系,以期为今后的研究和创作提供思考和借鉴。
一、戏剧结构分析的理论依据
自古至今,对“结构”潜心研究的中外理论家、创作者不在少数。苏联著名戏剧理论家霍洛道夫指出,“戏剧有它特殊的、专门的、许多世纪以来形成和磨炼过的结构规律。”戏剧结构的研究归根结底就是要找出其中规律,以便对结构进行分类,方便创作者取舍,从而为戏剧作品的舞台呈现提供最佳技术支持。不可避免的是,理论家对于结构的使用一定会依据某种前提,而这种前提本身则反映了理论家对戏剧艺术的认识和衡量尺度,如影响至今的结构“二分法”——开放式结构与锁闭式结构,等等。话剧传入我国虽刚过百年,但学者们对结构的研究成绩斐然。戏剧理论家、剧作家顾仲彝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戏剧结构进行了着重分析,提出了著名的“三分法”——开放式结构、锁闭式结构(包括回顾式和终局式)以及人像展览式结构。其中尤以“人像展览式结构”多为人所道。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孙惠柱在其《第四堵墙——戏剧的结构与解构》中提出了结构类型的“五分法”——纯戏剧式结构、史诗式结构、散文式结构、诗式结构和电影式结构,这是一种密切结合戏剧时代发展的分类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针对前文提及的当代九部历史剧作品进行结构分析,本文所采用的分类方法来自于著名戏剧理论家谭霈生在其《戏剧本体论》中所提出的三种结构类型:集中于主线路的运动形态、链条式的运动形态和并列交错的运动形态。之所以选择这种结构分类方法,是因为该分类法立足于谭霈生先生提出的“戏剧逻辑模式”:(人物)个性与情境契合,情境的推动力与凝聚力使个性凝结成具体的动机,动机则成为行动(动作)的内驱力。在谭霈生先生的结构类型阐述中,“每一种(结构)类型都与一种情境运动的特殊形态有直接关系,前者受制于后者”。历史剧的特殊性就在于其题材,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史实成为戏剧情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人物的舞台行动呈现势必要依托于具体的戏剧情境,如何组织情境便成为历史剧结构的亮点所在。因此,本文从谭霈生先生所提出的三种结构类型及其理论依据出发,分析当代九部历史剧作品,以期得出可供参考或探讨的结论。
二、当代九部历史剧作品的戏剧结构与人物呈现
(一)当代历史剧创作的主要结构方式
1.《商鞅》:一人一生的史诗大戏
谭霈生先生认为,集中主线路的运动形态所呈现的特点是,剧中情境与人物之间相契合的运动方式主要是以单线进行的。而这种单线并不是说只有一条线索,也可能是多条线索齐头并进,但有一条主线索,其他线索从属于主线索、为主线索的延展推进而服务。如大型历史剧《商鞅》通过三条线索——商鞅变法的政治线、商鞅和姬娘的命运线以及商鞅和韩女的爱情线并行推进。但这三条线索的核心是商鞅的命运线,即商鞅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帝王想称霸天下,因而他们实行变法推动了历史前进,其他线索都是商鞅命运线的依托。这是一部典型的基于历史事件铺陈结构、着重表现人物性格命运的戏剧。
《商鞅》全剧没有分幕。除开端可视为引子外,整部剧可分为20场,从第二场因为巫的预言、尚在襁褓之中的商鞅和母亲被父亲抛入大河,到最后一场商鞅被追杀、生母姬娘再次出现与儿同亡,展现了商鞅的一生。其中主要以商鞅变法图强、努力改变个人命运为主要行动轨迹,层层递进,刻画了一个刚毅果敢、锋芒在外、胸怀天下的商鞅。全剧中,只有两场戏商鞅不在场上,但他仍是场上人物行动的“目标”。其余各场戏都围绕商鞅并表现其不信命、敢作为的性格特征而展开——商鞅义母(实为生母)告诫少年的他要做一个自由人,而他却想成为人上人;少年商鞅被魏国将军公叔痤强收为义子,后公叔痤下令杀商鞅,商鞅痛斥公叔痤嫉贤妒能;商鞅赴秦后,与秦国朝廷众元老论辩“变法”;商鞅为谋光复大计、求取变法胜利而逐一“舍弃”亲朋……每一场戏的情境构成都与商鞅这一人物塑造相契合,“集中主线路”的结构特征也更加突出。不仅是《商鞅》,郭启宏的“传神史剧”、徐瑛的“春秋三部曲”大多都采用了这样的戏剧结构方式。
2.“传神史剧”:精巧布局下的“一人一事”
剧作家郭启宏创作的“传神史剧”几乎占据了当代历史剧作品的半壁江山。这不仅是指作品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作品具有的分量。近20年来,郭启宏有四部历史剧作品上演较多:《李白》《天之骄子》《知己》和《杜甫》。除了新近创作的《杜甫》在结构上有较大变化之外,之前的三部作品结构都采用了集中主线路的运动形态,但在“一人一事”的结构原则中布局却各有特色。
《李白》截取了“安史之乱”后李白立志除奸、报效朝廷的一段生命历程,着意刻画了李白心系朝堂却又不合官场的两难处境。为了更好地刻画这一时期的李白,剧作家采用了历史剧作品中少见的“锁闭式结构”。《李白》共九场戏,从第一场昂扬赴命,到最后一场悄然离世,以李白效命永王后的曲折命运为线,刻画了李白的“诗仙”本色。谭霈生先生指出,锁闭式结构“情境中总是包含着往事和人物关系的前史,它们对情节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因素又需要用某种方式交代出来。”李白曾经相救郭子仪是剧中重要的前史,且李腾空为救李白劳顿致死也隐含着他们之间超越世情的友谊,最终李白因郭子仪报恩获赦,也因“腾空子的死激起了入世的雄心”,耳顺之年毅然从军。剧中前史不仅影响了李白的命运,也决定了李白最终的人生选择。锁闭式结构与长流夜郎的情境配合得当,成就了传神史剧《李白》。
《天之骄子》的主人公是曹植。剧作家以曹操立太子为剧情开端,径直将曹植推到决定其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此为“起”;在太后卞氏的干预下,曹丕未能杀掉曹植,曹植被贬雍丘为王,此为“承”;曹植郁郁不得志,落魄酗酒,曹丕撞见后怜惜不已,兄弟情深令曹植决定放弃帝王心,此为“转”;曹丕兵败,流言四起,曹植执意献刀以表忠心却遭曹丕疑恨,甄皇后、二哥曹彰、侍妾阿鸾均被曹丕杀害,曹植悲痛欲绝,追问先王曹操兄弟二人谁应为王,曹操答曰,“可以作梁的作梁,可以作柱的作柱”,此为“合”。起、承、转、合,四幕结构了一部生于帝王家的诗人的命运大戏,也由此呈现出了一个才华尽显、锋芒毕露却报国无门的天之骄子形象。
《知己》更是有着精巧的结构布局——以“寻”为轴,首尾呼应,主线、辅线并行统一,该剧的主题是对“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知己(君子)之交寻而不得。顾贞观视吴兆骞为知己,吴兆骞因科场舞弊受牵连流放宁古塔,顾贞观为救吴兆骞回京甘心入相府做西席,忍辱负重、屈膝偷生,只为求得明珠出手救出吴兆骞,这是“寻”知己的主线;纳兰性德虽生于权贵相府,因为仰慕顾贞观且“一见如故、相知恨晚”,无怨无悔地帮顾贞观求助、催促父亲明珠,这是“寻”知己的辅线。第一幕吴兆骞于茶馆等顾贞观不得,去了宁古塔,是为“首”;尾声顾贞观于茶馆回江南老家,吴兆骞寻而未得,是为“尾”;两厢不得见,首尾呼应。从第二幕顾贞观入相府已数年之久开始,苦苦等待的过程煎熬着顾贞观与其身边人,及至第三幕第五场吴兆骞终于从宁古塔回来,却已非当年的狂傲书生,猥琐之态令顾贞观黯然离去,这便是该剧的高潮所在。而后吴兆骞在纳兰性德的“敲打”下尽管有所醒悟,却已不复从前。所以,纵使再寻顾贞观,也是寻而不得。这一部追寻知己的历史剧,真正写尽了文人的追求与辛酸。
3.“春秋三部曲”:“写意”时空中的历史主角
历史剧作家徐瑛的“春秋三部曲”,《刺客》《说客》上演较多,本文即以这两部为例,分析剧作家徐瑛赋予“春秋”的一段写意时空。
《刺客》的主人公是豫让,他在剧中的行动是为主人智伯报仇,刺杀赵襄子。这部含有序幕的两幕剧便是以豫让的刺杀行动为轴,场场递进,人物性格逐步展开。剧作从赵襄子得胜杀智伯及其门人、留下豫让开始,刻画了一个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人物形象。豫妻的劝说、絺疵的谋定而后动,也依然不能打动他“直接”刺杀赵襄子的决心;刺杀一次未果,易姓更名服劳役、假扮商贩,不断接近目标,再行动,甚至在自己好友絺疵坟茔处依然要完成刺杀行动;新仇旧恨,不惜自毁音貌都要刺杀赵襄子,最后行动失败,舍生取义,自尽身亡。可见,“义”在豫让心中是崇高的,他说“君臣相交,唯以义合”;豫让的“义”在于执行力,也在于他的从容淡定,认定目标便勇往直前,哪怕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
《说客》的主人公是子贡,子贡在剧中的行动是游说各国。齐国仗势进犯鲁国,为保国家孔子派子贡游说齐国退兵,子贡以“利”利导,相继说服齐国放弃攻鲁、吴国攻打齐国、越国随吴打齐、晋国备战吴国,以致战争泛滥,唯独鲁国自保,全面展现了他巧舌如簧、能言善辩且善于变通的人物形象。
从戏剧结构的角度,《刺客》《说客》都是并不复杂的线性叙事,随着行动的开端、发展、高潮、结局顺次进行。相比“传神史剧”精巧的布局,“春秋三部曲”的结构简单得近乎直白。那么,令导演林兆华倾心于“春秋三部曲”的原因在哪呢?一方面,一人一事、随事件发展直线推进的运动形态最为大众熟悉并接受;另一方面,为了表现剧本主题,剧作家对作品中时空的“写意”处理给予历史剧的舞台极大的表现空间。除了基本的史实背景设定,剧作家在剧中对具体时间、地点都予以“留白”,这种艺术的想象空间既留给了导演,也留给了观众。
(二)历史人物更丰富的生命运动轨迹
1.链条式的运动形态:多时空的立体呈现
与集中主线路的运动形态相比,链条式的运动形态突出的是相对独立的每一场戏。“全剧有统一的主人公(亦可没有),一般分成诸多场戏,每一场都有一个新的、相对独立的情境,内在于情境的悬念在一场戏中生成、发展,直到解开,使这一场戏自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元;而场与场之间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结(或用统一的主人公,或用贯串全剧的总悬念),使全剧环环相扣,形成链条式的统一体。”历史剧是否也可以以这种方式呈现呢?《我们的荆轲》《杜甫》两部作品做出了大胆尝试。
《我们的荆轲》讲述的是“荆轲刺秦”的故事。从第一节“成义”到第十节“刺秦”,每一节(每一场戏)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尽管十场戏之间有明确的逻辑关系,即对刺秦的层层准备与推进,但是各场戏的独立性却十分鲜明。而让这各场戏都串联起来的便是主人公荆轲。他在每一场戏中与不同的人物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这与刺秦相关的一众人等的轮番登场,从不同程度上促使了刺秦行动的最终发生。荆轲的人物形象,也正是在这些关系中被多层次地建立起来:从一个志向高远又自视清高的剑客,到朋友以性命相交且受命于太子丹的徘徊,再到挟制于名、决心刺秦的彷徨,最后到刺而不杀、留名千古的侠士……剧作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了“荆轲刺秦”这一历史故事,全面展现了一个有着复杂动机且犹豫不定、使得行动迟缓付诸的荆轲。颇具意味的是,剧作前九节着重表现了荆轲筹备刺秦的过程,而最终实现的“刺秦”仿佛是一场预定的表演,竟感觉不到半点儿侠客精神。曾经跟随荆轲一起谋划刺秦大计的田光、燕姬、秦舞阳、狗屠、高渐离,随着刺秦大计的实施与结束或自杀、或被杀,无一幸免。一场史上轰轰烈烈的“刺秦”就这么结束了。
链条式运动形态的结构方法,将不同的历史场面连结起来,使所塑造的主要人物相对独立又与其所处环境、所关联的次要人物以及事件紧密联系,不流于概念化,而是更为立体、生动。无独有偶,郭启宏最新创作的历史剧《杜甫》也采用了这种链条式的运动形态。
剧作《杜甫》的七场戏相对独立又息息相关。“序幕”中,杜甫与李白、高适、严武一起饮酒作诗,主要人物——杜甫“亮相”,呈现了一个诗才横溢又时时关心着国事的文人形象。每场戏中,杜甫始终在场。他与妻子杨氏“拌嘴”,道出了一个正身处窘境、生活困顿却心系国家的杜甫,也为之后的人物轮番上场埋下伏笔。杜甫与严武相见意欲谋求一官半职,因看不惯严武的官场手段,两人不欢而散;高适、严武先后前去探望,高适借请杜甫代笔送去生活补贴,严武则推荐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入幕严府,成为严武的参谋;满心欢喜的杜甫,与严武又因“章八之死”相互指责、剑拔弩张,杜甫愤而离职;赋闲在家、退居草堂的杜甫,郁郁寡欢,苏涣来访,为其解惑,杜甫心生佩服;是时,所处茅屋为秋风所破,为此诗兴大发,遂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纵观全剧,一代“诗圣”杜甫才情卓越、心怀民生、仕途不济、真实坦诚,整体形象跃然而出。杜甫这一人物形象正是在与不同人物关系的七场戏中表现出来的,且每一场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充分展示出历史剧的魅力。
从《李白》到《杜甫》,一位“诗仙”、一位“诗圣”,剧作家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戏剧结构去呈现人物,这不仅体现出剧作家对剧中人物的思考和揣摩,也表明了剧作家在时代进程中于戏剧技巧上的变化。
2.并列交错的运动形态:历史中的“群像”
九部历史剧中,《北京法源寺》无疑是最独特的一部。这部改编自李敖同名小说的戏剧作品,在戏剧表达上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历史剧作品。《北京法源寺》讲述的历史事件是“戊戌变法”,在戏剧舞台上,相关涉事人悉数登场,或畅言、或倾诉、或指责、或哀叹。观众看他们,既在戏里,又似戏外。
谭霈生先生对这种戏剧结构如是总结:出场人物较多,却没有统领全剧的中心人物;其中较为重要的人物虽有自己的行动线,但却难分主从;与分散的人物相契合的是,情境也是分散的,它们的运动亦不汇合成统一的主渠道,而是分流成一条条小溪;内在于情境的悬念也是各有指向的,有时相互并列,有时此隐彼现……一般地说,这类作品多以塑造群像为己任,以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生命活动汇聚成总体性的内在意义。
1921年,时任法源寺方丈的普净是1898年“戊戌变法”时寺内方丈佘云大师的徒弟,在李敖原著中,他跟随师父一起敬仰康有为、支持谭嗣同,在戏剧舞台上,他带着自己的徒弟重访当年。这种穿越时空的方法也被称为电影式结构,但是这种结构还不足以概括《北京法源寺》,因为《北京法源寺》打破时间界限的目的在于统一空间。只有在同一个空间内,才能实现方丈普净、小和尚异禀与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光绪、慈禧、李鸿章、恭亲王、荣禄、刚毅、李莲英、袁世凯等诸涉事人共处一台,随时切换,自由对话,畅所欲言。由此,“把事件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和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对之产生惊讶和好奇心”。这种“陌生化效果”,应该是编剧田沁鑫想要的现代人的历史态度:面对“戊戌变法”,面对晚清,我们不能一味地痛恨、责骂、惋惜,这都是感情用事;我们需要理性思考当时的境况如何,涉事人各自所为何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就像剧中“尾声”处“众人”所说:“解决中国问题,就是要寻找出路,任何障碍中国寻求发展的人,都必须回避”。这也是站在1921年的方丈与小和尚追寻往事的意义,这一年,有位名为“毛润之”的小施主来到了法源寺……剧作到此,也完成了以独立个体生命活动来凸显群像的任务。
三、戏剧结构:最重要的戏剧思维方式
历史剧的使命是历史人物的呈现,人物呈现得如何可以通过结构方法的运用获得一些思考。纵观戏剧发展史,随着时代进步和思想解放,戏剧结构在一代代剧作家的努力下不断出现新的尝试。然而,在戏剧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历史剧却鲜见其中。或许是中外剧作家(包括创作了多部历史剧的莎士比亚)在面对历史史实时都会不由自主地多一些审慎、少几分随性,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同样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结构予以呈现,而不同结构中的历史人物必然会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审美体验。
比如,唐代两位大诗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剧作家郭启宏的呈现方式迥然不同。李白的性格与命运集中呈现于他一心报国投靠永王却被误判为“附逆作乱者”的一段生命历程,杜甫的性格与命运则是在不同的人物关系(严武、高适、苏涣)中显现出来的。再看,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两位侠客——荆轲和豫让,莫言写荆轲的成侠之路,朋友(高渐离、秦舞阳、狗屠)、贵人(田光、太子丹)、红颜知己(燕姬)轮番登场,各自给予荆轲不同的影响,以致荆轲的刺秦决心犹豫不定,踟蹰成行;徐瑛笔下的豫让,则不受任何干扰和阻挠,为刺杀赵襄子一而再、再而三穷尽方法,直至自尽身亡。还有,结果不同却一心致力于变法图强的商鞅和谭嗣同,《商鞅》集中展现了商鞅的一生为何立志变法、又如何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毅然前行;《北京法源寺》却要从朝堂、恩师、挚友、奸雄、和尚等众群像的展示中才能窥见谭嗣同一心向死的决绝。正如谭霈生先生所言,为了表现一个人的一生,可以从其一生中精选一个片段,从中折射出这一人物的精神世界的深度与广度;创作者如果感到用这种结构方式不足以充分表现其灵魂的深邃,就需要在丰富的素材中进行选择、加工,把几个相对独立的片段剪辑成篇——这正是我们所说的“链条式的结构类型”。
从本文所选取的九部历史剧作品来看,虽然集中主线路的结构仍然是当代历史剧结构的主要方式,但是在集中主线路的结构布局中,剧作家已然凸显出各自的风格特征。如剧作家郭启宏非常讲究布局,从20世纪90年代的《李白》,到新世纪的《天子骄子》《知己》,剧作家在每部作品中都采用了不同的结构方式:锁闭式、起承转合、首尾呼应、主副线统一等,精巧的布局不仅增强了作品的戏剧性,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更是起到了直接的架构作用。与此相较,另一位剧作家徐瑛的“春秋三部曲”尽管也采取了集中主线路的结构,具体布局却另有一番景致。从上演较多的《刺客》《说客》来看,徐瑛的历史剧注重线性叙事,以时间为轴,讲究事件的逻辑推进。在“集中主线路”之外,当代历史剧突破性地出现了“链条式”和“并列交错”两种结构形式。“链条式”突出的是相对自由的小场面,“并列交错”则意在塑造群像。毫无疑问,戏剧结构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服务于戏剧目的——“塑造人物形象”,然而,剧作家处理剧情和性格的方法取决于那些在剧作家所属的阶级和时代中流行着的观念。当代剧作家的创新意识毕竟给历史剧增添了新的景象。从舞台呈现来看,不同于集中主线路的戏剧结构给予历史剧与以往不同的感官印象,历史人物形象也因此极具时代特征。这才是现代观众想要看到的历史剧。
谭霈生先生认为戏剧的逻辑模式是:情境与人相互作用,引发动机,导致行动。其中,“做什么”意指“行动”,“为什么做”则是指“动机”。于是,决定情境运动形态的结构决定了剧本人物“如何做”,即如何行动。这就是历史人物在结构中的(行动)呈现。
相较于其他戏剧,历史剧的独特即在于题材。这是由于观众对历史人物或多或少地了解与熟悉,使得历史剧中剧本人物如何呈现行动(为什么做、如何做)较之行动本身(做什么)更具吸引力。在看《天子骄子》之前,我们已然知道曹植争位无果,但是曹植如何放弃、又如何面对?在看《杜甫》之前,我们也知道杜甫一生穷困潦倒,可是这样一位才子怎么会有此境遇?晚清,一段力挽狂澜的“戊戌变法”已被艺术演绎过无数次,《北京法源寺》又当如何展现?这些疑问,无一不表明历史剧的结构(呈现方式)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因此,在历史剧中,戏剧结构决定了历史人物(剧本人物)的呈现方式,而呈现方式的优劣直接决定了历史剧的时代性与观众认可度。诚如傅谨在《〈说客〉:面对历史的一种姿态》中所言,“对历史的认知和把握是娴熟地驾驭历史题材的重要基础,更进一步需要的是对历史深层次的思考,而更为可贵的是从编剧到导演的戏剧思维,只有当编导的戏剧思维与历史观念恰好形成互补和对应,我们才会看到像《说客》这样的成熟之作。”可见,戏剧结构应该是历史剧作家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戏剧思维方式。
四、结语:另一种解读历史人物的方式
基于对当代九部历史剧的结构分析可以看出,剧作家根据人物及其特定情境的不同,其所选择的结构方式也不尽相同。一直以来,就历史剧而言,结构似乎处于一种微妙的境地:一方面,观众对于历史的经验认识通常是以时间为序,诸如一个朝代的更替、一段史实的推进,由此,历史剧的结构似乎不存在多样化的选择。另一方面,在观众走进剧院之前,对历史题材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诗仙李白其人、商鞅变法其事。因此,观众对即将上演的剧目便有了别样的期待:剧作家将如何呈现李白?如何讲述变法?究竟是以惯性的时间流逝为轴,还是有其他的叙事角度?不同结构中的动作对于塑造人物是否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一点,在影像时代的历史剧作品(20世纪90年代以来繁荣发展的影视历史剧)中有更强烈的诉求。鉴于此,结构对于历史剧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历史人物有特定的情境,情境的构成及其变化决定剧作家选择何种结构。纵观以上所分析的九部历史剧,尽管剧作家所使用的结构方式不同,但他们对历史剧创作、对历史人物、甚至是对历史都有着深刻的思考,也带给我们一些重要启示。
就历史剧创作而言,剧作家们不断打破旧有模式,不拘一格,从历史人物本身及其所处的情境出发找寻能立体、生动再现人物的方法,是历史剧创作带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如郭启宏创作的《知己》,剧作家敏锐地发现顾贞观与纳兰性德的“共同点”——可舍身为知己,主题呼之欲出;然而两人在年龄、身份、学识等方面有所差距,如何呈现他们这一共同点呢?剧作家选择了特定情境——“丁酉科场案”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这一事件使两人相识,借一主一次两条线索,将二人串联起来,突出主线索,强化知音难觅、知己难寻的主题。
就历史人物而言,剧作家既不为古往今来的评论所干扰,又不“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们以开放的眼光、现代人的角度来审视或解读历史人物的思想和格局。如“荆轲刺秦”的历史故事被传颂至今,大多褒扬的是荆轲重义轻生、勇于牺牲的崇高品格,他给人们留下的是一个英雄形象。但在剧作家的笔下,荆轲变成了一个与“我们”贴近的人物,他会信守与朋友的承诺,但对刺秦事件却有了犹豫、迟疑甚至是抉择等等,这些都不再那么崇高,可以说这是一个专属于剧作家本人的“荆轲”,又是一个与“我们”有着近距离的“荆轲”。对历史人物的重新定义或解读,是历史剧创作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发。
如果说历史剧创作最重要的是剧作家的创作方式和态度,那么它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回看历史、重新审视历史的方法论。如《北京法源寺》,它让我们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去重新审看中国近代史上那场凛冽的变法,对于今天的我们既新鲜又重要。“戊戌变法”结束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人经历了无数血雨腥风的战争、现代化的洗礼,如今回望,是否有足够的判断力重审当事人?文学原著作者李敖把“戊戌变法”置入佛法之境,以一座法源寺(原名悯忠寺)说尽唐、宋、元、明、清几代忠臣,描绘了谭嗣同如何在这里收获内心的平静。编剧田沁鑫做戏剧改编时,在充分尊重原著哲理思辨的基础上,突出直接参与“戊戌变法”的人物群像,弱化佛法悟道,法源寺在这里成为了一个超越时空的舞台,1921年的方丈及一众和尚对话了1898年“戊戌变法”的当事人。这不仅是历史剧《北京法源寺》突破常规结构布局的一种精妙做法,也留给我们对戏剧创作、对历史史实更多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