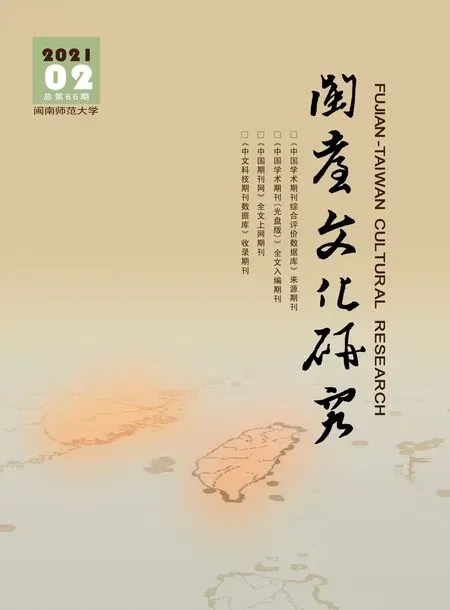力争毫厘间 万里或可勉
——《王阳明与福建》值得商榷的若干问题
张山梁
(中共平和县委宣传部,福建 漳州 363700)
一、缘 起
王阳明一生曾有“两次半”入闽,故与福建颇有渊源。正德年间,王阳明担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总制汀、漳两州军政长达四年有余。期间,他曾亲履闽粤交界的漳南地区,平息“山民暴乱”,并奏设平和县,强化地方社会治理和人心教化。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在八闽大地悄然兴起,成为一时风尚。因此,在当下国内“阳明热”的大背景下,挖掘、厘清、研究王阳明与福建的关系,自然成为热门话题,而编撰出版相关书籍更是人们趋之若鹜的事。
2020 年11 月,一部由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周建华、刘枫编著的《王阳明与福建》正式出版,公开发行。该书的出版发行,对于福建省挖掘、传承、弘扬阳明地域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引起国内阳明学界的关注。正如新书首发式的新闻报道所言:《王阳明与福建》是福建阳明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全书共18章,内容体系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阳明汀漳平叛,雷霆出击,荡平数十年盗贼;奏设平和县和巡检司,强化当地治安,奉行安民乐业之长策。第二部分写阳明心学入闽,由其后学积极传布和弘扬,心学在福建扎根生长,硕果累累。第三部分附上阳明奏疏、公移、诗,把与王阳明和王学相关的福建人、事汇编在一起,展示阳明莅闽、传道建功的生动文字记录。
作为福建阳明学爱好者,本人对此书的出版发行甚感欣慰。省政协文史委作为“组织政协委员及其所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推动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资料的征集、整理、研究、编辑及对台港澳和海外的史料交流工作”的机构,善于借助外力外智,聘请两名江西学者编著《王阳明与福建》(以下皆简称为“该书”),说明福建省有关方面对于挖掘、研究福建阳明地域文化这一工作的重视。幸哉!快哉!这无疑传递一个良好的信号,在福建开展阳明文化学术活动将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氛围与良好的环境。
然而,该书在公开发行后不久,不少国内阳明学界同行时常来电、来微信告知该书的一些学术“硬伤”问题,这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为此,本人认真拜读该书,并加以考究探微,发现书中的确存在一些瑕疵谬误,故初略汇总为若干问题,期待与该书两位编著学者商榷,以期辨明是非,存真去伪,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学案。
二、商榷内容
(一)平和建县时的县域及县名之由来
该书《前言》及第四章《初战漳州,设平和县》均认为:王阳明析南靖、漳浦县地置县,属漳州府,治所河头大洋陂(今属九峰镇)。县名“平和”,取“寇平民和”之意。
窃以为此观点有两个误点:一是新添设的平和县,并无析漳浦县之地而置;二是县名“平和”,并非取自“寇平民和”之意。
王阳明在平定漳南地区“山民暴乱”后,先后于明正德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1517年6月26日)、十三年十月十五日(1518 年11 月17 日)两度向朝廷呈交有关添设平和县的奏疏。在最初向朝廷建议《添设清平县治疏》中,王阳明的确采纳了福建按察司兵备佥事胡琏“将南靖县清宁、新安等里,漳浦县二三等都,分割管摄”建议,将其写进奏疏之中。但在次年上奏的《再议平和县治疏》中,却又采纳福建布政司转达漳州知府钟湘的意见:“原议漳浦县二都二图、三都十图,地方隔远,民不乐从,今议不必分割”,尊重州府、民众的意愿,没有将原议的“漳浦县二都、三都”割析给新添设的平和县。在之后的明嘉靖九年(1530),朝廷“析漳浦县二、三、四、五都为县,名曰诏安”。因此,该书“王阳明析南靖、漳浦县地置县”一说不确。
在《添设清平县治疏》时,王阳明所起的县名并非“平和”,而是“清平”;次年(1518),王阳明采信漳州知府钟湘“照得县名须因土俗,本职奉委亲历诸巢,询知南靖县河头等乡,俱属平河社,以此议名平和县”的意见,而“名平和”。可见,平和县名是尊从“以地名县”约定俗成之律,以县治所在地属“平河社”而得名。
至于“寇平民和”乃源于“寇平而人和”演变而来。此语出自王阳明弟子马明衡应平和知县王禄之邀撰写《平和县碑记》:“天子可其奏,谓地广民顽,即若居南靖之半,分理得入,将寇平而人和”。可见,“寇平民和”是马明衡对“平和”县名的理解与诠释,并非“平和”县名的取名之意。因此,该书“县名‘平和’,取‘寇平民和’之意”一说,疑是编著者的曲解与误读。该书在其它章节中还认为:“王阳明奏设平和县,取寓意‘寇平人和’‘平定咸和’‘平政和民’”,这些,都是如同一辙的揣摩、误解,并不是县名“平和”的取名原意。
(二)王阳明与平和县衙、城隍庙等的关系
该书《前言》及第四章《初战漳州,设平和县》均认为:多才多艺的王阳明亲自设计了平和县县衙和城隍庙等建筑项目,并主持了这批建筑的破土动工仪式——祭告“社土”(土地神)。
对此,窃认为有两个不实之处:一是平和县衙、城隍庙等建筑项目并非王阳明亲自设计;二是王阳明并没有主持平和县衙、城隍庙等建筑项目的破土动工仪式。
据载,王阳明于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初从漳州撤兵;四月戊午(十三日)班师回到上杭县。之后,再也没有来过漳州地区。《添设清平县治疏》是王阳明回到赣州巡抚衙门之后的五月二十八日拟制,并向朝廷呈报的。有关县城建设规划,王阳明在《疏》中只是采纳福建按察司兵备佥事胡琏对漳州府的批语:
就于建县地内预行区画街衢井巷,务要均适端方,可以永久无弊;听从愿从新旧人民,各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县治、学校、仓场及一应该设衙门,姑且规留空址,待奏准命下之日,以次建立。
另从《再议平和县治疏》中的记述可知,动工开建平和县城是在户部答复《添设清平县治疏》具题“奉圣旨:是。这添设县治事宜,各依拟行”之后的事。此时的王阳明正在江西积极谋划征剿横水、桶冈等地“山贼”,自然无暇顾及平和县城建设一事。再说,区区一县治之建设区画,何须劳驾巡抚?因此,该书“多才多艺的他(王阳明)亲自设计了县衙和城隍庙等建筑项目”,并非事实。或许是编著者采信了平和当地老百姓一种以讹传讹的“传说”而杜撰罢了。
在《再议平和县治疏》中,王阳明引用了福建布政司转呈漳州知府钟湘的报告:“于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1517 年12 月21 日),本职督同各官亲到河头,告祀社土,伐木兴工”。显然,《疏》中的“本职”是指“漳州府知府钟湘”,而非“王阳明”。
那么,开建平和县城的十二月初九日,王阳明到底在哪里?据明人钱德洪《王阳明年谱》记述: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班师。师至南康,百姓沿途顶香迎拜。
今人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篇》直截了当地载述: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九日,设茶寮隘,刻平茶寮碑,班师回赣。有奏凯诗咏。
而王阳明自己在给朝廷上奏的《横水桶冈捷音疏》中,则是明确提到:
是月(十二月)初九日回军近县,以休息疲劳;候二省夹攻尽绝,然后班师。
无论是钱德洪的《年谱》记载,还是王阳明本人的奏疏记录,都明确载明:明正德十二年(1517)十二月初九日这一天,王阳明并没有专程赴闽参加平和的相关活动,而在江西是奔波疲于处理横水、桶冈战役的诸多善后事宜,根本不可能分身前往漳州平和,更不可能参加该书所述“主持了这批建筑的破土动工仪式——祭告‘社土’(土地神)”的仪式。
(三)朝廷改命王阳明“提督军务”的时间
该书第四章《初战漳州,设平和县》认为:
王阳明这次(漳南战役)获得大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调兵大权——旗牌。有了旗牌,王阳明就可以不必千里请战,可以根据战场形势,随机训练和调度部队,王阳明提出: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处山岭相连,而地分各省,事无统属,彼此推托,只设巡抚一员,“责任不专”“军伍无制”,以致盗贼“东追则西窜,南捕则北奔”。为加强军权,请求朝廷给旗牌,提督军务,便宜行事,兵部尚书王琼“使从其请”。
对于该书所持的这一观点,窃以为编著者对“朝廷给旗牌,提督军务”一事,存在时事颠倒的误区。
王阳明在“漳南战役”中,朝廷并未授予“旗牌”,而是通过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教训,认为要彻底平剿盘踞在闽赣粤湘四省边界山区的“山贼”,必须解决“任不专,权不重,赏罚不行,以至于偾军败事”的问题,进一步申明赏罚制度,恳请朝廷给予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同时要进一步改革巡抚机制,改变“虽虚拥巡抚之名,而其实号令之所及止于赣州一城,然且尚多抵牾。而南赣地连四省,事无统属,事权不一,责任不专,巡抚只能处于无事开双眼以坐视,有事则空两手以待人”的尴尬境地,改命提督,授予兵权,才能一举荡平“山贼”。
五月八日回到赣州后,王阳明乘着“漳南战役”首战胜利的喜悦,当即拟制上奏《闽广捷音疏》《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向朝廷禀报“漳南战役”的胜利捷报,同时建议皇上能够“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悯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愤之莫伸;特敕兵部俯采下议,特假臣等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同日,王阳明还特地修书一封,致札兵部尚书王琼,恳求“授之以成妙之算,假之以专一之权,明之以赏罚之典,乞加劝赏”。这一请求,得到王琼的鼎力支持,才拥有“旗牌”的调兵大权。据《国榷》载:“(正德十二年七月)庚寅。巡抚南赣汀漳左佥都御史王守仁提督军务。给符帜。俾便宜行事。”
九月十一日,王阳明向所辖“八府一州”的各大小衙门发出通告《钦奉敕谕提督军务新命通行各属》,告知:
改命尔(王阳明)提督军务,常在赣州或汀州驻箚,仍往前各处巡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军马钱粮事宜,俱听便宜区画,以足军饷……其管领兵快人等官员,不拘文职武职,若在军前违期,并逗留退缩者,俱听以军法从事……其有贪残畏缩误事者,文职五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径自拿问发落。
很明显,朝廷改命王阳明为“提督军务”的时间,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十六日;王阳明通告各府、卫、所、县大小衙门的时间,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十一日。这两个事关王阳明改命提督军务的时间节点,均落后于其“漳南战役”班师回上杭的时间:四月十三日。也就是说,王阳明是在“漳南战役”之后上疏奏请,并得到朝廷许可,才被改命为“提督军务”,也才拥有朝廷所赐予“令旗令牌”之权力。因此,该书认为王阳明在漳南战役“获得大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调兵大权——旗牌”的观点,谬误之谈,与史实相距甚远。
(四)王阳明在漳州作战过程中的若干具体史实
该书第四章《初战漳州,设平和县》认为:
在平和,王阳明曾碰到许多不如意之事,如第一个小战役,身先士卒,靠前指挥,犯险突进,差点受伤。他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慎重用兵,慎重用事,终于取得漳南之役的全胜。
该书这段文字所举的例子并非事实。文中所举的“第一个小战役”是指福建官兵救援广东的“大伞之役”。其时,王阳明并未率兵入闽,何谈“身先士卒,靠前指挥,犯险突进,差点受伤”?所谓的“受伤之人”并非王阳明,而是大溪哨指挥高伟。
据《闽广捷音疏》记载:
据福建按察司整饬兵备兼管分巡漳南道佥事胡琏呈:……行据大溪哨指挥高伟呈报,统兵约会莲花石官兵攻打象湖山,适遇广东委官指挥王春等领兵亦至彼境大伞地方。卑职与指挥覃桓、县丞纪镛,领兵前去会剿。不意大伞贼徒突出,卑职等奋勇抵战。覃桓、纪镛马陷深泥,与军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静等八名,俱被贼伤身死,卑职亦被戳二枪。
王阳明在上报《闽广捷音疏》的题头,就开门见山说明该捷报是“据福建按察司整饬兵备兼管分巡漳南道佥事胡琏呈”,也就是说,该军情战报信息的来源是胡琏向王阳明呈报的;而胡琏在呈报战果时,又明确指出是“据大溪哨指挥高伟呈报”,原文引用高伟的战报内容。很明显,此战情信息内容的出处是,胡琏根据大溪哨指挥高伟上报的战况转报给王阳明的。如此一般,此处的“卑职”,所指的并非王阳明,而是战况最初呈报人“高伟”的自称。
王阳明不仅在《闽广捷音疏》提及此事,在《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案行领兵官搜剿余贼》中,也多次提到此事。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贼》曰:
随据参政陈策等呈:“据镇海卫指挥高伟呈,指挥覃桓,县丞纪镛,被大伞贼众突出,马陷深泥,被伤身死”等因到院……今据前因,参照指挥高伟既奉差委督哨,自合与覃桓等相度机宜,协谋并进;若乃孤军轻率,中贼奸计,虽称督兵救援,先亦颇有斩获,终是功微罪大,难以赎准。
《案行领兵官搜剿余贼》又载曰:
续据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道右参政等官艾洪等呈:“据委指挥高伟呈称,督同指挥等官覃桓等领兵克期夹攻,不意大贼众突出,陷入深泥,被伤身死;广东官兵在彼坐视,不行策救。”呈详到院……
本院即日自漳州起程前来各营督战,仍与各官备历已破诸贼巢垒,共议经久之策。钞案。
王阳明在这两份公移中,分别引用了陈策、艾洪两位官员依据高伟呈报的战情资讯,进行部署征讨事宜。在引用时,王阳明特别注明“据指挥高伟呈”的消息来源渠道。这就进一步说明“第一个小战役”中,差点受伤的是“指挥高伟”,而非王阳明。此外,王阳明在《案行领兵官搜剿余贼》中,明确提到“本院即日自漳州起程前来各营督战,仍与各官备历已破诸贼巢垒,共议经久之策”的具体行程路线、时间、任务,也就是说,王阳明启程前往“漳南战役”的前线时间是在发生指挥高伟“被戳二枪”的“第一个小战役”之后,出发点是漳州。
综之,该书认为“在平和,王阳明曾碰到许多不如意之事,如第一个小战役,身先士卒,靠前指挥,犯险突进,差点受伤”的言论,既有张冠李戴之嫌,又有时序颠倒之误,是无稽之谈。
(五)平和县城隍庙奉祀的神灵身份及其级别
该书第四章《初战漳州,设平和县》认为:
漳汀城隍庙本为县一级,但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初立县治,王阳明提议提高级别,为府一级建制。至于城隍庙的供奉,王阳明定了王维。
对于该书的这一观点,窃认为有两个错误:一是时至今日,漳汀城隍庙并无“府级建制”一说,所谓“王阳明提议提高级别,为府一级建制”更是子虚乌有之事;二是“城隍庙供奉的是王维”,并非王阳明所定,而是参照位于九峰的平和城隍庙的民间说词,该说法乃源自1923 年平和县长的一次“扶乩”。
在封建社会,县治所在地除了官署之外,城隍庙是必备的设施。因此,在明正德十二年底至十三年(1517~1518)期间,漳汀巡检司的城隍庙与县治所在地的平和城隍庙一同开建,其神位牌为“敕封显佑伯御城隍尊神、内宫太夫人神位”。应该说,这一神位的摆设,基本符合明代对于城隍之祀的相关规定。《明史·礼三》有记:
城隍是保,甿庶是依,则前代崇祀之意有在也。今宜附祭于岳渎诸神之坛。乃命加以封爵。京都为承天鉴国司民昇福明灵王,开封、临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为王。其余府为鉴察司民城隍威灵公,秩正二品。州为鉴察司民城隍灵佑侯,秩三品。县为鉴察司民城隍显佑伯,秩四品。衮章冕旒俱有差,命词臣撰制文以颁之。
目前,漳汀巡检司城隍庙的神位牌标明为“显佑伯”,也就说明其属县级城隍,并无出现“府级建制”的逾制现象。所谓“王阳明提议提高级别”一说,更是无据可查,只是地方民众为了自我吹嘘、抬高地位而编造的“故事”而已,不足以采信入书!
从目前存世的文献资料来看,王阳明并没有将漳汀巡检司城隍庙供奉者定位王维。至于这一说法,乃是近年来随着“阳明热”的产生,当地百姓参照平和城隍庙的民间传说而以讹传讹的,同样不足以采信入书!而平和城隍庙有关“供奉者为王维”的民间传说,实源自1923 年的一次“扶乩”。《平和城隍庙庙史》记云:
1923 年,城隍乩童曾兆伦起乩,书云:“吾系王维,大高爷乃高云中也。”当时在场的朱念祖先生(时任平和县长),对此将信将疑:“王维乃唐朝大诗人,怎么会是城隍爷呢?”为了解开这个谜,他决意与城隍爷试一试对联。
……从此他从怀疑的态度,变为对城隍爷的威灵显赫口服心服,马上手捧长香,朝拜城隍尊神。
从中可见,“城隍庙供奉者为王维”这一说法是起于1923 年的那次县长“扶乩”,而非王阳明所定。退一步讲,假若“城隍庙供奉者为王维”是王阳明定的,那么,当时作为县长的朱念祖先生必是笃信无疑的,怎么会有将信将疑的态度呢?很明显,所谓“城隍庙供奉者为王维”并非王阳明所定,而是民间在“扶乩”之后的一个口口相传的故事而已,不可嫁接到王阳明身上而载入史册。
(六)王阳明从漳南班师返赣行至汀州的时间
该书第五章《得胜述怀,军功吾心》认为:
明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七日,王阳明行至汀州,接徐爱来书,告买田霅上待耕,王阳明有诗答之。
该书的这一表述,存在时间上的差错,应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十七日”,而非“明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七日”。
明正德十二年(1517),王阳明从漳南战役前线班师返赣,先到上杭略作休整,再经长汀回赣州。无论是在《书察院行台壁》中述曰:“四月戊午,寇平,旋师”,还是在《时雨堂记》中的记云:“乃四月戊午班师”,无不表明其从漳南前线回到驻节地上杭的时间是“四月戊午(四月十三日)”。因此,王阳明抵长汀的时间一定是晚于四月十三日,不可能是“四月七日”。
束景南在编写《王阳明年谱长编》时,参考了嘉靖《汀州府志》的记载:“阳明四月壬戌复过行台……”,而认定“十七日,至汀州,徐爱书来,告买田霅上待耕,有诗答之。”王阳明返赣那年的四月壬戌,正是四月十七日。所以王阳明是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四月十七日,行至汀州”,并非“四月七日”。
(七)平和县儒学建成时间
该书第六章《寇平民和,风俗化成》认为:
县学在县治之南,明正德十四年(1519)设县时,南靖知县施祥建大成殿……
该书的这一表述,存在一个时间上差错,平和县学应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建成,而非“明正德十四年”。
明正德十三年(1518)十月十五日,王阳明在拟制《再议平和县治疏》时,引用了福建布政司的上报材料:
据知县施祥呈报,县堂、衙宇、幕厅、仪门、六房,及明伦堂俱各坚完;惟殿庑、分司、府馆、仓库、城隍、社稷坛,亦因风雨阻滞,次第修举,期在仲冬工完。
另据清道光《平和县志》记载:“儒学在县治南门内,明正德十三年议设县时,南靖知县施祥督建。”显然,平和县县学的建设时间应以督建者施祥的报告为准。因此,作为县学的“明伦堂”已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上半年完工,而不是该书所描述的“明正德十四年”。
(八)平和建县时社学的情况
该书在第六章《寇平民和,风俗化成》中,认为:
建县时,南靖知县建有二十一所小学,并置租一十五石以益之,后屡有增益。大致有二十四所:崎岭社学……
该书第六章《寇平民和,风俗化成》的大部分内容是节选摘录清康熙己亥《平和县志》的内容。可惜的是,编著者在摘录过程中,因囫囵吞枣了解志书内容,以致部分内容存在抄错的现象,甚至曲解了志书的本意。《平和县志》原文是:
社学。明社学有二:一曰“扁井”,在县治前,旧为医学;一曰“芦溪”,在清宁里中圃社。俱知县王禄于嘉靖九年建,并置租三十四石。三十四年,知县赵建复置租一十五石以益之。又有二所在新安里。万历二十二年,知县王俨将本社积租,申详修理学宫,报允。开支田议,归儒学收管,永为修学之资。院道批允。
国朝(清朝)社学久废。康熙五十三年奉巡抚满令,各县乡村设立社学。义学附城,议立者,三乡社。议立者,二十有四:崎岭社学……
志书明确指出平和最早的社学是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而非“建县时”所建;建设者是时任平和知县的王禄,而非“南靖知县”。至于“建有二十一所小学”,是编著者在摘录志书时,将尚未点校旧志中的“明社学有二一曰扁井……”的“二所”理解为“二十一所小学”;而“并置租一十五石以益之”,乃是断章取义所致。
(九)王阳明是否在上杭屯兵52天
该书第七章《古邑上杭,行台驻节》认为:
王阳明亲自率兵进屯上杭,于正德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从上杭城关出发,攻破象湖山(今永定湖山乡),一直到“余寇”清剿任务完成,回军上杭,四月戊午班师,王阳明在上杭屯兵时间为52天。
该书的这一表述,前后矛盾。王阳明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二月十九日从上杭出发前往漳州督战,直到四月十三日班师回到上杭,期间的52天。恰恰是王阳明不在上杭的52天,怎么能称为“王阳明在上杭屯兵时间”呢?
这一时期,王阳明究竟是在漳州,还是在上杭呢?不妨从王阳明的有关公文中寻找答案。王阳明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二月二十五日向朝廷上呈《给由疏》,明确“臣系巡抚官员,见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调官军,夹剿漳、浦等处流贼,未敢擅离。”在五月二十八日《攻治盗贼二策疏》中提及“案照四月初五日,据南康府呈同前事,彼时本院见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贼向往,行查未报。”可见,二月二十五日,王阳明已在漳州督战;四月初五日,尚未离开漳州前线。这从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王阳明在这“期间的52 天”内,并非屯兵上杭,而是一直身处漳州前线督战,未敢擅离职守。
(十)林希元等闽中人士是否为阳明门人或后学
该书第十章《闽海才子,道融姚江》认为:
此时林希元只是王阳明的道友,后逐渐成为王阳明的信徒。
林希元(1481~1565),字懋贞(一作茂贞),号次崖,泉州府同安县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南京大理寺评事。该书将林希元视为“闽籍阳明信徒”,窃以为是错误的。
该书编著者的这一观点应是在采纳钱明所著《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林希元至少可视为阳明的道友和政治上的同情者”的基础上,加以猜测,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林希元虽与王阳明、阳明门生弟子多有交往,更有学问切磋,尝学《传习录》,甚至不吝称赞王阳明是“一世非常之士矣”,但其在给马宗孔的信中明确表示自己不喜阳明良知新说,而欲承程朱之续:
忆阳明《传习录》,非朱子解《大学》“止于至善”为“事理当然之极”云。“至善”是心之理,曰“事理当然之极”,是义外也,兄之说或缘于此。夫阳明之说蒙昧不通,厚诬圣贤,区区已不取。今兄之说又似并其立言之意而失之。必如其说,当改物外求心,曰认心为物云耳。盖阳明谓“至善”之理在心,若曰“事理当然之极”是义外,是非朱子认心理为外物也。阳明之说既谬,而兄又失之,所以益远而不可通也。阳明之说亦精辩之,万物之理皆具于心,必求诸物,物通则心通矣。故曰“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至善”是“事理当然之极”,此理则具于心,非外物也。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子思曰“中者,天下之大本”,皆可证也。阳明以朱子“事理当然之极”之语,是认吾心之理为外物,非厚诬乎!今以曾子之释“至善”言之,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夫君臣、子之类皆物也,释“至善”而语此,必如阳明之说,则曾子之释非义外乎?似此之类,不能尽书,皆可以证阳明之说之谬也。
显然,该书将认为“阳明之说蒙昧不通,厚诬圣贤,区区已不取”的林希元,列为“逐渐成为王阳明的信徒”,谬也!误也!除了林希元,该书还将一些并非阳明门人、后学的人物也列入其中,如将被贬谪到镇海卫的丰熙、邵经邦编入“门人后学,过化八闽”名录之内;将学宗朱子的泉州人李廷机列入“门人后学,流寓上杭”名单之中。
三、余 论
阳明地域文化是指王阳明及其门人、后学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长期形成的历史遗存、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地域文化在于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一地有一地独具的特色,才彰显地域文化的多姿多彩。也正因为如此,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便用地域名来划分王学门派,在其所著的《明儒学案》就曾把阳明以后的王门分成七派,即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粤闽和泰州。《王阳明与福建》是一部具有明显地域色彩的阳明文化书籍,反映的是王阳明及其门人、后学在福建这一特定区域活动的轨迹,并对福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产生影响的探究。但该书并未全景式展现王阳明“两次半”入闽活动的跌宕起伏,且对一些门人、后学的介绍,没有突出其在闽阶段的活动历程和学术发展。如介绍阳明后学徐用检,着墨虽不少,但也只用“母丧服后补福建兵备”一句带过,而忽视了他启发、改变了福建著名学者李贽的学术思想,并成为李贽的重要师友。如此编著,较难让读者感受福建地域的阳明文化特质与魅力。
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作为该书的主编单位,借用外力外智编写福建阳明地域文化书籍,其出发点是好的。但由于受到经费、路途等客观因素的制约,编著者对漳州、汀州的一些地方史实、民间传说无法身临其境进行必要的田野考察、实地甄别,又未能较好地开展地方史志文献资料的相互比对佐证,更多是借鉴采信当地的一些文学作品,甚至是从网络上摘录一些文章进行编撰,以致出现“漳汀城隍庙……王阳明提议提高级别,为府一级建制。至于城隍庙的供奉,王阳明定了王维”等不实观点。从这点上看,开展地域阳明文化研究,田野考察、实地访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手段,不可轻视,特别是在网络资讯发达的今天,更需引起各位学人的高度重视。同时,作为该书的组织者,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如若多倾听省内一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如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武夷学院张品端教授、龙岩学院张佑周教授等人的不同见解,或许可以避免该书出现的一些常识性误区。
综上所述,该书虽有一些瑕疵纰漏,但其编著出版的意义却是积极的,有力推动了福建阳明学的发展,促进了“首届东南阳明学高峰论坛”在福州召开。“力争毫厘间,万里或可勉。”商榷是为了革弊端正,更是为了完善提升。期待该书再版之际,可以适当加以修正,以广大福建阳明地域文化,嘉惠学人。
注释:
[1]“两次半”入闽:第一次是明正德二年(1507),赴谪贵州龙场驿途中,迂道遁迹至武夷山;第二次是明正德十二年(1517),巡抚南赣汀漳等处,率兵入闽靖寇平乱;半次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奉敕勘处福州三卫所军人哗变,行至丰城听闻宸濠反变,遂返吉安起义兵,赴闽半途而返,故称半次。
[2]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
[3]林蔚:《〈王阳明与福建〉在榕新书首发》,《福建日报》2020年12月28日第2版。
[4]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前言第5页、第50页。
[5](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45页。
[6](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一,第424页。
[7](清)沈定均修,吴联薰增纂,陈正统整理:《漳州府志》(光绪本)卷之一,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页。
[8](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一,第424页。
[9]平河社,王阳明在之前的《添设清平县治疏》中,称为“平和”。可见,在当时“平和”与“平河”是通用的,并无它意解读。
[10]参考(清)金镛修:康熙《平和县志》卷九。
[11]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62页。
[12]张山梁:《平和:寇平而人和?》,《福建史志》2016年第3期。
[13]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前言第5页、第50页。
[14]王阳明在《时雨堂记》中载明:“四月戊午班师”;在《书察院行台壁》也记述:“四月戊午,寇平,旋师。”
[15](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九,第345~346页。
[16](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一,第426页。
[17](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一,第424页。
[18](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三,第1376页。
[19]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出版,第983页。
[20](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第387页。
[21]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45页。
[22](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七,第1107页。
[23](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九,第345页。
[24]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943页。
[25](清)谈迁著,张宗祥校点:《国榷》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3127页。
[26](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六,第606页。
[27]福建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47页。
[28](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九,第336页。
[29](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六,第594页。
[30](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六,第596-597页。
[31]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53页。
[3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四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286页。
[33]曾昭炬主编:《平和城隍庙庙史》,2000年,第23-24页。
[34]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56页。
[35](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四,第1010页。
[36](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十三,第994页。
[37]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第938页。
[38]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62页。
[39](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十一,第424页。
[40](清)黄许桂主修,曾泮水纂辑:道光《平和县志》卷三,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6页。
[41]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65页。
[42](清)王相修,昌天锦等纂:康熙《平和县志》卷之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8页。
[43]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72页。
[44](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九,第331页。
[45](明)王守仁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九,第346页。
[46]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119页。
[47]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第398页。
[48](明)林希元著,何丙仲校注:《林次崖先生文》,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58页。
[49]马宗孔,即马津,徐州人,明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从王阳明讲良知之学。
[50](明)林希元著,何丙仲校注:《林次崖先生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3~174页。
[51]丰熙(1468~1538),字原学,浙江鄞县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世宗即位,升翰林学士。因兴献王“大礼”议起,丰熙多次力争哭谏,帝怒,下诏狱,后遣戍福建镇海卫,卒于戍所。
[52]邵经邦,字仲德,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授工部主事。嘉靖八年(1529)因日食上疏言事。帝怒,贬戍福建镇海卫,闭门读书,居三十七年卒。
[53]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156页。
[54]李廷机(1542~1616),字尔张,号九我,福建泉州人。明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
[55]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79页。
[56]钱明:《王阳明及其学派论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4页。
[57]周建华、刘枫编著:《王阳明与福建》,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