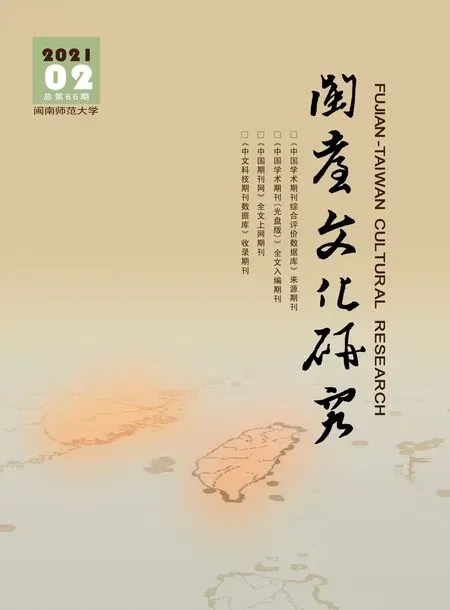管窥《吉陵春秋》中李永平的流散书写与原乡追寻
李怡涵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马华作家,即马来西亚华人作家;马华文学,即指马来西亚(包括沙巴和砂拉越)的华文文学。作为自婆罗洲去台留学的华人,李永平的身份是难以定义的。其本人不承认自己是马华作家,于1976 年宣誓放弃马来西亚国籍,入籍中国台湾。但学者们则普遍称其为马华作家:“李永平是早期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中独具风格的一位,他的写作指向个体、民族和国家,也指向了语言审美世界的终极”,然而,李永平“马华作家”的身份并不足以概括他复杂的经历和写作特点,王德威认为李永平兼具了台湾作家与马华作家的特点,将其称为“台湾马华作家”。相较之下,王德威学者对李永平的身份定义显得更为准确。
作为李永平的代表作之一,《吉陵春秋》繁体版1986年在台湾出版,余光中、龙应台、豊田周子等在台学者对该小说进行了探讨。简体版2013年与大陆读者见面,大陆学者也纷纷对其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归为四个方面:译本分析、小说主题、人物形象、叙事方法。《吉陵春秋》的书写包含了流散写作的特点,体现了作者对原乡的向往。但学者们并未对李永平在《吉陵春秋》中体现出的流散意识和原乡意识进行详细的探讨。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吉陵春秋》中的人物形象、文化习俗和地理描写,探究李永平在文本中体现出的流散书写和原乡追寻。
一、《吉陵春秋》中的流散书写
“流散”对应的英文是Diaspora,有离散、流散之意。温越指出,“流散(Diaspora)”源于希腊语,汉语可以译为“散居”“离散”“侨居”等。徐颖果中将Diaspora译为离散,并总结:“Diaspora一词源于希腊语speiro,该词是‘撒种’之意,dia 是‘分散’之意”。由此看来,“离散”和“流散”都指涉相同的事物,因而下文在介绍“Diaspora”的相关概念时便不再做区分和说明。“流散”最初被用来指涉犹太人在二战后的迁移现象,主要指散居世界的犹太人。随着世界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口的流动性逐渐增大,“流散”的概念也逐渐扩大,开始指向“当今全球化时代的移民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流散群体也随之壮大,因移民与人才流动产生的群体,如华人族群、印度裔族群、非洲黑人族群等都可归为流散群体。基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离散批评作为一种理论应运而生,主要“研究离散族裔群体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伴随离散批评而来的还有流散文学,流散在外的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的书写传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或是对昔日时光的感叹,或是对现下情景的愤慨。温越指出“流散作家由于自身迁徙生活的经历,在创作中不可避免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了作品以不同的文化元素或文化视角”,因而,我们常常可以在移民作家的作品中找到母国和居住国两国的踪影,管窥到移民作家们在流散书写中所体现出的文化身份困惑以及对母国和居住国的复杂情感。
作为台湾马华作家,李永平曾是一名马来西亚华人。祖辈们早年自广东迁移到婆罗洲的砂拉越,二战后,婆罗洲成为了英属殖民地,李永平在婆罗洲度过了他的幼年、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直至前去台湾求学。当英国败退,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排华情况愈加严重,马来西亚对于华文教育的打压更加明显。“1965年由于种族原因而导致新马分治后,马来西亚确立了‘以马来语为国语’‘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原则”。种种情形使得自小就热爱方块字的李永平不得不离开婆罗洲。由于多变的政治局势,李永平的作品充满了流散特点,无论是对作品中人物身份的描写,还是对地理时空的刻画,都体现了李永平内心的漂泊和矛盾。
(一)边缘人物的塑造
边缘性是流散文学的一个特点,也是对作家流散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摹写,作家们往往通过塑造边缘人物来展现自己精神上的流散状态。《吉陵春秋》中有两类遭受排挤、游离在外的边缘人物:一类是被放逐者;一类是自我放逐者。《拉子妇》中的拉子婶、《母亲的围城》中的流浪街头的老拉子,都是被主流人群所排斥的边缘人。
在《吉陵春秋》中,作者再次将这两类边缘群体刻画了出来。黑痴是万福巷妓女春红的私生子,在目睹刘老实砍死了母亲后,黑痴变成了痴儿。失去了母亲的黑痴只能四处流浪,遭人欺侮。他没有家乡、没有亲人,一直处在社会的边缘,被社会的主流群体所排挤。吉陵镇上的成群结队的光棍们总是戏弄憨傻的黑痴,“那七八个小光棍愣了愣,摸着满头的水,撒起了泼,把黑痴揪到了县仓墙根下,连人带猫就掼进了臭水沟里”。被排挤、被放逐一直是流散写作的特点,犹太人当年也是被驱逐出家园,从而成为流散族群。李永平在作品中对这类被排斥人群的刻画体现了他对这类边缘人物的同情和感伤。除了黑痴这样的被放逐者,李永平着重刻画了一群自我放逐者。刘老实在杀了与孙四房有关的人后便消失了,妻子被辱上吊自杀,迎神节上的看客们没有一个人前去阻止,对万福巷失去了信心的刘老实再也没有回到镇子上来,离开了母亲,离开了家乡,四处流浪。而做了一世好人的刘老娘在经历了“媳妇上了吊、儿子发了疯,杀了人”后,挽着包袱、带着诅咒离开了吉陵镇,也进行了自我放逐。被人们误认为是刘老实的外乡浪人也是一个自我放逐者,他扛着包袱,沿路停歇,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到哪里去。这些自我放逐者有一个共同点:为情势所迫而自我放逐,这与李永平的经历是相近的,李永平常称自己为“来自南洋的一个浪子”。婆罗洲、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都是与李永平紧密相联的地理空间,面对马来西亚联邦对华人族群的排挤、对华文的打压,李永平感到自己一直处于游离、漂泊的边缘地带。而流浪也是流散作家笔下行文的一个特点,自16 世纪西班牙文坛流浪汉小说兴起后,流浪者便成为了文学作品中常见的人物形象,流散作者更是通过流浪者的塑造展现了其所处时代的动荡和变换。
无论是放逐者还是被放逐者,这两类边缘人物都体现了作家的内心状态。陈召荣曾提到:“‘边缘性’(marginality)原指前殖民地边缘与帝国中心的关系,现在已多用于界定流散作家的精神状态”。流散作家多是因为外界因素或自身原因离开原居地,在离开故土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失落漂泊之感,作为曾被马来西亚联邦打压的华人族群的子弟,李永平迫不得已离家去国,他对被边缘化的痛楚自是深有感触,其作品中经常出现边缘人物便也不足为奇。
(二)身份与时空的模糊处理
混杂和模糊是流散文学的另一特点,多元的文化环境使作家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模糊,这种模糊性逐渐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家笔下的人物,这些流散者的形象总是“彷徨于祖国与移居国、原文化与移居国文化之间”。在《吉陵春秋》中,人物身份和地理环境都是不确定的,显然这是作者李永平的刻意为之。作为从婆罗洲转向台湾的马华作家,一方面需要考虑读者群体的转变,另一方面则是困于如何在多重文化中进行定位。
人物身份模糊是小说中隐藏的主题,小说中存在着大量未知身份的人群。疯癫的浪人没有姓名、没有身份。春红的黑痴、秦寡妇的私生子、胡四嫂的小十一都是父亲不详的孩子。父亲象征着血脉,父亲身份的模糊使得他们无处寻找自己的来源和归处。此时的李永平在童年故乡婆罗洲、祖籍地中国大陆与现居地台湾地区中游移,对于一个身处多重文化的作家来说,对身份和文化的选择无疑是艰难的。温越指出:“置身于两种或多种异质文化圈中的流散作家,将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矛盾与困惑融入文学写作,必然存在文化身份、文化选择问题”,李永平将这种身份选择的艰难体现在了人物身份的模糊上。
小说中的地理空间也是不确定的。小说中充满着中国大陆特有的色彩:“万福巷,原不叫这个名字。县仓才盖起来时,东边墙下那一条泥巷还叫田鸡弄”“后来有个军阀的小跟班驻进了县仓,靠田鸡弄那一排栈房,做了侦缉队部”。这样的描述使人仿佛置身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南方小镇,小说中的多处意象也充满着古老中国的色彩。但也有学者认为小说中吉陵镇的原型是存在的,就位于李永平的故乡婆罗洲。朱崇科提到作家钟玲曾亲自跑到李永平的出生地古晋探访,通过实地考察得出“吉陵”是以古晋城的华人社会为原型而产生的。混合着婆罗洲风情与中国特色的吉陵镇展现了李永平内心的矛盾,婆罗洲作为童年故乡,台湾作为寓居地,中国作为血脉之乡,单单选择其中一处都会有失偏颇,模糊的地点成为此刻游离在外的李永平的最好选择,因而在《吉陵春秋》中呈现了既非南洋又非纯粹中国的吉陵镇。马华作家们复杂的身份和地理问题使得他们常有漂泊离散之感,温明明在其书中借用黄锦树的文字阐释了李永平这类台湾马华作家们的身份苦恼:“多属往往也意味着不属:三重的有‘国’或无‘家’,处于一种暖昧可疑的位置,可能是三属,但也可能被挤于三者重叠的阴影地带,不被任何一者所接纳,漂流于无所属的无籍空间”。
二、《吉陵春秋》中的原乡追寻
原乡,顾名思义,原来的家乡。“家乡”与“故乡”二词的差别就在于时间的先后,“家乡”指的是现在的家所在的地方,而“故乡”则指已经离开了的家乡。由此看来,“故乡”与“原乡”的意义十分相近,帅震在其书中对这两个词的概念进行了区分:“故乡一词偏重于实存且具体的时空指涉以及固着的地方经验,原乡是族群历史与文化的源头,成为凝聚认同、维系文化血脉的重要着眼点”。原乡是一个群体精神上、文化上的起源,承载着族群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曾葵芬指出“原乡是人类精神家园的源头,也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苦苦追寻的一个催生文明系统和文化主体性的精神故乡”。游离在外、客居异国的作家们往往通过作品表达对家国故乡的思念,在文字中寻找记忆中的乡土。台湾作家白先勇,台湾诗人余光中、台湾马华作家李永平等都在其作品中极力塑造了想象中的家园,追寻精神上的故乡。帅震指出“追寻原乡是人类境况(human condition)的本能与宿命”,原乡追寻已经成为众多离乡作家们作品中的母题。对于迁居台湾的大陆作家们,原乡追寻是一段辛酸的路,白先勇的《台北人》满载着作者对大陆记忆的怀念和感伤,余光中的“乡愁”寄托着其对大陆母亲的留恋。而对于台湾马华作家们来说,原乡的追寻更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历程。
前文中提到台湾马华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传达出了漂泊离散之苦,但也在作品中找寻精神上的原乡。“流散并不意味着丧失了故乡情怀,疏离了文化身份,恰恰相反,流散的痛苦很大程度上是思乡的痛苦、离根的痛苦,事实上流散文学中的痛苦正是深刻的文化身份意识觉醒的表露”。祖辈的迁移、政治局势的变动,使得李永平的身份变得复杂,也促使他不断找寻真正属于自己的原乡,李永平的流散书写并未疏离了文化,反而在作品的潜文本中,展现了他内心真实的身份选择。婆罗洲是李永平自小生长的地方,毋庸置疑,婆罗洲时期的记忆为李永平的创作打下了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为李永平提供了写作灵感,而台湾的地域文化传统和习俗多传承自中国大陆。永平也曾坦言自己从小就热爱中国文化:“我喜欢的中国作家太多了!一定举出一位,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司马迁。我一直把中国的第一部通史《史记》看成中国的圣经、神州的创世纪,而这本书又是一个文字优美、意境高超的文学作品”。不难看出,中国的文化和婆罗洲的记忆都在《吉陵春秋》中有所体现。
(一)文化原乡
《吉陵春秋》中中国文化的踪影随处可见,中国的方块字、传统习俗以及古老信仰都构成了小说的文化基调。从词汇来看,“军阀”“算命先生”“送子观音”等满载着中国风情。甚至《西游记》也出现在小说中:“那算命先生手里捧着一部脱了线的西游记,一边看着,一边踱起方步来”。不仅是中国文字,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及民间习俗也经常出现。长笙为了求子吃香灰,在迎神节上跪拜观音菩萨,萧克三姐姐出嫁后回门等风俗如小说中。镇上的迎神仪式也与中国的传统习俗有重要的渊源。《吉陵春秋》中“观音神轿游街的盛大场面,实际上乃移用了每年3月,妈祖诞辰北港朝天宫妈祖出巡‘绕境’的仪式”。随处可见的中国文化习俗使得整部小说弥漫着中国味道,龙应台曾经把吉陵镇称为“一个中国小镇的塑像”。
除了肉眼可见的中国文字和习俗,贯穿整部小说的当属中国古老的神秘信仰。东方式的因果报应自长笙上吊自杀后便一直萦绕在吉陵镇。人们偶尔会在巷口见到挎着包袱的长笙魂魄;自长笙自杀,刘老实发疯以后,吉陵镇上再也没有下过雨;萧克三家中盘绕在房梁上的那条花头大蛇一直为萧氏家族招致厄运;穿洲过府的浪人拥有使小孩不断啼哭的神秘力量等事件都带有一种东方的神秘色彩。这些中国传统的灵异力量为李永平构建想象中的中国提供了素材。李永平从未到过中国大陆,他曾经想前往大陆,但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于是他便前往了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载体——台湾。中国诗书的积累、台湾后续的华文学习使得李永平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也使他能够在文字中深入追寻中国这个文化原乡。
充满着中国情调的描述使得故事的发生地点像极了中国旧时南方小镇,李永平在《吉陵春秋》简体版本序言中写道:“我笔下的吉陵镇,和居住在镇里的那群‘吉陵人’,他们的生活习俗和语言情感,倒让人联想到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南方某省、某县的一个村镇——我这一辈子还不曾回去的‘唐山’”。作品中的潜文本创作通常是在作家无意识时发生的,更加能反映作者内心的真实想法,中国古老的方块字和文化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李永平的心中,无论是在《拉子妇》《母亲的围城》还是后期作品《大河尽头》中,总能找到中国文化的踪影,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了李永平的文化原乡,他在序言中写道:“这个年轻时自我放逐、栖身宝岛倏忽四十年的南洋浪子,盼啊盼,总算盼到两岸关系解冻,开放交流,他的作品终于可以正式的、堂堂的在神州大陆——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心中念兹在兹的‘唐山’——出版了”。
(二)记忆原乡
《吉陵春秋》将李永平对中国文化的熟知和向往展现了出来,中国俨然在很早前就成为了李永平文化上的原乡。但我们不难发现,婆罗洲的身影也隐藏在故事中,甚至这个故事的灵感便是来自李永平童年记忆中一个独自行走在古晋这座丛林城市中的白发老婆婆,而万福巷和刘老实的棺材铺也都取自李永平的出生地——古晋,可见婆罗洲是李永平年少记忆的重要来源。
李永平笔下的吉陵镇是一座罪恶之城,小说的一半笔墨都在描写万福巷的满庭芳妓院,这与李永平在英属殖民地婆罗洲时期的记忆是相关联的。19 世纪末,大量的广东妇女和少女被拐卖出洋往马来联邦、婆罗洲和荷属东印度等地,海峡殖民地妓院中超半数的妓女是被拐卖来的。小说中的妓女秋棠便是在回家途中被拐卖到满庭芳的,而满庭芳中其他没有被描述的妓女又有多少个是被拐卖或诱拐来的呢?这一情节无疑是李永平对记忆中的殖民地社会的一种再现。虽然李永平描绘了华人社会中罪恶的一面,但老一代华人的美好也停留在李永平记忆中。刘老实的祖辈为了积德,每年都施舍棺材一个月,坚持了四十余年;萧克三的祖父白手起家,一生勤恳,指责儿子的荒唐,禁止孙子与游手好闲的父亲同住。小说中老一辈华人都是美和善的代表,象征着婆罗洲逝去的美好旧日,象征着李永平对旧时天真纯洁的追忆。
婆罗洲是李永平生命开始的地方,承载着他年少的记忆。在《母亲的围城》中,李永平隐晦地表达过他对婆罗洲的眷恋:“在母亲将船摇回镇子上时,我钻进舱里,躺了下来,闭上眼睛,心里忽然有一种惬意的感觉”。婆罗洲已成为李永平内心的眷恋,《吉陵春秋》的创作来源便是一位婆罗洲的老婆婆。他将童年记忆中的人物呈现在了大家面前,令我们对那个遥远又神秘的古晋产生了遐想:“在我的童年时期,在我出生、成长的那座岛屿,曾经蛊祟一整个支那城镇,造成一镇人心惶惑不安,延续数代之久”。李永平对婆罗洲的尊敬和热爱在其“婆罗洲三部曲”中深有体现,“‘婆罗洲三部曲’将是我这个老游子送给“生母”婆罗洲的最后献礼,以感念她对我的养育之恩”。迫于马来联邦的政治情形,李永平当年不得不离开自小生长的婆罗洲,定居中国台湾。对于李永平来说,重回婆罗洲已经成为不可能,但婆罗洲的记忆将成为他一生中宝贵的财富和精神寄托。
三、结语
李永平在《吉陵春秋》中结合了中国文化习俗和婆罗洲时期的记忆,构建出了精神上的原乡。汉字与中国文化是李永平寻祖辈之根、血脉之源的媒介,也给予了李永平文化上的滋养。婆罗洲是生养李永平的地方,年少时期的记忆成为了李永平精神上的寄托。可以说,李永平的原乡是婆罗洲与中国融合起来的原乡,李永平曾坦言:“我现在这么认为(一直这么认为,但大家不听我的想法),事实上我对婆罗洲、台湾、中国唐山都有同样的情感,把他们看成是三个母亲”,《吉陵春秋》中的罪恶书写,也并非特指某个地理方位,而是适用于任何地方。在李永平的多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习俗与婆罗洲雨林是共同存在着的。优秀的马华作家的华文创作离不开中国,也离不开南洋,若将这两种任一元素剔除,将不再是一部出彩的马华文学。多元性也是流散作家作品中的共同特点,李永平在其一生的创作中,通过中国的文字文化,通过婆罗洲时期的记忆,追寻着精神上的原乡。
注释:
[1][11]饶芃子:《流散与回望》,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第172页。
[2]胡月霞:《李永平的原乡想像与文字修行》,《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王德威:《原乡想象,浪子文学——李永平论》,《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4][6][7]温越、陈召荣:《流散与边缘》,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页。
[5][9]徐颖果:《离散族裔文学批评读本》,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第1页。
[8][10][14][15]温越、陈召荣:《流散与边缘》,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页,第7页,第29页,第5页。
[12][13][17][26][28][29][30][34]李永平:《吉陵春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4页,第1页,第3~4页,第23页,第6页,第10页。
[16][24]温越、陈召荣:《流散与边缘》,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18]朱崇科:《旅行本土:游移的“恶”托邦——以李永平《吉陵春秋》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9][21][23]温明明:《离境与跨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0页,第12页,第15页。
[20]帅震:《原乡的面影》,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4页。
[22]曾葵芬:《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原乡意识研究》,西安:世界图书出版西安有限公司,2017年,第155页。
[25][35]杨青:《一个南洋华裔青年的唐山情怀》,《深圳商报》2013年第C04版。
[27][31]朱双一:《赴台马来西亚侨生文学的中华情结和南洋色泽》,《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1期。
[32]范若兰:《性别与移民社会——新马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64页。
[33]李永平:《拉子妇》,台北:海山印刷厂,1976年,第38页。
[36]王润华、许通元、李永平、黄佳丽:《从婆罗洲到北台湾——李永平的文学之旅》,《蕉风》2017年第5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