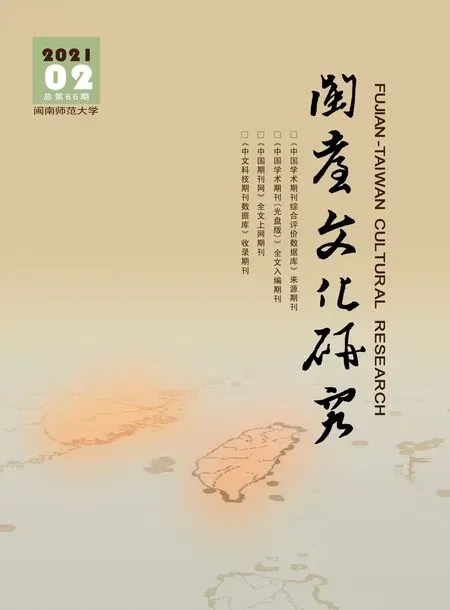聂华苓早期短篇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及其成因
张依珊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福州 215123)
一、前言
1949 年,聂华苓一家五口到了台湾,开始了十五年的台湾生活。在台湾,聂华苓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此期间她创作的作品以短篇小说为主。1964 年移居美国后,聂华苓自称为“边缘人”:“所谓‘边缘人’,即我们在生活的两个社会中都不是主流,但因为我们可以跨越两个社会的界线,所以对两边可以都关心、都投入、都加以理解。”实际上,聂华苓的作品从早期就开始展现出边缘性特点。
“边缘人”的概念来自于社会学范畴,源于格奥尔格·齐美尔提出的“外来人”概念。通奎斯特认为边缘性并不非得移民才会产生,也会因诸如教育和婚姻之类的内在变迁而发生。德国社会学家菲尔斯滕贝格将“社会文化价值和准则”作为衡量个体边缘性的标尺,提出“社会边缘群体”,这一概念实际上更强调那些区别于主流社会或社会多数人的个体,他们有着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在聂华苓的创作中,“边缘人”表现为不同的身份,他们的产生原因亦是多元的,而这些“社会边缘群体”的区间时常会出现重叠。
1980 年,聂华苓在1949~1964 年间创作的作品中,为大陆读者精选了十篇短篇小说,结为短篇小说集《台湾轶事》,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同年,出版于香港海洋文艺社的《王大年的几件喜事》则收录了聂华苓的十三篇短篇小说。结合两个版本进行研读,能更为完整地阅读聂华苓早期短篇小说。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聂华苓刻画了许多边缘小人物,展现出多重边缘性。
近年来有关聂华苓小说的“边缘人”研究,包括孙辰的硕士论文《国族流离的边缘发声——论聂华苓小说的边缘书写》,从多元维度探究《桑青与桃红》与《千山外,水长流》所展现出的作者的边缘态度;杨瑶的硕士论文《论聂华苓小说中的“边缘人”叙事》,就聂华苓长篇小说的“边缘人”进行了研究,讨论了“边缘人”的形象类型、精神内涵、叙事策略和价值意义;林佳,肖向东的《边缘生存的言说——聂华苓与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认同》,分析严歌苓和聂华苓的移民小说的“海外边缘人”,简要论述了海外华人的边缘生存状态;傅守祥,李好的《文化之根的漂移与嫁接——从聂华苓小说〈桑青与桃红〉看流散华裔的边缘生存与文化认同》,将《桑青与桃红》视为早期华裔流散文学的代表,探讨小说所展现出的边缘生存与文化认同问题,以上研究大多研讨聂华苓的长篇小说,极少提及短篇小说。但短篇小说在聂华苓的创作生涯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不仅代表其创作生涯的开始,还与其中长篇小说有互文关系。作为能够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能更精准展现社会生活的问题。研讨聂华苓短篇小说的边缘性,能更好理解聂华苓创作中的边缘意识,更好了解其边缘意识的流变。
本文拟从上述《台湾轶事》《王大年的几件喜事》两部小说集出发,就婚恋悲剧中的女性、新时代的老年人和政治纷乱中的公务员三部分,对聂华苓短篇小说的“边缘人”形象进行研究。
二、聂华苓早期短篇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
(一)婚恋悲剧中的女性
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在母性与妻性的两难中挣扎,曹禺笔下有《雷雨》的繁漪,聂华苓笔下则有《永不闭幕的舞台》的侯太太。侯太太的边缘性是多重的,她是父权中心社会的附属者,是传统伦理规范的叛逆者,也是母性与妻性间的两难者。西蒙娜在《第二性》提到:“母亲不是把女儿看做优越等级的成员致意的,她在女儿身上寻找自己的分身。她把自我关系的一切暧昧之处投射到女儿身上;当这个他我的他性确立时,她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侯太太与琬儿的关系,在乃琛(即A)出现后,从母女悄然转变为情敌。在侯太太的身上,妻性与母性发生了激烈的矛盾。侯太太爱上了侯先生的外甥,这是对传统伦理规范的挑战。但她在挑战的同时,感受到罪恶感,又以传统伦理规范束缚自我,“没有爱情的婚姻,简直就是地狱!无论如何,我要努力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然而,当侯太太发现女儿也爱上了乃琛时,她陷入了极其痛苦的处境,一方面她有母性的慈爱,另一方面她又憎恨嫉妒琬儿,“我厌恶她的笑,也嫉妒她的笑!”她还在日记中记道:“每逢我母女单独相对,我就是个最慈爱的母亲,一有A 在旁,我就变成了一个口喷地狱之火的魔鬼!”纵使内心对爱情十分渴望,侯太太也与许多旧式女性一样,被传统伦理束缚,以母性说服并压抑妻性,日日承受内心的折磨。
如果说侯太太嫁给侯先生是她的悲剧,《一捻红》中婵媛的悲剧则是成为了赖国熹的情人。婵媛虽委身于赖国熹,但她心里仍爱着叶仲甫:“她还要保留一部分——怀着宗教徒的心情保留着,没有希望,不求报偿。”她对叶仲甫与“叶太太”的执着,是她心中对过去的执着,是她在迫于生活时的坚守,卑微而坚定,甚至是一种节气——“岁寒不受霜雪侵”“劲节不推岷岭雪”。在战乱年代,有许多家庭被迫分离,一些人会成立两个家。林海音《烛芯》中的志雄也有两个家,一边是发妻元芳,一边是抗战时期陪伴左右的凤西。与志雄离婚后,元芳又嫁给了在大陆有妻儿的俊杰,在面对友人的质问时,元芳的回信如下:“我和俊杰的结合,是基于一个同样的感觉:我们如何渴望过着‘家’的生活。”对“家”的渴望,于元芳是希望在异乡能找个相互陪伴的人,于婵媛则是对大陆家乡的渴望。婵媛的设定与聂华苓一家有许多相同之处,聂华苓对大陆家乡、对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坚守,隐晦地投射在婵媛身上。同时,聂华苓的矛盾心态在婵媛身上亦有所暗示。婵媛对仲甫的感情是矛盾的,“她渴望仲甫,渴望昔日正常的婚姻关系,但她不愿再看到他了。”婵媛对仲甫的感情包含着一种羞耻与痛苦,她无法再单纯地回望,回望更添辛酸,这样的心态,恐怕也是许多随同国民党到达台湾的人们的心态。
侯太太在顺从与抗拒父权中心里挣扎,婵媛则在精神的痛苦与生存的满足之间为难。在聂华苓的小说中,女性不仅是传统父权社会的边缘人,在战争年代,她们在非正常的家庭关系中的边缘性更为突出。
(二)新时代的老年人
《寂寞》(又名《袁老头》)的袁老头喜欢对儿子说以前的光彩事迹,但儿子鲜少回应,“之耕有时也没精打采地回应一两声,有时便默不作声。”当他想向邻居“炫耀”自己的喜悦时,忙于家务的朱太太没好气,职场不顺的朱先生没心情,倒猪水的女人与他语言不通,万孝萱沉迷于音乐,就连儿子儿媳都不愿意主动和他分享日常生活,没有一个人真心理解和祝福他。《祖母与孙子》的祖母在淡水河畔远眺故乡,孙子却想去打鸟,催促她回家。孙子童言无忌道出了对祖母的嫌弃:“我才不要老,动也动不得,吃也吃不得,一脸的皱纹,连摇篮里的小妹妹看见你都要哭。出来还要人带着!”但让祖母最绝望难过的是孙辈的不理解,不仅是不理解自己,更不能理解自己对大陆家乡的感情:“孙子更坚决地说道:‘我不明白,这儿有什么可站的?’‘唉,我的乖孙子,你老了就明白了。’”祖孙之间,不仅仅是代际冲突,对待祖国故乡的感情,亦有所差异了。
与前二者一样,《高老太太的周末》的高老太太也是不被子女理解的老年人,但同时她也是传统礼教的边缘人与受害者,高老太太具有女性和老年人的双重边缘性。高老太太指责安娜·卡列尼娜为了追求爱情而出轨的行为,不理解儿女的恋爱。她和侯太太一样,嫉妒年轻女孩的婚恋自由,“现在太不成话了。女孩子都不老老实实地结个婚,交什么朋友,恋什么爱。”在母亲与子女的代际冲突中,面对着文琪文鼎的“心在曹营心在汉”,高老太太选择了让步。“她们隐藏起自己的怨恨,她们满足于自己的孩子们愿意给予她们的东西。但她们在孩子们身上得不到多少帮助。她们面对未来的荒漠无所事事,忍受着孤独、悔恨和烦恼。”高老太太把儿女都“赶”了出去,“她想起了死去的丈夫,假若他还健在,不也是一个老伴儿?她从来没有这样想念他,从来没有这样需要他。”这对于高老太太而言是很悲剧的。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在老伴生前死后,这是高老太太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与其说是“爱”,更不如说是需要陪伴,需要被需要。
聂华苓的短篇小说中的老年人是现代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是“陈旧”的,他们与社会有着隔膜,与子女也有着不可跨越的代沟。
(三)政治纷乱中的公务员
1.游离于“中心”之外的“边缘人”
沉默、枯槁、无神是当时台湾公务员的写照,正如《爱国奖券》的顾丹卿和《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的志刚/夫子(何政)。《爱国奖券》有两个版本,海洋文艺社版的顾丹卿是一个在工作压力下未老先衰的人,他认为人生是无聊的,“其实,人就是如此,不彻底,无论是快活还是烦恼,是爱还是恨,都不彻底,人生的可哀就在此。”北京出版社版的顾丹卿比海洋文艺社版更少语言描写,无论朋友谈论什么,他总是沉默,沉默展现出他最直接的无奈与愁怨。《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的志刚/夫子是一个悲观幽怨的单身公务员,在读书时代他是“公子哥”/活跃的诗人,但如今“单调的教书生活,给他留下了一张单调的脸,没有线条的脸;没有抑扬的声音;一脸的笑,总像在向人打躬作揖。”壮志未酬,去国怀乡,是古代士子远游常有之情。“伦理中心培养出的中国人身后的情感,使得游子之情显出一种两面性……另一方面如果总是进不去,总是处于一种‘离’的状态,其悲伤就是一种双重的悲伤。一是入国不得,不能完全自我实现的失落的悲伤,一是离家漂泊天涯的悲伤。”国民党败退台湾后,1949 年颁布了“戒严法”,进入“白色恐怖”时期。顾丹卿和志刚、夫子这样的底层公务员,无法得到当局“中心”的肯定,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却最能感受到“中心”的压力。在戒严时期,他们失去了原来的理想,也失去了原本的光彩,只剩下庸碌无为。
2.“边缘”与“中心”的转化
《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的王大年,有着丰富的象征意味。他是受到台湾当局嘉奖的模范教师,屋内挂着名不副实的“大年计划表”,私底下却与夫子谋划着养鱼赚钱的事。王大年是一个既有喜剧意味又有悲剧意味的人物,他认为人生就是财酒色(wealth,wine,woman),虽然他并未认真对养鱼进行计划,但他对自己的计划很自信。这种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和买爱国奖券一样,都是空想,与模范教师的荣誉称号形成了对比下的荒谬与可笑。但王大年是可悲的,他那“三朝元老”的资格,也只能换来“一间卧房兼起坐间,一间厨房。”联想到当时台湾教育界,甚至是政界,我们似乎能感到意有所指。“告诉你,老朋友,这是个分工的时代。”王大年理解的分工,就是“养鱼是我的责任。看鱼池是你的责任。”一个人日夜看鱼池不仅辛苦而且荒唐,王大年自顾自完成了“分配”,这种自以为是对夫子而言是强人所难。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基层充斥着专制与兵权的压制,而这种压制在基层又得到了拓展。政治压力与生活压力附在王大年的肩上,而他又将无法纾解的郁闷与怨气加在了比自己地位更低、能力更少的人身上,除了夫子,还加在妻子和儿女的身上。在父权中心社会中,即使丈夫在社会中的地位不高,但在家中他是最高权力者。王大年在家“阅兵”——让儿子小橡走正步,展现了社会向家庭的影响。王大年作为社会的“边缘人”,受到政治环境的冲击,但在传统等级观念中,他又将更弱者推向了边缘。
聂华苓短篇小说中的公务员,有沉默庸碌的一面,有激愤无奈的一面,也有无知可笑的一面,他们在政治纷乱中被挤到边缘,过着贫困拮据的生活,他们不复年轻的意气,寄托厚望于空想,但他们也会在父权家庭中实现边缘与中心的转换,显示出边缘与中心的密切关系。
三、聂华苓早期短篇小说中“边缘人”形象成因
(一)旧式大家庭的烙印
聂华苓生于一个旧式大家庭,家里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祖父认为“孙女是要泼出去的水,不必认真”,甚至连家中的听差都不看聂华苓一眼。在聂家,母亲、祖母、真君(祖父的续弦)等女性都是“边缘人”与受害者,聂华苓与母亲的关系深厚,母亲是个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被“骗婚”后成了“二房”。在父亲死后,母亲一房被父亲的长子驱赶,被指骂“聂家没有你说话的份!名正言顺,不是你!”聂华苓自小就感受到的“外人”的疏离感,最先来自家庭的父权中心思想。聂华苓的第一次婚姻亦是痛苦的,她嫁到了一个北方传统大家庭,同样的重男轻女,她在女儿性、妻性、母性的矛盾中,再度成为了“边缘人”。在一次电视台访问中,聂华苓说道:“我的疏离感不仅仅是地区的疏离、文化的疏离,比方,你在家里也可能产生疏离感,你与你的家人无法沟通等。”家庭带给聂华苓的疏离感,展现为作品的边缘性。在早期短篇小说中,聂华苓创造了带有本人及家族女性色彩的女性角色,如侯太太、高老太太,她们展现出对父权中心的迷思与抗拒,她们在顺从与抗拒中挣扎。然而,聂华苓不仅仅关注到传统伦理下女性的边缘性与悲剧性,她亦发现了“边缘”与“中心”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聂家,“奶奶是我们家的主心骨。她以柔韧稳定了家里暗中躁动的不安。”在作品中,侯太太以一己之力照顾生病的丈夫和一双儿女,高老太太一个人将儿女抚养长大,婵媛更是肩负着一家五口的生存。她们虽然是父权社会的“边缘人”,在家庭中却总是承担着“中心”的责任,她们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聂华苓不仅对旧式女性予以感同身受的怜悯,更将她对“边缘”与“中心”的思考展示了出来。
(二)漂泊人生的“疏离感”
聂华苓在《三生三世》的序中写道:“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聂华苓经历过军阀之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她从小就感受到一种社会疏离感。“我从小生活在武汉,武汉当时分为五个租界,我是生活在日本租界,虽然在自己的故乡,却总觉得自己是‘外国人’。那时候,日租界的小孩子的公园我们是不能进去的,‘华人与狗免进’么。所以,从小我就有着一种‘疏离感’。然后是抗战,我们从下江迁到重庆,依然有一种‘外乡人’的感觉。这种外乡人的感觉伴我一生。1949年,我到了台湾,更产生一种外乡人的感觉,更感到一种疏离感。”在台湾深感为“外乡人”的聂华苓,在创作时也时常关注与自己一样身处社会基层的“外乡人”。《爱国奖券》在《台湾轶事》中是首篇,与末篇《绿窗漫笔》相对应,一头一尾都含有对“回家”的期望。“他们全是失掉根的人;他们全患思乡‘病’;他们全渴望有一天回老家,我就生活在他们之中。我写那些小说的时候,和他们一样想‘家’,一样空虚,一样绝望——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在聂华苓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基本所有的主角都是“外乡人”,或是旧式女性,或是老年人,或是小公务员,他们都是社会边缘的人物,但他们身上的乡愁却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与年青人相比,老年“外乡人”的疏离感应是最深刻的。不同于白先勇对“没落贵族”的关注,聂华苓关心的是像母亲那样最普通基层的老年人。高老太太身上有聂华苓母亲的影子,即使母女感情再深厚,但母亲不支持聂华苓离婚,“那怎么行呢?有两个孩子呀!”她也和高老太太一样注意女儿的言行,认为哈哈大笑太不拘形迹。像高老太太、袁老头这样的老年人,是现代社会的边缘人。他们经历了时代的进步,但思想仍是传统的,与在进步思潮中成长的新一代是有代沟的。“外乡人”中的“老年人”身上的疏离感是双重性的,既有空间的影响,也有时间的影响。他们不仅有地理上的疏离感,更有来自亲人的疏离感。对于“年老”,年轻人如文琪认为是“可怕的”,如孙子认为是“麻烦的”,即使作为子女儿孙,他们不理解也不同情老年人的寂寞。聂华苓借高老太太发出怒吼:“老人就不是人?”直到今天,这种人文关怀仍是十分可贵的。
(三)身份认同的迷思
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被笼罩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中,台湾岛上人人自危。跟随国民党到达台湾的民众,逐渐意识到“反共复国”已成为空想。当局的文化政策切断了与“五四新文学”的联系,不仅造成了文化的代际冲突,也对民众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冲击。聂华苓是接受“五四”成长的一代,当“五四”被当局否定,他们的文化记忆便失去了“合理性”。“这种是一种以政治命令的形式而发起的一场记忆清除运动,它体现的是统治者以自我界定为核心而实施的国家意志。它的形式是撕裂性的,必然造成集体记忆的巨大中断。”集体记忆的巨大中断导致文化记忆的断层,拥有“被否定的”文化记忆的人会产生质疑,也无法辨认“我是谁”。聂华苓笔下的小公务员是政治底下的边缘人,他们参与过战争,却无法参与社会的建设,“个人无法找到在集体生活中的归属感,从而导致认同无法完成。”于是,他们身上出现了认同焦虑。海洋文艺社版的《爱国奖券》中,乌效鹏发出“一切的努力全落了空”的感慨,他对社会是不满的。除此之外,乌效鹏所唱的《四郎探母》的象征意味是可究的。是辽是宋,杨四郎受困于身份归属的难题。乌效鹏、顾丹卿等人则面临“家乡归属”的难题,大陆既是家乡又是“匪区”,大陆人民既是同胞又是敌人,在荒谬的对抗中,他们无法定位自己,也无法认同当局。但是,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对“中国人”和中华文化的认同。正如婵媛同样挣扎于身份认同危机,为了一家人能在台湾活下去,她成为了赖国熹的情人,但她却坚守精神上的忠贞,“她和三个孩子,一个老佣人,一家五口人,吃姓赖的,喝姓赖的,她可就是不肯姓他的姓!她说生为叶家人,死为叶家鬼!”即使因为种种原因会产生认同焦虑,但“根在大陆”的聂华苓对“中国人”的认同是坚定的,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感是深厚的。
四、结语
聂华苓的文学创作在台湾开始,早期以短篇小说为主,作品中出现了多种“边缘人”形象:以侯太太和婵媛等人为代表的女性为不幸的婚恋困恼,以袁老头、高老太太等人为代表的老年人仿佛被时代背弃,以顾丹卿、乌效鹏、王大年等人为代表的公务员则展现出“边缘”与“中心”的相互联系,这些“边缘人”的成因往往有所重叠,作者在写作时不免带有亲身经历的色彩,但归根结底离不开时代与政治的影响。聂华苓对“边缘人”的关怀与怜悯始终贯穿其创作,她对“边缘”与“中心”的思考在初期创作中就已有独到见解。聂华苓对传统伦理的思考,对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归属感,也在作品中有所展现,即使当时她身处于白色恐怖的台湾,她仍保有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注释:
[1][25]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编:《在电视上读书读书时间访谈录》,北京:现代出版社,1999年,第119页,第117页。
[2]原文参见成伯清:《格奥尔格·齐美尔现代性的诊断》,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7~138页。
[3]原文参见雷海花:《罗伯特·瓦尔泽小说中的现代边缘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年,第30~31页。
[4]孙辰:《国族流离的边缘发声—论聂华苓小说的边缘书写》,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5年。
[5]杨瑶:《论聂华苓小说中的“边缘人”叙事》,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9年。
[6]林佳,肖向东:《边缘生存的言说——聂华苓与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文化认同》,《大众文艺(理论)》2009年第10期。
[7]傅守祥,李好:《文化之根的漂移与嫁接——从聂华苓小说〈桑青与桃红〉看流散华裔的边缘生存与文化认同》,《杭州学刊》2018年第4期。
[8][1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Ⅱ》,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348页,第435页。
[9][10][15][17][18][19][21][22][美]聂华苓:《王大年的几件喜事》,香港:海洋文艺社,1980年,第153页,第157页,第9页,第16页,第31~32页,第255页,第253页,第258页。
[11][13][14][32][美]聂华苓:《台湾轶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63页,第119页,第131页,第58页。
[12]林海音:《婚姻的故事》,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6年,第182页。
[20]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23][24][26][29][美]聂华苓:《三生三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30页,第61页,第29页,第204页。
[27][美]聂华苓:《三生三世·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
[28][美]聂华苓:《台湾轶事·写在前面》,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年。
[30][31]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86页,第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