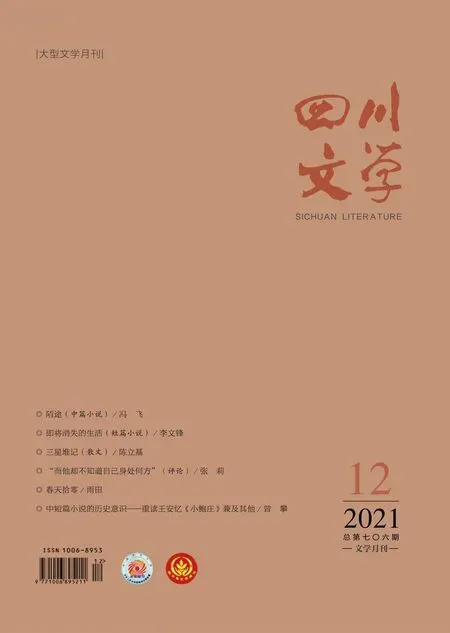即将消失的生活
□ 文/李文锋
上个礼拜,我最小的叔叔也死掉了。死因不明,具体是上个礼拜的哪一天咽气的,都没弄清楚。若不是好几天没见他独居在葫芦嘴旁边的土坯房子冒烟,我和天赐还浑然不觉,以为他又在闭门禅修呢。我们发现的时候,只见他盘腿坐在里屋正中间的一张稻草编织的蒲团上,没了呼吸,却保持着一副闭目养神的模样。
“有可能是饿死的?你看看,他连一张小小的蒲团都没占满。”天赐说,像是发现了什么线索。
“满仓的大米。他还种了好些蔬菜呢。”
隔天,我和天赐一起在村外的葫芦嘴的苦楝树下挖了个坑,先放入一口大陶缸,然后将他原模原样地挪进缸内。
“只剩咱两个了。”往缸盖上添加黄土的时候,天赐难过地说。
可不是嘛。偌大的村庄,二十多栋墙垣斑驳的旧房屋,现在仅剩我和天赐两人了。好像之前生活在这里的人,近些年来,全成了旅客,偶尔到此一游,拿手机拍几张照片,发一回朋友圈,连住宿费都省了。
最让人生气的还不止这些,你是没瞧见他们趾高气扬的做派:一方面,从小汽车尾厢里拎出些水果、牛奶之类的东西,假装出手阔绰地送给你;另一方面,却不拿正眼瞧你,那嘚瑟的眼神,仿佛在说:“好好品尝一下吧,都是些稀罕玩意儿,有生之年,恐怕你们很难吃得到。”
我就十分不屑地看他们那副嘴脸。很久以前便是如此。总之,我和天赐是不被同龄人喜欢的。比我们俩后出生的小屁孩儿们似乎也受到他们的影响,稍微长大一点点,便学着他们的样子,拖个大黑箱子,逐一离去。再往后,上了年纪的那部分人,说是进城帮他们的儿女照看孩子。呵呵,只有天知道他们的真实去向,反正我是没有丝毫兴趣去打听的。
“我们也离开吧?到我姐夫的建筑工地去学习安装模板,很快就能上手干活儿。”我说。
“我们走了,要不了几年,这里便会被那些疯长的竹子全部占领。”天赐面露难色地说。
出葫芦嘴,山势便分别往两翼伸展开来,其形状像极了一弯月牙。我还是个孩童的时候,人们四处开荒,竹子只在山丘脊背上呈线条状偷偷地发育。现在完全不同了,原本潜伏在地表下面的竹根,时常会钻出土皮来挑衅我们,仿佛认准了我和天赐总共才四只手,便肆无忌惮地四处乱窜,眼看快要进屋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这些破房子,想必他们早已看不上了。”
“瞧瞧,那边正在修建高速公路。听说不久以后,铁路也会通过这里。”他直起腰来,眺望着远处的山坳说。
“通了路,兴许他们会回来建工厂,说不准就变热闹了。”他继续说,深邃的眼窝里忽闪着丝丝光亮。
可即便他站得再直,算上一头乱蓬蓬的枯发,身高也突破不了一米六。关键是满额的抬头纹和干瘪的腮帮子,特别容易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他已年过五旬。事实上,天赐只比我大五岁半,才四十岁出头。按照辈分,他该称呼我一声叔叔,可压根儿没听他喊过一声“叔”。他还有一个哥哥,难得回乡,每次见到我,也是直呼大名,兄弟俩别无二致。
“工厂建成后,会招些女职工吧?”
“总不至于请男人做饭和打扫卫生。”
“到那时,托你嫂子出面,前去给你说个媳妇。”我笑着提议说。
见他弯下身子去刨土,不吭声。我继续说:“我还有点积蓄,到时全部给你。”
“我可不想被你娘诅咒。”憋了好一会儿,天赐回答,脸都涨红了。
“再说,就咱们这点钱,哪个姑娘瞧得上眼。”他接着又说。
“我已经很久没有梦到我娘了。”我望向无尽的原野深处,小声答道。
我姐生第一个孩子那年,我随我娘一道,头一回去到她所在的H市。出门之前,我娘见人便要说上一通:“那城市大得哟!望不见尽头的火车都要在里面跑半天。”
我只当是H城很大,没料想到路途那般遥远。连车厢中间过道,都挤满了站客。长途客车兜兜转转,几乎每隔十几分钟,就有人上下车。司机踩一回刹车,我的胃里便有一股酸臭气味往嗓子眼处上涌。挨到午后时分,客车总算停下来了,睁眼见到一长溜大大小小的汽车列队等候在码头边,时不时靠拢来一艘渡船,载走靠前的一截。
我记得下游对岸有一座石头山,横挡住半幅水流,崖壁如同刀削一般。直等到将近黄昏时分,落日变得越来越大,柔和的霞光散洒在颤动的江面上,宛若无数随波逐流的黄金薄片。而那山的背面,仿佛有一个巨坑,正等待着落日沉入。
“你若能留在H市干点什么,咱们便一家团聚了。”我娘对我说,语气里充满了期待。
那时我伫立在轮渡的甲板上,远观对岸数不清的高楼与直入云霄的烟囱,和其身后乱石兀立的群山背景,心里却生发出诸多忧虑来……
出渡口,便见一道并行的铁轨横陈在眼前,密集的人流和车辆被隔离在道口两边,我娘所描述的那种“望不到尽头的火车”正轰隆隆地迎面开来,呼哧呼哧地吐着白色气体,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
“它似乎在爬坡。”我疑惑地说。
“赶了一天的路,油料快耗光了吧。”
尾随它缓慢远去的方向,我们脚踩枕木径直前行。
我娘说:“很快便能走到。”
在我的步伐即将混乱、偶尔出现一脚踩空的现象时,我娘又说:“应该不远了。”
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我姐家的房子竟然找不到一扇窗户,无论白天黑夜,始终得亮着灯。估摸着,隔壁左右亦是如此,因为从外观来看,几乎别无二致。入门便是客厅,先下两级台阶,往里走,是一间小卧室和稍大一点的主卧。直线贯穿到后院,才见到厨房。总之,空间特别狭小。比如中间的小卧室,仅只能摆放一张条桌和单人折叠床。
“这张床是为咱娘准备的。”
“我睡哪儿?”
“客厅那张长沙发。”我姐回答说。
“你瞧,桌子上的杯子在跳舞呢!”火车路过的时候,我诧异地冲姐姐大声喊。
“没看见我把厨房里的油罐全放在地上吗?”她露出一副司空见惯的表情说。
办完大外甥的满月酒宴,我执意要离开。
“好多人去火车站扒拉车厢里的东西,能卖好些钱呢。”临行前,我娘语气兴奋地告诉我。
“那么高的车厢,你如何爬得上去。尽早别想这事了。”
“你看,我的腿脚灵便着哩。”
“可你都快六十了。”
“趁现在还能动,抓紧弄些钱,好给你娶个媳妇儿。”
至今仍然印象深刻,我离开H市的那天清晨,江上漫天飘浮的云朵,红似鲜血。如同后来我时常在梦中所见,我娘栽倒在轨道边,她的身旁,火车风驰电掣般驶过……
“那城市大得哟!望不见尽头的火车都要在市内跑半天。”我逢人便说。
“那城市大得哟!望不见尽头的火车都要在市内跑半天。”我分不清梦里梦外,逢人便说。
“那城市大得哟!望不见尽头的火车都要在市内跑半天。”那些年,我分不清梦里梦外,逢人便说。
“你还记得老篾吗?”天赐突然问我。
“早死掉了。听说他儿子为了躲避火葬,弄了一辆救护车把老蔑的尸体送了回来,连夜抬上毛村的后山,悄无声息地下了葬,连酒席都没置办。”
“咱要有他生前那一身做竹器活儿的手艺,用来收拾这些得寸进尺的竹子,想想看,是不是容易得多?”
“可是做出来的工艺品,怎么卖出去呢?”
“请两名业务员。咱们只管在家生产。”
“女孩子做销售,好像比较有优势一些。”
“将打谷场旁边的大仓库,稍做改造修缮,完全可以当厂房用。”
“住在村办小学那六间大教室里的扶贫干部,好像全都回城了。咱们去找村主任协商,租金先欠着,另外还能节省一笔不小的装修花销呢。”
“可是,那些人之前三番五次地来上门做工作,建议我们栽种楠木树苗,养殖国外引进的什么肉牛,你都不愿意搭理他们。”
“我们干的可算是民营企业,宣传政策常说要扶植民营企业。”
“问题是,老篾已经死掉了。”
“别忘了,他还有个徒弟,也住在毛村。”
“即便他的徒弟愿意重操旧业,咱这小庙,也供不起那么大一尊佛。据我所知,人家这些年搞小龙虾养殖,专供省城的水产市场,早发达了。”
我们沉默的时候,乌鸦的叫唤声自头顶处传来。天赐抬头瞄了好一会儿,突然弯腰下地,捡起几块瓦片,连续朝着苦楝树上乱扔一通,骂骂咧咧地大声说:“真他妈的晦气。”
之后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像只泄了气的皮球,直愣愣地看着脚尖的那一小块地面。
“要不,咱们也养小龙虾?”我提议说。
“想想看,他好好的篾匠手艺都不干了,改行养小龙虾。说明什么?”见天赐不吭声,我继续说。
“别忘了去年养生猪的事。辛辛苦苦地忙活大半年,眼看快出栏了,闹出个莫须有的非洲猪瘟,结果全拉去活埋掉。”
“政府发放的补贴款,足够弥补那些损失了。你怎么还是过不去心里那道坎呢?”
“没有养殖技术,也没有销售渠道,更不能指望政府补贴。风险实在太大了。”
“咱先去毛村学习,然后买他们家的虾苗,再把养大的龙虾交给他去销售,让出一部分利润,总该行得通吧。”
“这么算下来,还剩下多少利润?万一出点纰漏,又白忙活一场。”
话题再次陷入僵局。乌鸦的叫声消失不久,猫头鹰不知藏匿在何方,也跟着叫唤了起来。听起来,那声音忧伤而惊悚,好像来自遥远的天际,又似乎源于咫尺之间的地下深处。
“天快黑了。回家吧?”我说。
“明天咱们一起去城里找我哥,兴许他有更好的主意。”
“顺便跟你嫂子说说,帮你寻个好媳妇。”我笑着说。
从镇北的收费站入口上高速,全程将近一百公里,空调大巴只花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便抵达了长江大桥。
“上次去省城,经过了那座新修的鄂东大桥。”天赐指着上游不远处的另一座斜拉桥,告诉我。
我没有回答。顺流而下,我忆及那座横卧在江上的山,和那个站在轮渡甲板上仰面见到鲜红色云朵的清晨。仿佛这城处处弥散着令人窒息的悲伤情绪,让我眩晕、心悸,浑身冒冷汗。
“你带药了吗?”隐隐约约间,天赐好像在问我。
“我没事,休息一会儿就好。”我回答。
天赐唤醒我时,长途客车已经入站。
“你哥不来接咱们吗?”望着窗外空旷的广场,我问天赐。
“旁边的高铁站有出租车载客点。”
“你上回说,你哥家的房子要拆迁了。他还住在之前那个地方吗?”
“相隔不远。位置已经发给我了,咱们直接导航过去。”
“给了他们家很大一笔补偿款吧?”上出租车之后,我继续问天赐。
“我嫂子管钱。她向来喜欢喊穷,生怕我找她借钱似的。”
“是因为你之前找他们家借过钱,没按时偿还吧。”我笑着说。
“自打出生到现在,我还从未找别人借过钱。咱穷得硬气,不欠任何人情债。”他信誓旦旦地说道,一副要与我诅咒的架势。
出租车爬上一座跨越湖汊的高架桥,在即将进入一个山腰处的双向隧道时,突然转弯驶向旁边的匝道,之后便望见大片房屋坍塌的废墟,沿桥下道路右侧,延续数公里。左侧的湖畔,仿古的亭台楼榭掩映在层次分明的绿色植物间,宛若一幅人迹稀少的清明上河图。
“目的地在您的右侧,请寻找合适的地点停车。”导航语音提示。
“看样子,导航出了差错,竟将我们指引到这种鬼地方来了。”天赐说。
“打电话给你哥,确认一下,兴许就在那丛密林里面呢。”我指向不远处的坡上,笑着调侃天赐。
巧得很,却被我猜中了。坡上原本是一家早年间开山采石的堂口,如今经过灾害治理,人工种植了灌木和杂草,已然复绿。天赐哥哥住在堂口下面的几间临建工棚里。若不是他亲自来路边迎接,我们无论如何也很难找到进入密林的那条羊肠小道。这条步行小道,明显是被他一人走成形的。
“那些植被,是我当年领着施工队喷播上去的。工程竣工验收之后,工人都撤走了,老板请我留下来干养护工作。你们瞧瞧,长势多好。”天赐的哥哥仰面看着岩壁,向我们介绍。
“天天干这些农活儿,倒不如回乡下种地逍遥自在。”天赐带着嘲弄的语气说。
“瞎说些什么呢?种地赚不到钱了。老板从不过问我这里的工作,只要这些绿植不死,便月月有工资拿。”
“来了这么久,我还没见到嫂子,她去哪了?她情愿随你住在这种破地方才怪。”
“孩子正面临高考,她在学校附近的出租屋里陪读,忙着呢。”
“瞧瞧你这一脸失望的表情。”我打趣天赐,指着他的脸说。
“别忘了我们此行的目的,商量正事要紧。”
望着一脸茫然的哥哥,天赐说:“我们想操办竹器厂。如果能找到手艺像老篾那般出色的师傅,钱便像雨点一样落到我们头上来了。”
“老篾已经死掉了。”我补充道。
“想请你帮忙谋划一番。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养殖小龙虾的主意。”
“先声明,拆迁款全攥在你嫂子的手心里,她一个子儿都有没分给我。”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想想,自你结婚至今,我向你伸手借过钱吗?我们大老远来,只求你给拿个主意。仅此而已。”
“我有个朋友,福建莆田人,以前老往我们工地送竹跳板。听说这几年拓展了业务,不光生产竹跳板,还编制竹篱笆,建竹房子。可以咨询一下他,如果我还能联系得上他的话。”
“很多人发财之后,便不拿正眼瞧人,你确定他还记得你吗?”
“我存了他的手机号码,只是不常联系。若是听到我的声音,他肯定高兴坏了。”
说完,他拨通了那个号码,打开免提,等待对方接听。
“谁呀?我不需要小额贷款,别老打电话!”接电话的人说普通话,带着浓重的福建地方口音。
“兄弟,我是李天佑,还不记得我吗?”
“不认识。”
“我是你的老朋友,李天佑……”
没等这边继续,那边已挂断。看情形,对方似乎很忙,且态度极不耐烦。
“他原本是个热心肠的人,一定是最近更换了手机号码。”他表情尴尬地看着我们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
“仔细想想,还是不太可行,前几年人们建砖混结构的房子,竹跳板用量倒是比较大。现在大多改成了主体现浇,少量墙体隔断工程量,用脚手架施工更方便,轮到租赁公司发财了。”停顿了一会儿,他继续解释说。
“先进屋吧?哥,我有些饿了。”
“你看,也没准备什么吃食。但有酒、花生米和兰花豆。幸亏平常种了一些蔬菜,我去摘一些来下酒。”
三间片石垒成的矮房子,单看外观,倒也原始古朴,可一旦这种原始古朴延续到屋内,便令人倍感心寒。好在还有一张旧桌子,不然我们三个人就只能席地而坐了。处在这种返潮尚未结束的季节,有几块摞起来的石板隔在屁股下面,再垫上一片黄纸板,吃顿饭的时间,我的腰并没有感觉到不适。而天赐兄弟俩那没完没了的酒话,听得我实在有点坐不住。
“我饱了。”草草吃下一点东西,我说。
没有回应,仿佛我已淡出了他们的视野。
“你瞧见了,我住在这种地方,你嫂子竟然视而不见。她说,当初建房的地基,是她娘家人的自留地;买建筑材料的钱,是那几年她在水果批发市场摆摊儿赚来的;所以拆迁款也不关我屁事。我问她,是谁带着一大帮工人将房子垒起来的?然后她说,你白住了十几年,工钱早抵消掉了。”哥哥的舌头打着战,情绪激动地说。
“嫂子能干,众所周知。她还是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娶到她做媳妇,你知足吧。”弟弟脸红得像关公,笑着大声说。
“我快活不下去了。那么一丁点薪水,根本不够我抽烟喝酒。我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肉味了。”哥哥说话的声音有点哽咽。
我这才注意到,他们正在喝的白酒,一壶十斤装,市场售价应该不会超过十块钱一斤。至于香烟,同天赐平常抽的牌子一模一样,听他说过,四块五一包。医生以我的病情为由,不允许我抽烟喝酒,每次去复查,他都要反复强调好几遍。我想,即便他允准,我也不敢沾上这些嗜好。我害怕再次犯病的时候,没有人来照料我。
“为什么不同他们娘俩住一块儿?嫂子会做饭,伙食总归要强一些。老不吃肉,喝酒会很伤身子的。”弟弟说。
以前他老婆做饭,荤菜要留给孩子吃,理由是孩子正在长个子。现在变成了孩子只吃荤菜,连盛菜的盘子都不让碰了,还嫌弃他浑身酒气,弄出满屋子烟味。哥哥一边仰起脖子,喝光了杯子里剩下的酒,一边擦拭着眼眶。
“反正在哪里都能赚到钱。不如随我们俩回乡下去,家里有那么多土地,你见多识广,领着我们干,咱不愁没有活路。”弟弟接着说,他的嗓音带着嘶哑,开始结巴了。
“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
“哥,我都快不认识你了。你刚进城那会儿,娘天天盼着你出息,后来听说你被招进了市政公司,她跟人炫耀说,我儿子进了市政府办的公司,吃上公家饭了。我记得当时你烫卷发,穿一身羊皮短套,一副神采奕奕的模样。你看,如今怎么啦?像是变成了另一个人。”
“自打结婚之后,我没过个一天舒心日子。她娘家人看不起我,总说我是乡下来的,干的全是他们嫌弃的粗活儿,收入又低。孩子也不乐意见到我去学校接他,让我尽量离校门远一些。久而久之,连我都觉得自己比其他人矮一截儿。”
他给身前的酒杯斟酒时,几滴眼泪碰巧落入杯子里,他自己可能没有发觉,我也不清楚天赐是否看到。屋子里光线已经暗下来了,而我站立的位置,正好顺着一缕余亮。我想找到电灯开关所在的具体位置,有些担心他们将堆放在桌面上的兰花豆外壳全部吃光了,可扫视完所有的墙面,还是一无所获。但我分明见到一只灯泡悬挂在空中。
“天要黑了。”我说。
“锅台边的案板上有两截蜡烛。”
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我走进另一间光线更加暗淡的屋子,只见到一口锅架在半截油桶改造成的火炉上,炉门前堆积了好些劈碎的木头门窗外框。这种灶具我在乡下时常见到,只要有人家办酒宴,厨师便会自带这些家什上门来找活儿。此刻我若再去问蜡烛在哪儿,估计也是白搭,还不如自己找找。借助手机显示屏的光亮,在我转身大约一百六十五度的视角处,找到一张长方形案台,它其实是由两扇大门拼接在一起,背面还卡着门闩。
“看情形,晚上只能睡在那张案板上了。”我送蜡烛过去时,提醒天赐说。
“瞧我的记性,差点把正事给忘了。你们明天返程,将里屋那两扇大门给捎回去。俗话说,卖屋不卖门。虽然房子拆除了,但大门关乎一个家庭的脸面,可不能弄丢了。”
“如今谁还稀罕木头做的大门呢,不仅招蛀虫,还不防腐,都换成不锈钢材质的了。”
天赐这么说,他哥便不再说什么了,只顾低头喝闷酒,仿佛屋子里的空气突然间凝固了,两个大黑影被影射在墙面上,宛如播放无声电影一般。
他们沉默的时候,我想起了水库的应洪道旁那片林场。穿过葫芦嘴,再翻两座小山包,小时候我去那片林子掏过白鹤的鸟窝。前几年来了一伙城里人,搞什么科技农业,将之前的大杉树全伐掉了,改种了一大片猕猴桃。林业部门几次上门,帮助改良土壤,还免费赠送一套滴灌系统。现在可不得了,听说他们给果树全都安装了摄像头,推广客户前来认栽,跟养宠物似的。每逢节假日,便像以前生产队出工那样,女人们领着孩子,全都下地干活来了。
我把这件事同他们兄弟介绍了一遍。
“那些都是有钱人。我们可不行,除了那些荒芜的土地,我们什么都拿不出来。”
“我们有使不完的力气呀。月儿山下有几百亩不需要缴纳租金的田地,等咱们干出了规模,政府部门必定会来帮扶。”
“想形成规模,首先需要机械化作业,月儿山下沟壑丛生,别做白日梦了。还是想想竹器厂或养殖小龙虾,比较靠谱。”
外面的夜色似乎更黑了,屋内的烛火忽然明亮了不少。兄弟俩的对饮依然没有结束的迹象。至于他们反复争论的话题,无非总是那么几句话,彼此说服不了对方。我想,无论如何,人各有命,明天一早,我是一定要返程回家的。
出门见山,顺着近在咫尺的岩壁抬头望,巴掌大的一小块天空,几颗星星忽明忽暗。在一株稍大一点的樟树脚下,我寻得一块桌面大小的青石板,然后仰面平躺。的确是太困乏了,可我的脑子却转个不停。
那个时候,我独自从H市回到月儿山,小叔守在村口的大樟树下翘首以盼,见到我便说:“城里有什么好的,改天我教你阉鸡的本事,只要有手艺傍身,在哪儿都饿不死。”
他一生未婚,膝下无儿无女,始终视我如子。若不是后来小叔迷上了修行……
再见村口的大樟树,猛然间,方才意识到小叔的离世,像是从我的脑海抠走了所有的温暖部分,仿佛许久之前所受的一道伤口,此刻感知到了疼痛。
“就剩咱们两个人了。”我说。
“是啊!别指望谁会回来了。即便我们办成了竹器厂,哪有工人愿意来这种鬼地方打工呢。”天赐回答。
“守在月儿山,也未必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说不定那边正在修建的高速公路会穿过咱们村子呢?未来还有铁路,总会跟这里沾上边的。到时候,田地被征用,房屋拆迁,咱们什么都不用干,也能得到一笔丰厚的补偿款。”
“假如,你有一位像我嫂子那样的媳妇……”天赐说这句话的时候,同我四目相对,尔后,我们都笑了。
这时,乌鸦的叫声自葫芦嘴上传来,猫头鹰那令人惊悚的鸣叫声紧随其后,在空旷的原野间持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