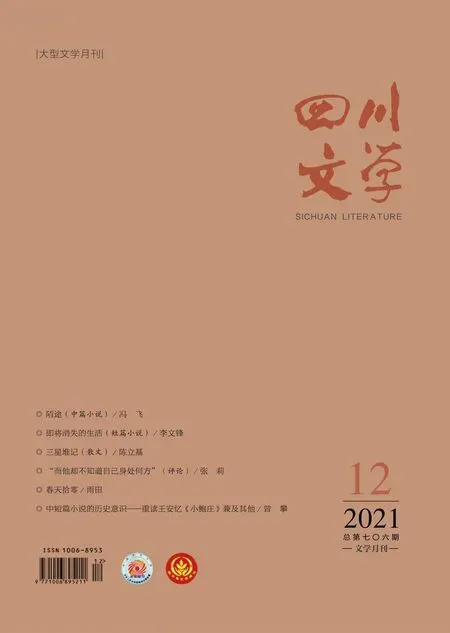光阴中的柔情
□ 文/胡正银
最柔软的不是水而是人心,是艺术,或者说是艺术的人心与人心的艺术!四川合江县,地处四川盆地边缘与黔北高原的接合部,半是山区半是丘陵,自然条件较差,但上天又给予了补偿,即让长江、赤水、习水三条河流穿境而过,使原本闭塞的边陲之地变得通畅,方便了中原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上的互补和交流。中原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交集、人文风情,这里都有。具体反映在那些埋在地底数千年的石棺上。某种程度上说,合江汉代画像石棺就是一部中国民族风物和民族文化的精美典籍。
高落差而又雨水丰沛的地里环境,使得合江高山地带山风粗粝冷酷,丘陵地域土肥水暖。山里生长竹木药材,丘陵谷地盛产稻米,物产丰富。赤水、习水两条河流在县城与长江交汇,成为古时由川入黔的唯一水路通道,是一交通要冲。《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秦灭,汉武帝及其政府开始对“西南夷”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派中郎将唐蒙出使夜郎,由合江县城入赤水河出黔北,说服多部同归附。此后又劈山修路,与夜郎往来密切,大量中原人口拥入,合江画像石棺,就在这两种文明的交汇中诞生。
在县城居住了若干年,离置放汉石棺的博物馆只几公里,但去的次数屈指可数。不是没机会,是不愿意走近它。人的通病是“熟视无睹”。几年前,随县文物局的人下乡,去凤鸣镇山里看一处墓葬群,说是里边有石棺。那里离县城四十余公里。去了之后,自感颇有收获。
那是一处幽深而静谧的所在,山梁小丘全被翠绿树林覆盖,山下一条小溪,溪水哗哗。我边走边羡慕,生活在这样地方的人,就如生活在绝美的画卷里。心里也盘算,如果允许,一定要重返乡下,在溪边修几间茅庐,度却余生。蜿蜒的小路,似乎与满山的绿一样没有尽头。老树沉稳,幼树撒欢,构成一幅清绝的水墨画。置身其中,抬头看天青云白,低头听溪水浅唱低吟。绿色与静谧,如同清晨的天光,黎明的窗口,敞亮得让人突然惊喜。我恍若在天光之上,任凭暖流行走于我的肉身,簇拥我的灵魂。
择其一而进,却没有石棺,墓室建得跟周边生活环境一样。借着手电的光,我被石板上精美的雕刻深深震撼。那一刀一刻、一锤一凿,无不充斥满满的情愫。石刻画像所反映的生活场景,竟是那么翔实、逼真,把人间的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或许是受那份真实的柔情感化。我的脚步很慢很慢,我试图从一个个精美的图案中读到些什么。头顶电灯的光异常透亮,石棺和棺身的美图同样透亮,只是没有影子。四周很安静,图与文字仿佛也在凝神屏气,冥思光的声音。
走完一个来回,数过一遍,得到的准确数字是,展室里摆放的石棺总共8具。在博物馆的后面,还有众多的石棺有序地排列着。粗略计算,共有40多具(口)。石棺的出土时间早迟不一。虽然每一具石棺都年岁已久,却依然保持完好的状态。在它们身上,依然能读出那逝去的故事与激情,在历经千年之后,表情仍不苍老。似乎,岁月只能肆虐人间,于厚土与坚石,却无可奈何。
合江画像石棺,这个名字其实潜出时光的记忆并不长。在博物馆的记载中,“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有出土”,但真正收藏时间却是起于1984年。在此之前,有十多口画棺已经遭到毁坏。现在看到的藏品,是之后陆续收集起来的。尽管或许只是所有汉石棺中的点点碎片,但并不影响对一个历史时段的探索。
我曾经请教过最早接触合江画像石棺的人王庭福,他曾任合江县文化馆馆长,从事过合江汉代画像石棺的课题研究。
我向他尝试了解合江画像石棺的风俗起源和墓葬范围、内容示向以及相关故事。
我们坐在他家的茶几旁,屋里飘着幽幽的茶香。他谈了一些自己研究的成果,唯一不能确定的,是自己百年之后能不能也用石棺。按理说,现代木材稀缺,石头取之不尽,用石棺无可厚非,可花费定然不是小数,经济上划得来吗?他的话让我从追索走进现实。很显然,他退休太早,后来的信息了解不多。他没有像我期待的那样有声有色地讲述有关石棺的更多故事,而是很平静地招呼我喝茶。好一阵,我们相对无言,各自品着飘香的茗茶。一只小猫跳上茶几,眼睛盯着我,喵喵叫几声。
汉石棺博物馆在合江老县城的最高处,出门一拐就是体育广场,紧邻合江中学。广场早先是开放的,市民去广场走走,然后到博物馆看看,打发闲下来的时光。数年前,广场划给了合江中学做体育场,封闭了,来博物馆不再是路过。博物馆是一栋老房子改建而成,很安静。站在门口,其实就站在了动与静的分界线上。耳畔传来的琅琅读书声,如同在黑暗里遇见光明。眼前的汉石棺博物馆,更显幽深,也多了些神秘,在读书声的覆盖下,以诱人的静谧引领我走向历史的深处。
太阳光线从天井的檐口照射下来,穿透井底与房檐的幽深,将空气撕裂。站在走廊上,仿佛能听到嗞嗞声。无心观察或许能称得上很美的环境,我依旧窜进展厅,走近那一具具曾埋藏千年的巨棺。每一次来,我一直关注的都是石棺上的画像,并没在意墙上一幅幅与之关联的文字。有次我踏进展厅的时候,文物局的一位朋友正在那儿,他说石棺上的画像其实就是一个个故事的拼图,墙壁上的解说中都能找到。我突然顿悟,我冥思苦索想要探寻的谜底,竟早已被识破并写成了文字,只怪自己太马虎粗心没当回事。
时间,是最杰出的掩藏大师。所有的美丑、传说、故事,在时间的摧残下,很快淡出和隐藏。超强的记忆,活泛的眼神,强不过生命的毁灭。除了依靠文字、画像,一切活动都会被时间抹平。对没有文字记述的画像,只能用推测或推理阐释。其实画像就是人的精心预谋,之于人的灵魂与心情,算得上是神来之笔。
石棺上的画像有自己的语言、色彩和线条的律动,它们在无声地与我对话。此刻,我用目光触摸它们潮汐般的心声。它们就像一条条从时光深处划来的船,我的思绪站在船头。石棺则如朦胧的大海,在飘来的声浪中起伏,托起我无尽的猜想。
其实,我的猜想在壁上的阅读中已经得到证实。据已发现和出土的石棺研判,其形制有两种。除眼前这一用石材雕琢绘有画像、可移动的石棺外,还有另一种依山雕琢,除棺盖外,棺体与山体相连无法移动的石棺,当地人称之为崖棺或石函。不过,第二种石棺没有画像。可是,我觉得无论有无画像,可不可以移动,这样的葬具已经超乎想象,它们在低调中透出一种让人不能不诚服的粗犷和情怀。在融化你心灵的同时,让你不自觉地飞升,放飞你的想象,潜入你的内心。
所有出土的画像石棺都有着华夏千百年农耕文化的特征,也是儒道文化的反映,其画像是绘画与雕刻相结合的产物,构图具有浓郁的中国画味道。创作者运用丰富的构思和巧妙的手法,把画面安排得既不疏散单调,又渲染突出了主题,体现了民间匠师艺术创作上的高深造诣。他们采用形与形的重叠,相互借用,展现出一种粗犷、豪迈的美,给人以洒脱无羁之感,艺术手法令人惊叹。
我的目光离开画像时,褐色汉代石棺罩在一片雪亮的灯光下,比藏在地底时多了几分神韵。铁画银钩般的画像酿造出我心情的五彩缤纷。前人的思维,总比现代人实在些。他们用石头做棺材,很大的原因应该是石头的不朽。渴望不朽,也许就是人类灵魂挥之不去的底色。
上午九十点钟,阳光已经把所有的雾霾清扫干净,白亮亮地挂在天空。天井里的青果树上,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停在树枝上,躲进树叶的阴影里。八月里,盆地的天空总这样,即便是晴天,也灰蒙蒙极闷热。躺在博物馆里的这些能移动画像石棺被玻璃密封着,像一个个冰雪透明的雕塑,静静地享受除湿后的恒温。当目光从它们身上扫过,我突然发现,过去与当下的时光,一下子重叠在一起。
公元前115年合江建县,到现在已经两千多年历史。漫长的岁月里,人们在劳动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画像石棺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人死后墓葬缘起何时,虽然无法判断出准确年代,但这种入土埋葬的形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无疑是非常进步的,体现了人类对自己的尊重。合江汉代墓葬有崖墓、砖室墓两种,画像石棺多出土于崖墓。
县城是驿站和商业中心,现在依然是人口聚集最多的地方。依长江和赤水河边,高楼大厦林立,陆路汽车飞驰,江中百舸争流,可以想见,当时作为与夜郎商贸流通的节点,其地位比现在重要百倍千倍,繁华是不必说。所以,崖墓主要分布在县境的长江、赤水河、习水河以及大小漕河沿岸的台地、斜坡、山崖上。崖墓凿崖为洞穴,以洞穴为墓。但石棺崖墓主要分布于以县城为中心15公里的范围内。这些年来石棺的出土,证明了这一点。
这些造型堪称完美的石棺,多数雕刻有精美画像。即便少量线条简洁、棺体无画像的,也做工精细,全使用天然青砂岩整石雕凿而成。棺盖成弧形拱状,四周基本与棺身齐平,棺口与棺盖之间有子母榫。棺身四壁与棺底相连。不难看出,无论是凿石造棺,还是在棺身精雕细刻,在那个科技极不发达的时代,无疑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此时,负责管理的小张走进来,手拿抹布擦拭罩在棺体上的玻璃,神情专注而虔诚。白色的高跟鞋,蓝色的牛仔裤,粉色的花衣,黑色的头发与灯光嬉闹着。玻璃罩里的石棺显得陈旧,如一个个从岁月中走过来的老人。
小张的青春与石棺的老成,构成一种难以言说的隐喻。
小张正在擦拭的一具棺口有一些残破,棺盖处露出了几个小缺口,破坏了石棺的完美。虽然,这或许会有一些视觉上的缺失,但并不影响其本真和精致。
石棺左侧是一幅车骑图。画面正中刻绘的是一轺车,车上坐二人,右为车夫,左为坐车的人,车中立华盖,前有两伍伯导引,后有两卫从跟随;右侧刻绘拜谒图。画面正中刻一四阿式顶房屋,檐下立柱采用一斗二升,两扇门关闭。屋内两人,右边一人戴冠着袍,席地而坐,示意客人就座,由是可知为主人。身前置一几案,上摆几碟菜肴。左边一人双手拱于胸前,作拜见状,当为客人。两幅画像构成一个完美的故事,表现出主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盛况。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本土性自我催熟的时代,经济繁荣,社会富足,所形成的文化,为后来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固化,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画像从线条到构图,都有大气奢华之感。就所发掘出来的墓葬看,虽然不能与帝王将相宏大的规模相比,但棺椁却要丰富多彩些。仅仅是石棺本身,就令人惊喜。帝王将相的墓葬耗资巨大,修得不同凡响,却同样被岁月腐朽为泥,而合江人另辟蹊径,却留下了不朽的文化。西南夷的汉石棺,和身带的画像一起,成了精彩的T形台,展示出了那个时段的社会风情。他们像一双双柔情满满的眼睛,平静幽深的水潭。合江,也因有了这些石棺,吸引来一束束温暖而智慧的目光。
尽管它们很珍贵,内含丰富而又纷纭,可是,汉石棺博物馆那种有些阴的氛围,很多人不喜欢。我常去的原因,可能基于研究与欣赏本身。
欣赏与研究,必须要有一个好对象,必须要与对象面对面接触、对话。汉代画像石棺作为合江文化沉淀的代表,安置的场所当然应深具仪式感、极富历史沧桑感。可以说是合江这座城市的文化精魂。即便如此,合江汉代画像石棺博物馆仍让我大感意外。博物馆设在一栋木质结构的老房子里,清代的“考棚”,初级考试,考童生的地方,房子本身就是文物。这倒方便了参观的人,既看到了石棺的古朴,又欣赏了考棚的精美,就如票友进戏院,一举两得。而石棺与考棚,则如深入骨髓的亲情,组成文化长路上的一个驿站,相互取暖,坐地论道。
令我惊喜的是,博物馆里的石棺画像多数是充满生活情趣和柔情的。有一次去,正巧文物局局长贾雨田在展室例行检查,他引我到3号棺,让我研究右侧的画像。仔细看后,发现是一幅刻画了众多人物的构图,画面六人二兽,形态各异,神态逼真。最重要的右端三层楼阁的底层内,刻绘了一个劳动场景:一人在践碓舂米。稻谷如何脱壳成米,在原始的农耕社会是个很麻烦的事。人类何时利用工具脱壳稻谷,没有准确记载,这个画像说明舂米在汉代已经普遍运用。桓谭《新论》里说:“宓牺之置杵臼,万民以济。及后世加工,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臼。”据考证,这种“延力借身重以践臼”的杵臼发展了很长时期。明代天工开物就说,“舂臼有两种,八口以上人家,掘地藏石臼其上,臼量大者容五斗,小者半之,横木穿插碓头(碓咀冶铁为之),足踏其木而舂之”。在合江当地,这种杵臼加工粮食的方式直到新中国成立时还存在。舂米图反映那个时代就已极具智慧的劳动文化。精细的构图、清晰的画面,依然带着泥土的芬芳。与这样的画像对话,远古而凝重,洋溢某种神往。我迷失在画像中。半蹲在展室里,傻傻地盯住好久,没敢动一动脚。虽然有备而来,但还是低估了其魅力,我不能容忍自己对画像的轻佻。
炽热的太阳光经过窗户玻璃的阻挡,再被石棺外罩玻璃的过滤,铺在石棺上时,温柔了许多。时间容不得我懒散。我尽量腰挺笔直,目光游走,始终不离画面笔画的龙影蛇形。我仿佛看见,一个个雕刻大师、一个个绘画巨匠,向我走来。
此刻,汉石棺画图里迷雾一般的文化内涵,似一股股清凉的甘泉,滋润我风尘中干渴的心魂。柔和的光,让画像格外显眼。凸起处,柔光润泽;凹下的线条,精准而不失灵气。贾局长出去了又进来,问我要离开了不,说是中午下班,展室要关门。我直起腰,不好意思地冲他笑笑。窗外,已经有学生嬉笑着经过,时不时射来明亮的眼神。恍惚间,我的视线弥漫在飘动的色彩里,天真活泼的童影,呼吸里的不正是由秦汉一脉而来的合江气息?我知道这是想象。我喜欢这样的想象,喜欢这样助我思绪飞翔的想象。或许,这就是一种情怀。
其实,我更青睐另一类画像。21号棺和22号棺是我去的次数最多、停留时间最长的石棺。这两具石棺刻绘的是一幅养老图。或许,是个人的偏好,但不排除赞赏。就个体而言,沉潜于内心深处的文化是最本真的。在整个社会层面,文化的精髓部分,常常隐藏于民间。两具棺的画像都彰显的是合江民风。
22号棺右侧图案就很典型。画像分两部分,左端雕刻一枝繁叶茂的大树,树枝上挂着盛水的陶壶,树下不远处,停有一辆辘车,一位老人坐车上。远处的田间,一男子手握锄头在耕作。不用说,辘车应该是男子带送老人的乘坐工具。专家说是董永侍父图,但谁又能说不是墓主人的生活写照呢?无论是董永也好,墓主人也罢,图像所表达的就是一个孝字,只是处理得很智慧。另一部分是一马驾棚车奔驰向前,车旁有侍从跟随。推测,这是表现墓主人发达以后回乡探亲的情景。不能不赞叹,沟壑纵横的石刻,展示出的却是笑容一般的柔情、溪流一般的亲切善良。
21号棺更带有明显的指向性。图像画面为一老人手持鸠杖,席地而坐。右边为一干栏式四角攒尖顶楼房,其上为一条奔腾的青龙,左边绘的是联璧纹。图像所表现的,是一位老人在愉悦地享受生活。汉代特别倡导尊老,特别在东汉,已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从皇帝到普通百姓,各阶层都出现了各种孝子故事。当时的统治者还用孝行考察一个人是否能胜任一方之职,并作为一种衡量标准,称为“举孝廉”。《汉书·礼仪志》载:“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率群臣躬养三老,五更辟于雍。”或许比不上乾隆的千叟宴规模宏大,但开了个好头。关于鸠杖,《续汉书·礼仪志》里是这样说的:“仲秋之月,案户比民,年七十者授以玉杖,八十九十礼有加。赐玉杖长尺,端以鸠鸟义饰。鸠者噎鸟也,欲老人不噎。”这样的一幅图案,好似一首单声部乐曲,听起来悠扬而明快;又如一声色醉人的画面,好像寂寥之中,有人在手抚古琴,弹奏来自远古的空灵与悠扬。
我曾经问过有关专家,为啥一定要用鸠鸟作手杖首饰呢?他有些惊讶,然后说,《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引《风俗通》中有这样一段话:“俗说高祖与项羽战,败于京索,遁薄中,羽追求之,时鸠鸟正鸣其上,追者以鸟在无人,遂得脱。后即位异此鸟,故作鸠以赐老。”他说信不信由你,反正书上是这样写的。古人诚实,这种记述应该源于生活本身的呼唤,源于内心的涌动,和崇尚敬老的灵魂,我岂能不信!不过后来我又找到了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是从医药的角度阐释鸠鸟的作用的。他说:“鸠鸟,名目,多食益气,助阴阳,以病虚损人,食之补气。食之令人不噎。”这个,或许是用鸠鸟作手杖首饰的真正缘由。在士大夫眼里,有帝王将相的传奇,凡事陡然高贵,而在普通百姓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石棺,是人类社会进程中最独特的一道殡葬风景。
据说,山东河南等中原大地也有出土,不知道其画像异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都带有浓郁的乡土故事,都融进了血缘至亲的情怀。人类意识中,棺材是人在生命终结后居住的“屋子”,是最后的安居之所。一个人生命中所演绎的历史,所经历的风霜雨雪,都汇集到这里。一切荣辱贫富,都在进入棺材那一刻终结。汉从秦继承修仙成道不老之说,信奉肉身不朽,大量葬具选择了石棺,没想到留下来的,仅仅是费尽心力开采出的石头和精雕细刻的画像。从这一点说,似乎有点得不偿失。但再现了岁月湮灭的过往,石棺和画像不是虚构,是过去人们的生活,使我们在今天还能与古人对话,还能为一脉传承的忠孝礼仪寻到根。华夏民族独有的文明,价值是无法衡量的。
石棺与河流,一静一动,参与并记录社会的进程,续写新的文化和历史。河流以动的方式储存时光,深藏众生的生死悲欢,从不会主动向人讲述岁月的故事。我们只有打开自己的灵魂,从浪花中去读懂密语,才有可能进入其记忆的内部。许多时候,静比动更有力量。石棺是静止的,石棺上的画像也是静止的。人们来注目,它看进来的人们。在它眼里,去去来来,悲欢离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守那一份爱、那一份情。漫长的人生只是一个瞬间,恒久的是情。它把想要说的,写在线条里,让现代人去推测、去猜。或许,初衷只是记录,只是为了彰显家风,只是褒扬亲情,未曾料想几千年后,能与今人相见。
这正是上班时候,博物馆门前一位清洁工人正在清扫落在地上的树叶。从学坎上老巷子里走来一老一小,四五岁的小男孩蹦蹦跳跳在前面飞跑,后面老人追着步子喊“慢点慢点,看摔了”。话没落音,小男孩果然噗的一声摔倒在地。清洁工人丢掉手中活儿,跑过去抱起孩子……一切又恢复平静,我的眼前依次是我自己的影子、牵手的爷孙、画像、河流和挂在苍穹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