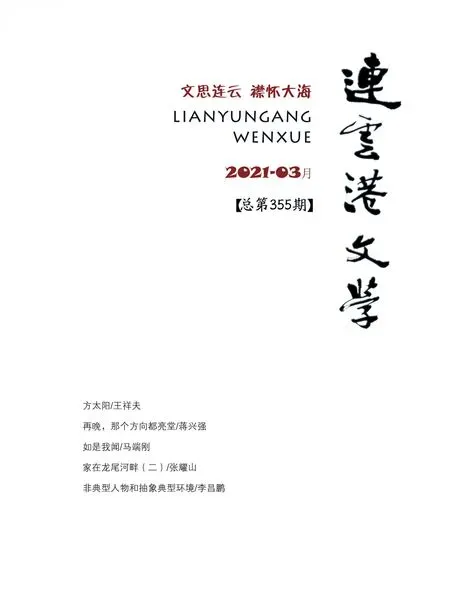家在龙尾河畔(二)
张耀山
童年的舞台
龙尾河上接长江,下通大海,由南向北从市区穿城而过,流经我家门口时形成一个U形的水湾,水湾旁边有个土堆凸于水面,土堆不大,约十平方,有点像半岛,这是我和伙伴们童年的舞台。
“半岛”承载着我的童年梦,是我童年的舞台。“半岛”向南百米便是贾圩桥,向北不远处是铁路桥,这是我童年目所能及身能所至的全部范围。东西走向的贾圩桥是城乡间往来的唯一通道,出贾圩桥向南通向灌云,向东可直抵“东山根”即今日的花果山。我家的“红房子”是城乡接合部的标志性建筑物,南来北往的进城人,看到了红房子便知道,离市区不远了。
贾圩桥是座木头桥,桥面不宽,仅能容一辆马车通过,桥上刷了厚厚的沥青。桥底下有架扳曾——一种较为原始的捕鱼方式。每到雨水季节,这里是我们小伙伴经常光顾的地方。
记忆中的贾圩桥不仅是南来北往人们的通道,同时也是人间通向“地狱”的“奈何桥”。贾圩桥的东桥头是一片坟茔,当地人称之为“小乱坑”,由此向东是“大乱坑”,这“大”与“小”不是以规模的大小而是以先后的顺序来命名的。“小乱坑”多为新坟,坟不大,只是一个小土堆上踩上两个坟头而已,甚至连个墓主的标记都没有,多数是无主坟。月黑风高,万籁俱寂的夜晚,常有“鬼火”在乱坟岗里飘移。红日高悬,天高云淡的白天,有时有“鬼风”卷起,上口大底口小,如同漏斗一般,夹着尘土向对岸居民区扑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鬼风”。“鬼风”在哪家门口停下来,足以将主家吓个半死。“困难时期”,每天有各种原因而死去的人,经贾圩桥在距其不远的“小乱坑”下葬。条件稍微好点的人家为死者备个薄皮棺材,条件差的人家索性用张芦席,雇个“土工”便草草地掩埋了。没有任何仪式也少有悲痛欲绝的呼号,这或许是死者家属自身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为了自己能继续活着保存仅有的能量,或许见怪不怪已经麻木了,在这贫困交加饿殍遍野的处境中,死亡本身也许是一种解脱。这种场景见多了,使我从小就形成了对“死亡”的旷达。
不过在我的印象里,我周围的邻居好像很少有谁家受到这场灾难波及,我想这应该得益于龙尾河的护佑。
马 艞
与龙尾河一水相隔的是新浦农场的地盘,市区人习惯将这片区域叫作马艞(音tiao)。稍作留心便会发现,新浦周边被称为“艞”的地方还真的不少,如宋艞、刘艞、东艞、西艞。在我小的时候,龙尾河的支流如扁担河、玉带河以及小沟小汊上都有艞的存在。曾经一段时间盐场还被普遍使用着,如今只有在个别人工景点偶尔能见到此物,大多是具有怀旧情怀的设计师的手笔,没有实用功能。我记忆中的艞是在河的两岸用木棍搭起台子,再用长而不太宽的木板连接起来,平时可以行人,有船来时移动木板,让船驶过,既经济又实用。这个“艞”字很生僻,属于地方用字,旧的《新华字典》上是査不到的。活字印刷时代,当地印刷厂要专门铸字,可见其应用范围非常狭窄。
二百多年前,明万历六年至清咸丰五年,由于黄河全部走苏北入海,泥沙骤增,使海岸线迅速向海州东北方向推进,海水退去,陆地形成。在这片新生的陆地上,艞便应运而生。可以这样说,新浦地区最初是由艞连接起来的城市。新浦附近,艞的地名有几十处之多,如宋艞、刘艞、东艞、西艞。马艞只是其中之一。
随着新浦的发展,灌云、东山根一带农民,到新浦卖草、卖水、买日用品的人越来越多,来往的人必须过龙尾河。河面很宽,水流很急,海潮更是潮潮相应。为了进街,人们在现瀛洲桥北不远的河面上,架了座木缺,这便是马艞。
百年前的一天,刘顶附近小马庄农民马开贵领着妻儿逃荒于此,搭个丁头舍安家落住,靠过往行人给点零钱维持生计。日子长了,马家在艞头摆了地摊,买点瓜果梨枣、茶水之类的,这儿便成为行人的歇脚地。这座无名的木艞,也因马家看守,被称之为“马艞”。久而久之,龙尾河西的新浦人把河东新浦农场这一带,统称为马艞。
后来,马开贵老人去世了,他的儿子马怀景、孙子马德喜相继接班,看守此艞。全家三代,一看就是几十年,直到艞的功能被桥所替代,马家人才离开马艞。(参见韩世泳先生马艞之得名)。
新浦农场的居民主要分布在马艞和刘艞两个区域,大多来自移民。据说是新沂某地修建水库,将库区的村民搬迁过来的,有点类似于如今的“三峡移民”。龙尾河边的邻居习惯管他们叫“新沂侉子”,从骨子里排斥这批外乡人。
“农场”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体制也很独特,他们的职工拿工资,享受城里人的计划供应,却干着农活,这种不工不农的体制却釆用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农场是团级建制,下面分为营、连、排、班。它坐落在新浦地区却不受地方政府领导。这是一个不工不农不军,亦工亦农亦军,体制独特的部落群体。
毛主席老人家曾说:“工人以工为主,农民以农为主,军人以军为主。”农场人犯难了:我们到底以什么为主呢?在我们外人看来,既然是农场,理所当然地以农为主,只不过与纯“泥腿子”相比,农场的机械化程度高一些而已。
农 场
一年一度的海州白虎山庙会,龙尾河畔的居民会像农民一样去赶会,购置一些简单的农具,焦虑地等待农场庄稼“开镰”。由于是机械收割,会有零星麦穗遗漏,加之麦茬地要急于翻耕种水稻,在这间隙里龙尾河畔的居民会蜂拥而至,“拾遗”“补缺”。农场的“东方红”拖拉机还在收割,一些城里的妇女背着歪篮和口袋在此焦急地等候,一声“放门”令下,妇女们争先恐后涌向麦地,双手并用,眼到手到,动作娴熟。一个麦季捡上一两百斤小麦是不成问题的。回到家后用石磨磨成面粉或面糊。农场那边的小麦还没装进麻袋,这边的小麦粥巳端上饭桌。可不要小瞧这一两百斤小麦的补贴,再加上计划供应粮,掺兑一点粗粮,精打细算,足够熬过一个夏天。接下来就是秋收,如年头好的话,一个冬天也能应付过去。
由于农场实行大面积机械化作业,会有许多小面积不规则的土地被闲置或遗漏,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说过龙尾河畔大部分居民来自农村,几千年的农耕文化,使他们对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依赖和挥之不去的眷念,干起农活来更是行家里手。所以我们的邻居们在河的对岸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拾边田”。占据了如此这般的地域优势,即使在“困难时期”,也没有受到多少威胁。
由于龙尾河水的分隔,把两岸居民的身份给模糊甚至颠倒了,产生了有趣的现象:河东岸是农村的城里人,河西岸是城里的农村人。
假大门
龙尾河东岸,距河边不足百米处有一条小铁道穿农场而过。小铁道的起点是新浦火车站,终点是华北桥头港务处。其功能是将火车站上从山西河南等地运来的煤装上小火车运到港务处卸下,再装上船通过水路送到沿江各地。由于小火车的煤装得很多,加之铁轨不太平整,在运输过程中,尤其转弯处受离心力的作用,会有少许煤块撒落在路基上。居民们将它扫起来装到筐子里,运气好的话,一天能捡上几十斤,足以解决烧饭取暖之需,如有剩余还可以换点散金碎银以补柴米油盐之用。
出贾圩桥向南百余米有座“假大门”,是新浦农场的标志性建筑。之所以称之为“假大门”,是因为它并没有门,如同法国戴高乐广场的凯旋门,她的象征意超越了她的实用价值。起初“假大门”是在松棒骨架上披上松枝,顶部有飞檐,中间有伟人照片,两边挂着伟人手写体对联,颇有几分古典建筑的韵味。不知什么原因,“假大门”失火烧掉了,等我们跑去看热闹时已化为灰烬,空气中弥漫着松香的气味。后来,农场在原址上建了一座永久性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坚固又气派,是龙尾河边一道景观。但尽管升格了,身份没变。
进入“假大门”是新浦农场的场部,农场的首脑机关。除了有办公场所还有礼堂和篮球场。篮球场经常举办农场职工篮球比赛及大型娱乐活动,每到这时我和小伙伴们都会去免费蹭看。
篮球场还有一大功能是露天电影院。几乎每星期都会放电影以丰富农场职工的文化生活。那时,看电影是很奢侈的精神需求,市区里有工人电影院、人民舞台、草棚球场等专业放映场所,但是需要掏钱的,即使是学校包场,像我们这样贫困的家庭也付不起这笔费用。所以,只要听说农场放电影了,我们整天都走神,无心放在学习上。
有一天来迟了,电影快要结束了我们才赶到,好在最精彩的部分往往留在最后。等我们气喘吁吁地找个地方坐下来看时,总觉得有点纳闷,电影中所有演员扣扳机,用刀砍人,甚至日本鬼子扇肥胖翻译官的耳光,用的都是左手,而且声音特别洪亮,我们模仿着用左手在自己的脸上反复抽打好几次都达不到电影上的音响效果。电影结束时我们才发现,我们位置坐反了。好在,这晚的电影是两部连放。第二部电影内容是表现战争题材的爱情故事片,后来知道,这部电影的片名叫《刘堡的故事》。看了几分钟听不到枪炮声,实在没劲,我们坐不住了,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玻璃瓶子到球场周围的芦柴地里捉萤火虫去了。
夜晚空中飞舞的萤火虫给人以神秘而奇特的感觉,抓它时生怕烫手,越是好奇越有诱惑力。大概是放电影强烈的光线将萤火虫逼到了芦柴地里,很密集,一把能抓上好几只,孩子们对信手拈来的东西不感兴趣。当我们准备鸣金收兵时,忽然看到芦柴地里有两人,仔细看好像是一对男女拥抱在起。无论在电影或在现实生活中都是第一次看到这一“逆天”的场景,于是好奇心再度被燃起。我们屏住气息,撅着屁股,调动孩子所有的思维能力,急切地等待电影以外这段爱情故事的延伸,可是他俩不配合,像木桩一样傻愣愣地杵在那儿,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太扫兴了,于是我们悄悄地撤离了。
第二天我们将这段“艳遇”告诉同学时,他们既兴奋又羡慕。
偷 瓜
农场是我们的大后方,她为龙尾河岸边的居民提供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有吃的,有用的,还有玩的。
河对岸正对我们家门口的河坡上,有一间红砖砌的房子,夏天芦苇长高了只能看到房子屋顶,冬天芦苇割了才能见到它的全部。房子不大,当然也不需要太大,里面只住着一个老头。孩子眼中的老头姓郑,不过四十来岁的模样,花白头发,留着稀疏的胡须,个子很高,说话傍腔,是个移民。听说他的拳脚功夫了得,家边喜欢舞刀弄棒的小男孩想向他拜师学艺,都被他一一拒绝。据说他是从朝鲜战场上退役下来的残疾军人,除了农场发给他的工资以外,每月还有相当可观的津贴。邻居们私下议论说他不能结婚,老大不小了仍孤身一人。
为了照顾他,农场的领导安排他的工作就是负责看管河东这块面积不大的瓜地。这是一位守土有责的老人。有一天,他无意间发现靠近河边刚长出来的瓜纽少了,于是潜伏芦苇后面,当我们的小伙伴们再次匍匐进入他的领地时被逮个正着。我眼睁睁地看着三个小伙伴光着屁股跟在他的后边,被带进了瓜棚。该我出面了——这是小伙伴们长期玩耍形成的一种默契。
走过贾圩桥,沿河边向北不多步有一架“小艇”,艇板很长但并不宽,一受重力就上下弹跳,人在上面行走是需要配合的,艇板的起伏与脚步的起落必须合拍,稍有闪失,会被弹到河里去的,我硬着头皮终于过去了。
入夏以来三个小伙伴整天泡在河水里,身上晒得黑里透亮,看到他们一字型蹲在瓜棚里,接受老头的训斥,十分好笑。他们双手紧紧抱着膝盖,尽可能多地遮住羞处,其实这里是男人的世界,女人一般是不会到这儿来的。我知道他们装出可怜相,无外乎是想博得老头的同情罢了。我的到来让郑老头喜出望外,太阳快要落山了,再不让孩子回家,孩子的家长们会要责怪他的,关键还没有孩子们偷瓜的直接证据。龙尾河边一直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作“偷瓜不算贼,逮到一顿擂”。我替他们赔了不是,小伙伴们也各自做了检讨,这事就这么简单地了结了,老头十分大度地放他们走了。未走出瓜棚几步,老头又把我们叫住,我们刚刚放下的心又重新提了起来。回头看时,只见老头手里拿着一个很大的香瓜,一掰四瓣,嘴里不停地念叨,靠近河边的瓜还没有熟透,摘下来太可惜了。老头给的瓜确实很好吃,但与偷瓜吃相比却少了一份刺激,少了一份成就感,因为偷瓜的初衷不仅仅是为了解馋。
在孩子们的眼里,“偷瓜”不过是一场游戏而已,但“偷”字毕竟带有贬义,是一件不光彩、见不得人的事情。用不良手段占取他人的财物,受到罚戒,理所当然。
在回家的路上,我们建立攻守同盟,此事只限我们几人知道,不得外传,并发誓赌咒,绝对保密。可是第二天一早,有两个同学就被老师叫到了办公室,放学之前就偷瓜一事在全班同学面前作检查,中午到家就挨一顿痛打,这一连贯动作环环相扣,是谁告的密,我们心知肚明。
我们四个人是课外小组成员,所谓课外小组,就是同班同学彼此家居住较近,自愿组合报班主任老师备案的课外学习小组。它不仅是教室空间的外拓,也使得老师的权力延伸,任何人在课外稍有风吹草动,第二天老师便会一清二楚。在我们四人中,我胆子最小,又是“和事佬”,是值得他们几人信赖的人。按“排除法”是谁在使坏,我们都心里有数。可那小子还自作聪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从那以后我们做什么事都尽量避开他。
陇海铁路
十多年前,在《中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因为与连云港有关,所以至今还隐约记得一些章节的大意。文章的作者认为中国南北的划分以淮河秦岭为界,其界线很模糊,缺少准确性。在他看来,中国的南北方划分应以陇海铁路为限,清晰明了。甚至还有理据相佐证。南方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船,它只能行驶到连云港的临洪闸,再向北去就只能驾车了,这符合“南人善驶船,北人善驾车”的区域属性及地理特征。
任何一个新观点的提出争议便随之跟上,尤其是陇海铁路沿线的郑州、西安、兰州等省会城市,要将这些地方一劈两半,同一个城市,隔着陇海线,形成南北对峙局面,这给执政者们带来好多无法调和的麻烦。如北方是强制供暖区,而南方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个待遇。这种观点遭到口诛笔伐在所难免。
殊不知早在这位专家提出这一观点的几十年前,新浦地区行政区域就是以陇海铁路来划分南北的。铁路以北的社区叫“路北街”,铁路以南的社区叫“路南街”。专家的观点仅为一己之见,是否科学合理,似乎与我关系不大。但考虑情感因素,我多少能接受一点这位专家的建议。
“半岛”以北的陇海铁路与龙尾河一纵一横,形成交叉之势,铁路桥上每天有无数趟列车吐着浓浓的白烟呼啸而过,龙尾河水放大了它的轰鸣声,这于我而言其诱惑是巨大的。
有一天下午,我逃学了,这是我谋划已久后伺机实施的行动。我沿着龙尾河向北上了铁路桥,顺着陇海铁路一直向西,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铁路的路基很高,比下面的平房高出一大截,笔直的铁路将市区分成南北两块,形成两个不同功能区域。铁路以北是新浦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政府机关、工人电影院、露天球场、百货大楼、人民医院、汽车站及为数不多的楼房大都坐落于此。铁道以北居住的人群多以机关干部、商业服务人员、医生为主。经济上稍显富裕,工作上也较为体面,是靠拿工资吃饭的社会阶层。铁路以南多是平房,巷道多是土路,如遇连日阴雨居民们只得光脚走路。所住居民多用煤油灯照明,夜幕降临时漆黑一片,公共设施较为落后,生活条件较为艰苦,是苦力劳动者、小商贩和手工业者聚集地。位于解放路与通灌路交会点上的气象台,共四层,高高耸立,俯视整个城区,学校曾经组织学生来此参观过。登高四处望去,风景一览无余:东边是龙尾河,西边是华北河,南边是扁担河,北边后潮河,整个市区的核心区域被河水环绕;花果山、凤凰山、南大山、白虎山呈簸箕状拱着大海,藏风纳水,山似腾龙水若舞凤,此乃风水宝地也。
我的双脚有节奏地轮番敲击在不宽不窄的枕木上,两条铁轨向西无限延伸,交汇处便是又圆又大的太阳。乐而忘返,回到家中,已是掌灯时分。狼吐虎咽地吃完饭后,父亲从我的被窝里拿出了书包,刹那间,我魂飞了魄散了。接下来就是挨了一顿打,“乐极生悲”这个道理我懂,自己犯错误,受到应有的惩罚,理所当然。
这次逃学,我一个人,自由自在地行走在高高的铁路基上,饱览了整个城区,受点皮肉之苦,值了。
默 契
时下孩子挨打的事少有发生,而我小的时候挨打可是家常便饭对于我们这一辈人来说,每次挨打的背后都是一段难忘的经历,所以没有挨过打的男孩,他的童年生活一定是单薄且不丰满的。就家长而言,“棒头出孝子”的古训为家长打孩子提供了理论支撑。不过家长打孩子恪守一条铁律,就是“打屁股不打头”,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是有科学道理的——让你长记性,且不至于伤筋动骨。而就孩子而言,每次挨打后,都会有经验总结和教训吸取,从而减少挨打的机会。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失败,使我们聪明起来了。”我很讨厌有的小伙伴见要挨打拔腿就跑,大人拿根棍子骂骂咧咧地紧追不舍,如此这般,有失斯文。
父亲毕竟是读过私塾又喝过洋墨水,在同辈中算得上是个文化人。文化人自有文化人的行为方式:一打二嚇(海州方言,意同吓),是父亲打孩子的过程中行之有效的方法。他打孩子时不是让你饱受皮肉之苦,而是要达到惩前毖后的效果。他喜欢把打孩子的行为,从理论上拔得很高,而在实施方面拿捏得准确到位,使打与被打之间情投意合。
我注意到父亲在打我的时候,往往是拳头举得很高而落下来的力度却很轻。若是在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袄,面对挥舞的拳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点很是关键,就是打与被打之间要形成互动,要随着父亲拳头的落点和节奏做出相应的哭喊和求饶,不过这种哭喊求饶掌握分寸,如果你要像驴一样地嗷嗷叫,他会知道你在戏弄他,其结果会适得其反。总而言之,就是要给足父亲居高临下的成就感,还要让他感觉到你认错的诚恳。这时如果有人出面稍作劝解,我象征性地做出自我反省,表示下不为例,这场游戏般的惩戒也就草草收场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权当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