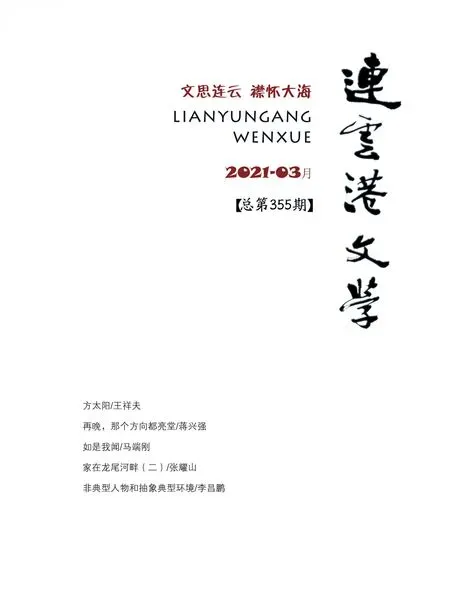再晚,那个方向都亮堂
蒋兴强
空灵的月夜,蛙声如歌,我正贪婪地深吸着那久违的草香和淡淡的苦味,大舅家的少爷来电话,说他们还有几分钟也拢了——来看望我八十七岁的父亲。我责备几个小”行头“(巴蜀玩笑话),都月上三竿了,还跑到弯弯拐拐的乡下来。幺表弟却说,再晚,二姑这个方向都亮堂;二表弟也在旁边吼,再远,都觉得二姑家很近。
是啊,百年沧桑,地覆天翻。从爷爷那代算起,到我们的儿孙,蒋家、糜家你来我往,就像一缸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在这条山路上,已留下五代人的足迹了。
一
据老人们讲,爷爷刚十岁,太爷爷就去世。但爷爷在三个弟弟面前是长哥——长哥如父!
爷爷才十二三岁就帮人跑船,上三汇、达县,下重庆、武汉,本来他可凭手头的积蓄,在十五六岁,娶回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可爷爷却把推船拉纤存的血汗钱,拿出来给二爷爷修房子。待二爷爷把媳妇一娶,又把个头小做事心细的三爷爷,送到中滩桥学裁缝,在场口路边安家。不到三年,又帮幺爷爷成亲……
几个弟弟有了家室,爷爷却过了定亲的年华。幸好,爷爷做事能干,高大帅气。很快街上一李姓姑娘,喜欢上了爷爷。哪知结婚不几年,这位奶奶没留下半个嗣后,竟撒手西去。
爷爷忘不下奶奶,媒人介绍别的姑娘,他总是不屑一顾。直到十年后,爷爷快到四十,才有了和他般配的女子。
这女子姓糜,一手好绣,还读《春明外史》《金陵春梦》,前夫是军官,不知是前夫战死,还是妻妾争宠斗狠,有了退意,每次爷爷下重庆,船一靠岸两人就要见面。渐渐地,才知道那女子是渠县老乡,离爷爷住的观音溪十七里,娘家在吴家场观音寨下的来家院子。说是有次,女子托爷爷从重庆给她娘家捎了几锭银子和些细软,时逢码头以说媒为生的老妇听到风声。爷爷刚回到船上,老妇便带来一个女子,说只要爷爷以那些托带之物交换,女子便可嫁给爷爷。
沿途水路,土匪出没,随便找个被盗遇抢的借口,就可让女“老乡”无话可说。可是,爷爷拒绝了媒婆的好心,谁知,却在过险滩时发生意外,木船撞上暗礁,爷爷被冲了五六里,连衣服裤子都冲没,而那装在木箱里的银子、细软,却被爷爷完好无损地连箱抱在怀里。
从这以后,女子有啥需捎给娘家的,或娘家有土特产要带到重庆去的,爷爷便成了她的免费“快递”。再后来,那女子就果断嫁给爷爷,成了我的奶奶。
那时,蒋家是三间土墙茅草房,糜家是六间大瓦房,从观音溪码头到奶奶娘家,弯道多坡路陡,还多是土路,只有从甯家碾子到吴家场的十里,才是石子、泥巴混合铺出的土公路。
可想而知,在这条路上,当年爷爷走得多用心多神圣。
这条路成就了爷爷的爱情,也是爷爷最温馨的路。
二
遗憾的是,奶奶嫁给爷爷后,一直没有孩子,不得不抱了爷爷二姐的小儿做了养子——他就是我父亲。
爷爷能干,奶奶内秀,在他们的耳濡目染下,少了血缘温度的父亲,就比常人要多几分自尊,有些孤傲。于这样的男儿,能入眼入心的姑娘,必然是花中之花。为了延续烟火,父亲才十一二岁,爷爷、奶奶就张罗寻亲,不是不满意对方父母有些拖沓窝囊,便是看不上人家姑娘略显平常。直到父亲十八岁那年,奶奶见娘家有个生得水灵、绣活农活百里挑一的远房侄女,便赶紧托媒婆去探口风。对方父母一想,小伙灵性能干,两家虽隔了四五房,却比很多亲姊妹都好,便同意了这门“表亲”。
小伙定了亲,常常借农忙去帮女方栽秧挞谷,姑娘也偶尔过来帮“姑家”收割做饭。一天,姑娘来帮男方家挖干田,早上过一座名叫矮子桥的石桥都好好的,傍晚却被洪水淹了一米多深。小伙想借势留下姑娘,女子却说,哪有女娃儿没出嫁就在男方歇的?扭头就绕道向下游两公里远的杨家桥走去。谁知,到了那里,河水涨速太快,两百多米宽的河面,洪水已没过墩子一尺多,下面五六十米,又是滩崖。
别说女子,即便是男人,面对那振聋发聩、一泻千里的洪水两腿都会哆嗦。小伙亲生父母就住在河对面,从小他常常从这过河。而平时手都不让他牵的姑娘,面对身强力壮的小伙,两眼一闭——背我!
姑娘趴在小伙背上,双手紧紧搂着小伙脖子。小伙反手把姑娘一掂,就背着她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蹚水而过。哪知,这一幕被一老和尚看见,竟写下一首《龙头凤头》:
豆蔻佳人阻激流,
儿男权作渡人舟。
偶将糙手挽纤手,
恰似龙头对凤头。
一对红莲浮水面,
十分春色惹人愁。
轻轻放在沿江岸,
两耳不言各自羞。
就这样,第三年,他们生下我——这就是父亲、母亲当年的恋爱、婚姻,这条路也是父亲、母亲名副其实的罗曼路。
到20 世纪50 年代末,这条路才渐渐出现了变化。中间的石板路,也多了一两公里;公路上,偶尔有了一两个道班工人的身影;同时公社还要给生产队划一段需养护的公路,每到十冬腊月,两边就会出现热火朝天的场面:男人满山遍野捡运乱石,女人坐在路边用小铁锤碎石,“叮叮当当”的碎石声、嘻嘻哈哈的说笑声,此起彼伏。不久,乡与乡之间,修了公路,一条条岔路通向村里,或直达一个个晒场,晒场旁边都有一排屯粮的保管室。
三
遗憾的是外爷、外婆,一个刚过四十、一个五十多就去世了。60 年代末,漂亮的小姨才十七岁也因疾而终。外爷一家,就剩下大舅、二舅、我母亲。
俗话说,娘亲有舅,与两个舅家,我们走动得就多些,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也最深。
大舅农民,没文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针匠;二舅,聪明,当过兵,国家邮政基层负责人;我母亲,灵性勤奋、百里挑一的能干。
许是手工针逐渐被机制针替代、加上子女太多之故,大舅家当时的经济条件略差;只有按月发工资的二舅家,日子相对好过一点;我们家地处土瘦地薄的石头岩边,因了满山的青石,又挨渠江,父亲才可凭手艺挣几个零钱,填补家里称盐打油,但比二舅家差得远,比纯粹的农民家庭又好点。
多半因父母不通晓世故,到十五六岁,我对人际仍是一窍不通。只知道每次大舅二舅家来人,母亲会提着一把菜刀从装粮食的木仓里切出半截油亮亮的腊肉,合点干咸菜炒上一大碗招待他们;年年过了中秋节甚至进入十月,全村没有腊肉,我们家常常还悄悄留着一块或半截最肥的腊肉。母亲说,好东西是留到客人来吃的。这个月份,大舅、二舅家来人,母亲必定会煮上半截,不炒不蒸,将煮熟的腊肉切得又厚又大,然后夹一摞又肥又大的,放在他们的干饭下面。爸爸是家里的顶梁,碗底有三小块;我们正长身体、爷爷“机器老了”要油水,碗底一般是两块;母亲却是添了几匹菜的米汤稀饭,腊肉一片都没有。
久了才发现,母亲招待大舅、二舅是有区别的。大舅一家在腊肉快结束的月份来,哪怕只剩下半截,母亲也会毫不犹豫地拿出来,招待他们;但若是二舅家里的人在这时来,母亲会把最后一点腊肉留着,立马搲上半碗粮食,从外向屋里撒,一群鸡“咯咯咯”涌进屋,门一关,逮一只大公鸡或不生蛋的母鸡,给杀了招待他们。渐渐地才明白,母亲把最后一块腊肉煮给大舅家里的人吃,是考虑大舅家经济困难,肚子里的油水少;二舅家里的人来给杀鸡,是因为鸡肉贵,连汤都很香很香。
当然,大舅、二舅两家待我们,也非常热情。每次一听说,要到舅家,我们几姊妹都要争着去。父亲、母亲一旦说这次只能谁谁去,没被同意的,脸一下就掉下来,“嘴嘟起能挂几把夜壶”。
到了去那一天,不需人喊,早早起来换上新衣。一路上,满脑子里都是舅妈从灶房端出好菜好饭的身影。
两个舅家待我们都好,但炒的菜做的饭却不一样。
去大舅家,如果是端午以后,大多没腊肉了,不管多烈的太阳,大舅会马上从坡上回来,锄头一放就上街去。一会巷道里必定传来两声轻咳(痨伤病),只见大舅手上提着一块四指宽、尺余长膘肥油水多的宝肋(前夹)肉,一进屋就对耳背的舅妈大声说,赶紧烧了,炒起给外侄老爷下饭!
不一会,一大碗回锅肉就上桌,合菜很少。大舅喊拈肉,我们很斯文地拈一块,那肉又大又厚又肥,解馋!大舅妈见我们客气,就重叠着往我们碗里夹一箸,自己则象征性地拈点,像提醒几个老表要谦让讲分寸似的,指指桌子中间,“树民、糜龙、糜军,吃,吃”。小老表建国,在几弟兄中,个儿小,最文静,常常是一对小眼睛先察言观色,再相机行事。让人心生柔软,不得不在生活、学习特别是在写作上,对他有意给些提醒。
去二舅家,我们都爱先到二舅的单位去,那里有我们梦寐以求的工作,也有我们仰望的亲人,于母亲亦是她的荣耀。每次我们去二舅那里,二舅都会微微一笑,你先去家里吧,一会我就回来。
后来才明白,那笑和让我“先回去”,颇有深意。
那笑,一是二舅知道我们是为打牙祭去的,二是我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从我身上似乎看到了他妹妹的影子;让我“先回去”,是他得上街去割肉,还有割上肉回家煮,不仅可以省点钱,还体体面面招待了客人,表弟表妹们也能沾点油水。
我们刚一到,二舅就会背着个绿色的邮政包或一个细篾密背篼回来,悄悄走进灶屋,给舅母几句一交代,才出来问我学习怎样、妈妈怎么没来、爸爸在干啥。一阵聊天后,舅母的饭菜也上桌了。舅母切的肉片薄,不大不小,分量却不少,调料香,炒出来的颜色黄。两个表弟、四个妹妹,也礼貌斯文。饭一吃,二舅进灶屋去舀点清水把口一漱,就上班去了。如果我们要在那里歇,晚上舅舅得回来吃夜饭;如果我们要回家,舅舅会礼节性地叫我们在那里耍,我们执意要走,他会提醒我们一路上车子来了要靠边,莫在河边洗澡,别和人“角野”(闹事),聪明些,让人不是“莽子”(笨蛋)。
我们家与两个舅舅家,几乎形成一种默契。两个舅舅、舅母的生日,即使对其他亲戚都说“那天莫来”,也不得对我们说;我们父母生日,哪怕是暴风骤雨、农活忙翻天,舅舅两家也会来人。因为都知道,他们再没更亲的人了,只有借这个时间,姊妹间走走。两个舅舅来,有时是两人一路来,大舅背个卖针的灰布包,遇上有人需要,顺便卖点;二舅挎着邮政局的投递包,里面有几张报纸,有时会找人开后门,给称两斤盐或买两条肥皂来,每次我们一看到二舅那个包,都羡慕不已,会暗暗想,将来要是像二舅这样有份工作多好啊!
然而最开心,还是每年的正月初二到初四这几天。按巴蜀风俗,除正月初一这天得给祖先上坟外,初二一吃早饭,父亲、母亲都要带上孩子,提上弯弯腊肉去给健在的外爷、外婆和舅舅、舅母拜年,等一家一顿两顿地吃遍,舅舅、舅母才会带上孩子,反过来给姑父、姑妈回拜还礼。这几天,都是和最亲的几家人在一起,大人喝烈酒抽叶子烟,笑声四起,小孩蹦蹦跳跳,亲密无间。在舅家,多半是在竹林里捉迷藏,到观音寨看水库,去有庆街上看耍狮子。一次,和大我几岁的远房小舅玩,大舅听说我被欺负了,狠狠一顿开骂,人家是客到嘛,你是个啥子狗屁舅舅?而舅舅家里的人到我们家,大多是正月初三初四了,他们都爱去看河,那水宽宽坦坦、清清澈澈,一眼望去浩浩荡荡,逶迤悠然。
玩着玩着,我们会跑到刚砍过的甘蔗地里,从一堆一堆的蔗叶里寻找半截甘蔗和扔下的嫩甘蔗,你一截我一截地解渴,有时还会上山掏鸟蛋,下沟捉螃蟹,然后,几把干柴,一根火柴,烤得喷喷香,你一只鸟蛋,我一只蟹腿,吃得津津有味。
不知不觉成人了,表兄表妹们间,还是大带小,弟称哥。是合作伙伴,亦是竞争对手;是同行,又能形成合流;遇有商机,总能默契发力。现在,大舅、二舅、我母亲,早已去世,大表哥,已六十多岁,年龄最小的表弟也过不惑;资产几百万的比比皆是,上亿的也不是传说。宝马、奔驰几乎家家有,只有我在文化单位,有些清贫,但儿子优秀。想回老家,乡村路修到了地坝头,犹进天然氧吧;度假耍周末,朝去晚归,堪比邻游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