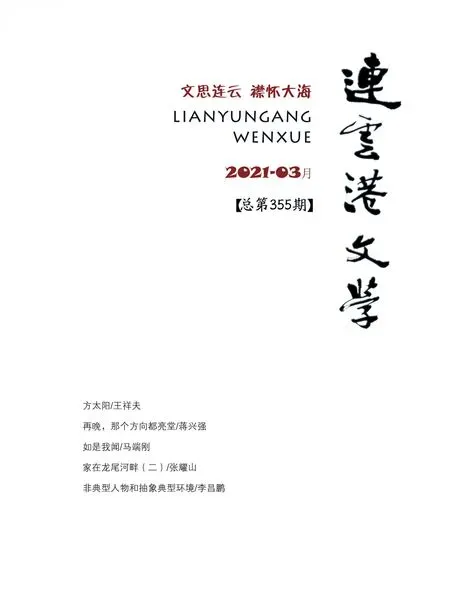席草
冯学青
席草,我童年记忆里一种温情的草,柔软、秀芹而有韧性。
席草的外表光滑、青绿而笔直,有点像大葱的形状,直径如筷子那般大,最高可长到两米多。小时候,我们总喜欢在新割回来的草堆里玩耍。青翠、笔直带着泥土和青草气味的席草堆在一起,就是我们小孩子的欢乐天堂,我们在上面或坐或躺或翻几个跟斗,冰丝丝、滑溜溜的舒服极了,我们还偷偷抽一把拿到别处扭成绳子来跳,或用绳子打个结吊着树杈当秋千荡。这种不起眼的草,带给我童年时光的快乐是那么纯粹和质朴。
我娘家地处雷州半岛西部,气候温和,20世纪70 年代,我们村人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席草和编织草席。乡亲们编织草席卖的钱,买日常用品和支付孩子的读书费用自不在话下,人手多的积蓄一两年就能够盖上新房。在当时的农村,这样的日子过得算是红火。听老一辈说编织草席是我们村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传统手工技艺,在附近称得上是著名的“草席村”。
手工编织的草席柔软轻便,易洗易干,凉爽耐用。新织好时带有灯芯草淡淡的青草味,很是好闻。那时农村每家的孩子都有三五个,大人也没有那么讲究,小孩夜里尿尿,直接透过草席漏到地上,湿了的那块照睡,没有空去经常洗席子,任由席子被尿浸泡又自然干,往往一张席子其他地方都好好的,就孩子睡的地方烂了,我记得我家里就最多这样的烂席子,烂了的席子不舍得丢,供我们小孩子晚上铺在家门口乘凉。
在我读小学阶段,我家每年会织出大大小小100 多张席子,每张大席子最多可以卖到8 块钱,小的卖4、5 块钱,如此算来,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父亲说我家的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是靠卖草席买的,接着有了凤凰牌车,再后来,把房子粉刷一新,购进两个大衣柜和一套木沙发,还给教书的姐姐买了手表,这样的装备进了山区的农村家庭,很是值得炫耀。1980 年,被人从广西介绍过来只有19 岁的美丽姑娘,一进我家就同意嫁给我同年龄的哥哥,哥哥现在还说主要得益于席草赚点钱成就一段美好的姻缘。
我家的席草地在小溪边,父母去席草地劳作时间总要等生产队收工后的傍晚。我常常跟着父母去,我会帮拔杂草,会帮父母把割好的席草整理顺直,但我往往只做一会就受不住同伴的诱惑,到小溪边玩水、抓蚱蜢,抓到蚱蜢,用一根派不上用场的席草剥成细丝系住蚱蜢的腰身,放到溪水里游泳,间或到田垄边摘地稔还有叫不出名字的野果吃,往往玩兴未尽,父母就叫收工了,才懒洋洋帮扛一小撮席草踏着暮色回家。
每个夏夜,晚饭一过,父亲就拉亮门口的一盏15 瓦的路灯,拿出他自制的尺子来度量席草。席草按长度分三种,一种是一米五的,适用于大床,一种是一米二的,用于中床,还有一种长不大的最短最细小的草,那种只有做成90 公分的小席子。度完分好类后就开始破草,粗壮而且够长度的上等草占的分量是大多数,那种草一般父母不给我和弟弟破,怕我们破不好,影响织成席子的美观,卖不到好价钱,一般都是分给哥姐破,我和弟弟只准破次等草。破草也要讲究技术,用刀子从中间破开,但是要求分开两半是均匀的。在昏暗的路灯下,我们一家就为新割回的席草忙碌。我和弟弟往往工作不到一小时,就相继在地上的烂草席上睡着了。有一次,我嫌小弟弟尿湿草席,选择在长条木凳上睡,哪知道一个翻身掉到地上,说也奇怪,母亲说我摔到地上也不醒继续睡,母亲怕我摔伤,从此不让我再睡木凳,说睡地上的草席凉爽又不怕摔。
编织一张草席要经过摘草、晒草、纺线、穿线、织席、晒席等10 多道烦琐而细腻的工序。其中,最主要的一道工序是织席。编织时,需要两人配合,一人在旁边往席架中插入席草,一人坐在席架旁用力上下压打席草。送草、打压、锁边……“唰”的一声,一根细长的席草紧紧地栓进了席面,一根连着一根,每一根都凝聚着一家人辛劳的汗水,才织成一张草席。我家数父亲和母亲最会编织,其次是大姐和二哥。父母工作多,大多时候是大姐和二哥一起编织。大姐掌压锤,二哥穿草,每一根草穿过,姐姐使劲压一锤,再把一边的草尾卷成结,再向相反方向拉起锤子,第二根草穿入,周而复始的循环,一张席子的编织最快也要一天才完成。每次听着打压席草的嗒嗒声,二哥穿草的唰唰声,看着二哥和大姐飞快运作的手,感觉这是无比生动美妙的情景。我最最高兴的是席子织好了,父亲就会骑上自行车驮着草席到附近的小圩供销社去卖,然后买一斤半斤的肉回来给我们几兄妹解馋。不用顾虑席子卖不出去,那时有供销社专门收购,席子按等级卖钱。所以,我最盼望的就是有席子织好,盼着父亲卖完席子回来的身影。有时父亲高兴又有空,就会带上我和弟弟去卖席子,父亲卖完席子,揣着钱一脸幸福地带我们在街上转悠,再买几毛钱的零食给我们吃。那种生活虽然不很富裕,但踏实而满足。
80 年代末,由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掀起去珠三角打工的热潮,庄稼人再也不满足于那一亩三分地,我们村里的年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很多田地荒芜,只有少数家庭仅种几分水稻够自家食用。有种蔬果的农户,也是选择能够机械化耕作的土地。加上种植席草和编织草席工作繁杂,相对收入低,加上受到机械化的冲击,手工编织草席在市场上渐渐失去优势,慢慢地,种植和编织草席被遗弃,想必不久后,这种手工编织席草的工艺会失传了。
如今,我的家乡再也寻不到席草的踪迹,各种各样的竹席、藤席、冰丝席充盈着市场。席草,这种伴我快乐成长,带给农民富足生活平常的草,就这样淡出了农民的视线,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留给我悠悠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