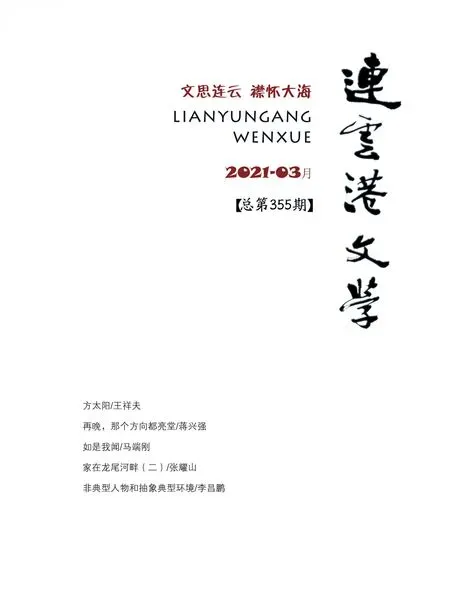荒凉等待
董赴
那份荒凉依然留驻在我心里。
很多年了,即使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匆忙谋生中,习惯了太多的平庸、隐忍、麻木和忘却,我依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汗湿了的后背,咸渍着的眼睛,少有衣带当风的快意,多的是陷没车轮的沙土和艰难的跋涉。置身于其中,才能感受到那种似乎简单至极的宁静与博大。
无边的苍茫和寂寥,深蓝色天穹下,泛白的天际丛林如黛,喧嚣隐隐;或绿或黄扬着穗的芦苇、艳艳的红柳,沿掺杂着草茎碎屑和石子的沙土路两边四处蓬勃;土堆上的孔洞和鸟兽的脚印比比皆是;偶尔扬起的一线蛛丝在空中泛亮;高起、坍塌的河岸宛如大地的伤口,逶迤绵延。
而至今让我讶异的是,何以十七八岁的年龄,就有了不止一次去寻找那种繁芜锥心的拷问的执着。是因为荒原的苍茫与寥廓,让人从心底领略一种渺小一种壮阔?还是瘦弱身躯里潜涌的激情、不屈和迷茫找不到一丝突破口?
也是在很多年以后才真正领悟到,那个在辙痕深陷的沙土路上踽踽独行的我,所以要远离身后的城市和人群;或许源于一种天性里的荒凉,等待一种灵性的交合,一种无言的容纳,一种理性的沉淀,一种跨越时间、空间的象形与点化。
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周日下午是在那儿度过的了。书包里是累累的课业,我却无心去品读哪怕一页。酷暑还没有到来,午后的阳光没遮拦地投射下来。我坐在泥块堆垒的河岸上。风在耳际带着哨音,缕缕云气在天顶散化。近处开着黄花的原野上,野兔闪电般掠过,灰色的蜥蜴四处奔窜。河滩里一脉浊红的水流潺缓,岸涂抹着阴影,时不时能听到土块坠落的微响。
那一边满是球状的耐旱植物,蔓延在灰色的沙脊上。不远处,倾斜低平的坡脚,胶皮轮的辙痕穿过淤泥的河滩。偶尔有头戴白帽的维族长者扬鞭吆喝而来,让人揣想那哺育着的深处的风景,是挺倔的白杨、胡杨,掀起尘土的羊群,干打垒的泥墙院落和葡萄藤架下的荫凉?还是不分四季的漫漫黄沙,和焦渴中依然固守着的劳作、安分与从容?
长久地坐着,荒丘灌丛略带干涩的气息,把宁静揉进心底。我听任枯苇在脚下碎裂,甩下鞋子仰卧或是赤脚走上泥岸、沙丘,直到西天红霞散漫。此刻,自然对我,不再是一种对应,而是交融。漫溢的寂静,生命的律动,风的喁喁细语,连同投石般地飞鸟,都摒弃了语言这一外在形式。而以形象的真实,沉默的真实,亘古流传生生不已。
曾经不止一次地揣想古人彼时的模样,没有高大建筑物的视觉遮拦,没有五色五音的无孔不入的诱惑。广阔的田地延展,河川的滔滔,山峦的植被丰沛。恪守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夜晚的群星闪耀,蚊虫低吟,一灯如豆或是凝望一轮圆月。天地的广大明了,朴素无言才孕育了言简意赅的《易经》和老子的五千言,才有了野马尘埃的慨叹,有了翼若垂天之云的瑰丽与壮观。而这之后的纷争,无止境的利欲追求,蒙蔽了我们的心智,弱化了我们的勇力,也改变了我们生存的态度和赖以生活的自然。
沧海桑田,当面对荒凉时,不变的永恒、善变的瞬间足以让你感受到人的渺小和对天地的敬畏。千百年来它繁衍了众多生命,领略了风霜雪雨的冷酷。它平静地任风刮过,鸟掠过,平静地忍受干渴,平静地接受每一滴雨水。
而人世间总是免不了太多的平淡、执着、苦熬、利欲,反反复复的肯定与否定,自我的累加,信仰的破灭,看习惯了的不平,几经悲喜的无奈。类同蚁虫的忙碌,生命历程的开演,小单位里的纷争,个人喜好的划定,物质享乐的丰裕贫乏;大至历史长河裹挟的衰落与新生、盲从与谎言,民族性的挑战与应变,无一不顺应着消歇与寂灭,无一不预示着潮涨潮落,无一不昭示着古人早已了悟的——“易,不易,变易”。
而人为什么要活着?而活着的意义在我又是怎样的含义?我总是想给自己一个可以信服的解答。而最终在无数次的试炼与蜕皮中,挣扎出更多“已经存在,就可以选择”的明了时,那份荒凉其实已深入骨髓了。
午后的阳光穿透云层,金黄的草色,蓝天下晶莹闪烁的积雪,让人憧憬希望。
仅仅驻留在岸边,是看不到风景的。越过沙脊,在初雪消融的原野上艰难地行进,疲惫不堪时;仿佛天尽头现出隐隐的树丛。愈走愈近,原以为冷寂的沙枣树丛竟然包裹着热闹的所在,野兔掠过满地枯叶的田埂,一人多高的凉棚背依着刺棵扎就的篱笆。再往下齐整的林带里土路贯穿了田地和人家。牛在吃草哞叫,几个快乐的孩子在嬉笑打闹。远,到底有多远呢?荒凉背后其实充满了生命,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
心的风景瞬间湿润,一颗心其实很阔大,一个人其实很阔大。
犹记得那个手执杏花、指尖冻得通红的女孩,满眼含笑地等待着我的路过,只为了那无言的一刻,能坐上车座把脸贴覆我的后背。谁能料到此后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痴心的等待、不灭地执着,乃至聚聚散散;分离又试图聚合的努力终因交错而无法弥补。有缘无分,过于机巧的界定,其实是无法让两个相似灵魂彻底解脱的。少年时父母眼中笑谈的早恋,因为岁月的绵长感动了不止一代人。但身处其中的人是否就一定是人们眼中爱的终极呢?
人其实是需要补充的。你无法框定自己的生活,就像你不知终点和流向一样。岁月流逝,现实中温情地一抱,常常足以抵消诸多浪漫的续集。不妨让一份美丽沉淀心底。不妨让大雨中同执一把伞的不会重复的相依,成为两个人可以生死相守的意境。
人生苦短。一只小虫子的生命和一个人的一生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只是思考生命的本分——接受。人何尝不是如此?源于痛苦的蜕变,或走入成熟的麻木,也只是个体形形色色的表象。终极的一刻,其实有多少悔意袭来,多少憾事无奈。诚如苦禅的“悲欣交集”,既有了悟的明澈,又满含生命的交错。
而苦难和艰辛,只是心里的受与施。接受现实而不是浮夸地毁灭自己。不期望能改变什么,除了自己。
一切都是短暂的。红尘一看客,天地一浊人。我之浊,源于包容丰富。我之看,缘于爱缘于悲悯缘于交错。
大雨不期而至。天边雷声隆隆,交错的闪电勾勒出雨云的轮廓。而后雨点砸落,溅起尘烟。在簌簌的芦苇草丛里,狂舞的枝叶应合着风声、雨声,涤荡了夏日的喧嚣与溽热,而荒原里的生命蛰伏在地穴中。我的荒原在这样的磅礴浇漓下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虫的覆灭还是叶的新生?
十七八岁的年龄就这么一次次固执地去守望、去等待,而全然不顾身后喧嚣的市声。在后来写出了《没有年轮的季节》之后,逐渐坚硬的基石,挣脱痛苦的孕育;我知道不再是一种逃避,而是物我交融后的心灵涅槃。
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他们没有出众的容貌,超人的才华,甚至多得是无法改观的执拗与盲目,普通与平淡。但时日渐久的相濡以沫的生命磨合与血缘牵系、亲情打磨,无言的扶持,耐心的承受,温暖的点化,常有的争执,妯娌婆媳必有的磕碰,柴米油盐的概莫免俗,为人父母的心性成长,家庭意见的雪上加霜,亲戚才可能的揭短,婚姻破裂的断层附带,唯恐提前的对生命完结的恐惧,一切的一切让我留存了许多平实、温暖、琐碎、伤痕、牵挂的记忆。
常常想,柔滑的肌肤在指尖下流淌出动人的音符,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欣羡的了?常常想,没有这世故人情衍生的诸多和维系,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生命的契合不只是精神的盛宴,更应该是忘我的演出,血脉的奔涌,人事的汇集,天地的华章、苦难的点缀和烦恼的麇集。
很庆幸,还能有那样的才情,还能有那样的冲动,还能有勇气和平静去迎接每一个生命的黎明和这之后的可能到来的终点。
在一个还算温暖的家庭里,去写作智慧与汗水结晶的能感动他人的文字,在我已是知足。
人生无常,生命脆弱。但找到自身意义的人应该是幸福的。就像多年前在深夜里汲取着思想的养分,让那些透明的未来、古今纵情演绎一样。
我等待着,等待着荒凉的淹没;等待着这之下,生命的蓬勃和多样的匆忙。
遥远的回响
夯土的高台上似乎仍奏响一缕梵音,慈悲的禅语蜿蜒抚触苏巴什一脉浊红的渠水和两山间干涸曲折的堤岸。舒爽与安然的六月,褐色山体链接的阳光中,豁开的浑黄册页,倾泻着辽远蜃影的锋芒。
依山势由南而北的砌筑里,棱角和光影勾画着克斯勒塔格寺残存的形体。两千年前汉唐时期倦红的暮色里,悠远的钟磬,芸芸的颂念和香火,曾经照亮过这个荒僻角落的关口,穿越丝绸秘道的商贾旅人喝着苦咸的茶水,望着高处戍卒泛亮的甲胄,在烁烁篝火的涂绘里裹着怎样的憧憬和寒意睡去。
克斯勒塔塔格寺,位于柯坪县苏巴什河龙口,和隔岸的乔格塔依戍堡,是汉唐时期,龟兹到疏勒联结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四城的枢纽和汉唐佛教文化在西域传播的羽翼之一。
从柯坪盆地往北,穿越卡拉塔克山,渡托什干河,过乌什,经别迭里关隘,便可进入唐“安西四镇”之“碎叶”及中亚草原,亦即丝路新北道。向西,进苏巴什峽口,便可进入荒旱群山中被称作“柯坪—布鲁特古道”或称“柯坪—阿合奇古道”。这条古道,沿喀什噶尔河往东可直达姑墨和龟兹。往西则经疏勒溯源到葱岭至西亚波斯等。
虔诚的佛教僧侣借由这条古道,前往南亚印度学习佛教,或传播来自中国中原与西域的文明。张骞,汉代西域首任都护郑吉、鸠摩罗什、唐玄奘、班超和高仙芝西征中亚都曾经过这里,以边塞诗著名的岑参也随都护府军队途经阿恰勒平原并写下不朽的篇章。
少有人知道,在这片沙漠荒原占据74.2%的苦寒之地,仍然留存着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后1000 年之间中原移植来的“华夏文明”,西边传来的古代波斯文明和当地发展起来的“塞克”文明。
佛教自公元前二世纪传入龟兹,兴盛于汉唐和魏晋。当时,佛教寺院广布西域。龟兹石窟壁画和古代文献以及考古成果,印证了汉唐时期南疆大部地区包括焉耆、库车、阿克苏等地生活的人群,大都是操雅利安语或称龟兹语的印欧白种人或东伊朗语的白种塞人以及羌人和汉人。
南北朝至唐,柯坪盆地佛教兴盛,修建了以克斯勒塔格佛寺和九拱门大佛寺为代表一批小乘佛教伽蓝。坐落于苏巴什河龙口南北两岸的克斯勒塔格山峽谷口山坡地带的克斯勒塔格佛寺,屡遭宋代初年及之后的历次宗教战争、边疆烽火,导致佛寺历经毁建。1974 年修建水泥厂时,直接的取土方式使山坡下的建筑荡然无存。
佛寺通体由阶梯相连,自上而下高度达30 多米,恢宏庄严。遗址山坡中部残存一处5—7 级人工台阶,有一间长、宽、高均5 米的残墙和宽约1.2 米,长5 米的甬道,甬道两侧墙体中下部有残存壁画,现已被淤土覆盖。甬道地面铺有厚约1 厘米的石膏层,上面堆积有厚约20—50 厘米厚的黄土层。甬道上部向北联结以高大的殿宇,殿宇长约15米,南北宽约9 米,残高约7 米,地面也铺有厚约1 厘米的石膏层。殿宇其上为山门、正殿和残塔身等建筑,均系黄土土坯建筑。地面堆积土厚约20—40 厘米。决绝的风骨,成就了丝绸之路上巍然屹立的地标,历史上中原与西域血脉相继的传唱。
龙口的东北岸半山残破的丘达依塔格戍堡遗址,主体建筑群呈南北向品字状分布,均用土坯砌筑。东部山梁上沿山边缘有一残长约45 米的土坯墙,北端与残高8 米的观望楼墙基相连,南部也有残墙房址。建筑主要集中在山峦南部,主戍堡平面呈方形,长约7.4 米,宽4 米,残高6 至8 米,沿山梁山体多处修筑土坯墙,形成屏障。戍堡扼守“柯坪—布鲁特”古道,地势险要,雄踞山口,向西傲视克斯勒塔格大峽谷,向东俯瞰柯坪盆地。
而柯坪西北部克斯力河谷左侧的扇形台地,色日克托格拉克墓葬群——见证了西域历史中重要的篇章,也是先辈们最后的栖息地。
拾级而上,这座古老的寺址,每一步,都仿佛踩踏在厚重与空茫之上。历经剥蚀的建筑群落,红柳枝层叠和夯土砌筑堆垒的骨架,虬结的四壁,沉陷的地面;在荒旱的山脊上俯瞰田园,在旷野的风霜里咀嚼古今。
阳光热烈,鸟雀的飞掠和啁啾给寺院更加增添了一份静谧。汩汩渠水的两岸,柳叶低垂,周边的杏树籽实累累,空气里一股甜香。林荫路两边,凉棚、饭店,秋千比比皆是,洒了水的路透出尘土味的阴凉。
然而宁静祥和却始终离柯坪遥远。即使是近代,阿古柏的兵锋仍掳掠过风尘仆仆的羊群。五六万人口的小城,苦咸汁水的历史,汉唐以来的戍守与交流,用逾古的承载吸纳繁华与璀璨,衰落与新生。灵魂托寄,文脉折射,在久远撑持下淋漓抒写关于礼佛、虔心、坚守的拓印,在洪荒秘境里繁茂着一块块绿洲,禅意的归隐和萦绕的世俗在边地角力。
戍途的边卒,往来的商贾,封土的堆叠,湮没的希望,循环往复的朝代更迭,单调枯燥的心灵守望,甚至一成不变的景色,佛法的摆渡借着寺塔的浸润,让人心生皈依的栖伏和超越习俗的震撼。它穿越时空,是醍醐灌顶的醒觉与证悟,是乱世迷茫无助的豁然开朗,是心澄如水时的释然洒脱,是孤绝地域和普世价值岑寂与达观的滥觞。怅惘来去,与冲决的河道相比,生生不息的物种与群落反而充溢了浩荡景域的丰沛、自足、韧性与希望。
静守安然的克斯勒塔塔格寺已历经千年富庶繁华,消隐委顿;季节中浩渺而深邃的星空与荒旱苦寂的白昼轮回,驼铃远逝,似乎仍能聆听观照冥冥的佛法、族群的断裂与重塑。此时巍峨天山山脉的支脉阿尔塔格山的峻陡与大坝一起锁住一泓浅碧的库水,而不远处野榆、白杨、田地围绕着寒彻的渠流繁茂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