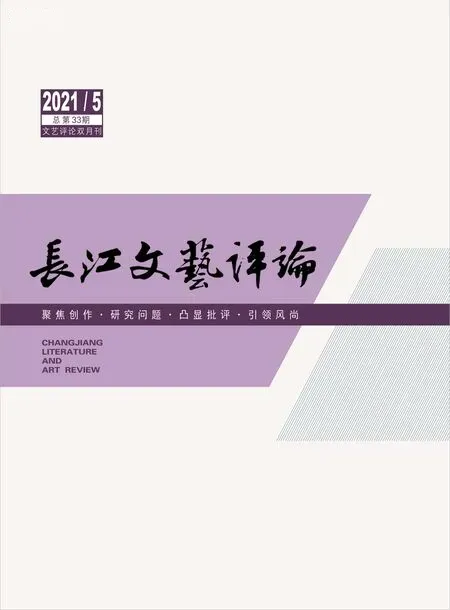深入乡村振兴现场“现实”书写如何可能
——评南翔《苦槠豆腐》
◆那 琳
自1981年9月在《福建文学》发表处女作《在一个小站》以来,南翔的文学创作之路于持续思考、不断积累和长期实践中缓缓铺开。作为当代文学版图中较为典型的学者型作家,南翔以历史的眼光,深入挖掘现实、聚焦社会热点,潜心创作,镂冰雕琼,作品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其短篇小说蕴含的反思历史、深掘人性、关注生态、洞察社会的主题是学者型作家南方立场、民间情怀、作家担当、人文关怀的集中显现。
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批评家在从事文学研究的同时提笔创作,但“学者批评家很难有效地克服他们作为学者批评家的身份所带来的生活经验与艺术感兴上的限制”,因此,像南翔一样长期坚持写作的学者型小说家并不多见,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兼具作家的生活积累和人文学者的艺术修养。南翔著有小说《南方的爱》《前尘:民国遗事》《女人的葵花》《绿皮车》《抄家》《回乡》等,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作家》等发表作品数百篇,曾获得上海文学奖、北京文学奖等文学奖项,连续两届提名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其短篇新作《苦槠豆腐》通过第三人称客观叙述,以临危受命的朱县长上任后,乡村特色产业的打造、推出及振兴构想的破灭为核心事件和叙事线索,秉持客观性的审美原则和现实的批判意识,用写实笔法和典型化路径,围绕核心人物朱县长,描绘乡村振兴事业在东坑乡的实质进展。切入时代肌理,究其宏图大志破灭的根源之所在。
由一处“景观”到一类现象
《苦槠豆腐》将视线集中在一个自给自足、小富即安,“既无动力,也无压力”的南方县城。小说的核心人物朱县长志在短期内推出媲美周围四县的特色产业,调研间隙,餐桌上儿时常见现已稀缺的苦槠豆腐一跃成为县长理想中名扬天下、带动该县经济发展的一大地方特色,与苦槠相关的产业成了他大力扶植的对象——“不干则已,一干就如哪吒踩上了风火轮,红红火火,飞快如风”,一切来得实在突然。“大姑娘坐轿子——头一回(脸上哭,心里笑)”,万事开头难,但县长对自己拿出令人认可的成绩,作出地域贡献胸有成竹,颇有自信。听到外出务工返乡后,现在村里做小本生意维持生计的村民对县长、乡长提出的苦槠产业甚是期待,朱县长更是喜形于色。
在县委、县政府班子扩大会议上,朱县长立下带领班子成员有所作为的宏图大志,举周围四县因各自推出的特色产业而得名的例子,发出“就为拿一个别称,我们县也应该奋发有为”的感叹。在县长、乡长、秘书一行前往调研的途中,肖助理阿谀奉承,从中取巧,称像朱县长一样轻车从简的人“多乎哉,不多也”。朱县长笑道“你当我是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鲁迅塑造的孔乙己是饱受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毒害,迂腐不堪、四体不勤,被社会遗忘,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所吞噬的悲惨形象。朱县长一番大干快上,最后以失败告终,降职调离后逐渐被乡人遗忘的命运,也让人不禁在朱县长与孔乙己之间产生无限联想。
一番调研后,朱县长当即动员各家各户“不留余地,不见死角,不容落单”,大力垦荒伐木种苦槠,可谓极端。面对部分代表的质疑,急于求成的朱县长断然否定、充耳不闻,整个东坑乡很快就如风卷残云一般被苦槠树大面积覆盖。秋收时节,屋前屋后栽种的苦槠树苗由于水土不服,养育不当而相继枯死。与此同时,线下宣传、线上推广、多方发力,却仍然难以扭转苦槠制成品供过于求的既成局面。随之而来的,还有村民接连不断的诉状,苦槠产业以失败告终,现实状况与朱县长的主观意愿背道而驰。
退休多年的经济学家对朱县长为何“求仁不得仁,天不从人愿”做出了解释。现实生活中“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正是由于不同的商品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效用,才会使得各种商品都有其产生并售卖的需要。因此,提高产品的多样性,可以让各种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还可以避免消费者都买某种产品或都不买某种产品的极端现象。企业和地方经济要根据不同的偏好进行差异化生产,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市场的平衡。而东坑乡大力发展苦槠产业的单一走向,恰恰违背了这一常识。况且苦槠是朱县长儿时品尝,现已从地方民众餐桌上淡出的舌尖记忆,普及尚有难度,何谈名扬天下?由此可见,朱县长振兴之梦的破碎绝非偶然,诚为必然。在新的乡村发展战略下,东坑乡呈现的“景观”并非特殊个案,而是一类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通过乡村振兴在东坑乡的实质进展,反观乡村振兴大潮下,许多地区因急于求成而缺乏对区域特征全面的分析和细致的考量,甚至违背生态、经济发展规律,凭领导干部的一己之见“大干快上”后落得事与愿违的苦果,值得无数以“朱县长”为代表的基层干部深入反思。乡村经济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对乡村经济科学定位的基础上,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充分汲取乡村发展的历史经验,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避免“大干快上”“一刀切”“一窝蜂”。无论是乡村振兴事业的整体规划还是具体生产模式的选择,都要充分认识到乡村现代化建设任重而道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
时代背景下流动的乡村意象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急剧加快,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其中部分定居城市繁衍后代,核心家庭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与此同时,部分底层民众面临回不去的乡土与难以立足的城市,身处双重困境,被逼仄到更为狭小的生存空间。城市化导致农村空心化,引发了农业劳动力缺乏、土地荒芜、留守儿童及空巢老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催生了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乡村传统的道德秩序和价值体系在汹涌而来的经济浪潮面前显得怯懦无助,传统乡村在新旧交替中无所适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如何在文化迷失中寻找符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已成为整个中国亟待解决的难题,也是文学需要在场记录和积极回应的“现实”。
“市场或消费拥有的意识形态试图将一切解释得理所当然的时候,文学的声音可能揭示出问题内部隐藏的复杂维面。”城乡发展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成为新世纪文学关注的热点。这一时期,周大新的《湖光山色》、贾平凹的《高兴》、李佩甫的《城的灯》、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格非的《春尽江南》、余华的《第七条》等,皆以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思考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广大农村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及城市扩张后,农民远离乡土,在城市打拼挣扎的艰难处境和立足城市后的迷惘与彷徨,深刻地表现了城镇化对以往城乡关系的巨大冲击,展现了社会变革浪潮中个人的痛苦挣扎和命运沉浮。
新时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呈现出更加丰富驳杂的图景。“以农为本、以土为生、以村而治、根植于土的乡土中国,转变为乡土变故土、告别过密化农业、乡村变故乡、城乡互动的城乡中国。”乡村与城市交织在一起,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触角已经伸向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文化的变迁让一部分人在现实中无处落脚,灵魂“流离失所”。文学随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由沉浸在乡土大地的田园牧歌式书写和执念于人民性的宏大叙事,转向对底层生存图鉴的描摹和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过程的艺术化呈现,内容丰富,新作迭出。但作家们面对这一现象时,似乎更偏向于做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们为衰落的文明唱挽歌,为扶贫攻坚的光辉形象唱赞歌,而对在一种文明兴起的同时潜在的社会问题避而不谈。文学长期沉浸在一个平静、安逸的“温柔乡”,难免会与时代现实产生隔阂。如何在小说中展现新的乡村样貌,塑造现代社会农民群像,构建适应时代文学发展的乡土书写审美体系,进一步反映现代化进程中乡村面临的困境,都是作家面临的难题。
南翔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和作家的担当,将目光转向“脱贫攻坚”热潮下被忽略的非贫困、不涉及“脱贫摘帽”的乡村。塑造了以朱县长为代表的基层干部形象和以东坑乡为例,长期受自给自足生产模式影响的乡村,客观地呈现乡村产业振兴之难,让读者看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问题。面对当下的社会变革,南翔敏感于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在现实生活中汲取丰富的创作资源,以个人独特的语言风格,生动而深刻地记录和书写现实。关注底层精神危机、个人的生存与挣扎,洞悉社会大变局时代的世道人心、人情冷暖,挖掘时代的“痛点”。
是困境还是突围
南翔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意识的作家,始终对社会热点充满了强大的洞察力和敏锐的感知力。从南翔整体的创作来看,他的短篇小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洞见他创作的独特之处。短篇小说“受制于社会政治和艺术风尚的拘囿,比较长篇,它在思想艺术上受到的损害也更严重”。而南翔的现实题材短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艺术贴近现实的审美创造。在小说情节为胜,故事蔚然成风的时代,南翔的小说抛开平庸的表现形式和流于形式的现实主义,更懂得舍弃和留白。以象征和隐喻影射现实,近距离观察社会现实,坚持为人民写作,以达现实素材的审美升华。通过一类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或普通人的生存处境一点点辐射开去,为读者提供多重解读的可能性和宽广的阐释空间。正如《苦槠豆腐》通过生动再现乡村产业振兴的发展历程,客观地呈现乡村产业振兴之难,挖掘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问题,引导读者探究其症结何在。与南方都市小说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的现代化场景不同,南翔的笔下是城镇化浪潮下“艰难行进”的农村。南翔以丰富的个人经验,呈现历史转型中的时代症候和城镇风貌,写出振兴只停留在基层干部的事业线上,从而掩盖了普通民众,看不到时代乡村振兴改革中农民的形象,听不到群众的声音。所以,如何在人本主义和现代性的视角上,呈现社会发展过程中个人的命运,将他们从失语的状态中解救出来,也是今后读者更希望看到的。
文学抵达现实的纵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作家对精神现象的关注和揭示。文学必须对“现实”有所回应,有所记录,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更要从“五四”以来形成的新文学传统中汲取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在传统和现代的交融中坚守文化的立场和理想,记录“真实”,回应“现实”。小说创作是“戴着镣铐起舞”,是内心诉求与现实处境之间的一场博弈。小说创作打破重重围墙,抵达真实生活的现场,除了要求作家历练创作的智慧外,更需要的是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和良好的创作心态,否则只能在客观叙述的盈尺之地上打转。南翔以历史的眼光、深厚的人文底蕴,深入挖掘现实、聚焦社会热点,在现实题材写作的困境中寻求突围的路径。
类型化的都市叙述令人眼花缭乱,身处南方乡域的农民被现代化的洪流冲向边缘,在人人为都市繁华竞相代言的同时,为农民发声似乎成为一种不被青睐的选择。南翔以客观视角介入现实题材的创作,不直接评价,但却能通过他的叙事智慧,体会到文字背后涌动着的力量。他在思想上延续了自“五四”以来注重寻求个人精神出路的新文学传统。但与此不同的是,“五四”启蒙作家们的精英身份使他们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逐渐远离了大众,而当下的学者型小说家们则在不断的文学尝试中打破了这种局面,在小说中既有对普通民众、底层大众、社会精英的塑造,也有超越文本之外的理性精神和普世价值。而他的美学观念,正是在这种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对关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生态问题的书写中逐渐凸显的。对社会现实观察得越仔细,研究得越深入,对事件及细节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从他的小说中获得真实的力量。
从小说中多少能看到南翔的影子,这影子的“主人”或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良师,或是通晓立身处世之道的智者,或是辗转家庭与社会之间忙碌奔波的行人,或是在天地之间思悟生命真理的哲人。读他的单篇小说是难以品出其中“滋味”的,只有将目光转向他的整体创作,才能渐渐感受到他的小说在血肉中涌动着的脉搏。
注释:
[1]南帆:《不竭的挑战》,《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3期。
[2]刘守英,王一鸽:《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中国转型的乡村变迁视角》,《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
[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4]郜元宝:《关于“学者型作家”和“教授小说”》,《文艺报》,2014年7月17日第0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