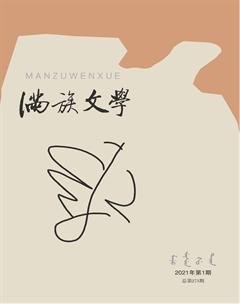改革时代的“阳明学”:再谈
孙少平 罗雅琳
电视剧《大江大河》让人想起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里有热爱读书的贫苦青年孙少平,《大江大河》里的宋运辉也是类似的形象。不过,比成为煤矿工人的孙少平幸运,宋运辉考上了大学。他或许更像孙少平的妹妹,那个学航空航天专业的孙兰香。而想到这里,一个问题突然涌上心头——为什么路遥要写孙少平?如果说,孙家三兄妹代表了80年代末的路遥为农村青年所设想的三种前景——乡镇企业家孙少安、农民工孙少平、女大学生孙兰香,那么,难道不是有了孙少安和孙兰香这两位成功榜样就足够了吗?一男一女,一商一学,既有物质层面的富裕,也有精神层面的提升。为什么路遥还要写一点也不成功的孙少平,还非要把他推向故事的前景?
然而,最吸引人的还是孙少平,不仅是那个和省委副书记的女儿恋爱的孙少平,更是那个吃着丙等菜、在漏风的工地里、在饥寒交迫的日子里、在庸俗的大环境里始终热爱读书的孙少平。是的,丙等菜。在《平凡的世界》的开头,路遥就写道,在孙少平就读的那所县立高中,大部分人吃的都是“既不奢侈也不寒酸”的乙等菜,孙少平则属于吃丙等菜的少数人。路遥一向高举现实主义大旗,但就“吃丙等菜”这个细节而言,孙少平绝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的生活环境甚至比一般人更要差。路遥为什么要这么写?
再来说读书。在电视剧《大江大河》里,宋运辉的苦读是为了高考。《平凡的世界》里孙兰香的读书与之类似。作为路遥的同代人,刘震云也在曾引发轰动的小说《塔铺》里写到了农村年轻人的读书。《塔铺》中的父亲为了给“我”去县上借一本乡下没有、但对高考至关重要的《世界地理》教材,连夜来回赶了一百八十里山路。在这段感人的情节里,对于农村孩子而言,高考是读书的绝对目的。可是,孙少平读的是什么呢?《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红岩》《创业史》《参考消息》《各国概况》《天安门诗抄》《白轮船》《简·爱》《红与黑》《牛虻》《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传》,还有杰克·伦敦和艾思奇,都和让农村子弟可以跳出农门的高考毫无关系。在当代文学史上,这样“报菜名”式地、不断往外蹦书名的年轻人往往是下乡知青或者高干子弟,比如《晚霞消失的时候》和《公开的情书》里的那些北京青年。《平凡的世界》里省委副书记的女儿田晓霞,大概是这群人的一个变体。在路遥的另一部代表作《人生》里,农村青年高加林虽然也喜欢读书看报,但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城市女孩黄亚萍炫耀关于国际政治和能源问题的新知识。像孙少平这样爱读无用之书的农村青年形象,可谓少之又少。
2018年12月18日,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路遥和蒋子龙成为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仅有的两名作家。蒋子龙得到的评价是“‘改革文学作家的代表”,而路遥得到的评价是“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家”。将这两个评价进行对比,再联系起一代代农村青年从孙少平身上汲取的宝贵精神养料,这使人不由地玩味:在事业上并不成功的农民工孙少平,为何有着独特的“鼓舞”意义?
经常有人将路遥笔下的农村青年与《红与黑》中的外省青年于连进行对比。于连珍藏着《圣赫勒拿岛回忆录》,对于拿破仑时代的向往使他憎恨自己所处的平庸年代。阅读给了他不切实际的幻想,書中的伟人使他增添了对于现实的强烈不满。《平凡的世界》中也出现了《红与黑》。在等待矿井放炮的时间里,孙少平原本在独自阅读《红与黑》,班长则建议他给大家讲讲其中的故事。当讲到于连从窗口爬进“那位小姐”的卧室时,在强烈的嫉妒之下,三十多岁还没成家的工友安锁子将《红与黑》扔进了煤溜子。于连将一本书奉若珍宝,而安锁子则将一本书视若寇仇,两种极端的爱憎都源自他们太想让书本里的世界成为现实。现代小说里有太多太多这样的形象了,比如读了骑士文学就要外出探险的堂吉诃德,再比如读了浪漫小说就希望像书中人物那样生活的包法利夫人。看起来最没文化的安锁子,遵循的正是现代人的普遍阅读法则。
那么,什么是孙少平的阅读法则?打开《平凡的世界》,随手摘录两段他的读书感言:
段落1:是的,他除过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以外,再有什么呢?只有这些书,才使他觉得活着还是十分有意义的,他的精神也才能得到一些安慰,并且唤起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某种美好的向往。
段落2:他读这些书,并不是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他从这些书中体会到,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人吃苦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一生不可能做出什么惊人业绩,但他要学习伟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这就是他读这些书的最大收获……
这两段话里充满了转折。孙少平对自己物质上的匮乏和前途的可能平凡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只有“一天几个黑高粱面馍”、“并不指望自己也成为伟人”,但与此同时,他依然渴盼着从读书中获得精神的安慰。正是这种对于现实与书本界限的清醒认识,使他与于连、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和安锁子们区分开来。
对于孙少平而言,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用书中世界映照出对现实的不满,而是用书中的伟大德性培育精神的高贵。这种精神的高贵与实际的社会身份无关。孙少平明白,虽然自己在“业绩”层面无法成为伟人,但他可以在“生活的态度”——也即“精神”的层面与伟人平起平坐。农村青年不得不面对各种实际的出身限制,在80、90年代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之下尤其如此,乡镇企业家孙少安或者大学生孙兰香的成功实属难得一遇的机运。然而,在孙少平身上,路遥给出了一种别样的期许:即使不能在“业绩”上有所成就,人依然可以获得精神上的高贵。或者说,奋斗精神本身就已赋予人们一种高贵性。当代的成功学多如过江之鲫,但都将成功视为某种固定的物质标准:事业有成、物质丰裕。而对于那些注定无法达到这一高度的人而言,这样的成功标准显得太过残酷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市场经济来临前夕,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已经初露苗头。路遥一方面为农村青年在“业绩”方面树立了乡镇企业家孙少安和女大学生孙兰香这两大榜样,另一方面,通过孙少平这一形象,路遥也留下了一种在“业绩”失败的同时依然可以通往精神高贵的可能。
再一想,猛然发现,孙少平关于“业绩”与“态度”、事功与精神的区分,不就是阳明学中的“成色”和“分两”之说吗?在《传习录》中,弟子问王阳明,伯夷、伊尹和孔子的才力并不相同,何以都被称为圣人?王阳明则回答:“人到纯乎天理方是圣。金到足色方是精。”如果说尧舜好比万镒黄金,文王孔子好比九千镒黄金,那么伯夷和伊尹就只有四五千镒。虽然各人的“分两”不同,但他们都“纯乎天理”,就金子的成色而言,他们都是“精金”——“盖所以为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两。”因此,王阳明得出结论,凡人只要肯锤炼心志,即使“分两”上不够,但只要“足色”便是精金——此即“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道理。那么,从这一视野反观《平凡的世界》,孙少平“虽不能做出惊人业绩,却可以学习伟人的生活态度”的自白,其实正是阳明学不看“分两”看“成色”的变体。如何鼓舞一个人去投身某项事业?当一切都尚属未知之时,如果紧盯结果的成败,无疑使人患得患失而举步不前。然而,孙少平的心灵体悟却告诉人们,即使“业绩”不成,但只要有过奋斗的过程,他就已经站到了与伟人同样的精神高度。这或许是“鼓舞”的精义所在。
乍看之下,这种人生价值与个体事业成败无关的逻辑,似乎接近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名言。保尔·柯察金全身瘫痪、雙目失明、没有工作能力,但他依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足:“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因为他的生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也在阅读着这本小说。不过,在保尔那里,人生价值之所以与个体成败没有关系,是因为有一个更高的、更具总体性和远景意义的存在——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决定了意义的来源。然而,到了写作《平凡的世界》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种总体性的意义源泉已经不复存在。孙少平则给出了新的成功定义:在他那里,成功与个体的“业绩”和宏大的人类解放事业都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与艰难的生活奋斗、与心灵的磨砺历程相关。从而,孙少平得以取代保尔·柯察金,成为中国90年代在艰难中苦苦挣扎与怀疑的千千万万底层青年的新偶像。
在小说中,孙少平读的另一本书是伏尼契的小说《牛虻》。事实上,孙少平在结尾处脸上留下的疤痕,使其也接近于“牛虻”的形象。值得注意的是,《牛虻》也是保尔喜爱的书。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保尔推崇“牛虻”的原因是:
我赞成他的忠诚、他那无穷的接受各种考验的力量,我赞成那种受苦而毫不诉苦的人,我赞成那种革命者的典型,在他们看来,个人的事情丝毫不能与全体的事业相比。
在保尔看来,“牛虻”之所以“受苦而毫不诉苦”,是因为他将“个人”放置于“全体”的框架之中。孙少平同样是“受苦而毫不诉苦”的那一类人。不过,生活于一个不再具有“全体的事业”的时代,孙少平面对个体痛苦的方式是将它理解为一种“考验”,不是保尔所经历的“革命考验”,而是一种“生活考验”。路遥经常写到小说人物所面临的“考验”:孙少平在黄原做苦工的前三天是“闯过了第一关”、“经受着牛马般的考验”;田润叶在丈夫残疾之后,也勇敢地去面对“新的考验”。一旦被理解为考验,痛苦也就有了意义。面对奋斗过程中的种种痛苦,路遥的解决方式既不是让个体与整体直接对接,也不是将孤零零的个体抛入残酷的竞争之中。和对于“业绩”与“态度”的区分一致,在这里,路遥同样淡化了对于结果的强调,而是通过对个体日常行动之意义的肯定,为奋斗者找到了充满希望和踏实感的立足之基。这种对于日常实践中所体现的更高意义的重视,同样与阳明学有着内在的吻合。
沟口雄三曾在著作《两种阳明学》中区分中国和日本存在着的两种阳明学。日本阳明学接受的主要观点是“心即理”,强调从自我主体出发的强大能动性。《平凡的世界》中不乏这一层面。孙少平与省委书记女儿恋爱的浪漫奇遇,常被当代读者视为穷人的白日梦。主打玄幻作品的网络作家猫腻曾表示,《平凡的世界》是一部最好的“YY(意淫)小说”。“意淫”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反过来说,“意淫”也意味着从无到有的过程,意味着发挥“心”的无限力量以超越世俗的限制。这正是阳明学的要义之一。日本幕末志士就从阳明学的这一面中汲取了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豪气。孙少平的远行与漫游,他不断想去更艰苦的地方挑战自我的内在渴望,也都与阳明学对于“心”的无限活用之重视有关。但是,如果将之视为孙少平形象的重点,那么,他和一般的励志偶像其实并无二致。
《平凡的世界》往往被归入“改革文学”的谱系。不过,和另一位“改革先锋”蒋子龙的代表作如《乔厂长上任记》和《开拓者》相比,或者和“改革文学”的其他代表作如柯云路的《新星》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相比,路遥笔下主人公的身份截然有别。“改革文学”的主流作品往往将故事放置在一个国有大厂或行政单位中,从厂长、书记等领导者如何铁腕推进改革的角度自上而下展开叙述。“出现问题—解决问题”是“改革文学”的常见思路。小说中的工人与农民们,都不过是厂长和书记在现代化改革中需要面对的一个个问题。因此,对于“管理科学”的探讨常是改革文学的重点。然而,《平凡的世界》中尽管也出现了省委副书记田福军之类的角色,但他只作为故事的后景存在。路遥的真正主角是孙少平这样出身贫寒、地位低微的农家青年,小说的重点是孙少平、孙少安、孙兰香、田润叶和田润生等农村青年人的精神成长史。当小说主角被设置为厂长和书记们之时,改革也就成了一种自上而下推行的、因而外在于普通民众的政治观念。相比之下,当小说聚焦于孙少平这样的底层农村青年的成长,改革也就与普通个体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历程有了感性的关联。更进一步说,这透露出对于人的两种不同看法:在前者那里,人是为了实现改革所需要调动、需要得到高效利用的生产元素;在后者那里,人的精神提升是改革过程中更为重要的主题。
沟口雄三强调日本阳明学与中国阳明学的差异。有别于重视发挥内心主体性的日本阳明学,“以时代要求为动力而产生的”中国阳明学更强调实践的重要。此前的朱子学强调静坐内观,这是一种高度精英化的道德涵养方式,为生计奔波的普通民众是无法实行此道的。然而,王阳明则强调“事上磨炼”,从而下层百姓也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实践中参与到儒家的道德修养中去。由于中国阳明学不再追求观念化的道德,而是强调在实践中进行磨砺,从而,它完成了“儒教大众化”这一重要转折。路遥把“改革文学”的主人公从厂长和书记下放到普通民众,甚至下放到“吃丙等馍”的孙少平身上,也就完成了“改革的大众化”。“改革”的理念不再必须通过少数领导者的铁腕举措才能体现,在路遥看来,像孙少平一样的底层青年不是只能被动接受改革理念的弱者,他们为生活所展开的艰苦奋斗已经是改革精神的耀眼闪现。
“改革的大众化”当然不是靠一本书来完成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新星》和《沉重的翅膀》等“改革文学”的代表性作品完成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彼时的“改革”尚在小范围内展开。如果我们意识到,从1988年开始,国家允许农民进城务工兴办服务业并提供各种劳务,逐渐放开了农民进城自由流动的限制,那么,在广大孙少平一样的农民青年步入这个即将到来的、充满机会与残酷的时代之前,路遥为他们写下了《平凡的世界》这部激励之书。孙少安和孙兰香是“业绩”成功的榜样,虽败犹荣的孙少平则提供了在奋斗过程中获取精神高贵的可能。这是路遥留下的一缕温暖与希望。
【责任编辑】邹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