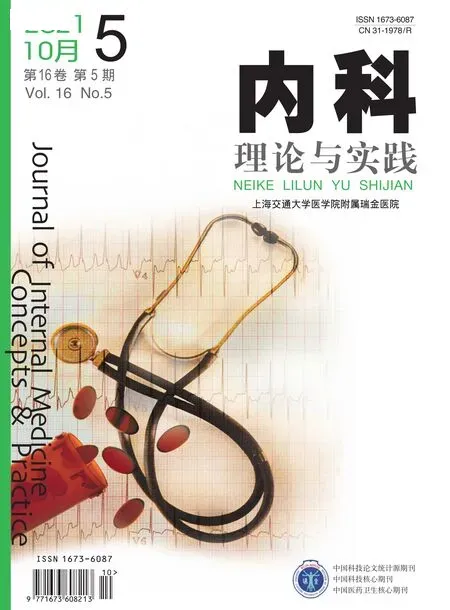肝豆状核变性的中西医药物治疗概况
王 训, 韩咏竹, 杨任民
(安徽中医药大学神经病学研究所,安徽 合肥230061)
肝豆状核变性 (hepatolenticular degeneration)又称威尔逊病(Wilson disease,WD),是一种常染色体隐性遗传铜代谢障碍疾病[1]。1912年金尼尔·威尔逊(Kinnier Wilson)系统描述该病是一种“进行性豆状核变性(progressive lenticular degeneration)伴有肝硬化的家族性神经病变”。Ciarla(1916年)在意大利神经病理学杂志首次使用“Wilson disease”的名称,Hall(1921年)指出WD是隐性遗传病,并使用 了 “肝 豆 状 核 变 性”(Dégénérescence Hépatolenticulaire)的术语。1985年Frydman等将WD基因定位于13号染色体,1993年Petrukhin、Bull和Tanzi等确定为13号染色体长臂上(13q14.3)的ATP7B基因,编码140 kD铜转运P型ATP酶[2]。现已明确WD由于铜转运ATP7B酶功能缺陷,导致铜蓝蛋白合成减少、胆道排铜障碍,肝脏、脑、肾和角膜等组织器官过量铜蓄积,出现进行性肝损害、锥体外系症状、精神症状、角膜色素环(Kayser-Fleischer ring,K-F环)等。WD通常在青少年期发病,是迄今少数几种可治疗的神经遗传病之一[3]。
WD的现代药物治疗简介
自威尔逊论文发表近110年来,关于WD药物治疗的里程碑式研究不断出现(见图1)。1948年Mandelbrote发现金属络合剂二巯基丙醇肌内注射治疗WD患者;1956年Walshe发现青霉胺是一种更为有效的铜络合剂;1961年Schouwink发现口服锌剂可显著降低肠道铜的吸收;1982年Walshe发现曲恩汀(trientine)作为铜络合治疗;1986年Walshe引入四硫钼酸铵用于青霉胺和曲恩汀不耐受的WD患者[4]。2003年美国肝病研究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ver Diseases,AASLD)发布并于2008年修订WD实践指南;2012年欧洲肝病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the Liver,EASL),2018年欧洲儿科胃肠病、肝病和营养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Pediatric Gastroenterology,Hepatology and Nutrition,ESPGHAN)分别发布WD临床实践指南[5],均指出WD患者需终生治疗,主要目标是减少铜摄入和促进铜排出,防止铜的再积聚。药物治疗大致分为初始阶段和维持阶段,即有症状患者的初始治疗选择络合剂(青霉胺或曲恩汀);维持治疗以及无症状患者的一线治疗均建议合适剂量络合剂或锌剂。AASLD和EASL指南均指出四硫钼酸盐的新兴作用。2008年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神经遗传病学组发布WD指南并于2021年更新[3,6],推荐二巯丙磺酸钠(sodium dimercaptosulphonate,DMPS)、二巯丁二酸钠(sodium dimercaptosuccinate,Na-DMS)和二巯丁二酸(dimercaptosuccinic acid,DMSA)为铜络合治疗,并肯定了中药对WD的辅助治疗作用。多年来循证医学发现,青霉胺的临床驱铜疗效佳,但药物安全性差,10%~50%的患者用药早期发生短暂的神经症状加重[7],30%~47%的患者因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而被迫停药。曲恩汀相对不良反应较少,仍有神经症状恶化的风险;锌剂排铜作用较弱,多用于无症状患者或维持治疗[8]。由于WD多种表型与呈现年龄重叠以及多系统受累,使得诊断和治疗更加复杂,目前指南対于WD的神经和精神症状以及某些特殊情况的管理有限。国内对WD的认识起步较晚,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尝试用中医药、中西医结合等方法治疗。WD中医学注重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大量的临床及实验证实中医药治疗WD的良好疗效,推动中医药治疗WD的不断发展。

图1 WD药物治疗主要时间轴[3-6]
WD病因病机的中医认识
中医古代文献对WD缺乏明确记载,对其发病机制的认识迄今尚未统一。根据其临床表现多有震颤、舞蹈样手足徐动、扭转痉挛、精神障碍、肝脾肿大、腹水等不同,中医学归属于“颤证”“风症”“痉症”“癫狂”“黄疸”“积聚”“鼓胀”等范畴[9]。目前大多专家[1,10,12-13]认为WD的中医病机主要为先天禀赋不足,肝肾亏虚,筋脉失养致震颤、肢体拘急;虚火炎上,心神被扰致神志癫狂。虚久致实,铜毒内聚生风、火、痰、浊、瘀等,肝脾失调致黄疸、鼓胀;脾开窍于舌,痰浊郁久则舌不利致流涎、构音不清。WD的核心病位为肝、脑,与脾、肾、胆关系密切,肝肾不足、铜浊蓄积是其病因,铜毒滞络为主要病机,贯穿于WD全程,在疾病的不同阶段,主要病机有所不同,临床当予明辨。
WD的中医辨证分型
由于WD的病因病机目前尚未统一,其辨证分型亦各不相同。根据中医八纲及脏腑气血辨证理论,洪铭范等[10]将WD初步分为肝肾阴虚、气血两亏、湿热内蕴、痰蒙心窍、痰火扰心等5种常见证型,其中部分病例可表现为虚实夹杂或混合共存。杨任民等则将本病归总为肝肾阴虚,虚风内动型;肾阴不足,枯骨髓减型;湿热内蕴,积聚鼓胀型;火灼肝胆,胆热液泄型;阴血火旺,火扰心神型[9]。李宗亮和胡纪源[14]研究1 043例WD患者发现,发病年龄不同则中医证型有所不同,儿童多见肝肾不足、肝肾阴虚、湿热内蕴型;青少年证型不仅存在肝肾阴虚、肝肾不足、肝郁脾虚、脾肾阳虚等虚证,同时兼有湿热内蕴、肝风内动、痰瘀互结、痰瘀阻络和痰蒙心窍等实证;而中年人以气血两虚、肝肾阴虚多见。王共强等[15]通过对21篇中医文献中736例WD患者进行分析共发现13个中医证型,其中肝胆湿热、肝肾阴虚、肝风内动、痰湿阻络为主要证型,也反映了WD中医辨证分型的复杂与混乱。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中医药治疗对难治性神经遗传变性病的影响,WD的中医证型客观化、标准化、规范化研究越来越受重视。韩永升[16]对185例WD患者临床客观指标研究显示,不同证型WD患者在年龄、病程、血尿酸、K-F环、腹部超声影像等客观指标存在显著差异;肝肾不足证WD患者的K-F环阳性率最低,血尿酸水平明显高于肝肾阴虚证、湿热内蕴证和气血两亏证;肝肾不足证肝脏B型超声(B超)表现为纤维化的星光点征,湿热内蕴证多为肝硬化的结节征,而肝肾阴虚证和气血两亏证的B超则为中度损伤的岩层征和树枝状征;大部分肝肾不足证的肾脏超声无异常改变,而湿热内蕴证肾脏超声异常率达50%;肝肾阴虚证均无腹水,而湿热内蕴证的腹水发生率达46.36%[16]。另有学者尝试对WD的血清标志物、基因突变类型与中医证型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发现不同WD中医证型之间存在一定差异[17]。目前WD的辨证分型尚离不开四诊合参的方法,不能脱离中医证候的本质而孤立地进行现代医学指标研究。
WD的中医药辨证论治
多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WD进行了中医证候学、证型及理法方药进行了研究,根据“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谌宁生[11]将WD辨证分为4型:①痰湿阻络型,治宜祛风通络、醒脑开窍,方用涤痰汤加减;②肝风内动型,治宜滋养肝肾、柔肝熄风,方用大定风珠加减;③热毒内盛型,治宜清热解毒、泻肝降火,方用龙胆泻肝丸加减;④湿困脾胃型,治宜芳香化湿、健脾和胃,方用藿朴夏苓汤加减。崔世麟[18]根据WD患者首发症状辨证施治:①以锥体外系症状为首发者,证属中州阳微、痰湿内留,治宜悦胃醒脾、化湿祛痰,方用苓桂术甘汤合二陈汤;②以精神症状为首发者,证属肝失条达、疏泄失司,治宜柔肝疏郁,方用一贯煎;③以肝脏症状为首发者,证属脾肾阳虚、气机阻滞,治宜温阳疏利,选用茵陈术附汤加味;④骨关节和肌症状首发,属肾精亏损、髓海不足,治宜补肾健骨强筋,用左归饮和六味地黄丸交替应用;⑤皮肤变黑为首发者,证属气滞血瘀、肌肤不润,治当活血通络,方用桃红四物汤;⑥月经失调为首发者,证属痰湿阻络,治宜清痰祛湿,用济生导痰汤治之。杨任民团队则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归纳总结,提出WD的辨证分型论治[9]:①肝肾两亏、虚风内动证,治以滋补肝肾、息风定振,拟大定风珠加减;②阴血火旺、火扰心神证,治以滋阴降火、安神定志,方用二阴煎和生铁络饮加减;③火灼肝胆、胆热液泄证,治以清肝利胆、通腑渗湿,方用肝豆汤合茵陈四苓散加减;④湿热蕴结、积聚鼓胀证,治以活血软坚、攻下逐水,拟中满分消丸加减;⑤肾阴不足、枯骨髓减证,治以填精补气、益气益血,拟补天大造丸加减。然而,临床辨证施治应以临证时患者病情为据,按中医八纲、脏腑等辨证理论为指导进行辨证、遣方用药,更应结合现代医学客观指标,注意避免含铜量高的中药。
WD的病证结合中西医治疗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杨任民等[19]发现根据传统中医WD属“肝风内动”的理论,拟传统的“平肝熄风”类含铜量高的中药,如虫类药(僵蚕、蜈蚣、全蝎、地龙)及贝壳类药(龟板、鳖甲、珍珠母、牡蛎)等,导致病情反而加重。基于WD的现代医学铜积聚病理基础,结合WD的中医病机证候,应用病证结合分析WD患者系铜毒积聚、肝胆湿热、经脉瘀滞而出现肝、脑损害等症状。对中药反复筛选尿排铜拟定具有清热解毒、通腑利尿的“肝豆汤”(大黄、黄连、黄芩、穿心莲、半枝莲、萆薢),治疗37例WD患者,近期有效率达81.08%。1993年杨任民等[20]更新了的肝豆汤配方(大黄、黄连、黄芩、鱼腥草、半枝莲、泽泻)治疗WD 107例,发现能明显促进尿铜排泄,改善血清铜氧化酶,总有效率为84.1%。韩咏竹等[21]采用肝豆片治疗WD 32例,总有效率为71.9%,并与DMSA的疗效进行了比较,发现肝豆片虽然排铜稍弱,但作用持久温和、不良反应小,更适用于病情较轻及无症状的患者。
随着病证结合治疗WD取得临床满意疗效,杨任民团队[1,9]据WD不同临床类型和病理生理,对肝豆汤进一步优化组方。肝豆(汤)片Ⅰ号主治湿热内蕴型,具有显著的尿及胆汁排铜作用;肝豆(汤)片Ⅱ号主治肝肾阴虚型,在肝豆汤加用保肝、利水、退黄中药,WD患者肝硬化腹水、黄疸等;肝豆(汤)片Ⅲ号主治气血两亏型,系在肝豆汤加用补气生津、补血止血中药,有明显的保肝退黄、补血止血的功效;肝豆(汤)片Ⅳ号主治痰蒙清窍型和痰火扰心型,系在肝豆汤加用化痰止浊、醒脑开窍中药,有控制精神症状、改善睡眠、调节情绪的作用。胡文彬等[22]应用肝豆片Ⅰ号治疗WD患者,有较显著的尿排铜及胆汁、粪便排铜增加,临床流涎、构音障碍、皮肤变黑及肢体水肿等症明显改善。薛本春[23]对存在肝纤维化及肝硬化的WD患者,分别加用肝豆汤Ⅱ号、Ⅳ号方,证实其均能明显改善患者的肝功能及其肝纤维化指标,并可能通过抑制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tissue inhibitor of metalloproteinase 1,TIMP-1)水平,而发挥抗肝纤维化作用。
一、病证结合中医药对WD铜代谢障碍的调节
病证结合中西医协同治疗WD在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体内蓄积铜的排出、减轻药物不良反应方面,明显优于单用西药。杨任民等[24]用肝豆汤联合青霉胺、Na-DMS、葡萄糖酸锌治疗418例WD患者,显效26.64%,有效率93.1%,并发现肝豆汤可明显增加尿铜排泄。对198例WD患者采用肝豆片和DMPS联合治疗2个月,出院后予DMSA和青霉胺交替服用,并同时服肝豆片和葡萄糖酸锌以维持治疗。近期疗效临床痊愈率11.11%,有效率84.85%,随访6个月~24年,临床痊愈率及显效率均增高。周志华等[25]将1 001例WD住院患者随机分为青霉胺、DMSA、肝豆片及中西药结合组(青霉胺/DMSA交替+肝豆片)共4组,连续3年分别对各组患者驱铜治疗前后的病情评估和K-F环等相关检查进行比较发现,4组长期治疗均使患者体内蓄积的铜和K-F环分级呈下降趋势。尤其中西药结合组显示出更佳及更持续的改善效应,驱铜效果明显,明显改善肝功能、神经功能,并可有效防止单用西药组引起的白细胞减少,不良反应轻微,疗效优于单用青霉胺和DMSA。
二、病证结合中医药对WD高铜诱发肝损伤的修复
由于ATP7B蛋白主要在肝脏表达,其功能障碍导致铜离子首先在肝细胞内异常蓄积,无论是肝型患者还是脑型患者,即使症状前期的WD个体,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肝脏损伤。因此,明确高铜对肝损伤的机制及其治疗靶点,也是现代中医药治疗WD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近些年,诸多学者对肝豆汤治疗WD的疗效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汤其强等[26]通过建立WD皮肤成纤维细胞模型,观察加入含肝豆汤兔血清前后细胞内Cu2+、Zn2+等微量元素含量的变化,显示肝豆汤具有显著的细胞内排铜作用和使细胞内锌含量增加的作用。董健健等[27]研究显示,含肝豆汤兔血清培养的TX(toxicmilk mouse)小鼠肝细胞及肝豆汤灌服治疗TX小鼠,体内铜含量显著降低、锌含量显著增高,ATP7B、抗氧化蛋白1(antioxidant protein 1,ATOX1)、超氧化物歧化酶铜伴侣蛋白(copper chaperone for superoxide dismutase 1,CCS)和细胞色素C氧化酶17(cytochrome C oxidase 17,COX17)的表达水平增高,而铜转运体1(copper transporter 1,CTR1)、MT的表达水平降低,证实了肝豆汤能通过调控铜代谢通路的相关蛋白,改善TX小鼠肝细胞内ATP7B蛋白的亚细胞功能定位障碍,在一定程度上纠正铜代谢异常。另外,肝豆汤可降低细胞内氧化应激水平,减轻铜对WD肝细胞的损伤,组方中姜黄、大黄、泽泻、三七这4味药在修复肝损害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而三七的作用尤为明显,并可降低WD肝纤维化的病理损害过程,有效缓解WD铜负荷的肝损伤[28-29]。
三、病证结合中医药对WD高铜诱发神经元损伤的保护
WD的神经系统症状由脑组织损伤引起,主要是肝外铜毒性的结果,其毒性涉及如线粒体毒性、氧化应激、细胞膜损伤、DNA交联和酶抑制。通过驱铜治疗,神经系统症状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逆的,但约20%的患者预后不良、严重残疾或死亡,早期治疗可以预防脑损伤和神经系统症状[30]。
杨任民等[31]对肝豆汤(片)联合铜络合剂治疗WD患者长达24年的随访观察,发现中西药联合治疗可使包括脑型在内的大多数WD患者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并能长期存活。徐陈陈等[32]以TX小鼠乳鼠神经元原代培养的方法建立WD神经元损伤模型,含肝豆汤兔血清可显著降低TX乳鼠神经元内的铜含量和活性氧 (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的释放,并可显著降低TX乳鼠神经元细胞内酸性神经鞘磷酯酶 (acid sphingomyelinase,ASM)、神经酰胺(ceramide,CER)、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c-Jun氨基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p38-促分裂原活化的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胱天蛋白酶3(caspase-3)、胱天蛋白酶-9及细胞色素C(cytochrome C,Cyt C)等蛋白及mRNA的表达水平,而胞外信号调节激酶(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ERK)1/2、X-连 锁 凋 亡 抑 制 蛋 白(Xlinked inhibitor of apoptosis protein,XIAP)和mRNA的表达水平增高,表明肝豆汤可通过减少脑内铜含量,进而调控Cyt C/胱天蛋白酶信号通路,达到减轻铜蓄积对神经元的损伤;以TX小鼠为动物模型的体内实验也验证了上述研究结果。赵雯等[33]通过均匀设计拆方研究发现,肝豆汤效应中药为黄连、姜黄、泽泻和金钱草,可下调TX小鼠脑组织p38和Bax的表达水平、上调ERK和Bcl-2的表达水平,抑制神经元细胞的凋亡,促进神经元细胞的修复。
总结与展望
中西药联合治疗WD的疗效明显高于中药或西药单独治疗,不仅避免了西药长期服用的一些不良反应,也弥补了中药起效慢、排铜弱的缺点。中医药对WD的治疗强调整体观念,与现代铜络合剂相比,中医药疗法促进铜的排出、减少铜的蓄积,同时也能活血通腑,阻止和延迟肝硬化发生,并保护和促进肝、脑组织等功能恢复,可长期维持治疗[34]。采用中医药治疗WD还应关注:①对于WD的中医治疗要重视整体观念、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既要符合中医辨证理论,更应切合WD铜蓄积的现代病理机制;②由于WD临床表现复杂多样,给中医辨证施治带困难,目前辨证方药多是小样本、回顾性总结,缺少前瞻性、多中心、双盲对照大样本的循证医学统计分析;③中医的“证”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年龄、病程、临床症型等因素在WD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中医证候不同,统一并完善WD的客观化、规范化、现代化的证候学指标,辨证分型、随证用药;④WD的病因明确,现代药物治疗方法相对局限,但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更为缺乏。因此,WD的中医药研究是一系统工程,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以建立以病证结合为基础、证候要素为核心的中医辨证新体系,结合现代药理遣方用药,以进一步提高中医药治疗WD的疗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