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大手笔
菡 萏
一
前些天,与朋友说起张爱玲的小说,提到《半生缘》时,竟不知不觉,把整本书复述完。每至精彩处,情不自禁连赞“大手笔”。那一刻,恍然大悟,所谓大手笔,只不过四两拨千斤,以小见大的细节之美。隔着几十年苍茫无垠的岁月迢递而来,那些隐秘的链条,潜藏在记忆深处,源源不断地复活。仿若昨天,那么鲜明,像刻骨的仇恨,或忘不掉的恩情,如影随形。而非东晋文人王珣梦见的那支如椽大笔,肩负着所谓的重大使命或笔力雄健者的皇皇巨制。
它贴着读者的心脏,如此简单。
故一直想写篇《顾太太旗袍鼓出的那一块》,那个细节,太撼人,涵盖了全部章节,乃书眼。钱即命脉,亦断崖;也是恩情,或陷阱。钱的双面性,支撑着整部书走完它的岁月,是起因,亦是连锁,延续着人之命脉,左右着人之神经,甚至终结着一个人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
所以《半生缘》看似写情,实写钱。
第十二章豫瑾结婚,顾太太去参加婚礼,说好要来的曼桢并没来。顾太太不免心慌,以为曼露垂危,遂草草吃了两口饭,赶至女儿曼露家,得知的却是曼桢被强奸的消息。在曼露的软硬兼施下,顾太太心慌意乱回至家中,恰巧碰见世钧在此等曼桢。见世钧,她如遇亲人,百感交集,有千言万语要讲。遂说道,上楼去说。那刻,她想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他,此乃本能反应。门是锁着的,掏钥匙时,她摸到旗袍里一大叠钞票,那八成新,温软厚墩墩四四方方的钞票是曼露给的。须臾,她改变主意。待进屋,世钧想听的下文,已然不在。钱,让顾太太瞬间冷漠、心硬下来。她的天平随即倾斜,觉得对不起曼露。她在找借口,对不起的应该是钱。
可见,钱是一道门槛,门里门外,截然不同。钱,也是转折,人之生命与书内情节的转折。张爱玲如此安排,便是大手笔。钱,也是许多人逾越不过去的鸿沟,瞬间催生化学反应。拿人钱,忠人事,哪怕放弃亲情。钱又是试金石、温度计,且屡试不爽。没钱可以按照自己心意途径办事走路;受人钱财,就得拐弯,昧着良心,帮人掩饰。所以那刻,丧失了救曼桢的机会。顾太太舍弃了曼桢,就像当初舍弃曼露一样。
此情节,在第七回有场预演。顾太太深夜从曼露处回来,曼桢躺在床上,看见顾太太搭在椅背上的旗袍鼓出一块,便说:“妈,以后不要拿姐的钱,给那姓祝的知道了,只说姐姐贴娘家,还不知贴了多少呢。”即不想和祝鸿才有瓜葛,然而顾太太拿惯了,她的旗袍曾一次次鼓起,每次都是温软软的一大叠,那是曼露卖血肉的钱。
现今进入电子时代,年轻人对纸币已然陌生;但纸票年代,大多数人有切身体会,钱即温暖,即踏实。有钱,方心安。
曼桢受害后,顾太太坐视不救是事实,也是豫瑾后来明知道顾太太在六安,不去拜望的原因。如果祝鸿才再奸,或屡屡强奸,只怕曼桢的小命也就没了。
若此时,顾太太告诉世钧,世钧设法营救,曼露那边不可能扣着不放。曼桢获救,不会再与曼露有染,以她的话,只当被疯狗咬了一口;亦不会觉得自己不洁,她相信世钧,而世钧又是那么值得信赖。
曼露和祝鸿才合谋构陷曼桢后,祝鸿才曾担心过不了顾太太这一关。曼露却胸有成竹,轻描淡写道,妈是最好对付的。足见曼露多么了解顾太太,摆平其母易如反掌。手段呢?无非是钱。曼露许诺,搬家后,家用全包,日后供弟弟伟民、杰民出国留学。顾太太软了下来,为利益,为曼露描绘下的宏伟蓝图。张爱玲拿捏得很准,既写出了顾太太的懦弱,也写出了她嗜钱的癖好,或不得不爱钱的本色。顾太太初听曼桢被奸,虽曾惊讶焦急,但终究没震怒、谴责、咆哮,有情绪上的反馈爆发,或拼了老命也要带走曼桢的决绝。留下曼桢,便置之于虎口,她的思路始终被曼露牵着走。她在这座豪宅里唯唯诺诺,究其原因,是欠曼露的。
曼露十七岁那年,因父亲病故出去做舞女养家,供弟弟妹妹们读书。由一个纯洁少女,卷进欢场,许多男人张开血盆大口等在那,其中就包括在曼露身上花了许多冤枉钱而未得的世钧的爹。那时的曼露,尚想维持作为独立生命个体的尊严,而欢场的男人,只一个字:嫖。所以曼桢对世钧才有那句话:“不知道嫖客和妓女哪个更高尚。”
一个女人,一旦陷入那种行当,等同混入兽界。用“兽”这个词,一点都不过分。没爱的性交,本就是兽。人身上,或多或少隐藏着这种动物本能。能抵御的,唯思想情感,及法律。那种场所,是冠冕堂皇的兽界,而女人即待宰的羔羊与玩物,任谁都无法保全自己,这点顾太太不会不明白。
时间应是十年前,最小的杰民给淑惠送钥匙时,已七八岁。曼桢和世钧又谈了两年恋爱,曼露二十七岁左右,曼桢二十四岁的样子。曼桢对世钧说过,父亲死那年,她十四岁。即十年间,曼露从一个纯洁少女变成舞女,再沦为妓女,出嫁后,变成魔鬼,是个过程。线路一清二楚,自然而然,曼露不断丢失自己——初恋、尊严、人性、心脏,直至变态,也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
若她的父亲不死,曼露的归宿应是极其美好的。嫁给豫瑾,豫瑾人好有才学,没负累,后来成为家乡小县城医院的院长。且那时他们的感情极好,豫瑾称其为紫衣的姐姐。
情景有点阳春四月的味道,春和景明,丁香淡淡,巷子里摇曳着这对少男少女柔和美丽的身影。怎奈家庭变故,情缘被拦腰斩断。曼露做舞女后,顾家这头便退了亲,退亲的肯定不会是曼露。顾太太心里明白,这是条不归路,是黑夜,亦是火坑,得在里面烧着。
曼露融入那个血淋淋、声色犬马的烈焰蒸腾的世界后,石库门的烟火日常,清平和蔼已与己无关,属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与蔡金芳家捉襟见肘的穷苦日子也泾渭分明。那是场纵欲高歌的假面舞会,男人偶尔出来放纵挥发荷尔蒙的地方。小民的日子,虽清苦,却内心殷实;而欢场,虽华丽,却肮脏,是空的。
二
那有没有曼露不做舞女的可能?
顾先生走的那年,顾太太最多也就四十岁,她最小的儿子杰民应该才出生,她并不老。顾老太太也就六十多岁,这个算法,不会太出格。如果当时,杰民留给顾老太太带,顾太太出去做事,帮佣或像蔡金芳那样在菜场摆摊,不会完全行不通。曼露也出去做事,像张爱玲小说《创世纪》里的滢珠那样去药店做营业员,尽管曼桢说姐姐文化不高,但大小也是个初中生。伟民去卖点烟卷,曼桢帮衬家务,即便不能读书,糊口并非完全难事。
无论合不合理,是不是出于今人臆想,但顾太太好像并没朝这个方向做出半点努力,轻而易举就把曼露送了出去。牺牲曼露,全家安逸,上学的上学,居家的居家。
但事物并没绝对的必然性。
曼露的血雨腥风,一路周旋,他们是不必晓得的。曼桢读了书,毕了业,在打字间谋了事。曼露的恩情,曼桢始终记得,所以一再维护姐姐。回顾曼桢与世钧相恋的两年,基本琴瑟和谐,虽因豫瑾,世钧吃过一点小醋,但几乎略无参差,只涉及曼露时,方摩擦。曼桢问,结婚后,还和不和姐姐来往?这是她关心的,她不能舍弃姐姐,是姐姐牺牲了自己的纯洁,庇护了她的纯洁,且让她受教育,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这是无法回避的实情。曼露也对祝鸿才说:“我这一个妹妹,我赚了钱来给她受了这些年的教育,不容易的。我牺牲了自己造就出来这样一个人,不见得到了儿还是给人家做姨太太?”
当曼桢可以挣钱时,曼露的作用已在削减。她沦落为暗娼后,常在家待客。说,曼桢大了,和她住一起,不方便。曼桢是个花季少女,来者皆色鬼,曼桢一天到晚裹在蓝布罩袍里,怕自己的美外泄,但还是被垂涎了,青春是遮不住的东西。伟民也大了,觉得耻辱。全家巴不得曼露赶快嫁掉,恢复正常人家的安稳日子。曼露人老色衰,成为弟妹们发展的绊脚石,负面影响越来越大。曼桢和世钧所面临的婚姻就验证了这点,因曼桢和当年的李璐,即曼露化名的舞女长得像,而引起世钧父亲的怀疑。
欢场,男人纵欲之所,世钧的父亲便是一例,也是很多有钱人的例子,包括世钧的舅舅、张爱玲的父亲等。逢场作戏中,若对哪个动了心,还可以弄回去做小。
当然,如果看老舍的《月牙儿》,就不能过分苛责顾太太,母女俩做妓女,尚不能养活自己。毕竟我们没生活在那个时代。
三
书内还有一个细节,极触目。第二章,曼桢回家,曼露正在楼梯口打电话。她新学了一种笑声,尖锐刺耳又娇滴滴,继而哈哈。空洞虚假。学,意味着非自然流露。一个人不能靠内质吸引人时,只能凭这种夸张的外在声音姿态敷衍弥补,所以叫卖笑,再苦,都不能哭。而她果绿色长缎旗袍,腰际那个黑隐隐的手印又异常触目惊心。作者道:“跳舞时,人家手汗印上去的。”这个人家不会是女人,但张爱玲没用“男人”二字。她下笔柔和谨慎,极细致,不想过分鄙薄曼露,尤其从曼桢眼中,对这种生活方式有任何批驳,所以文字是有弹性的,尽量为曼露洗脱。但读者阅此,依旧恐怖,有点证据的味道。那件旗袍便是曼露生活状态的写实与见证,等同流动的作案现场。
一个无头无脸之人,只留下一个手印,不能不令人惊悚。
此乃一只男人的手,也许是许多男人手的叠加,隔着一层衣服,里面的肉才是目的,至少不会拒绝。所以张爱玲,写曼露的过去是虚的、间接的,笔墨吝啬,似大段流水,空空落落,反而愈发清晰。这便是大手笔,侧锋出奇,非正面着墨曼露光怪陆离的舞厅生活与床上实景。一个手印,涵盖了曼露十年的沧桑人生,炼狱般的生活。她打情骂俏,堕落,但那回不去的春天,她比谁都清楚和酸楚。
想今之小说,有的何等露骨,非写到山穷水尽,淤塞人心不可。又有何现实意义?人在性之上,方为人,人加文即人文。简而含蓄,才是教养,所以张爱玲的小说有国际化意味。《茶花女》专书妓女,亦零镜头。
此时,曼露已画好红白黑骇人的舞台装,只是头发还没梳,散乱着。即将正式出门。这件八成新的旗袍,不会是没洗过的,那么这个手指印是洗不掉的。此细节太有冲击力,像个耻辱柱,钉在衣服上。这层衣服又是那么珍贵,脱了,更无尊严可言,等同一具行尸走肉。然而对麻木的曼露已不算什么,就像后面合谋强奸曼桢一样,对她也不算什么,见怪不怪。
但于观者,却是心有余悸的,曼桢用外人的目光审视姐姐,愈发流落,所交男友愈发不堪。曼露的狰狞、做作、低俗,一目了然,是其内心真实写照。十七岁,那个单薄柔弱的身影渐行渐远,已不复存在。魔性场所,已把她培养成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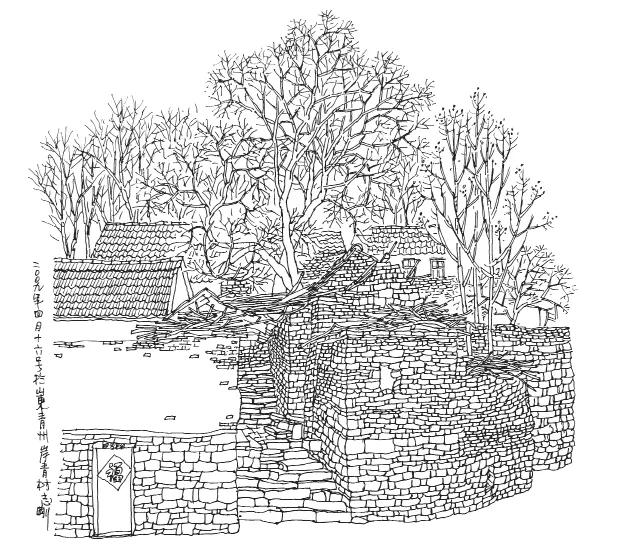
那隐隐的手印印在旗袍上,更印在肌肉心脏,世俗对她的解读上。
只是曼桢当天还在对世钧说,姐姐人善,没心机。后面发生之事,无疑教训了曼桢这一天真想法。
祝鸿才作恶后,顾太太先是着急说坑死人了,这还了得。曼露便抛出条件,祝鸿才娶曼桢,她做小。顾太太随即又觉得委屈了曼露。条件谈妥,安抚好顾太太。顾太太要去看曼桢,曼露不让,说,曼桢吵着去报警。顾太太这时反觉曼桢不懂事,这事怎能张扬,也不怕丢人。张爱玲行文至此,非常狡猾。顾家住的吉庆坊是个繁华所在,店面鳞次栉比,世钧第一次去,便见阿宝夹在几个丫头婆子间,在公共龙头下冲脚。尽管顾家独门独院,里面尚有房客,曼露那样招摇,做什么行当不言而喻。哪怕伟民、杰民再训练有素,也无济于事,何况阿宝是个喜欢传播是非之人。一些男人接踵出入,顾家状况一目了然,讲脸面,早没了。另外他们并非根深蒂固的上海人,在上海并没亲友,只是寓居。所以顾太太的担忧,纯属掩耳盗铃。
无非钱在作祟。曼露又说鸿才已在社会上有点地位,传出去如何。随即把祝鸿才包裹得高大上。坏事,若抹上一点金子的光亮,也就柔和起来。
知丑尚做,知恶尚做,已足够恶。
四
人之审美不同。曼露结婚后,坐小车子穿貂皮回家,有点衣锦还乡的味道,此乃她的骄傲。因是曼桢的姐姐,世钧不免多看了一眼,无非是位中年妇人。曼露的年龄只比曼桢大三岁,这十年的风尘岁月是极其残酷,催人老的,与实际年龄相去甚远。她自己都疑惑,变得如此厉害?而曼桢依旧是个娴静纯真勇敢的青春女子。三岁,已隔着漫长的人生冬季。张爱玲执笔含蓄。曼露坐小车子,穿裘皮,在世钧眼里不算什么,他家本是开皮货店的,也有车夫。那种生活,是他尽量要甩开,而非要争取的。
而曼露觉得,世钧那双眼睛挺坏的,直往她身上溜。这个“溜”字,轻薄挑逗,极传神。无非反映两点:一,曼露过分自恋,相信自己的魅力;二,天下男人在其眼中都一样,也符合欢场女人的口吻与想法。溜,有贼眉鼠眼之意,贼,即偷。
所以每个人皆有自己的人生定位及臆想剧本,自己亦是井底之蛙。
为此曼露碰了更大的壁。她以为豫瑾因爱她,十年荒芜,一直未娶,即便喜欢曼桢,也是源于曼桢长得像她。所以在豫槿要走的当天,特意穿了件紫色旗袍赶回家,幽幽地站在豫瑾面前,导致豫瑾像见了鬼,不得不赶快逃离,且把两人往昔情意一笔勾销。这便是现实,两种审美路径。
曼露以为祝鸿才,有钱即为成功人士。说白了祝鸿才就一嫖客加暴发户。在性上,不可能只有曼露。曼露婚后吃醋,想用妹妹吊住他的胃口,本就浅薄幼稚。
在顾太太眼里,祝鸿才这样有钱,姐妹共侍一夫未尝不可,并没太委屈曼桢。顾太太眼里的女人也都一样,无非结婚生子,找个有钱人,终其一生。顾老太太,更是在豫瑾面前一顿夸耀,曼露嫁得如何好,成为她晚年所遇最得意之事。
作者写了两种价值观对冲,起杠杆作用的依旧是钱。
曼桢旨在精神培养,曼露重在皮肉建设,虽无奈,却是分野所在。皮肉必然衰老,精神愈发明亮。
而在曼桢眼里,祝鸿才不过是个油头粉脸、喷着浓烈香水的油腻男。世钧这种新青年,连一鹏那样的贵公子,都不屑,何况祝鸿才这种暴发户?实乃两股道,两种价值观,新旧文明的对决。只是世钧的好,不被世人所知,他的温良醇厚,真诚低调,没被金钱拘囿熏染的个性,是黑夜里的金子。作为贵公子,他从没嫌弃顾家寒酸,哪怕顾太太、顾老太太怠慢于他;也没因曼桢的姐姐是妓女,而退缩。他喜欢的是老百姓温柔的日常,情之需要。见惯了有钱人的哀怨陈腐,想走一条全新的道路,怎奈依旧支离破碎。
曼露是为钱牺牲的,所以知道钱的好,钱是她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她用色去赚钱,钱色成了她致命的咽喉与伤痛。她的人生是酸性的,翻滚在人肉世界的波涛中,与那些人鬼混,势必把自己变成那些人。
顾先生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家,曼露一直行使着母亲的责任。她替母亲顾太太抛头露面,像只袋鼠,带着全家。包括这处房产,是她原来同居客人顶下的。她那时尚鲜艳,别人肯花钱。现实是残酷的,她只能不停地做,否则全家何如?张爱玲恰巧写出了这种人生无奈与悲凉渺茫。即便后来曼露结婚,给尚不宽裕的祝鸿才开出的条件是负担一家三代的费用。只是这个家,已怕她的连累。
所以即便她构陷妹妹,她的母亲都不能震怒激动,讨要道理,而是最后与其合谋,如何欺瞒老太太和弟弟们。
人以群分,豫瑾、淑惠、世钧、曼桢属同一类人,代表新的、时尚风气的先行者,是进步的。余下之人,尽管阶层不同,依旧固化在旧的世界里。
曼桢究其一生,始终没走出原生家庭。从反抗逃离,孑然一身,到后来为孩子嫁给落魄的祝鸿才,照顾母亲顾太太终老,看着他们在灯影里打牌,觉其是两个世界。一直到离婚,自己属于自己,真是漫长而曲折。且极具讽刺,伟民并没出国,亦不能养老,给顾太太重男轻女的思想,狠狠打了一记耳光。
一个作家的小说,大多复活自身记忆。钱,张爱玲亦知其好,在香港求学期间,安竹斯先生曾私人给她一笔奖学金,内里有破烂的五元一元的纸票,她觉得是世上最值钱的钱,却被她母亲轻轻输掉。旧的票子是暖的,带着人的温度。也就是那次,张爱玲对其母很失望,有了更深的心理芥蒂。
关于曼露旗袍上那黑隐隐的五个手印,也非空穴来风。其母黄逸梵出国后,父亲的姨太太常带着幼小的张爱玲去妓院,与往昔姐妹厮混。张爱玲自小心思细密,于那些红香鬓影,早以窥探到五个黑隐隐的手印,且烙进童真脑海,遂嫁接过来。
细节成全美,成全了整篇文字。这个美,非单纯之美,而是一篇文的出其不意,大省之处。省,乃省略,亦醒悟,兼而概括延伸。
五
张爱玲这种毫不起眼的大手笔,在其小说中,比比皆是。几个字,往往隐藏着千军万马。写自己如是,《小团圆》里第二章,她在香港求学,日本人打来。
“‘我差点炸死了,一个炸弹落在对街。’她脑子里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告诉人。告诉谁?难道还是韩妈?楚娣向来淡淡的,也不会当桩事。蕊秋她根本没想起。比比反正永远是快乐的,她死了也是一样。差点炸死了,都没人可告诉,她若有所失。”
此乃书中原话,盛九莉说的,即现实版张爱玲的话语。几句话暴露了张爱玲的人际,她能来往的,比较亲的,或比较重要的只此四人,足以代表她的前半生。
韩妈,她自小的老仆,待她极好。她姑妈曾吃醋,韩妈对我们都不如对小莉。韩妈很多时弥补着张爱玲母亲的角色,张爱玲可以揪着她脖颈松懈的皮肉、画她微阖的大眼睛,很有点佛造像的意味。她与韩妈没隔阂,曾想赚很多的钱,把韩妈救出来。而于自己的母亲蕊秋,也就是黄逸梵,连过马路牵手都觉得是一把细竹管横七竖八夹在自己手上。没肉,也没温暖,这种肉体距离,也代表心理距离。
一个贵族小姐,最亲的却是一个和自己毫无血缘的老妈子,不能说不可怜。楚娣是九莉的姑姑,也是其母好友,她妈妈出国后,曾一度拜托楚娣照顾九莉,所以张爱玲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到1952年离开大陆,楚娣与之相处最久。但楚娣独立淡然,九莉并非所有话都能与之说。
蕊秋,九莉的母亲,即黄逸梵。在九莉眼里是高高在上,飘忽不定的,一会飞到这,一会飞到那。于其生命,常常缺席。血缘代表牵扯,但非代表亲密,所以九莉说,就没想起。
她崇拜迷恋母亲,又鄙薄她。尤其那次打牌输掉她奖学金之后,心也就凉了。
而比比是个乐天派,原型是张爱玲的好友冉缨。她是不怕死的,敌机轰炸,尚能在楼顶房间,边洗澡边泼水唱歌,与她说等于白说。
当九莉面临生死大事时,她的惊恐没人可说,能听她说的韩妈已归回自己的世界,生死如何并不知晓。
她是孤独的,生死都没人关心,至少她这样认为。她的父亲,因打她拘禁她,而彻底被她排除。弟弟也不在这张名单里,张爱玲记仇,发现弟弟给二哥哥,他们的一个表哥写信,说她玷污门楣后,也就生分了。她本心疼弟弟,可情感又是那么复杂,气他的不争气、不上进、不独立。
偌大世界,只剩下孤零零的自己,所以她更需要爱。当胡兰成这个温存倜傥儒雅的男士找上门时,一下子就沦陷了。
《小团圆》即仿真版的张爱玲自传,毫不走样的张爱玲人生图谱,只是内里人物易了名。胡兰成的文,张爱玲见胡之前,一定看过;胡兰成其人,也不会不知。世人念念不忘,她和胡的因果情缘,其实只不过两三载时光。很多人说,是张爱玲恋父情结所致。此观点还是稍嫌偏颇。张爱玲与社会鲜有来往,亲戚男性,几乎都是遗少,熏染很深的旧习气,包括她的弟弟,即便穿上西装都不属于新青年。她逃离,需要一种既陌生又亲切的东西,而胡的审美以及对文学的敏锐与之相契,没违和感,故擦出火花。
胡兰成逃亡,她与胡陷入情感危机,有了小说里的燕山,即桑弧。桑弧并不老,恋父情结不攻自破。她与桑弧的恋情有淅淅沥沥的小雨及黄昏之美,迷离,秘而不宣。只是那时她还顶着汉奸妾的名声,桑弧不能娶她,她也没有想嫁。至于后来的赖雅,也只是精神寒夜里的毛毯。
张爱玲1952年离开大陆时三十二岁,只肉体出了国。心依旧留在上海,笔亦踯躅上海。后来的文,皆祭奠,翻涌着寂寞的乡愁。空间对其毫无意义,只是庇身场所。
有人说她完全可以融入美国社会,写点当地事物。那便不是张爱玲,她取悦的唯自心,热爱所熟知的生活。骨子里依然中国,读者的定位依旧是中国人。
朋友曾与我讨论,张爱玲的小说与毛姆小说,孰优孰劣。其实,没可比性,显然毛姆的小说走得更远一些。中国人侧重人性,外国人侧重情怀。情怀是有共性的,读者因情怀而震撼;人性却是凉薄刻骨的,深谙本民族事物。
毛姆,张爱玲喜欢的一位作家。
张爱玲自卑也骄傲,与同时代的林徽因相比。林徽因有自己的小文化交际圈,即贝多芬俱乐部。这种事,张爱玲绝对不会做。张爱玲的自我与林徽因的自我不同。林徽因在交际中得到快乐;张爱玲在文字中游刃有余,获取满足。
世俗即不自由,张爱玲,最大化在寻找自由。所谓的自由,乃精神产物。为名为利皆非自由,入乡随俗,即捆绑,所以她尽量摆脱俗世。故其作品纯粹,没丝毫目的性,属裸体社会写真。中国人中庸务实,刀刀是血,张爱玲也不例外,小说虽冷峻,亦空灵。虚是最好的东西,像画画,意到笔不到。
所谓大手笔,便是给读者留下一大片锦绣天空。虚,乃波纹,举重若轻的多边形人生。
——张爱玲美学风格的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