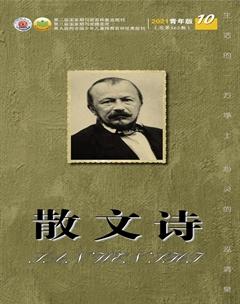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世界
丁方 高海军 汪家明 孙小宁 赵雪芹 冷冰川 王小川



丁 方:巴荒的作品不是简单的一个画家靠着一种感觉,对一种物象和色彩的感觉,实际上它是文学+思考+哲思+生命的体验,用俗话说,是用肉身丈量大地,经过沉淀和糅合之后再进行的创作。
高海军:理想主义很重要,要有情怀,有理想,这是非常让人尊重的,因为艺术是很崇高的,也是辛苦的,画画儿真是又苦又累又孤独的事。
巴荒的画关注人和自然、人和神,关注宗教、神性,以及和大地的关系,在心灵里面,潜意识里可能也有这种天然的激荡。
不管哪个民族,哪个时代,生命都是一样的,都有审美的、共通的、最美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普遍的标准,是我们的价值,而不是形式多变、多样。去掉表面那些浮躁,怎么关注人的存在,关注人的社会价值,这才是最重要的。
孙小宁: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看到这样一种形态和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自然就去采访了她。从回忆的角度,她那时候住在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旁边的宿舍,非常小。我就跟她每次都面对面地沟通,我就觉得好像是坐在高原上一样,周围的东西好像不存在,只有这么一个人跟我讲西藏的事情。我一直想写她,也陆续地写过,但是我觉得,她所有说的这个点,我都能感觉到,但是,当时的心力不一定能够传达,一直就是这样的存在。
巴荒特别难得,在大家都轻飘飘的时候,这么一个有重量感的灵魂,有时候它会挤压你。因为你会觉得,那样走可能更轻松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个撞击,然后说,不行,好像对于自己的灵魂来说,应该自己去汲取一点儿什么,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下去。我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的召唤。说白了,每个人灵魂里面的这些东西都会在成长的路上碰到,你对宗教的思索,你对人文历史的探求,这些都会反馈到你自己对自己灵魂的互相映照。现在我觉得,肯定比我当年能够离她近了一些,但是,也不一定说怎么个近法儿。从细节上来说,这个人让我感到特别真切,她走得多远,你只要进到这个场,那些东西就都会复活,所以,我觉得特别珍贵。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人走在你的前面,让你永远可以看着她,她就是这么一个珍贵的存在。
丁 方:巴荒画肖像的时候考虑的问题非常多,我是从我的内心来反推的。她在考虑肖像永恒性的问题,文艺复兴的肖像很明显地能看出不是画一个人此时此地的具象,而是想把此时此地的肉身放在永恒的空间里,让以后的人再看到后都感觉到是当代的,又是穿越时空的。在这方面,她会花很多心思来组织画面,包括色彩的组织、造型的组织。比如说这个封面的形象,这个脸就会让人想到这张脸和当地的地貌的构造是同构的,怎么表现?这种陡峭的线条,就跟西藏的很多山是一样的,是同构的,没有很多植被,刀削斧劈。这就牵扯到一个很普遍的东西,藏族在真正有穿透性眼光的艺术家心中,人与山是同构的,内在构造是一样的,你画山就是畫人,画人就是画山。这样的话,把有血肉之躯的人与山同构的话,就是永恒了,所以,她在这里开辟出了一个新的绘画语言的探索。
孙小宁:人就是跟自己的品性特质相关,我跟冰川老师交往就会觉得很轻松,我跟巴荒交往会觉得有一个东西压过来,我必须要接着,这也激发了我的使命感,我必须接着,就是这种感觉。这是不一样的,她有一种生命特质,你跟她的要求不太一样,你想让她轻松是不行的。每个人不一样,每个艺术家也不一样。
王小川:小姨对我来讲,她在美术圈子里是一个有独立个性的人,我说你干嘛要有独立个性,你干嘛不跟别人合作?你不能去说服这种事情,在很长时间里都有这样一种冲突性。
后来慢慢地,自己也开始变化了。
这种优秀的东西不是从外在找的,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可变得更加的重要。因此,我慢慢开始往回退,开始寻求自己内心的精神力量。这种情况下,我会理解小姨了,她把自己的感受看得非常重,而不是强求跟自己连接,被外部的商业环境,被别人的主观意见吞噬掉,这样,就会有内心的原动力量。因此,我就开始往内看。
我觉得,跟艺术能媲美的是科学性的东西。科学家在佛教的认知里也有他的位置,但是肯定不够,这些连接里面若没有精神性的东西同样也会被吞噬掉。因此,我们追求自在,追求尽可能走向天人合一,把自己跟这个世界融合到一块儿。小姨今天谈的是自己的美术简史,能与自己之前的东西贯穿到一块儿,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这样离上帝的角度就更近一点了。所以,这种精神滋养对我依然会有,而且比原来更加和谐了。
汪家明:破坏也是一种美学思想,美学思想有各种各样的。说到出版,搞设计也是这样,现代网格设计得很标准,修改的时候就要破坏,就要出了网格,整个设计就生动起来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先是完美,再是破坏,也可以先是破坏,后是完美,总而言之,破坏的作用是很大的,它会在你画不下去的时候,最后一破坏,就出来了。
冷冰川:一个艺术家就是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