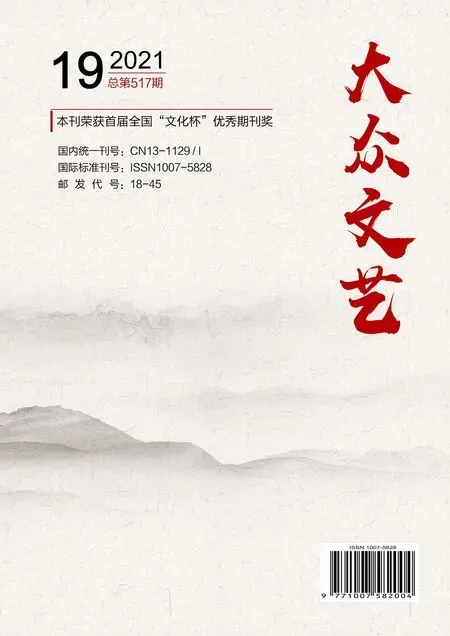侯孝贤诗化电影风格刍议
程玉悦
(山东工程职业技术大学,山东济南 250200)
侯孝贤,1947年4月8日生于广州梅县,不到一岁时,举家迁到台湾。其父曾任广东梅县教育局局长,办过报,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对他影响深远。原本打算在台湾住几年就回大陆的父母亲和祖母先后客死台湾,给并当时未成年的侯孝贤留下终生的眷恋与遗憾,形成了其电影中弥漫着的漂泊意识和乡愁情节。这样的经历让这个年轻人过早地亲历了生离死别和生活艰辛,也理解了生命卑微、世事无常;这经历也成了他电影的根本叙事动力。侯孝贤从小受父亲影响喜欢读书,特别喜欢武侠小说和线装杂书,也看布袋戏和皮影戏,受戏曲浸染很深,武侠小说和古典戏曲中劫富济贫、忠孝节义等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无形中深入侯孝贤的内心,形成了他质朴温厚的性格、任侠仗义的风骨;侯孝贤也大量阅读了台湾的言情小说、黄春明、陈映真等人较关注现实的作品,以及鲁迅、张爱玲的作品;后来又在朱天文的推荐下,读沈从文的作品,深为感动,形成了他冷静客观的现实视角,清新自然的乡土情怀,沉潜悠远的古典诗情。在服兵役期间,看了英国影片《十字路口》,从此立志以电影为终身事业。1969年考入台北国立艺术学校电影及剧戏系,1972年毕业,做了八个月计算器推销员之后到李行导演剧组做场记,从此走上电影道路。
似乎由于过早经历了生离死别而尤为早熟,从1983年的《风柜来的人》起,侯孝贤采用长镜头、大远景、固定机位的方式,拍摄一群年轻人的躁动、迷惘与成长,就形成了他“冷眼看生死”的超脱眼光。这标志着他个人风格的形成,虽然后来一度被称作“票房毒药”,但侯孝贤始终坚持、完善自己的电影风格。如果说固定机位、景深镜头、远景,使侯孝贤形成了“静、隔、远”的典型镜像风格,那么比兴修辞和散文化结构,就形成了他的诗化电影节奏和作者叙事特质。
一、比兴修辞与电影诗
侯孝贤的电影具有中国传统山水田园诗式浓厚的诗情,宁静、淡远。可说是“寄至味于简古,发纤秾于毫末”的电影诗,这不仅是侯孝贤电影中国画般的摄影风格所致,而且是因为他的“电影语法是电影诗”,就像阿城所说的那样。侯孝贤善于运用长镜头,但他并不是把镜头绝对静止地放在一个视点,而是让镜头运动于相同或相似的场景,获得一种古典诗歌般的和谐的节奏和温雅的韵律。《童年往事》中有一段经典的镜头:先是一个门廊甬道中固定机位的远景,三四个老年人在阳光下慵懒安静地分坐在两边的长椅上养神,间或地说上几句家常话,几个青年从镜外跑着打将进来,前面跑,后面追,老人似乎习以为常,丝毫不为所动。镜头一转便又是其他的情景了,可后来的叙事中又间或地出现同一个机位,同样的景别和构图,也依然有老人在那廊道里歇息,只是季节与时令有了变幻,人也不一样了——有些老人已经故去。如果说侯孝贤的一部电影是一首诗歌的话,那么一组场景的叙述便可看作一个有着音乐节奏的诗歌小节,而每一个具有同样机位和节奏的长镜头便是一个与其他小节具有同样韵脚的诗句。参照《诗经·小雅》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看得更清楚。
昔我往兮,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诗经·采薇》
昔我往兮,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涂。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诗经·出车》
四字的句式,循环往复的结构让诗句充满韵律与音乐的形式美感。第一节有“昔我往兮,杨柳依依”的诗句,第二节同样的句式结构中又一次出现诗句“昔我往兮”,让诗句有了复调一样的音乐效果,也渐渐形成了一个让人更易于接受的程式化节奏,之后接着出现了不同于第一节“杨柳依依”的“黍稷方华”,既与前面的句式保持了形式的和谐,又有了内容上色彩的更新。侯孝贤的电影之所以具有温文尔雅的诗意,正是源于诗化的镜头语言与镜头语言循环往复的组合方式,即是说侯孝贤电影语言的语法结构是比兴式的,具有某种音乐性的节奏和程式化的形式意味。其电影中先后重复出现的场景具有与《诗经》中反复出现的诗句一样的意义,负责把场景组织起来的镜头运动则与诗句韵律化的组合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昔往”与“今来”的辗转回环中,“杨柳依依”与“雨雪霏霏”的变化,透出的不仅仅是情景的变幻,更是季节的流转、光阴的流逝——人鲜活的生命在时间流程中感知着天地自然的气息起伏、音色变化、哀欢冷暖。天人同构、物我同一的比兴修辞让诗经历经千年之久,依然鲜活地传达着那种一咏三叹、曲折委婉而又天真活泼的深情。
侯孝贤电影隽永委婉的风格便是得益于诗经式的比兴修辞。《童年往事》中,父亲因为头部被棒球击中而丧失自理能力,整日坐在门口躺椅上,面无表情、目光冷淡。电影常有意无意地插入这个镜头,让躺椅上的父亲作为每日平凡而琐屑的生活背景而存在。没有任何解说,而父爱缺失的疼痛与母亲一人支撑家庭生活的艰辛已经无声地溢满画面。直到有一天,电影中第一次出现门口躺椅上没有了父亲的空镜头,只有一把椅子,在风中微微摇动。与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达到的术艺术一样,昔往今来的时光流逝中,“我”已经渐渐长大,母亲已慢慢衰老,躺椅还在,而久病的父亲终于离去了。日常家庭生活相似场景的积累和细节变化的微妙暗示,以比兴的修辞方式将物是人非的悲哀、亲人离去的悲痛与生命的平凡脆弱委婉、深沉地表达出来。
二、散文化结构与作家电影特质
侯孝贤拒斥好莱坞戏剧化的、公式化的电影情节。作为一种文化商品,好莱坞电影既无关于现实,也无关于历史悲情、世道人心,但对于侯孝贤而言,这种言说似乎成了一种道德义务、一种文化心理需求。他充分汲取了沈从文的精神气质,从大的历史视野去看待个体生命的浮沉,生命日常的点点滴滴,就不比重大的历史时刻不重要。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悲欢离合的人间戏剧,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无非就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因此,一家人围在饭桌前吃饭,成了侯孝贤最喜欢拍摄的家庭生活场景。
关于自己一部电影——《最好的时光》的创作动机,侯孝贤说“生命中有许多吉光片羽,无从名之,难以归类,也不能构成什么重要意义,但它们就是在我心中萦绕不去。”侯孝贤甚至说这些难以归类、无以名之的生命片段,成了他的义务,成了他必须加以偿还的情感。这一段话不仅说明了侯孝贤的创作动机,也透露了他的电影特质和风格追求。他的电影并不追求戏剧性,表现“将平淡无奇的片段切除后的生活”(希区柯克语)。在侯导看来,生命中“无从名之,难以归类”的吉光片羽一样弥足珍贵,平淡并不比戏剧性的时刻不重要,这也是中国人对于生活与生命的朴素理解:平平淡淡才是真。这样的生命体认与对生命中吉光片羽的尊重,决定了侯孝贤采取散文化的叙事结构,才能更为自由舒展地表达出他对生命惊鸿一瞥的理解与感悟。侯孝贤认为,西方人逻辑性强,更强调电影情节的戏剧化,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自古希腊悲剧以来的叙事传统,但中国人则不同,我们拥有的是另外一种抒情的诗歌传统。正是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侯孝贤才采取自己更为擅长的散文化叙事方式。散文化的叙事方式一方面让他的电影充满了自由灵动的诗意,另一方面让电影失去了情节吸引力和戏剧张力,电影的意义不是情景结构和叙事符号所定义好了的,而是需要观众本人深入电影情境和角色内心去体会领悟。这让侯导的电影在叙事上失去了引人入胜的戏剧性效果,却从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内敛含蓄的意味与沉潜的省思深度。《风柜来的人》中几个成长中的青年常常打架,坐在海边发呆,也会在海边肆无忌惮地快乐舞蹈,即使海浪打湿衣衫也在所不惜。与侯孝贤来说,并不是什么特别伟大的意义才促使他拍一部电影,一段记忆,一份感动,一缕情绪足矣。关于《悲情城市》的创作动机,侯孝贤说他是受到听到的歌曲的触动,“想把台湾歌那种江湖气、艳情、浪漫、土流氓和日本味,又充满血气方刚的味道拍出来”。
并不是出于对所谓的“意义”的探寻,对于电影形式的热衷,也不是出于商业上的考虑,侯孝贤的创作动机中占首要地位的是萦绕在他心中迟迟不去的,不吐不快的感情、体悟与生命认知,他甚至认为这是他所亏欠而必须偿还的。这电影不是俯就于市场或其他,而首先是对于自己内心的尊重,这就注定了侯孝贤电影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与作家电影的特质。
三、结语
与其说侯孝贤在拍电影,不如说侯孝贤是用电影的方式书写关于自己生命体悟的诗情散文,或者说侯孝贤在拍迥异于西方戏剧电影的另一种影片,一种渗透了东方式生命沉思的作家电影。电影没有明确地讲一个善恶分明、节奏明快的故事,而是靠点点滴滴的细节积攒,汇成涓涓而淌的情感溪流,靠散乱的情节片段连绵成历史的天空。
注释:
①刘昌奇,程玉悦.历史的悲情与永恒的乡愁——侯孝贤电影的美学意蕴[J].艺苑,2015(4):90-92.
②刘昌奇,程玉悦.静、隔、远:侯孝贤电影镜像语言分析[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36-138.
③阿城.且说侯孝贤[J].今天,1992(2):21-22.
④姜宝龙.专访侯孝贤:电影是一种乡愁[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7(6):56-60.
⑤孟洪峰.侯孝贤风格论[J].当代电影,1993(1):66-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