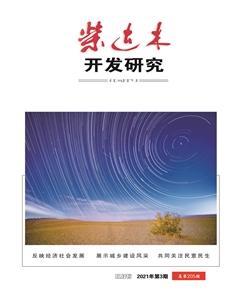犹记当年行路难
20世纪70年代,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当通讯干事更是少不了跑基层。因为习以为常,所以并不觉得下乡有多么难熬。一说下乡,便提上牙具袋立马走人。其间,让人无奈、让人郁闷的事当然也有,但这些不是基层生活的难以适应,而是行路的艰难。
海西州有32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有些省份一二个省的面积之和。在如此广袤的地域中,下去走走,不可能都是安步当车,也不可能是骑自行车。在青藏铁路西格段通车之前,汽车应该说是这里最快捷、最理想的交通工具了。可汽车却不是谁想坐就能坐的。那个时候,无论县、镇还是州上,都只有少得可怜的几辆北京吉普,州、县的领导出行,尚且不能百分之百地保障車辆,像我这样的一般干部,就更不敢心存奢望了。通客运班车的地方倒还好说,买票乘车就是了。难办的是,很多地方索性不通班车。还有一些地方,像茶卡、希里沟、察汗乌苏、香日德等地,虽然也通班车,但却只有过往车辆,而没有始发车。到这些地方,要想乘班车,那就得先看看车上有没有空位(因乘客下车而空缺出来的位置)。直到现在,我的脑海中还会常常叠印出这样一组画面:繁星满天,四野寂静,寒风瑟瑟,我裹着一件厚重的老羊皮大衣,从乌兰、都兰的县政府招待所或者茶卡、香日德旅社,匆匆忙忙赶往运输站。运输站营业室的窗口紧闭着,待你好不容易敲开一点缝,睡眼惺忪的营业员便很不耐烦地冲着你说:“没座位了,明天再说。”既然班车无望,那就只好坐在公路边上,眼巴巴地等待过往的货车,希望师傅能顺路捎带自己一程(由于客运运输能力严重不足,那时候,货车带人的现象相当普遍)。一见有汽车过来,就连忙站起来招手。可车上的司机就像没看见你似的,一往无前地把车开走了,留给你的是一股滚滚烟尘和难以言喻的失落。一辆车过去了,又一辆车过去了,而你依旧还在老地方待着。继续等下去吧,希望非常渺茫。下决心“撤退”吧,又怕错过了万一到来的机会。一直等到人倦了,只好又怏怏然地返回招待所或旅社。第二天,还得如此这般地重复着那种枯燥乏味的等待和守望。在一连几天都不能开拔的情况下,我们甚至不得不使用这样一个“绝招”——让一些我们采访过的女知青帮助我们挡车。她们“招摇地”站在公路边上,我们则隐蔽在公路涵洞等一些不显眼的地方。车果然停下来了,我们飞也似的跑过去,当师傅知道她们原来是在为我们挡车的时候,既不好意思拒载,又不肯让我们白占便宜,于是就气哼哼地命令我们坐到汽车的货厢里去(他的驾驶室里本来也是可以坐的)。
如果只是自己等,也就罢了,问题在于,有些时候,你还陪着客人,让客人也跟着自己遭罪,心里就特别过意不去。1975年9月,新华社青海分社记者黄昌禄到海西采访,州委宣传部让我陪同。黄老师是坐着班车从西宁来到德令哈的,我和他从德令哈到茶卡(因为要采访茶卡盐厂)也是坐班车,一路还算顺利,可再从茶卡到都兰和格尔木,就特别不顺了。在茶卡,我们等了一天,才颇费周折地通过茶卡交通监理站找到了一辆便车。在都兰的运输站盘桓了一天之后,我有点着急了,就去找县委办公室的领导,希望他们能为我们提供帮助,但办公室的领导表示爱莫能助,因为县上仅有的几辆车都出去了。回到招待所,看见院子里停着两辆挂有军队牌照的吉普车,接着又碰见海西军分区的一位我认识的参谋,知道这车是他们的,我的眼前顿时一亮,心想:有门,可以走了。但当我说明情况后,这位参谋却说:我们是陪同首长下来检查工作的,车上无法再带人了。还说什么呢?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我不能不仰天长叹了。就这样,我们不得不在都兰又无谓地消耗了三天。黄昌禄先生堪称名记者,在少数民族题材报道方面卓有建树。他所采写的通讯《苦聪人有了太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都被列为高等院校新闻专业的教材。对于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师,作为东道主的我却不能提供起码的方便,内心深感愧疚。尽管黄老师一再说:“没关系,基层就这么个条件。”但他越是这样说,我就越发觉得自己无能。
现在回过头来看,货车司机一般不愿带人,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有他的任务,为啥非要多此一举呢?再说,从安全的角度考虑,带个人也未必就好。
能在驾驶室里占据一席之地,已属幸运。还有不少时候,因为驾驶室里已经满员,就不得不委屈自己,坐到卡车的货厢里去。记得那是1971年的12月上旬,德令哈市以西的绿草山煤矿发生了事故,矿上在给州革委会的报告中说,这是一桩“舍身救人的英雄壮举”。州上恰恰也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需要这样“洋溢着共产主义精神”的先进典型,政治部宣传组遂派我和德令哈广播站的编辑王文泸去绿草山煤矿采访。我们接到任务后,毫不迟疑地赶到了德令哈运输站。正在运输站给汽车加油的青海石油局的几位女司机(她们一行有四辆车),得知我们有公务在身,刻不容缓,就慷慨地答应带我们到绿草山。这几位师傅和蔼可亲、善解人意,令我和王文泸大为感动。鉴于她们的驾驶室里已经满员了,我们便主动提出到没有篷布的货厢里去坐。车上拉着水泥,有些水泥袋子因磨损而有了裂缝,风一吹,水泥粉末便扑扑簌簌地飞扬开来。12月上旬,海西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那一天又偏偏刮着五六级大风,车一走动起来,风势更加猛烈,冻得人不住地打哆嗦。穿在身上的皮大衣,感觉就跟一层纱布似的,全然失去了它的御寒能力。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就按照与师傅事先的约定,在驾驶室的顶盖上用力敲击几下,让师傅把车停下来,然后下车,在公路边上跑一阵子。待身体增加了一点热量之后,再回到车上。就这样,在不到200公里的行程中,我们竟下车做过了三次短跑运动。那一天,要不是几位师傅不嫌麻烦,多次停车,真不知我们会被冻成何等模样!到了绿草山煤矿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仍然觉得浑身发冷,因而就一股劲地给炉子里加煤,希望那熊熊燃烧着的炉火烧得旺些再旺些……
在不通汽车的地方,或者是实在搭不上车的情况下,就只有步行和骑马了。不要说像乌兰县戈壁公社、蓄集公社这些离州上不算太远的地方,我们可以不在话下地徒步往返,就连比这更长的路,我也走过不止三五次。有一年夏天,我在都兰县采访。县上的同志为我提供了一个巴隆公社的采访线索。我搭乘一辆便车到达公路边上的伊克高里农场。一打问才知道,我要去的巴隆公社塔文托洛哈大队离这里还有几十公里呢,那里不通汽车。在问清道路之后,我毅然决定徒步前往。没想到,这么空旷偏僻的地方,竟然会有那么多又大又凶的蚊子。一见有人走来,蚊子便疯狂地围拢过来,在你的头上盘旋,在你的耳边嗡嗡,弄得你烦不胜烦,一时没了脾气。不得已,我只好把外衣脱下来,蒙在头上,以抵御蚊子的侵袭。差不多走了一天,才到达塔文托洛哈。好在社会治安状况很好,一个人走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倒是没有多少安全方面的忧虑。要是猛乍乍跳出几个拦路抢劫的歹徒,那我可就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这一切,在今天“食有鱼,出有车”的人们看来,也许不可思议。只有那些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何况,当年的行路难,还不仅仅是“出无车”的问题。同时,还表现在出行风险系数较大这一点上。路况、车况普遍差,运输力又那么紧张,加上环境、气候等多种因素制约,不危险才怪呢!我亲身经历的风险,记忆深刻的有这样几次:
1975年9月,我从都兰县乘班车到格尔木市采访。车过诺木洪之后,我忽然发现高速行驶中的客车有点偏离了方向,便下意识地抓紧了前面座位靠背上的扶手。说时迟,那时快,在我还来不及进一步判断吉凶的时候,轿子车已经离开了公路,向湍急的诺木洪河俯冲过去。司机发现情况不妙,赶忙来了一个急刹车。但因刹得过猛,车子一跳老高,立时震碎了几块窗玻璃,并把几个乘客从窗口甩了出去。万幸的是,客车此时恰好进入河滩地段,已经倒下去的轿车,被河滩里的沙子淤住了车轮,因而没有彻底倾覆,车上乘客的生命这才得以保全(甩出去的人中有的伤势很重,命悬一线)。由于我的右手在扶手上抓得太紧,车一倾斜,胳膊便被严重扭伤,此后的一个多月就只能吊着绷带生活。
1995年10月,我和王文泸在尕海电厂采访。星期六,我们回家换洗衣服。第二天准备再去电厂的时候,发现厂里到德令哈来接人的一辆大卡车上挤得满满当当的,再要硬挤上去,似乎很难有立足之地。这样一来,我们决定星期一再去。回到家里没多久,就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我们想上而没有上的那辆车在快到尕海时翻了,当场死了六个人,受伤的更多。我们不得不为自己的英明抉择而庆幸。
1983年10月,我和青海日报的记者邢秀玲、州文联的作家王泽群,陪同《文汇报·笔会》副刊的主编徐开垒先生去格尔木市采访。快到大柴旦的时候,王泽群提议:“我们就从饮马峡穿过去吧,这样走路近。”我想也没想就同意了,既然有近路,何必“舍近求远”呢?饮马峡的路實际上并不好走,峡里满是大大小小的石头,车子颠簸不说,有些石头,不费一番气力,也是很难绕过去的。最大的问题倒不在饮马峡,而是出了饮马峡之后。吉普车从峡口出来不久,就进入了察尔汗盐湖。我和泽群其时已在海西州工作了十几年,我们都认为自己对察尔汗盐湖并不陌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自以为熟悉的盐湖上,我们和海西州委车班派出的司机统统迷路了。往前走一阵,觉得不对,便又折返回来,再走一阵,还是觉得不对,遂又回头。反正,任你怎么走,就是走不到公路上。眼前,只有茫茫苍苍的盐湖,只有像拖拉机翻耕过的一大片漫无边际的土地(那是盐湖在长期的风吹日晒下形成的一层厚厚的盐盖),而没有任何特征性的标志,没有任何可以唤起人记忆的参照物。天哪,察尔汗盐湖有5800平方公里之大,照这样转悠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得出去呢?油箱里的油消耗完了怎么办?到了天黑还找不到公路又怎么办?一时间,我们几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慌了起来,我们深深感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弱势。司机更是紧张得脸色煞白,一头冷汗。在这之前,媒体上刚好披露了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一想到彭加木,我的一颗心不由得又提了起来,脉搏的跳动也像加快了许多。难道我们也要变成彭加木,失踪在察尔汗盐湖?正当我们茫然而又无奈地在盐湖上瞎转的时候(已经转了几个小时),一个雷达站的小战士竟然鬼使神差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是他把我们从察尔汗盐湖这座迷宫里引领出来。车一上公路,我们都禁不住潸然泪下。
往事随着岁月的推移已然远去,但每每回想起那些已逝的时光,总不免让人动容!
(作者简介:王贵如,原海西州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