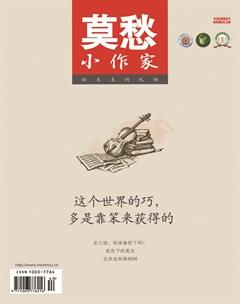偶然想起的人
吃过午饭,我坐在办公桌前刷手机,看三个扛煤的老头儿拍的抖音。三个老头儿一脸沧桑,皱纹里填满了煤灰,说起台词就像吼叫一样,让人忍俊不禁。这时我突然想起来,老三大爷好像没有了。究竟是不是没有了,怎么没有的,记忆都有些模糊。
老三大爷一直就是老头儿的模样。有天,家里突然来了客人,嗓门特别高,笑声也特别响亮,好像半空隐隐的雷声。这是我对老三大爷的第一印象。他推着一辆自行车,后座上绑着一个大竹篮,里面有“啾啾”的叫声,原来是三只可爱的鹅苗。不知道老三大爷为什么给我家送来鹅苗,后来才知道他做事从来都没有因果关系,突然而令人诧异。反正鹅苗很快在我家长成了大鹅,既能看家,又能下蛋,成为家人的宠物。
老三大爷算是父亲的同事。父亲在医院里是司炉工,老三大爷是勤杂工,平时打扫卫生,冬季到锅炉房临时帮忙运煤。也许是单身汉的缘故,他乐意躲在锅炉房那间局促的休息室里消磨时光。破旧的电视机24小时不停播放,他就歪在床上看电视或者打盹。而大多数时间,他都是在和人“吵架”,没有来由的,抬杠或者争吵。唯独对我,有着难得的温柔和耐心。
一次,我因为肚子痛,被父亲用自行车驮到了医院。父亲带着我见了医生,却查不出什么毛病。父亲去上班,我就在锅炉房的大院子里“探险”。遇见老三大爷,他笑着问:“你家‘哈尔滨呢?”“哈尔滨?”我一头雾水。他哈哈大笑,后来我知道这是他给父亲起的外号,父亲名字叫“斌”。“说肚子痛是不是不想上学?”他声音小了下来。“没有……”我臊红了脸。他又哈哈大笑起来。晚上,老三大爷不知从哪里带回来一大块牛肉,“给你们做牛肉面啊!”他高聲吼道。那晚的牛肉面什么滋味,我也忘却了。
上了高中后,我也来到了城里,去锅炉房找父亲要生活费时,常常碰到老三大爷。他越发苍老,头发稀疏地附在头皮上,好像寒风里的几根衰草。“小子,来要钱啊?可省着点花,你爹腰都累弯了。”他开玩笑般地嘱咐我。家里兄妹多,都在求学,重担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如果离发工资的时间还远,父亲就会动用另一个“小金库”,那是老三大爷让父亲替他代管的工资,也是默许父亲支用的。
老三大爷常常为杂物间里少了几个纸箱暴躁不已,却又因为听了几句顺耳的话,把整包的香烟扔给人家,甚至拉着人家去喝酒。父亲说他挣钱不要命,理由是:“非典”期间,医院的隔离病区收治发热病人和疑似病例,他主动报名去打扫卫生。锅炉房的同事对他的举动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我却认同一条,他是个胆子极大的人。
这天下班回到家,我想起午间的疑问,问了父亲老三大爷的状况,果然是故去了,是年前在医院的新冠病毒隔离病区里,打扫卫生时突发脑梗去世的。这次父亲没有说老三大爷要钱不要命,只是叹息他的突然离去,让人情感上难以接受。
“老三大爷享年多少岁?”我问父亲。
“大概六十五六岁吧,他的院长兄弟去年刚退休!”父亲回答我。
至今不知道老三大爷的真实姓名,“老三大爷”是他在家中排行为三而得名,还是另外有的绰号,不得而知。
时光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带走了一个人,因为他的平凡普通,很少会有人会记起吧,而我也是偶然想起的。
张海洋: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多家报刊发表有小说百余篇。
编辑 沈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