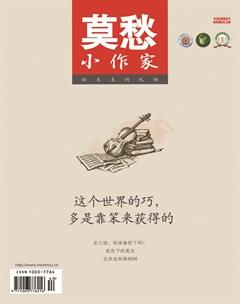流淌在心里的沙沟
1
粉娣说,等放暑假,她上海的姨娘要接她去玩几天,语气里满是得意与炫耀。我才不羡慕呢。上海算什么,暑假里,我要和爸爸妈妈坐帮船,去沙沟卖小猪。哗哗数着票子的爸爸,有求必应,吃的穿的玩的,可劲儿买。上海,远得如日出之后的一层薄雾,模糊地缩在东边,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整个青少年的记忆里,沙沟,才是我的天堂。
里下河洼地,交通不便,农民除了种地,主要副业是养猪。我的爸爸头脑活,擅长养猪。母猪一窝产下十几个小猪,他比照应我们还精心。三四个月后,小猪长到二三十斤,当苗猪出售。仔猪交易市场,我们顾河村没有,镇上也没有,县城边上有,可离我们老远老远,感觉跟天边的上海一样。邻近的沙沟就是约定俗成的我们顾河人的闹市。
在我心里,沙沟比县大,比市大,跟世界一样大,它容纳一切精彩,储蓄我对城市元素的所有向往。而今回想,那些精彩场景纷至沓来,争先恐后挤到笔端。
2
沙沟大得让我心慌。在家,妈妈是我最烦的人,可在沙沟街上,我攥着她的衣角,生怕走丢,回不了家。沙沟的石板街,不是江南的青石板,而是黄麻条石。里下河地区,只有黑得冒油的土,稍微有些硬度的,就是河底生姜状的石头蛋,学名“地骨”,爸爸罱河泥时经常有,可这算不上石头。真正的石头,只在课本上见过。沙沟的石板街,让我猜测它神秘的前尘往事:这些黄麻条石从哪里来?怎么来的?走过哪些车马?行过哪些人物?像庄稼一样生长在乡野的孩子,既无先生说古,更无书籍滋养,除了惊奇,依然是百思不解的迷惑。这些迷惑,有的至今还存着。
石板街上坑坑洼洼,两边商铺林立,农家生活所需应有尽有,馓子、桃酥,瓜秧、豆种,火叉、铁锹,烫头发的、做皮鞋的、卖唱片的、敲白铁皮的……几个月甚至半年赶一次集,爸妈把家用所需都要备齐。我不关心这些,就觉得麻团真甜,真香。沿街的店铺卖冰水,一个玻璃盒子里,一半黄色,一半橙色,上下喷涌,循环往复,玻璃上贴着红字:“冰水,一角一杯。”盯着翻腾不息的冰水,一不留神,麻团吃噎着了,那杯冰水妈妈不买不行。果真琼浆玉露啊,世上竟然有这么好喝的水。因为这杯水,什么时候想起,沙沟都是甜的。
爸爸非常宠孩子。妈妈的爱有些不一样。一条烟火尘俗的街,多少诱惑等着我啊:想捏个糖人,想买本小人书,想吃根紫甘蔗,想要件花衣裳……什么都想。爸爸无原则应承,妈妈很生气,凶爸爸:“你就喘吧!”日头下,爸爸晒得黑黑的脸,一笑露一口白牙,耳朵上的小肉钉欢快地跳。妈妈的责备一点作用没有。
第一件滑雪衫在沙沟买的。那年我十岁,也是和爸爸妈妈去卖猪,猪卖完了,数着沾猪粪的钞票,爸爸豪气地问我想要啥,我指着街边店里的红色卡腰滑雪衫,就要那个。价钱应该很贵,妈妈肉疼,爸爸笑眯眯付了钱,安抚妈妈,只要菩萨保佑,小猪平平安安的,多大事啊。在爸爸那里,什么都可以通过小猪解决。
村里人都知道,我家的猪养得好,我们家的猪圈顶干净。母猪的猪食,爸爸自己拌煮。猪圈内,冬天炭火取暖,夏天纱帐防蚊。母猪临产,爸爸日夜宿在猪圈,给小猪接生。体质弱一些的小猪,生下来呼吸困难,爸爸顾不得擦一擦,给它做人工呼吸。猪是我们家的聚宝盆,儿女的学费,田里的化肥农药,四季的人情往来,全指望它们呢。我们家的小猪,个个油光水滑。对小猪能卖好价钱,爸爸从来都是信心满满。
3
猪市在沙沟的哪个方向,我真记不清。帮船夜里走,每次都在黎明前靠岸。帮船靠岸,爸爸帮船老大蹿出跳板。正值壮年的父母齐心协力,把装小猪的藤条筐火急火燎地抬上岸。不是一筐,是三五筐。每筐两三只小猪。交易市场没有围墙,散落的,又是约定俗成的,灯影幢幢,一堆人喧嚣嘈杂。
猪市是早集,一个时间一个价。爸爸对行情了如指掌。他指挥我们看护归拢到一起的猪,看管大人热得脱下的衣裳,还有购物的竹篮、打油的壶、买饲料的蛇皮口袋,等等。他操一根竹杠,穿过猪筐上口的编织眼,和妈妈一人一头,屁股一抬,猫了腰直奔离水边三五十米的猪市。我们家的猪筐一落地,就围上来不少人,有买家,有开行的。开行的,类似今天的中介,每成交一头猪,他们都要收取一定的费用。爸爸和他们老熟,忙里偷闲开玩笑,声清气朗。筐里的小猪卖完,爸爸妈妈返回再抬。一栏小猪全部售完,爸爸胸口的口袋鼓鼓的。这时候,沙沟的石板街才醒,爸爸要带我们去街上犒劳犒劳肚子。
有时帮船的停靠点被别的船只占了,船主会让我们从木排上走上岸。木排整齐、安静地泊在水边,一棵棵又粗又圆,爸爸告诉我,有杉木,更多的是美国花皮松,打家具好得很。
爸爸老早就雄心勃勃要买木排,替儿子打家具,好娶儿媳妇。卖小猪攒的钱差不多了,爸爸真买了五棵花皮松,木排行的主家用“油葫芦”把松木从水里吊到爸爸的水泥船上,爸爸就这么运回了家。找来油锯工,开成片板,一块砖一块板,间隔着透风,从我十一岁一直到我二十岁,沙沟河里的木排就这样搁在我们家的閑屋里,也一并风干在我的记忆里。
爸爸的观念其实很传统。他自立门户早,吃的苦比同龄人多,总想尽可能给自己的儿子多些庇护。二十岁那年,我参加工作了,在老家的联办初中做老师。在爸爸眼里,这一点不稀奇,女儿迟早要嫁出去。他屋里没打算留我。
我在老家教了三年书,那是怎样一段时光呢?我常常找不到准确的语句来描述。说冷清寂寞,那是自然。除了隔天来一次的邮递员,没有书籍,更没有网络,心里常常很空。看到同来的年轻人,通过种种途径纷纷离开这里之后,有一些失落和彷徨,我对爸爸说:“给我打个书桌。我要读书。”
爸爸舍不得他从沙沟拖回的花皮松,这些木板,他有计划,怎么可以轻易挪作他用。读书不是读好了嘛,都成公家人了,每月几百元工资,还读什么书。
再催他,我咬着嘴唇,都快绷不住哭了,爸爸终于决定给我打只新式的书桌。用他从沙沟运回的花皮松,只用两张板。
书桌做成了,合心合意,有学校里的办公桌宽,抽屉多,带弧度,乡村人家没见过这样的桌子,够新潮的。爸爸说不上漆,以后我出嫁了,这桌子还可以重新上漆,新崭崭放到弟弟的婚房。
我在这张书桌上翻着自学考试的书,偶尔也写写寂寥、无助的心思。从1993年到1996年,大把大把的时光在这张桌子边流逝。
我与沙沟,隔着一片茫无涯际的水域。其实是有边有岸的,只是目之所及,一派苍茫,不由人不心慌。其实,见与不见,岸都在那里。
为生活奔忙的脚步总是停不下,我的沙沟几乎被岁月的风尘掩埋,某一天,熟悉的穰草味将其唤醒。写下这些文字,致我逝去的里下河的青春。
王树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文案,爱好文学,作品发表于多家报刊。
编辑 沈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