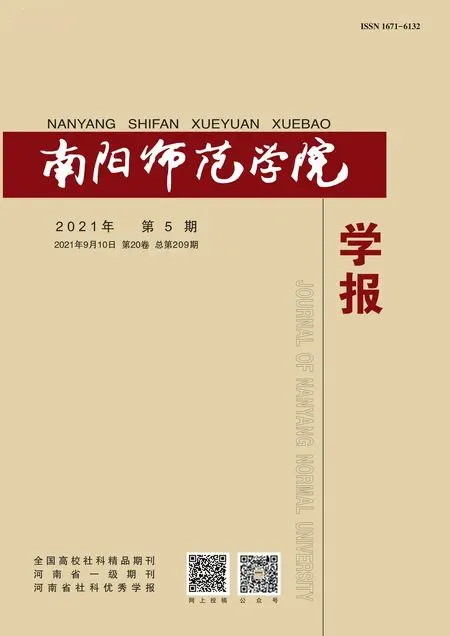弥纶古今:夏承焘先生的词律研究
——以遗著《词例》为中心
赵友永
(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00)
20世纪30年代,《词例》正在编撰的消息曾刊登于《词学季刊》创刊号,并简略介绍了其著书大纲。近百年来,词学界一直期待其成书出版。此书“规模宏阔,洵为巨制”[1]3,施议对先生曾高度评价这部著作:“这是一件伟大著作。”然而这部伟大著作的书稿最终未能整理誊清,虽然积累了许多的材料,却还只是一个“半成品”。正如施先生所言:“全部工程,尚需一代人,或者二代人的努力才能渐见头绪。”[2]297亦如刘少坤先生所言,此书的出版“必将是词学界一大盛事”[3]76。2018年5月,吴蓓先生主编的《夏承焘全集》由浙江古籍出版社陆续分册出版,其中《词例》一书的影印面世尤为引人瞩目。正如吴蓓先生在《词例·前言》中所言:一则由于时局纷扰,二则夏先生编纂计划的游移反复及身体情况的原因,皆给此书编纂带来了很多实际上的巨大困难[4]3。虽然此书中的许多观点在之前已经化作单篇文章,广为人知,从已经整理成文、正式发表的若干篇文章看,夏先生所作考订,辨例周详,并多见新创之说,且已为当代治词学者奉为圭臬[注]例如《词四声平亭》,以具体词例证实:一、温飞卿已分平仄;二、晏同叔渐辨去声,严于结句;三、柳三变分上去,尤谨于入声;四、周清真用四声,益多变化;五、南宋方杨诸家拘泥四声;六、宋季词家辨五音分阴阳。。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未见词学界有专门论著介绍评鉴其学术价值,可见学界尚未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意义。词律学在近几年渐有兴盛之势,若不参考吸取夏先生这部重要著作,相关研究势必会有一定缺憾。本文不揣荒陋,特为表出此书的成书特征及其突出成就,以见夏先生在现代词律研究史上的独特贡献。
一、博举其例,以治词律:前所未有的词学研究著作
据夏先生本人记述,此书的编纂缘起,在于受到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启发,“阅《古书疑义举例》,拟作一书曰《词例》”(一九三二年正月)[5]260。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自称“称刺取九经诸子……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依,或亦读书之一助乎”[6]1,少年刘师培看后“叹为绝作”,“以为载籍之中,奥言隐词,解者纷歧,惟约举其例,以治群书,庶疑文冰释,盖发古今未有之奇也”[7]1。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夏先生的学术视野已然十分广博,他并不准备做一个仅仅深耕词学的专家,而是有意追求经世致用之学。早年受到阳明心学影响的夏先生,对于宋明理学有着浓厚兴趣[4]3,故而其交游者也涉及诸多学科的学人。夏先生也十分欣赏钱穆先生的学说,甚至致函表示钦佩[5]404。在其日记中,夏先生也常记录对经、史、子、集等各类科目的研究思索,甚至在30年代一度准备改行学医[5]405。正是这个原因,夏先生的学问气象极为广大,视野也非常广远。故而俞樾之书进入他的视野是十分自然之事,追步模仿此书也足以见得夏先生深远广大的学术雄心。
此书最终的定名也是经过一番考索。夏先生细究了古书中带有“例”字一书的渊源,在其书封面上,有如此字样:“考《唐书·艺文志》载姚合《诗例》一卷。《书录解题》廿二唐右补阙刘悚鼎卿有《史例》三卷,知几次子也。”所以本书取名为“词例”,一则较为简洁明了,二则更为古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一书凡七卷共八十八条,针对秦汉典籍中的特殊语法、修辞和书面语情况,分门别类进行解疑。这些问题,古人一般称之为字例、词例和文例。其目虽简,其例实多,故而尚有很多增补的空间。相比于古书修辞训诂,词律问题看似微观细琐,实则极为复杂。由于词体格律的严格繁复,加之七百年来积累了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便决定了此书的体量不会小,编纂的困难程度也不会低。在日记中,夏先生早已事先拟定了《词例》最初的五十八条目[注]可参见夏承焘的《天风阁学词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0—264页。下文关于日记内容多自此书而来,故不复标明页码。,这当然还是一则简约目录,却也由此可见对著书最初的设想。现今底稿已经影印,其目录条例与原先的设想大体一致,而其体量却已然远超当初的设想。
据《词学季刊》创刊号《词坛消息》记载,此书约分字例、句例、片例、辞例、体例、调例、声例、韵例诸门,并称“《词律》究一词之格律,此书将贯全宋、元词为一系统”。现今我们将其草创之凡例、目录罗列如下:
凡例 十华阁主
一、抄调名作小字,如辛弃疾贺新郎“马上琵琶关塞黑”。辞不必自我出。
一、论韵论律,戈载、万树已评者,此择其大者,并补其未备。
一、每大例分小例,□[注]□表示不易辨别之字,由于手稿年代久远,又曾经有剪贴,不免多有破损模糊之处,识读困难。原文少有标点符号,多为笔者所加。细家一好例多者举最奇特者,或举名家为例,如音律举白石、清真,俚语举山谷,腔调举柳永。各词话须阅。引词话源码。
一、词在韵文之位置之体裁,与三百篇及汉魏乐府同,(删去数字:《三百篇》、乐府至唐律而极凝,至词乃解放)各例皆须参诗及乐府,可命学生作《乐府辞声例》。每例之中皆须依时代述其变迁之迹及其原因。[4]6-8
在日记中,夏先生针对《词例》结构最初的设想是:“《词例》八卷:韵例、声例、调例、体例、片例、辞例、字例、句例,每例分数十子目。换头入片例。”[注]此为摘自夏先生日记手稿本,待出版。其中第二条“上声”一例又分为两部分,这在全书中算是较少的。现今目录顺序依次为字例、句例、片例、换头例、调例、体例、辞例、声例、韵例,其中以调例、辞例、声例、韵例四种篇幅较大,小例皆在四五十条左右,句例、片例、换头例其次,有二十多条,而以字例、体例则较为简短,不过十条左右。手稿中偶有红色笔迹,如“字例”中“移字”,当是后来补录进去的。
至于本书中条目较为繁多的章节,我们以《声例》为例。这是本书的核心内容,篇幅较巨;再则,四声问题作为词律研究的根基,自古以来就是词学研究中较为困难的一个问题,也极为重要。现将《声例》一章五十条小例目录详细罗列如表1所示。

表1 《词例》第八章“声例”部分小例五十条目录一览表
由上文目录列表可见,《词例》全书记录着夏先生数十年来考斠词律时的诸多创获之处。关于体例设计,在底稿封面上,夏先生有手迹云:“大例中当再分析小例,同中求异。”可知,其全书架构正是围绕这两句话铺展而来。全书以《词律》《词谱》《词林正韵》各类词谱、韵书为论律举例之本,以个人札记《彊村丛书》等词集丛书及词话、词学专著等为补充。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我们也能从上文具体内容,明白其书体大思精之一隅。
值得指出的是,俞樾之书虽胪列例证,详加诠释,犹不免受到“缺乏高度的理论概括,编排体例不尽科学”之讥[8]25。这种批评未免“强人所难”。这类著作本自读书札记而来,最终汇集为一部胪列训诂之法的工具书,意在指导初读古书之人,且受体例所限,故宜胪列而不宜论证,以其类似工具书故而长于疏解而不便于说理。胡适也提出过“例不是证”[9]205的说法,正是如此。吕思勉先生曾深感今人不知古书体例而有言,“经义史事,二者互有关系,而又各不相干”[10]30,而举例疏解之书典与论证之著述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此。《词例》也正是因为体例所限,举证皆当有定说,只是书中很多问题在当时甚至在今天都很难得出一个明晰的结论,故而这也是延缓此书完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原因。俞平伯《〈周词订律〉评》云:“综观此书,采撷详备,校订勤劬,似缺一种明通之思想以贯串其间,而其实用之价值不以此大减,欲研治《清真词》者,固必须参考,而填词者得之,亦有逢源之乐,无畔之失,纵或失之于严,犹取法乎上也。”[11]684其说甚是中庸,借以评《词例》,亦可谓的当。
二、勤求博采,潜心体认:《词例》对古今著作学说的斟酌取裁
当代学者曾高度评价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一书:“既融会自己《平议》中的心得,又广采前人尤其是顾炎武、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刘台拱诸清代学者的成果。”[12]103因为受俞樾之书启发,夏先生《词例》一书自然也肖其体例,广征博引了古今诸多研究成果。
(一)广泛札记前代词集文献
根据夏承焘先生日记可知,《词例》一书大体是在1932到1933年间构建的,这段时间内夏先生用力最劬,“几乎每日都有订补”[4]1。在此期间,夏先生更多的还是逐次阅读《词律》《词谱》以及唐宋金元名家词别集诸书,在阅读时斠其声律,研其用声、韵、句式、分片等,进而补入《词例》书稿之中。
《词例》一书前几页中,夏先生记录了草创此书之时的许多设想,其中就包括“征引书目”,今节录摘抄如下:
书名上注数目皆《彊村丛书》本,如词集中可考词千阕,各大家词皆须再校。
《词学季刊》《词通》《词比》须参考(榆生论□体亦须考)。
《彊村丛书》眉批当补入,取其重要者为《唐宋词艺术形式特征》,其余材料作札记。
字例、句例或分入辞例体、调例中。每例中皆为史□叙述。
《词例》着手于民国廿一年正月初二日,阅《词谱》始于民国廿一年正月四日,完于二月八日。[4]3
在夏先生这两年的日记中,也多处可见他阅读唐、宋、金三代词家别集,斠定四声,继而补入《词例》中的记录。如夏承焘日记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6月27日“阅《飞卿词》,札入《词例》。其用平仄之严,几乎一字不苟”。其他又如“札《清真集》严上、去之辨者入《词例》”(7月14日);“阅《词林正韵》,入《词例》”(8月14日);“午后雨阅《花间集》,札《词例》”(8月15日);“阅《乐章集》,札《词例》”(9月7日);“翻鄮峰词作词例,颇有所得”(9月20日);“接赵叔雍复,允假《全芳备祖》《翰墨大全》……札《词例》,《彊村丛书》第十七本完”(10月29日);“札《词例》,翻《彊村丛书》完”(11月4日);“阅四印斋《明秀集》,札《词例》完”(11月5日)。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词家别集多是取用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彊村丛书》、王国维《唐五代二十一家词》、夏夫人游俶昭抄本《宋元卅一家词》、赵尊岳校刻《宋金元人词》等。其中《彊村丛书》最引人注目,书内天头处多有夏先生墨笔批校,是撰写《词例》最先的准备。此书共计存词集170种,今藏温州市图书馆。
(二)征引近人论著、意见
这一阶段,夏先生也经常与同时代学人面谈或者去函争讨四声问题,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与冒广生的讨论:
归途访冒鹤翁于福煦路模范村廿二号,一揖坐,即谈诗词,谓年来治《乐章》、清真、白石诸集,圈去词中衬字,以见其本体。其法先以上下片互校,再一家同调互校,后复参之他家。以《乐章》集相示,一词中有圈去十余字、三四句者,间以昆曲为旁证……灯下阅鹤翁校《乐章集》,有数条可入《词例》。此老读词极细心,尝遍校方千里与清真词,四声多不合,谓文小坡、万红友谓其甚依四声,实等放屁。大抵反四声、反梦窗为此老论词宗旨。(1938年9月10日)[13]45-46
这些都是极为难得的文献材料,不仅记录了夏先生当时作《词例》研讨四声的思索,也留存了他与当时学人私下之间争论的细节。这些材料在各类期刊中未见发表,是许多论著中无法获得的,弥足珍贵。
20世纪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夏先生增补《词例》的思路开始转变。这是现代学术蓬勃发展的时期,虽然中国当时正值兵荒马乱,广大学者仍旧笔耕不辍,诸多著作陆续出版。此时的夏先生思忖“用科学方法解析词之体例”(日记,1939年5月5日),对于之前遗留的手稿,他认为需要“以科学药其痼弊”(日记,1939年3月21日),“旧作《词例》,仅能襞,尚须再深用力”(日记,1939年5月5日)。词律研究不同于词的创作与赏析那么具有“人文”性质,本质上还是属于一种需要实证的学问,这就注定必须依仗于精通音乐、声韵、文字的专门学者,以极其专门且系统的理论方法进行验证统计。三四十年代,现代词学已然建立,词学研究者们开始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对之前的词律研究梳理反思,这批学人如叶恭绰、冒广生、龙榆生、吴庠等多有质疑清人成果,纷纷撰文发声。夏承焘先生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在当时的四声之争中,他甚至还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如他1942年写就的《词四声平亭》,以精心撰写的宏文“舌战群儒”,主张四声有其道理,不可废止,捍卫了词律研究的阵地[14]302-326。
虽然如此,现代学术的缤纷成就还是进入了夏先生编撰《词例》的视野之中,现代学术中讲求实证、精密分析的风气也便于论证词律。在此期间,诸多论著的精当之说被他精心选取、录入书中。除了底稿前几页所列举的王易《词曲史》、龙榆生笺《东坡乐府》之外,见于其日记的著作尚有很多,如“阅《音韵学史》,札入《词例》及《著述例》”(1938年3月8日);“心叔示《广韵》及马宗霍《音韵学通论》,中有《唐人用韵考》《宋人用韵考》二篇,各札一过入《词例》”(1938年10月12日);“夜阅徐先生《诗经形释》《诗经声韵谱》,札入《词例》”(1940年12月18日);“阅《同声》月刊二期……俞感音《填词与选调》,当榆生作,分析词调声情甚详,颇不满近人好为涩调,适与予意合。可札入《词例》”(1941年2月15日);“接詹祝南坪石中山大学函……《中国文学之倚声问题》一文,文可札入《词例》,分析颇精”(1942年,2月3日)。其中阅读参考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最为值得留意。“校《中原音韵》入作三声例。戈载之说,间有例外……于徐家珍处借近人《中原音韵研究》一册来……”(1941年8月15日)夏先生阅读《词林正韵》生发疑惑,具体疑惑为何,日记中并未言明。既然生疑,夏先生便迫切需要得到专业研究的印证,故而当天就借来了书籍。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自述读书心得:“阅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谓挺斋始分阴阳平,由元人混读唐宋时之清浊音。此语待问。得心叔函,论入作三声。”(1941年8月16日)夏先生抄录赵氏此书的内容在“入派三声之例外”一条,“《词林正韵》定清入作上,正浊作平,次浊作去,而周德清□未明言其理,而予测其大略如此”。“今案《中原音韵》例外有如下各字……此在全书不足十之一二,戈说为可信。注母据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4]208-216赵荫棠的《中原音韵研究》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彼时的赵荫棠还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生,导师是钱玄同。钱玄同在审查报告中对其论文评价道:“综观全书,精采极多。对于《中原音韵》一系韵书为源流派别之叙述,本编当为第一部也。”[15]167然而由于“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再加上学术界投入的人力和精力都远较中古音系和上古音系的研究为少”[16]63-81,因此这部著作在当时还是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夏先生当时征引此书,可谓是当时视野所及之内较为先进可靠的著作了。
(三)保存稀见词学文献
夏先生向来珍视《词例》,加之体例原因,必须要广征博引,是以需要遍览很多古今相关著作,更需留心裁取,择其尤精要者。正因如此,使得《词例》此书保留了一些稀见的珍贵文献。如《声例》“入派三声不拘”条,就分别征引了张尔田、吴庠的来函:
张孟劬谓曲音则然,宋词未必有此区别,即便有此区别,而宋时方音不同,亦未必与《中原音韵》相合。(卅年八月来函)注定入声字,眉孙谓见于刘融斋,查《艺概》。又谓朱古微〈金缕曲〉“||— — — —|”句第六字前用仄,必是入声,宋词有此例(待查)。唐人七古末三字作“—|—”者仄亦必入,如韩《山石》“黄昏到寺蝙蝠飞,山月出颠光入扉”,是。(查韩、杜他诗)不尽然,因入声声脆。[4]500-511
张尔田认为,宋人填词真相未明,不当以后世韵书与宋人词作强行相格,因宋人填词押韵未必如此“齐整”严格;吴庠以刘熙载《词概》、朱祖谋词作为例,讲明词调“吃紧处”。尽管征引此类学说,夏先生对于张尔田等人的看法尚保留疑惑,故而于文字末尾处加上疑问符号。
这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材料是“厉鹗手批”《词律》,又常常被称作“厉批《词律》”或者“厉评《词律》”。关于此书,词学界早就有过记录,这里只做简单介绍。20世纪30年代,夏承焘、龙榆生两位先生偶然从湘潭袁思亮处借来厉鹗手批《词律》,经众人检阅后认定可信,然苦其繁冗,故而夏承焘嘱托学生沈茂彰整理此书。1936年,沈氏初步整理成《万氏词律订误例》一文发表于《词学季刊》第三期第四号[注]可参见《词学季刊》第三卷第四号,第41—80页。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夏先生指导弟子沈茂彰以“例”字拟题作文,可见此时对于俞樾之书之法的高度推崇,可视为夏先生师弟间合作的典范。详见此文前言。,本欲继续整理,以便成书出版,不料战乱骤起,只得将书归还袁氏。《厉评词律》观点十分犀利精到,驳正万树《词律》诸多问题,是十分难得的文献。许多年来,此书下落不明,而沈茂彰整理进程如何也不得而知。如今《词例》手稿中多处引用有《厉评词律》材料,十分引人注目。据对比《万氏词律订误例》可知,多有此文不载之文,如下文:
厉评:“是语此等句乃水到渠成,一举呵就,不得分句读也。故吾甚服升庵之言曰:腔调一定而作此语言所到时有参差,在歌者纵横裁度取合拍耳。”[4]96
即便是《万氏词律订误例》整理发表过的文字,《词例》所征引也较原文更为全备,如《词律》卷九《唐多令》主无“衬字”一条,厉鹗批驳万树“词无衬字”说。我们现将同一来源的引文分别胪列如下,其中加下划线的文字为《万氏词律订误例》所无:
真迂云,自有词馀,便有衬字,即据梦窗词中“也”字,非衬而何?余更问红友谓词无衬字,从何而来。红友不通至矣,尽矣。此句神情全在“也”字,如以“也”字为误多,则“纵”字、“不”字无着落。衬字俱属误多矣。[4]24
从上文对比便不难发现,《词例》引文确实比《万氏词律订误例》要更为完备精准。《词例》一书多有裁用《厉评词律》之处,兹不多引。
《词例》在编纂过程中可谓广征博引,除了常见的正史、词律、词谱、词选、词话、曲学著作外,还征引了学术论著、手札、信函、笔记等材料。正因如此,夏先生对这部著作也格外看重,“念《词例》虽琐琐札录,然材料殊丰,不忍终弃”(1957年4月28日)。1978年,夏先生在其《月轮山词论集》前言中回忆其治学经历时说:
我二十岁左右,开始爱好读词,当时《彊村丛书》初出,我发愿要好好读它一遍;后来写《词林系年》、札《词例》,把它和王鹏运、吴昌绶诸家的唐宋词丛刻翻阅多次。三十多岁,札录的材料逐渐多了,就逐渐走上校勘、考订的道路。[17]1
对比上文,我们不难看出,《词例》一书正是夏先生毕生心血所在。此书不但集合了他前半生治学时的诸多读书札记,也随处闪耀着他对词学研究的诸多思考,而后的诸多成果也正是从《词例》流出[注]在确定编纂《词例》之后,夏先生先后撰写《词四声平亭》(1940年)、《四声绎说》(1941年)、《填词四说》(1943年)、《词韵约例》(1944年)、《词律三义》(1947年) 、《阳上作去与入派三声说》(1948年)、《读词常识》(1952年)等论著,而其论点皆可找出从《词例》中流露出的痕迹。。
三、研声斠律,袪魅解疑:《词例》在 “律”“韵”研究上的突破
戈载《词林正韵·发凡》有言:“词学至今日可谓盛矣,然填词之大要有二:一曰律,一曰韵。律不协则声音之道乖,韵不审则宫调之理失,二者并行不悖。”[18]35律韵问题可谓是词律研究的核心所在,而其中“律”所涉及的主要是四声。《词例》一书之中,声例、韵例部分最为关键,虽然早就比勘校对过诸多唐宋名家词集,相关材料也十分充足,夏先生在编纂这两部分时却也是“迟迟吾行也”。《词例》前六册在1933年便已经大体完成,而声例、韵例则持续了许多年,正是因为此问题较为棘手。
声律研究上有两个十分紧要的问题。一是四声,诸如就有“入派三声”“上入代平”“上去连用”“去声”等词律学中争执已久的问题,甚至四声本身就一直是一个很容易引发争论却又极其重要的论题。万树在《词律》中特别强调了“上去”“去声”“入声”以及“不可移易处”之后,词人填词大多奉守不疑。到了道光年间,吴中地区开始严辨四声,甚至和韵宋人词无一字不随其四声,这其中的典型代表便是戈载[注]清代朱绶《桐月修箫谱序》云:“近年来填词之学,吾吴为盛,戈氏首发音律之论,绶与沈闰生氏坚持之,得井叔而知为学之未有尽也。”清代俞樾《绿竹词序》云:“道光间,吴门有戈顺卿先生,又从万氏之后,密益加密。于是阴平、阳平及入声、去声之辨细入毫芒。词之道尊,而填词亦愈难矣。”清代蒋敦复《香禅精舍词集序》云:“往时戈殁翁订正《词律》特严四声,于宫调尚未及究,学者已苦其难。”可参见冯乾编校《清词序跋汇编》第2册,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857页、924页;第3册,第1345页。。由吴中地区开始,讲求四声的风气蔓延全国,新兴的常州、临桂等派也受其影响,填词及编写词话都甚是重视四声。吴中地区词人对于四声中“入派三声”“上入代平”等理念很是熟稔,然而运用在词中后却引发出一系列问题。例如很多词人在其词作中自注某仄声字“作平”,某入声字“读去”“读平”,某字如何反切,以至于招致批评[注]如彭凤高《卷楼词话》云:“惜乎词人不知此理,将上去硬填作去,孰为可怪。”可参见彭凤高著《词削》,清咸丰抄本,上海图书馆藏。转引自昝圣骞著《晚清民初词体声律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页。。四声通转本是在词乐存在的情况下才产生的问题,至词乐失坠以后,这种问题便失去了生存土壤,如果将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加以研究则可,若师心自用,盲目“转换”便会带来很多麻烦。在词乐尚存时,四声之通转也是因人而异,然而填词者仍可以乐为基准,不至于失律;词乐消亡后,填词便很难再论,况且四声之“声转”也是有其一定之理,未可随意揣测[19]。
第二个难题则是词韵。清人认为:“词韵旧无成书,盖因雅俗通歌,惟求谐于声律,不以韵拘。故虽填词之盛,莫过于宋,而二百余载绝无撰韵之人。”[20]词韵起初未被重视,到了明清之际,词中押韵的问题开始引发。其中《菉斐轩词韵》这部韵书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由于这部韵书中没有入声之部,历来认为是为北曲而设,没有入声之部便有“曲化”倾向,这是很多词人不能接受和承认的。清代学者编纂的词韵著作有《学宋斋词韵》、许昂霄《词韵考略》、吴宁编《榕园词韵》,嘉道时期,又有王讷《晚翠轩词韵》。尤其是道光年间,吴中戈载《词林正韵》一书问世,广受好评,被王鹏运收入《四印斋所刻词》后,名声日隆。虽然《词林正韵》问世一百多年以来在词韵中处于权威地位,批评声音及修订工作却一直存在,新编词韵也层出不穷,如谢元淮作《碎金词韵》,郑春波作《绿漪亭词韵》,叶申芗作《天籁轩词韵》等。民国年间,夏敬观也曾发表《戈顺卿词林正韵订正》二卷。时至今日,难有令人信服的定说。
关于声律问题,夏先生立足于《词律》《钦定词谱》二书,一方面以此二书作为词作举例之源,另一方面搜集其论四声例证,然后广泛征引前代词话见解。在其遗著《词例》中,声韵部分数十条的例目将词律问题辨析得十分细致。唯其细致,因而也甚有创获,这种创获甚至打破了之前人们对于声律问题的常规认识,令人震动。律韵问题十分庞杂,此处我们唯有举其大要以讨论《词例》的创获之处。
(一)去声代平
宋人沈义父在《乐府指迷》中提出:“腔律岂必人人皆能按箫填谱,但看句中用去声字,最为紧要。”[21]280万树则在《词律》中赋予去声一种独特的地位,认为去声最为“起调”,如其《词律·发凡》着重强调:“大致词之拗调,其用仄声处,重在去声,即其去声字不能易上入声。何也?三声之中,上入二者可以作平,去则独异。故论声虽以一平对三仄,论歌则当以去对平上入也。当用去者非去则激不起,用入且不可,断断勿用平上也。”[22]15卷五《柳梢青》下注云:“此调后第二句‘残阳乱鸦’四字平平仄平,其仄字宜用去声,乃为起调。观古名篇,无不如是。”[22]151而《词律》中甚至不厌其烦,多次赞美去声使用之妙。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不必赘引。
正是《词律》特别重视去声,对于去声“另眼相看”,在四声问题上,万树定下一条铁律:去声不可代平。这在《词律》中也多次被严正申明。如卷三《女冠子》第三体,万氏讲明入声可借以作平,去声则不可。“……只李之‘质’字,蒋之‘怯’字,皆是入声可以作平,若去声则不可耳。”[22]111-112卷九《握金钗》,“‘和’字去声,不可作平读”[22]313。卷十三《满庭芳》第三体黄山谷作,“‘荷’字、‘水’字、‘山’字以用平为主,上入亦不妨,切不可用去声”。在卷十七《宴清都》下注文,更是全书内蕴所在,万氏自述作去声不可代平理法:
夫词曲中四声,以一平对上去入之三仄,固已,然三仄可通用,亦有不可通用之处。盖四声之中独去声另为一种沉着远重之音,所以入声可以代平;次则上声亦有可代,而去则万万不可。[22]391
正是因为万树严明去声的无可代平之理,后世多从其说,鲜有质疑违背者。精通此道如楼俨,一贯反对《词律》“以上作平”之说,其《洗砚斋集》及参修《词鹄》《钦定词谱》对于去声的独特地位也未有任何反驳,甚至十分赞同万树。周济也提出“红友极辨上去,是已。上入亦宜辨,入可代去,上不可代去,入之作平者无论矣,其作上者可代平,作去者断不可代平。平去是两端,上由平而之去,入由去而之平”[23]1645。这皆是对于去声不可代平之说的进一步细化。吴衡照《莲子居词话》也对万树四声之说评价颇高:“红友《词律》,一一订正,辩驳极当。所论上去入三声,上入可替平,去则独异,而其声激厉劲远,名家转折跌荡,全在乎此,本之伯时。”[24]2043-2044陈元鼎《词律补遗》更是提出“去平不能相同”[25]的说法。可见万树去声之说已然深入人心,成为词律学史中的铁则定律。
然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夏先生在其《词例》条目“上作平”下俨然列有“去作平”一条分目。为使读者明晰此间委曲,兹详细征引:
去作平,此例甚少,列平作去下
〈绕佛阁〉“气”下二字吴文英作平16,25。
《酒边词》24〈点绛唇〉次句“不向光影门前过”,“向”当平。
《竹斋诗馀》1〈沁园春〉“舟从海道”。
《东浦词》《一剪梅》 “只怨闲纵绣鞍尘”,“怨”字。
白石改清真《满江红》 “无心扑”为平声。
《词律》3,赵长卿《点绛唇》“翠涛拥起千重恨。砌成愁闷……泪痕羞揾。”“翠”“砌”“泪”皆须去。厉评谓“翠”字易安作“柔肠一寸盘千缕”,“砌”字,和靖作“余花落处”,“泪”字,白石作“凭栏怀古”,和靖作“萋萋无数”,觉范作“风吹平野”,易安作“连天衰草”。知得去声固妙,即用平声亦不妨碍者也。[4]496
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保持去声的独特性属于词律中四声的“底线”,如果这条界限被打破,那么四声将濒临被解构的边缘。虽然夏先生《声例》一章设置了“去声作平”一条,且明言“知得去声固妙,即用平声亦不妨碍者也”,却也显然感觉到了于理未安——他自然要考虑到自万树以来的这一条“铁则”,故而在条目下自注:“此恐不成例,作平者乃前人平仄不拘处。”且以《厉评词律》之说列于文末:“向谓作诗之道,以平对仄,作词之道,去对三声,故上入可作平,而去声断不可乱……”《词律》卷十一《西园竹》注文中,万树提出姜夔“莫”字借作“暮”字,“音亦未可知”[22]269。万树此处显然有骑墙之论,既然已经将去声对应三声,何以此处又“节外生枝”,提出入声作去之论?厉鹗等人显然对此论感到费解,故而针对性提出质疑。夏先生引用厉评,应该也是思忖未定。在《填词四说》等后出文稿中,夏先生再未有提及去声作平之说,这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然而作为手稿,先备录文献,不作定说,也是无可非难的。
(二)词中押古韵
在词韵问题上,夏先生的词韵研究也很有突破。《韵例》一章在条目设置上提出很多明确的纲目,也在戈载《词林正韵》基础上迈出很远。清初的词学家在编撰词韵书籍的过程中已经发现,唐宋各家词人所守之韵有宽有严、不尽相同,词学家们于是提出“借叶”“叶古韵”“方言叶”等理论来进行解说。而有些词学家则反对词有“借叶”等说法,直接批评词人未能守韵,认为唐宋部分词作的用韵是错误的[注]如康雍之时的许昂霄在评注陈允平《绛都春》(飞梭庭院绣帘闲)一词时谈道:“‘痕’字、‘昏’字,不宜与‘寒’‘娟’等字同叶。其《词韵考略》,既以今韵分编,而入声又有‘古通’‘古转’‘今通’‘今转’‘借协’,也把握不定,大类诗韵。 再如张炎《西子妆慢》‘遥岑寸碧’一句,‘碧’字入声不当与上、去同押。晚清王鹏运四印斋本依戈载之说注云:‘碧字借叶,方彼切’,非失韵也。周稚圭改作‘残山剩水’,非是。”可参见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影印本,第147页。。至于“古韵叶”,《钦定词谱》中诸多词调注语之下力主此说,如《黄莺儿》《风流子》《醉翁操》等。戈载在《词林正韵·发凡》中以为“词韵与诗韵有别,然其源即出于诗韵”,他认识到词韵源于诗韵而又有所变化,因此不能以诗韵代替词韵;词韵虽然较宽,但某些规则较诗韵又更为复杂,否认词韵与古韵的关系,“若谓词韵之合用。即本古韵之通转。则非也……所论皆古韵,与词韵之分合,绝不相蒙,勿谓吴郑皆宋人可据为则”。可见,戈载当不会赞同词中押古韵这种说法。
夏先生既不赞同词中“叶古韵”的说法,也针对《钦定词谱》中的一些论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了使读者详细了解夏先生论韵之见,我们特详细征引原文如下:
13,叶古韵(《词谱》)用古韵例与韵杂类参看。
孙光宪《风流子》“听织,声促,”屋与织古韵通2,22。
白石《侧犯》“谁念我”与“句”叶(参《斠律》),角招“渺” 叶“袖”。
山谷《归帝京》豆有韵,下片云“恨啼鸟、辘轳声晓”,汪东谓以乡音叶,非是。清真《西平乐》,麻韵,过变“道连三楚,天归四野”,郑文焯谓“楚”“野”古音相谐。黄侃曰“野”字或是平仄通叶,“楚”字非韵。宋人词中无用古音相叶之理,吴偶合耳。[4]625
由上文可知,夏先生提出“宋人词中无用古音相叶之理”,对于疑似之例,也认为不过是“偶合”。同卷,夏先生抄录了《厉评词律》的观点:
词虽名为诗馀,亦有古近之分,如《小梅花》《醉翁操》《哨遍》等,当以古义行之,古用韵亦可从古。稼轩“江”“东”通用,故不可谓之失韵,亦岂得谓之“借叶”乎?[4]625
虽然引用了厉鹗评语,但是夏先生并不信服:“焘案,文焯时以古文义校宋词,汪东谓宋词人用字从俗,不当以古体论。依照宋词人,似亦不致用古韵叶,此体在当时故近俗不好高骛古也,疑当时方音偶近古音耳(江昱先疑及此,见前)。”[4]626对于戈载的认知,他也提出批评:“宋人作词多从当时之音,与他文不同,戈载谓之借韵,固属强立名目,然谓以古音通□,则尤非也。”[4]627
我们注意到,戈载《词林正韵》中并无古“借韵”之说,唯其《翠薇花馆词》卷十四《辘轳金井》一词小序中曾有提及:
第三句“玉钗微袅”,既非“溜”字借韵,复与“竹坞阴满”平仄无二,始叹宋本之妙,而两调之果为一调也。[26]
夏先生此处所谓“借韵”恐是“借音”之误,这种说法较为著名,原因在于《词林正韵发凡》中,戈载特别指出了宋人词中有“借音”的现象:
唯有借音之数字,宋人多习用之,如柳永《鹊桥仙》“算密意幽欢,尽成辜负”,“负”字叶方布切;辛弃疾《永遇乐》“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否”字叶方古切;赵长卿《南乡子》“要底圆儿糖上浮”,“浮”字叶房逋切。[18]86-87
由于戈载明言“词韵与曲韵亦不同制,曲用韵可以平上去通叶,且无入声”,又认为“以入声配三声则一也,此皆曲韵也”。然而词中押韵是复杂的,即便是戈载《词林正韵》融合了《中原音韵》体系,也不能概词韵之全,所以偶有溢出者。如黄庭坚《鼓笛令》词中“眼厮打过如拳踢”一句,以入声“踢”字与去声“戏”字相押,入去通叶,这便不合他秉持的词韵从严的原则。对于这种情况,戈载在《词林正韵·发凡》中提出自己的解释,“踢字作‘他礼切’”。对于宋词中这种特例,既然他否定了“古音通转”,只好解释为“此皆以入声作三声而押韵也”,同理,这便也是“借音”。尽管戈载认为“词韵与诗韵有别”,分列韵部也大致考虑到宋词用韵的实际,但自有其立场:他虽承认“宋人词有以方音为叶者”,却认定那是“究属不可为法”。戈载的立场与万树、毛先舒相似,旨在规范词韵,进而摆脱伶人乐工的粗俗习气,进而使词体雅化,进入士大夫文学的行列。然而戈载这种解释并无根据,甚至有些字声注明了反切,也不过是曲为之说的杜撰罢了[注]清代戈载《词林正韵·发凡》举九例以证阴入相叶,许多词学论著常加引用,鲁国尧《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则提出其中四例疑非是:如戈氏认为柳永黄莺儿(园林)-13“暖律潜催幽谷”,谷字作公五切叶鱼虞韵;又如,晁补之黄莺儿(南园)-5“两两三三修竹”,竹字作张汝切,亦叶鱼虞韵。此皆据万树之说(见《词律》卷十四)。然而《词谱》卷二十四及《全宋词》认为“谷”非押韵地位,“竹”应作“篁”。可知戈载之说不免有杜撰成分。详见鲁国尧的《语言学文集 考证、义理、辞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页。。所以夏先生评价戈载“借韵(音)”一说为“强立名目”,这是较为可信的。至于词中押古韵是否如夏先生所说是“此方言合于古韵耳”,还有待词学界进一步探究。正如夏先生书中所言,“要确定某首词是否阴入通叶,要校对版本,辨识句读,考究韵律,明了音理,辨别词曲”,学者当留意此说。
四、余论
《词例》是一部体例独特、广博便宜的词律宝典。书中抄录了古今诸多关于词律的精彩议论,也保留了很多稀见的重要参考文献,且时有夏先生的精彩评点,汇集了夏先生词律研究的毕生心血。此书涵盖自宋代以来,尤其清代的诸多重要词律学思想学说,可谓集大成之作,也是三百年词律研究之结穴所在,而夏承焘先生的学术地位亦当以此书进一步奠定夯实。本文仅能展示其碎金片玉,尚有诸多精彩而重要的词律学说,有待词学界进一步的开掘与发展。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会使词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