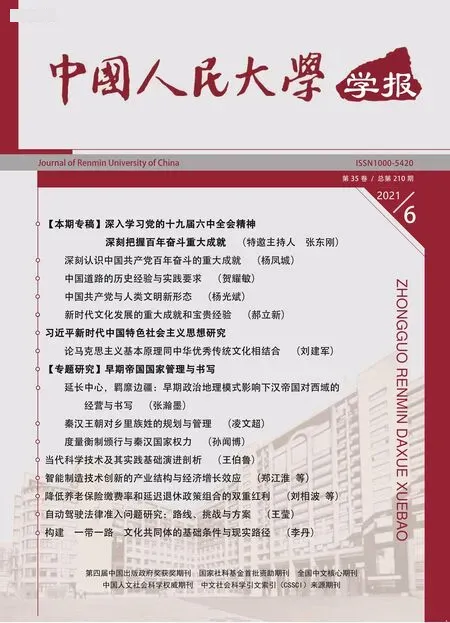自动驾驶法律准入问题研究:路线、挑战与方案
王 莹
随着物联网、定位导航等技术的持续推进,自动驾驶技术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国内外产业界积极投身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探索自动驾驶商业运营模式。各国政府也积极提供产业战略及立法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图把握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交通革命与产业升级契机,占领智能网联汽车这一全球汽车产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后疫情时代,我国自动驾驶技术迎来关键发展机遇期。在产业发展方面,自2020年6月滴滴出行面向公众开放自动驾驶服务以来,众多车企纷纷加入自动驾驶出租车赛道,自动驾驶出租车服务在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地相继出现。在行业标准方面,2020年3月,工信部发布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公示(1)参见《〈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稿)》,https://www.miit.gov.cn/jgsj/kjs/jscx/bzgf/art/2020/art_205898e525fe4959946e49af229d928f.html。,为我国自动驾驶技术大规模产业落地提供了统一的国家分级标准。在政策支持层面,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科技部等11个部委于2020年2月联合发布了《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将健全自动驾驶法律法规确立为主要任务之一,提出“开展智能汽车‘机器驾驶人’认定、责任确认、网络安全、数据管理等法律问题及伦理规范研究,明确相关主体的法律权利、义务和责任等,推动出台规范智能汽车测试、准入、使用、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完善测绘地理信息法律法规”。
与自动驾驶技术和政策的积极进取相比,我国自动驾驶立法仍保持足够的审慎。美国大多数州及德国、日本、韩国等国都已针对L3—L4级别的自动驾驶进行立法(2)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全球自动驾驶战略与政策观察(2020)》,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012/t20201229_367256.htm。,最近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自动驾驶与网联车辆工作组也为L3级别自动驾驶技术法律设定了细化的准入标准。(3)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vehicles with regards to Automated Lane Keeping System,ECE/TRANS/WP.29/2020/81,https://undocs.org/ECE/TRANS/WP.29/2020/81.面对自动驾驶立法的国际潮流,目前我国自动驾驶立法显得有些滞后,仍主要停留在自动驾驶道路测试阶段,商业部署与应用也处于初级探索阶段,因此,有必要把握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脉搏,紧跟全球智能交通革命浪潮,对自动驾驶立法先进国家的自动驾驶法律准入经验进行比较法研究,梳理我国自动驾驶商业化部署与应用的法律路线,探讨自动驾驶法律准入的具体方案,为自动驾驶立法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借鉴。
一、自动驾驶法律规制图谱与法律准入路线
融合环境感知技术、智能决策技术与控制执行技术的自动驾驶技术是人工智能与物联网最有前景的技术应用之一,但因其技术融合性、场景开放性、高速运行性等特征,也存在潜在的交通安全风险。在探讨自动驾驶法律准入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自动驾驶技术风险规制原理及发展路线进行简要论述。
(一)自动驾驶法律规制图谱
传统上法律应对风险的规范手段主要有事前和事后两种机制:前者是预防型的,侧重于侵害发生前的防控;后者是反应型的,在侵害发生后对侵害进行归责、追责及救济。规制的主要目的是激励有益的、可欲的行为,威慑预防消极的、不可欲的行为。为实现该目的,美国自动驾驶法律专家Walker Smith Bryant绘制了一幅自动驾驶技术规制图谱,根据使用规制工具的主体是公共主体还是私主体、规制措施是针对未发生的行为(即事前的行为)还是针对已发生的行为(即事后的行为)进行了分类。针对公共主体使用的规制工具有:事前规制包括自动驾驶系统技术标准规定、过程性监管规定、准入门槛规定;事后规制包括刑事、民事惩罚、强制性或准强制性产品召回、调查与听证。而针对私主体的规制工具包括:私人技术标准、工业实践标准、保险条件等事前规制工具;侵权与令状请求、商业名誉与销售影响等事后规制工具。上述任何一种规制工具都能够对自动驾驶系统是否可以被应用、以何种方式、何时、何地、由谁来应用产生影响。(4)Automated and Autonomous Driving Regulation under Uncertainty,Corporate Partnership Board Report,https://cyberlaw.stanford.edu/files/publication/files/15CPB_AutonomousDriving.pdf.
事前规制工具与事后规制工具形成应对新兴科技风险的完整闭环:事前规制设定新兴科技主体参与者在技术研发、测试、应用过程中的行为标准与安全范围,形塑其防范技术风险的注意义务类型与边界;事后规制则是在损害发生或不利事件之后,对上述技术参与主体追责,为受损害方提供法律救济,而归责的依据就是事前规制所确定的技术参与主体的行为标准与注意义务范围。我国学界对自动驾驶交通事故的过失责任、责任主体、责任原则等事后规制及两难困境、道德算法等法律与伦理问题已有较多著述,而对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如何引入自动驾驶技术测试及应用,如何通过立法或法律解释探讨迫在眉睫的自动驾驶车辆及系统合法性问题较少论及。本文将聚焦自动驾驶技术事前规制领域,探讨我国自动驾驶法律准入的路线及方案。梳理美国、德国及我国自动驾驶规制路线可以发现,自动驾驶技术进入法律的视野均经历了从道路测试到商业应用的发展历程。而在具体法律准入内容方面,从上述自动驾驶规制图谱可以看出,无论是针对公共主体还是针对私主体,事前规制均是针对自动驾驶技术或车辆标准、技术应用过程(即参与交通行为)进行规制,德国道路交通法也主要是针对自动驾驶系统功能及驾驶员地位、权利义务进行规定,为自动驾驶的商业应用设定行为标准,也为技术风险防范或损害发生后进行事后规制提供前提与依据。因此,下文也将从产品准入法及交通行为法两个层面探讨如何为自动驾驶的商业化应用提供事前法的合法化框架,以期为我国自动驾驶商业化应用立法提供比较法参考与理论指导。
(二)自动驾驶法律准入路线:从道路测试到商业应用
自动驾驶融合环境感知技术、智能决策技术与控制执行技术,通过传感器采集数据及车联网(V2X)通信传输将环境数据、地理信息输入自动驾驶算法模型,由算法模型进行冲突避让、路径导航与规划的算法决策,并基于驱动/制动/转向/悬架的底盘一体化控制完成驾驶操作。(5)李克强等:《智能网联汽车(ICV)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载《汽车安全节能学报》,2017(1);李力、王飞跃:《智能汽车:先进传感与控制》,5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自动驾驶算法模型测试调优需要大量数据,除了虚拟驾驶平台模拟场景外,更需要真实道路行驶的数据进行技术更新,因而道路测试对于自动驾驶技术发展至关重要,是自动驾驶研发与实现商业应用不可或缺的前置环节。自动驾驶功能完善则需要大量驾驶场景输入进行持续演进和迭代升级,为保障车辆在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中安全、可靠行驶,需要通过模拟仿真测试、测试区(场)测试和实际道路测试等综合手段进行大量测试、验证。将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智能网联汽车置于实际交通环境中,通过道路环境和交通参与者等元素随机组合的场景输入,可以更好地实现智能网联汽车与道路、设施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相互适应与协调,验证并不断完善车辆面对真实复杂道路场景的行驶能力。(6)鉴于道路测试是自动驾驶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应用的前置环节,其也相应成为自动驾驶技术规制的前沿阵地与试验田。
综观我国及世界各国自动驾驶法律规制的经验,一般都遵循从道路测试到示范应用、再到未来商业应用的路径。所谓道路测试,是较高级别的自动驾驶汽车在上路前已完成车辆性能、可靠性、耐久性等试验之后,对实际交通状况进行适应性匹配的过程,是一种用实际路况完善自动驾驶系统标定的过程。示范应用是在充分道路测试后对于即将进入产品化车辆的进一步验证。道路测试是智能网联汽车发展的重要环节,是自动驾驶系统从设计、开发到功能完善,直至产品化的关键一步。(7)相较于道路测试规定路径、时间与测试内容的验证方案,示范应用可与社会活动紧密结合,基于公众出行和货物运输需求提供服务并实施驾驶任务,验证车辆在限定区域范围内的实际运行能力。面向公众的示范应用不仅可以充分验证车辆的人机交互能力,还可提升公众对于自动驾驶技术的认知度和信赖感,为即将到来的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功能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8)参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2-3、23、2-3页,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08/03/content_5629199.htm。
1.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阶段
美国是启动自动驾驶技术研发和规制最早的国家,早在2012年,佛罗里达与加利福尼亚州即已通过法案允许自动驾驶道路测试,随后哥伦比亚区及内华达、密歇根等州相继通过相关立法。(9)Autonomous Vehicles/Self-Driving Vehicles Enacted Legislation (ncsl.org),https://www.ncsl.org/research/transportation/autonomous-vehicles-self-driving-vehicles-enacted-legislation.aspx.早期这些州的立法主要针对自动驾驶道路测试,规定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进行自动驾驶的道路测试或操作以及向测试车辆和驾驶员颁发许可等。(10)早在2015年底,美国加利福尼亚、哥伦比亚、佛罗里达、内华达四个州或区已通过自动驾驶测试方面的立法,11个州正在制定自动驾驶测试立法,11个州未通过相关立法。参见Automated and Autonomous Driving Regulation under uncertainty,Corporate Partnership Board Report, https://cyberlaw.stanford.edu/files/publication/files/15CPB_AutonomousDriving.pdf。
德国虽在自动驾驶技术研发方面稍逊于美国,但其政府与立法机构却一直努力引领自动驾驶法律规制。德国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委员会于2013年组建由政府、产业界、协会及学术界专家组成的自动驾驶圆桌会议作为自动驾驶政策咨询机构,并在该咨询机构工作基础上于2015年9月发布了《自动和联网驾驶战略》,旨在保持德国作为领先供应商、世界领先市场、规则建立者的地位,积极推动自动驾驶等工业4.0关键技术在德国的研发、测试与投入生产。(11)BMVI.Strategie automatisiertes und vernetztes Fahren,S.3-4,https://www.bmvi.de/SharedDocs/DE/Publikationen/DG/broschuere-strategie-automatisiertes-vernetztes-fahren.pdf?__blob=publicationFile.作为该战略实施贯彻的结果,德国政府近年修订了国内法律框架,推进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发布了针对自动驾驶的伦理准则《自动化和网联化车辆交通伦理准则》,并积极参与构建自动驾驶的欧盟及国际标准规范,在该领域创设自动驾驶框架前提条件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德国原则上允许所有德国区域和道路开放自动驾驶测试,道路测试主要由《德国道路许可规定》规范,自动驾驶牌照发放及测试属于州权限范围,在开放道路测试的车辆必须由人类驾驶员可以随时介入,自动驾驶系统须随时能够开启或关闭。(12)https://www.bmvi.de/DE/Themen/Digitales/Digitale-Testfelder/Digitale-Testfelder.html.如果自动驾驶车辆无法满足一般的车辆生产许可邀请,可以根据《德国道路许可规定》第21条申请单独生产许可或根据该规定第70、71条获取例外批准。
2018年4月,我国交通部、工信部与公安部出台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地方性实施细则,对自动驾驶道路测试主体、测试驾驶人及测试车辆应具备的测试条件与义务、测试车辆事故数据管理、交通事故处理等予以规范。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划分为通用技术测试、专项技术测试与试运营测试三大类型。(13)参见《〈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政策解读》,http://jtw.beijing.gov.cn/xxgk/zcjd/202011/t20201119_2140422.html。在自动驾驶发展初期部署试点示范项目,能够在可控范围内促进产业链创新,完成自动驾驶的技术验证、功能测试、性能检测等任务,并将自动驾驶安全可靠地引入交通系统。(14)参见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研究中心:《全球自动驾驶战略与政策观察(2020)》,http://www.caict.ac.cn/kxyj/qwfb/ztbg/202012/t20201229_367256.html。在自动驾驶由研发测试转向示范应用的发展趋势下,我国各地政府也开始出台指导自动驾驶示范应用的规定。2019年9月,上海出台了《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15)参见《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管理办法(试行)》(沪经信规范〔2019〕7号),http://www.sheitc.sh.gov.cn/cyfz/20190910/0020-683620.html。,成为全国首个颁发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应用牌照的城市。2020年8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局、公安交通警察局发布了《深圳市关于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的指导意见》(16)参见《深圳市关于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的指导意见》(深交规〔2020〕6号),http://jtys.sz.gov.cn/zwgk/xxgkml/zcfgjjd/gfxwjcx/content/post_7989105.html。,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细分场景的应用示范工作,允许在制定应用示范方案和应急预案、统一安装车载终端等条件下申请开展载人应用示范、城市环卫作业应用示范、载货及其他专项作业(第2条)。在各地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及示范应用规定基础上,2021年7月,工信部、交通部、公安部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工信部联通装[2021]97号)(17)参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https://www.miit.gov.cn/jgsj/zbys/gzdt/art/2001/art_ab9a6a34a61842df8c90793bf1672327.html。,以推动汽车智能化、网联化技术应用和产业发展,规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表明我国自动驾驶从道路测试到示范应用、再到商业应用的路径已日渐清晰。
2.商业应用探索阶段
随着自动驾驶技术的进步及技术安全性在道路测试中逐步得到验证,自动驾驶技术在公共道路上商业化应用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美国为在联邦政策层面协调各州自动驾驶立法与行政命令,2016年9月,美国交通部通过国家高速公路管理局发布了《自动驾驶政策》,规定自动驾驶技术级别及适用于自动驾驶车辆开发测试与生产阶段的实践指引,目前已相继发布了四版《自动驾驶政策》指引文件。(18)USDOT Automated Vehicles 2.0 Activities,https://www.transportation.gov.据美国国家立法机构会议的统计,2012年至2021年,美国至少有4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审议了自动驾驶相关立法,2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颁布了自动驾驶相关立法,11个州颁布了州长行政命令(19)Autonomous Vehicles Self-Driving Vehicles Enacted Legislation (ncsl.org),https://www.ncsl.org/research/transportation/autonomous-vehicles-self-driving-vehicles-enacted-legislation.aspx.;2017年至2019年,有22个州的自动驾驶立法涉及商业化应用。(20)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Issues in Autonomous Vehicle Testing and Deployment,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R/R45985.
德国2017年5月通过了《道路交通法(第八修正案)》,以修法方式对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技术进行概括性准入,以突破现有行政监管与法律框架对自动驾驶的桎梏,明确允许使用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功能操作车辆,只要该自动驾驶功能“按规定使用”(第1a条第1款),成为世界上首个对自动驾驶技术进行法律准入的国家。2021年7月,德国通过了《道路交通法和强制保险法修正案——自主驾驶法》,标志着德国已跨越自动驾驶公共道路的自动驾驶、无人驾驶车辆测试阶段,开启公共道路商业应用,并根据自动驾驶技术级别的演化与发展引入L4级别自动驾驶。(21)Straßenverkehrsgesetz in der Fassung der Bekanntmachung vom 5.März 2003 (BGBl.I S.310,919),das zuletzt durch Artikel 1 des Gesetzes vom 12.Juli 2021(BGBl.I S.3108)geändert worden ist,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stvg/BJNR004370909.html#BJNR004370909BJNG000101308.
我国目前自动驾驶的法律文件主要局限于道路测试领域,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应用的法律基础阙如,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发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与合规瓶颈,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机动车概念及相关汽车产品标准仍然拘泥于机械驾驶时代的技术框架,未引入自动驾驶汽车或智能网联汽车概念并根据该概念做出弹性标准规定。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框架下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禁止驾驶员在驾驶机动车时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以及禁止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上述规定在L3及以上级别自动驾驶技术条件下不仅不合时宜,而且成为后者商业落地之路上的法律路障。2021年3月,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公布了《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22)http://www.szrd.gov.cn/szrd_zyfb/szrd_zyfb_tzgg/202103/t20210323_19416162.html.,对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准入和登记、使用管理、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车路协同基础设施、道路运输、交通事故及违章处理、法律责任等问题进行规定,突破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和示范应用阶段,扩展至自动驾驶车辆准入、应用、事故处理等阶段,是我国第一部规制自动驾驶商业应用的地方性立法。若获通过,该条例即成为国内第一部针对智能网联汽车的地方专门性立法,标志着我国自动驾驶立法正式扩展到商业应用领域。2021年3月,公安部公布了《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23)https://www.mps.gov.cn/n2254536/n4904355/c7787881/content.html.,对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进行道路测试和通行、违法和事故责任分担做了规定。该修订建议稿的公布意味着在国家法律层面自动驾驶立法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限于主题与篇幅,本文并不专门探讨自动驾驶致损责任制度这一事后法内容,而是更加聚焦地在自动驾驶准入法上回应自动驾驶技术产业落地与发展所提出的合法化需求,从自动驾驶技术产品准入与自动驾驶使用(即交通驾驶或参与行为层面)探讨自动驾驶商业落地的方案。但由于上述两方面的事前规制手段涉及产品准入法与交通行为法的行为规范与注意义务设定,也为自动驾驶事故责任追究提供了依据与标准,故也将在产品准入法与交通行为法方案中附带探讨相关责任问题。
二、自动驾驶准入法制定
自动驾驶汽车的商业应用首先面临自动驾驶汽车上市与使用准入法方面的障碍,故应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概念中引入自动驾驶或智能网联汽车概念,允许自动驾驶汽车在道路上通行,并尽快建立自动驾驶汽车产品准入制度标准,推动自动驾驶技术产业化发展与大规模商业应用。
(一)自动驾驶的应用准入:自动驾驶概念的技术功能性界定
我国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条第3项将机动车界定为:“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行驶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轮式车辆。”该机动车概念仍然停滞于机械驾驶技术时代,在智能驾驶技术条件下已显得不合时宜,应根据最新自动驾驶技术发展在我国法律中引入自动驾驶概念,对其进行技术功能性界定。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第155条引入了自动驾驶汽车相关规定,但并未对自动驾驶汽车予以定义,仅在第150条将机动车概念修改为:“‘机动车’,是指以动力装置驱动或者牵引,上道路通行的供人员乘用或者用于运送物品以及进行工程专项作业的、符合机动车国家标准的轮式车辆。”试图通过增加“符合机动车国家标准的轮式车辆”的表述来涵盖智能网联汽车,但这种仅仅通过标准扩容而舍弃法律界定的方式过于含糊、简略。我国于2021年7月最新发布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附则第37条第1款),关于自动驾驶汽车的定义采用了产业界通行的智能网联汽车的概念: “本规范所称智能网联汽车是指搭载先进的车载传感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并融合现代通信与网络技术,实现车与X(人、车、路、云端等)智能信息交换、共享,具备复杂环境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等功能,可实现安全、高效、舒适、节能行驶,并最终可实现替代人来操作的新一代汽车。智能网联汽车通常也被称为智能汽车、自动驾驶汽车等。”该概念也为《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所采纳(第3条)。该规定侧重于描绘自动驾驶的技术融合性特征与效益愿景,是一种技术描述性概念,未指明自动驾驶应达到的技术功能,也未能反映自动驾驶系统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并非规范的、功能性的法律概念。这种概念规定缺乏法律上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无法为行为人提供行为指引及界定注意义务,也无法为损害事故发生后的归责与追责提供依据。
德国2017年修改的《道路交通法》引入第1a条第2款对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技术进行法律界定,规定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汽车是拥有技术设备以实现下述功能的车辆:“1.为完成驾驶任务(包括纵向和横向导轨),能在车辆启动后控制车辆;2.在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功能控制车辆的过程中,能够遵守指引车辆行驶的交通法规;3.可以随时被驾驶员手动接管或关停;4.可以识别由驾驶员亲自控制车辆的必要性;5.可以以听觉、视觉、触觉或者其他可被感知的方式向驾驶员提出由驾驶员亲自控制车辆的要求,并给驾驶员预留接管车辆的充足时间;6.指出违背系统说明的使用。自动驾驶汽车的制造商必须在系统说明中做出有约束力的声明,表明其汽车符合前述条件。”(24)Straßenverkehrsgesetz in der Fassung der Bekanntmachung vom 5.März 2003 (BGBl.I S.310,919),das zuletzt durch Artikel 1 des Gesetzes vom 12.Juli 2021 (BGBl.I S.3108) geändert worden ist,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stvg/BJNR004370909.html#BJNR004370909BJNG000101308.
德国《道路交通法》最新修正案引入L4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规定,允许在特定运行区间具备相应技术条件的车辆在保障技术监督员能够及时介入的情况下进行无人驾驶。笔者根据其第1e条规定将车辆配备的技术设施应达到的功能梳理如下:(1)在指定运行区域内独立完成驾驶任务,无须驾驶员进行干预,也无须技术监督员持续监控车辆行驶状况;(2)在只有违反交通法规才能继续行驶时主动进入最低风险状态(减速或在安全地带停车),并及时通知技术监督员;(3)配备避免碰撞系统,在损害发生不可避免(即道德困境)时应分析不同法益的重要性,优先保护人类生命,在对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无法避免时,不将个人特征作为判断权重;(4)应能识别出系统极限、技术故障,并能够向技术监督员及时发出通知;(5)可以随时由技术监督员停止运行,当技术监督员停止车辆运行时,车辆主动进入最低风险状态。只有具备上述技术条件的生产商,才可以向联邦机动车管理局申请获得自主驾驶功能的车辆的运营许可。(25)Straßenverkehrsgesetz in der Fassung der Bekanntmachung vom 5.März 2003 (BGBl.I S.310,919),das zuletzt durch Artikel 1 des Gesetzes vom 12.Juli 2021 (BGBl.I S.3108) geändert worden ist,http://www.gesetze-im-internet.de/stvg/BJNR004370909.html#BJNR004370909BJNG000101308.
上述规定在法律层面界定了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技术须达到的自主驾驶控制、人车切换等安全攸关的功能条件,为不同级别的自动驾驶技术设定了法律要求,以确保道路安全、生命健康、财产等重大法益不受侵害。我国立法者可以考虑借鉴德国交通法自动驾驶车辆的功能定义,将自动驾驶技术应达到的最低技术功能条件作为法律概念界定的依据,引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附则第119条第3项关于“机动车”的规定之中,增加自动驾驶汽车或智能网联汽车作为机动车的新技术类型。这种从技术功能角度界定自动驾驶汽车概念的模式实际上也框定了其产品技术准入门槛,即规定自动驾驶汽车上路应用须达到何种技术功能要求。这种概念规定也界定了生产商(包括整车制造商及自动驾驶系统提供商)设计、制造自动驾驶汽车整车、配件及自动驾驶系统的注意义务类型,例如自动驾驶控制功能、系统无法胜任时的识别及提醒功能、人车切换功能、最小风险管理功能等分别对应厂商或系统提供商保证交付车辆具备相应功能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后追责的法律依据,为责任制度这一事后规制工具与准入制度这一事前规制工具提供了有机衔接。
(二)自动驾驶车辆产品准入
根据我国《标准化法》第10条的规定,汽车标准属于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强制性产品准入成为目前自动驾驶汽车量产的桎梏,例如,我国 GB 11557-2011《防止汽车转向机构对驾驶员伤害的规定》中要求转向必须由驾驶员通过转向盘直接操作的规定,以及现阶段自动驾驶系统、人机交互、数据记录等技术标准,都滞后于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商用化(产品准入)需求,阻碍自动驾驶技术创新及商用化步伐。(26)参见刘宇、申杨、柳贾宁:《智能网联汽车商用化的市场准入路径》,载《汽车纵横》,2020(11)。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第155条规定:“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开展道路测试应当在封闭道路、场地内测试合格,取得临时行驶车号牌,并按规定在指定的时间、区域、路线进行。经测试合格的,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准予生产、进口、销售,需要上道路通行的,应当申领机动车号牌。”但该法并未对自动驾驶产品准入做规定。《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14条虽引入了智能网联汽车的产品准入制度,规定“符合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地方标准或者团体标准的产品,列入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目录。在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制定公布前,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可以向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提出产品相关准入条件豁免申请,经评估同意,列入深圳市智能网联汽车产品目录”,但该规定一方面缺乏上位法基础,另一方面在相应地方标准与团体标准暂付阙如的情况下易陷入依赖豁免程序的死循环,阻碍常态化的产品准入制度的建立,故有必要尽快构建我国自动驾驶产品准入制度与标准。
为构建我国自动驾驶产品准入制度,推动自动驾驶汽车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工信部于2021年4月发布了《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就智能网联汽车应达到的技术功能、生产企业安全保障能力、产品准入过程保障、产品准入测试等做了规定。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准入过程保障要求包括整车尤其是驾驶自动化系统的功能安全过程保障要求、驾驶自动化系统预期功能安全过程保障要求和网络安全过程保障要求(附件2),体现了自动驾驶等人工智能产品准入的动态性特征,即不仅要求产品出厂时符合安全标准,也要求生产者对自动驾驶系统运行中的安全风险能够识别、防御(包括对系统无法胜任驾驶任务的识别及对网络攻击等风险的识别、防御),也符合上述美国学者Smith所绘制的系统技术标准规定、过程性监管规定、准入门槛规定图谱。2021年8月,工信部印发《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工信部通装〔2021〕103号),要求企业履行产品性能告知义务、加强组合驾驶辅助及自动驾驶功能产品安全管理,确保汽车能自动识别自动驾驶系统失效及是否持续满足设计运行条件、采取风险减缓措施以达到最小风险状态、进行人机交互切换、事件数据记录系统和自动驾驶数据记录系统,以及满足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网络安全等过程保障要求。
因此,自动驾驶技术产品准入法层面不仅要求自动驾驶车辆及系统设计、制造须达到传统汽车的安全技术标准,而且须达到自动驾驶所要求的环境感知监控、动态驾驶任务、人机协作共驾等技术标准。(27)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vehicles with regards to Automated Lane Keeping System,ECE/TRANS/WP.29/2020/81,https://undocs.org/ECE/TRANS/WP.29/2020/81.如果说传统工业时代汽车等产品的准入标准是单向的、静态的标准,即产品在投入市场时应达到的功能水准相对确定、封闭,那么人工智能时代的自动驾驶汽车等智能产品的准入标准就相对具有不确定性与开放性,多变的交通场景、开放的网络与数据环境以及算法自动决策因素决定了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标准呈现动态的、过程性的特点。传统工业产品的生产商只需将产品投入市场即完成任务,不再参与产品的使用环节,而智能产品尤其是智能网联汽车的生产商则需继续参与汽车的使用(交通驾驶过程),需要对自动驾驶系统进行持续的监督、更新,否则可能因驾驶系统的训练数据缺陷或软件安全漏洞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例如,2020年6月,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下属的联合国世界车辆法规协调论坛(简称为UN/WP29)通过了《联合国统一车辆信息安全与信息安全管理系统审批规定》(Proposal for a new UN Regulation on 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vehicles with regards to cyber security and cyber security management system)(28)https://unece.org/DAM/trans/doc/2020/wp29grva/ECE-TRANS-WP29-2020-079-Revised.pdf.与《联合国统一软件升级与软件升级管理系统审批规定》(Proposal for a new UN Regulation on uniform provisions concerning the approval of vehicles with regards to software update and software updates management system)(29)https://undocs.org/ECE/TRANS/WP.29/2020/80.,规定生产商须履行持续的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与算法、软件更新义务。上述工信部《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也要求企业应加强数据和网络安全管理、规范软件在线升级等,确保在线升级安全、保证技术参数变更不影响产品一致性等。
(三)自动驾驶技术级别准入
自动驾驶技术尚未完全发展成熟,仍处于不断的技术升级过程中,在进行立法概括准入时,应在立法中妥当解决法律的安定性与技术快速迭代之间的张力,立法与最新技术发展保持同步的同时预留未来技术发展空间。
SAE自动驾驶国际通行标准于2021年4月进行了更新,文件引入了远程协助与远程驾驶等概念。远程协助是指在无人驾驶情形下,当自动驾驶系统遇到未知的交通形势而不知如何继续行程或完成驾驶任务时,由在车外的人员向车辆发出指令,协助其继续完成驾驶任务,使得L4、L5级别更具有可操作性。如上所述,德国最新《道路交通法》修订草案也新增L4自动驾驶技术级别并引入自动驾驶远程监督的技术方案。相比之下,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规定的自动驾驶技术级别相对落后、保守,其第155条第3款规定:“具有自动驾驶功能但不具备人工直接操作模式的汽车上道路通行的,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另行规定。”由此可见,目前公安部的修订建议稿主要针对L3(有条件自动驾驶)技术级别,技术上较为滞后。《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3条第2款规定:“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包括有条件自动驾驶、高度自动驾驶、完全自动驾驶三个技术等级。”由此可见,该条例虽涵盖L3、L4甚至L5技术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但对具体技术实现路径未做规定,更未涉及远程驾驶辅助等规定。不过,我国得益于5G通信技术居世界领先地位,且采取车路协同技术路线,百度等车企在车路协同、5G云代驾技术、自动驾驶平台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研发探索,未来我国自动驾驶立法应在自动驾驶技术级别方面与国际最新技术保持同步,不局限于《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所限定的L3级别的自动驾驶车辆,要对L4、L5级别进行概括性的立法准入,树立符合世界一流自动驾驶技术水平的最先进自动驾驶立法典范。
三、交通行为法规范调整:以人机协作为中心
由于自动驾驶技术应用于开放的公共交通场景,其法律准入不仅涉及技术与产品准入,也涉及上述场景下技术应用的许可性与适应性问题,因而需要在交通法上赋予自动驾驶车辆合法地位并对其使用行为进行规范,根据自动驾驶技术特征构建驾驶人与生产商的行为法规范。机械驾驶时代对使用或驾驶车辆的人类驾驶员行为通过交通法进行规制即可,而智能驾驶时代自动驾驶车辆生产商或供应商也通过对自动驾驶系统的控制参与到道路交通之中,因而在行为法层面除规制传统的人类驾驶行为之外,也需对自动驾驶车辆生产商或系统供应商的行为进行规制。
(一)自动驾驶模式“驾驶人”的定义与定位
自动驾驶融合了电子控制、人工智能、网络通信及互联网技术等,对原有以人类驾驶员为核心的车辆功能、作用的重新定位,不仅改变了人类驾驶员在环境感知、分析决策及车辆控制等驾驶任务中的作用和职责,逐步分担驾驶任务并最终完全替代人类驾驶车辆,而且将由此改变自汽车问世以来人类以汽车为交通工具所形成的生活、工作方式以及经济、社会和法律环境与秩序。(30)参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https://www.miit.gov.cn/gzcy/yjzj/art/2021/art_bd5ef75343a44e01b3bc87cb7593bc45.html。传统道路交通法对交通参与人的行为法规范是根据机械驾驶时代的车辆技术、道路设施条件以人类驾驶员为中心设定的,应根据自动驾驶时代驾驶操作从以人类为中心逐级到以自动驾驶系统为中心的过渡规律,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中不符合上述转变的技术规范与行为规范,以适应L3以上级别自动驾驶技术条件发展的要求。在L3以上的高级别自动驾驶技术模式下,自动驾驶系统进行环境感知、路径规划,与人类驾驶员协作甚至主导驾驶操作,机械驾驶时代的人—机关系发生改变,使得传统的“驾驶人”的角色功能也发生改变,人类虽然仍坐在车内,但并不必须亲自完成驾驶操作,而是可以从事阅读、接听电话等非驾驶活动,形成自动驾驶时代所谓“没有马车夫的马车”这一新的交通风景线。因此,对于L3以上级别的自动驾驶而言,到底是谁在“驾驶”飞驰在道路上的汽车,如何在法律上界定车内的人类角色,是智能交通法律首先必须思考的问题。
1.人类驾驶员作为驾驶人方案
德国《道路交通法》也对自动驾驶模式下的人类驾驶员做出了明确的“驾驶人”(Fahrzeugfuehrer)法律定位,规定驾驶员也包括“启动该法定义的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功能、利用其控制汽车驾驶的人,即使其在按规定使用该功能的时候不亲自驾驶车辆”(第1a条第3款),赋予驾驶人借助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功能不亲自进行驾驶操作的权利(第1b条第1款)。德国《道路交通法》通过上述驾驶人定义将操作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的人等同于驾驶人,这一驾驶人定位意味着其法律地位与机械驾驶时代的驾驶员的地位并无根本差异,具有以下两重含义:
其一,该法将自动驾驶系统视为帮助人类完成驾驶操纵的技术手段或工具,仍维持了人类驾驶员的核心角色定位。该法第1a条第2款第3项规定,只有在驾驶员能够随时接管或关停自动驾驶功能时,使用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功能才是法律许可的。这意味着驾驶员随时可能重新亲自操纵驾驶,仍然对车辆控制有自由决定的空间,只要其亲自控制或者随时能够重新控制车辆,就对车辆驾驶具有事实上的支配力,就属于《德国交通法》第18条第1款意义上的驾驶人。(31)Vgl.Buck-Heeb,Dieckmann.“Die Fahrerhaftung nach § 18 I StVG bei (teil-)automatisiertem Fahren”,NZV,2019:113.
虽然其第1b条对高级别自动驾驶的驾驶人新增了警觉义务与接管义务,但仍保留了人类驾驶员或操作员的驾驶人主体地位,在责任制度方面也维持以车主责任为主导的交通事故责任分配结构。(32)Vgl.Greger.“Haftungsfragen beim automatisierten Fahren”.NZV,2018:1,5.这表明该部交通法仍然承袭了机械驾驶时代的技术底色,采取渐进式的立法路线,并未改变驾驶人、车主、汽车制造商之间的基本权利义务格局。
其二,赋予操作自动驾驶系统的人以驾驶人地位,也暗含着否定自动驾驶系统主体地位之意。这一立法决定追随欧盟学界的主流意见,未采纳《就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向欧盟委员会的立法建议(2015/2103(INL)》赋予具有深度学习能力和自主性的最复杂的智能机器人以“电子人格”(Electronic Person)的法律地位和责任主体地位的倡议。(33)European Parliament Resolution of 16 February 2017 with Recommendations to the Commission on 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 (2015 /2103 (INL)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A-8-2017-0005_EN.html?redirect.虽然自动驾驶具有算法决策功能,能够根据行车目标、车辆状态及环境信息等,通过状态机、决策树、深度学习、增强学习等决策方法进行路径规划与驾驶操纵(34)参见李克强等:《智能网联汽车(ICV)技术的发展现状及趋势》,载《汽车安全节能学报》,2017(1)。,但这种决策机制不同于人类大脑的决策,依赖于算法模型、训练数据,不能视为意志自由基础上的自主决策及意思表示。(35)参见王莹:《法律如何可能?——自动驾驶技术风险场景之法律透视》,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6)。
2.自动驾驶车辆生产商或供应商作为驾驶人方案
关于谁是自动驾驶车辆处于自动驾驶模式的“驾驶人”,美国联邦交通管理局曾将Waymo L4级别以上的自动驾驶系统解释为驾驶者。(36)谷歌在2015年向美国联邦交通管理局提交无需人类驾驶员的无人驾驶汽车计划,交通管理局在其问询答复中声称,可以将其设计的自动驾驶系统视为驾驶员,认为其设计的汽车将没有过去一百多年历史意义上的驾驶员。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谷歌是否能够证明及如何证明其自动驾驶系统能够满足带有驾驶员的汽车的标准。参见https://www.digit.in/news/car-tech/googles-self-driving-car-ai-can-be-considered-as-the-driver-28964.html。美国州自动驾驶相关立法或者并未对该问题明确规定,或者做出不相一致的规定。美国《车辆自动驾驶操作法案》建议将自动驾驶供应商定义为车辆在自动驾驶模式下的“驾驶人”:一个有资格的实体(Entity)可以向州声明它愿意成为特定自动驾驶车辆的法律意义上的驾驶人(legal driver)。(37)Automated Operation of Vehicles Act,https://www.uniformlaws.org/HigherLogic/System/DownloadDocumentFile.ashx?DocumentFileKey=ff535c03-32e1-7cd8-4f6b-f48a12017c41&forceDialog=0.自动驾驶供应商可能是自动驾驶系统开发商、车辆制造商、配件供应商、数据供应商、车队运营人、保险公司,隶属于上述主体的公司或者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市场参与主体,重要的不是其在供应链或商业模式中的特殊角色,而是其是否愿意被识别为驾驶人以及是否有能力满足该法案所规定的技术及法律要求。
该法案将自动驾驶供应商规定为自动驾驶车辆处于自动驾驶模式的驾驶人的构想,超出了对驾驶人概念的传统理解,颇具创见。Bryant Walker Smith教授倡导对“驾驶”进行符合自动驾驶技术进步与驾驶安全性宗旨的目的理性的解释,认为驾驶并不局限于传统交通法概念上的理解,即从驾驶座位上对车辆进行直接操纵或对车辆移动进行物理上的控制支配,而是可以包括自动驾驶系统算法的智能操纵。(38)Bryant Walker Smith.“Automated Vehicles Are Probably Legal in the United States”,Tex.A&M L.Rev,2014(1):433-439.其作为上述法案报告的主撰写人,将自己的上述学术观点应用于法案的驾驶人定位方案,将参与自动驾驶研发或系统运营并能保证满足自动驾驶技术与法律要求的机构或个人界定为自动驾驶模式的驾驶人。
将自动驾驶供应商规定为自动驾驶车辆处于自动驾驶模式的驾驶人,不仅是法律概念选择或解释路径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该概念所带来的交通法上的法律主体地位、相关交通参与人的行为规范、权利义务及责任分配等一系列法律问题。显然,将自动驾驶供应商定义为驾驶人,也就将自动驾驶供应商纳入交通法的规制对象范围,成为道路交通参与主体,赋予其与传统驾驶人相同的权利及施加相同的义务,例如关注路况、遵守交通规则、谨慎驾驶等。如若违反交通法上的注意义务,则也应如同传统驾驶人一样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国现行交通法将驾驶主体界定为经过培训持有驾驶执照的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9条第1款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19条第1款规定:“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的人,可以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将经测试主体授权负责测试并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对测试车辆实施应急措施的驾驶人称为“测试驾驶人”(第6条),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征求意见稿)为了涵盖示范应用情形,又将“测试驾驶人”改为“驾驶人”。上述自动驾驶路测及示范应用阶段的部门法规章均使用“驾驶人”概念,以与道路交通法机动车驾驶人的概念及内容相衔接。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未对上述机动车驾驶人的规定进行修改,第155条第2款规定:“具有自动驾驶功能且具备人工直接操作模式的汽车开展道路测试或者上道路通行时,应当实时记录行驶数据;驾驶人应当处于车辆驾驶座位上,监控车辆运行状态及周围环境,随时准备接管车辆……”这一修订也延续了上述测试规定的规制经验,将利用自动驾驶系统完成驾驶任务的人赋予等同于驾驶人的法律地位,从而形成对德国道路交通法修订经验的路径依赖。
在L3级别自动驾驶技术条件下采取这种渐进式立法路线,可以避免对驾驶员、汽车制造商及其他交通参与人间的权利义务格局造成冲击,有利于降低立法成本及维护法的安定性。但由此会产生自动驾驶模式下人类驾驶员与自动驾驶系统驾驶权重叠与权限界分问题,对此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二)驾驶行为规范调整:警觉义务、接管义务、最小风险管理义务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不得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等。鉴于L3以上级别自动驾驶技术能够代替人类进行部分环境感知、路径规划与驾驶操纵,从而允许驾驶员抽离或短暂抽离驾驶行为,上述规定在技术进步面前已经不合时宜。如何根据L3、L4级别的技术特点进行自动驾驶系统与人类驾驶员的权限分配,实现交通风险的最优化管理,是当前自动驾驶法律准入的核心内容。
1.人机协作的驾驶权限分配与风险分担
德国《道路交通法》虽然将启动并利用自动驾驶功能完成驾驶任务的人定义为驾驶人,以赋权或扩权的方式(即赋予驾驶员借助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功能不亲自进行驾驶操作的权利)为自动驾驶技术的使用予以法律准入,但同时也根据L3级别自动驾驶的人机协作技术要求引入新的驾驶人义务,即施加其对驾驶环境保持警觉的义务和在自动驾驶系统不能胜任时的接管义务(第1b条第2款)。警觉义务是指在不亲自驾驶的期间,必须保持警觉,以便能随时履行法定的接管义务。接管义务是指,当高度或完全自动系统向驾驶员发出接管请求、驾驶员意识到或者基于明显状况应当意识到车辆不再具有高度或完全自动驾驶功能所预设的使用条件时,有义务立即接管汽车驾驶。
《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第26条规定:“道路测试、示范应用驾驶人应在车内始终监控车辆运行状态及周围环境,当发现车辆处于不适合自动驾驶的状态或系统提示需要人工操作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第155条第2款也规定了驾驶人保持警觉的义务及接管车辆的义务。上述规定是否妥当,值得深思:
其一,L3级别自动驾驶技术条件下驾驶人究竟具有多大的抽离驾驶行为的行动范围,以及仍然保留多大程度的驾驶行为约束,在法律上制定确定的行为规范并非易事。在这一点上,德国的立法经验似乎也未尽如人意。德国学界有观点批判2017年修订的交通法赋予驾驶员更加严格的义务违背了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初衷,设置全程警觉与接管义务实际上并不符合L3 级别以上的自动驾驶技术的设定,因为L3级别自动驾驶感知技术能够通过算法决策完成主要驾驶功能并感知与监控交通状况,且能够在自动驾驶系统无法处理的情况下提醒驾驶员对车辆进行控制。如果要求驾驶员全程保持警觉并随时准备接管车辆,则极大削弱了自动驾驶系统的技术应用优势。(39)Vgl.Koenig.“Die gesetzlichen Neuregelungen zum automatisierten Fahren”,NZV,2017:123,124.自动驾驶允许人类驾驶员从驾驶任务中抽离,不需要始终监控环境,需要的仅是最低程度的注意以能够重新接管车辆。因此,开启自动驾驶功能而不对环境进行监控本身并不违反注意义务,只有违反了最低警觉要求才违反注意义务。但最低警觉的注意义务的类型及具体内容并不明确,哪些驾驶以外的行为是法律所完全许可的也并不确定。法律规定的逻辑结论只能是,开启自动驾驶功能的驾驶人应确保事实上在有必要时立即控制车辆。(40)Vgl.Lüdemann,Sutter,Vogelpohl.“Neue Pflichten für Fahrzeugführer beim automatisierten Fahren - eine Analyse aus rechtlicher und verkehrspsychologischer Sicht”,NZV,2018:411,414.所谓最低警觉的义务实际上很难界定,相当于施加了一般性的注意义务,妥当的做法是根据L3级别及以上的自动驾驶技术特点,将环境监控的义务完全转移给车辆,取消所谓警觉义务的规定。当车辆处于L3级别以上的自动驾驶模式时,系统就有义务在该运行区间内对环境进行监控并在发生无法胜任的突发交通形势下及时通知人类驾驶员,驾驶员有义务在接收信息通知后立即接管车辆;如未及时接管而导致交通事故的,由驾驶员承担交通过失的责任;若车辆未发出通知信息或发出通知信息不及时未给驾驶员预留适当最低反应时间的,由汽车生产商承担产品缺陷的质量责任。
德国最新立法修订仍保留了上述L3级别驾驶员的权利义务规定,未对学界批判做出回应,而是直接增加L4级别规定,允许车辆在特定运行区域取消驾驶员但设置技术监督员行驶。技术监督员无需对驾驶环境保持警觉,但当系统发出通知或在系统无法胜任、面临系统极限时,须从外部停止车辆运行,采取启动车辆的替代机动措施,或者在车辆进入最低风险状态时,立即与车内乘员建立联系,并启动必要的措施确保道路安全(第1f条第1款)。(41)Vgl.Haupt.“Auf dem Weg zum autonomen Fahren”,NZV,2021:172,175.
其二,既然L3级别下人类驾驶员的警觉义务、接管义务范围都存在争议,就更不宜将上述义务延续至L4级别。根据我国工信部《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及SAE自动驾驶级别国际标准,L4级别是在特定运行区间及条件下自动驾驶系统负责全部环境监管与动态驾驶任务,虽然可能在罕见情况下需要人类接管,但人类驾驶员接管并非实现交通安全所必须——人类驾驶员未及时接管时车辆可以进入最低风险状态,即减速或在安全地带停车。因此,上述《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与示范应用管理规范(试行)》与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建议稿)》的规定不符合L4自动驾驶技术级别的要求,也为人类驾驶员设定了过高的注意义务。根据该规定,若车辆未进行最低风险管理因而发生交通事故的,驾驶员因未履行警觉和接管义务须承担交通过失责任(可能是侵权责任甚或《刑法》第133条的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责任),未免过于严苛。而《深圳经济特区智能网联汽车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26条规定:“驾驶人应当按照道路交通规则及智能网联汽车使用手册的要求,掌握并规范使用自动驾驶功能。驾驶人应当在车辆发出接管请求或者车辆处于不适合自动驾驶的状态时立即接管智能网联汽车。”该条例未规定驾驶人的警觉义务,将监管环境的警觉义务全部转移给智能网联汽车或自动驾驶系统,从比较法的立法经验与教训上来看,更符合L3级别以上自动驾驶的技术特点,因而值得肯定。但该条例仍保留了接管义务的规定而未具体区分技术级别,值得进一步讨论。如果说L3级别设定驾驶员的接管义务是妥当的,但L4级别下人类驾驶员的接管并非驾驶安全所必须,在人类未及时接管时系统应进入最小风险状态避免事故发生,即条例第27条规定的最小风险运行原则:“车辆发生故障、不适合自动驾驶或者有其他影响交通安全的异常情况时,不配备驾驶人的智能网联汽车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移动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或者采取降低速度、远程接管等其他降低运行风险的有效措施。”也就是说,此时未及时接管引发交通事故的,应当归责给系统未及时采取最小风险运行措施,而不应归责给驾驶员,才符合该技术级别的特征与风险分担模式。因此,应取消L4级别人类驾驶员的接管义务,代之以车辆生产商的最小风险管理义务,既能防范因放松驾驶员义务权责衔接空白导致的交通安全危险升高,又可以避免权限重叠导致动态任务接管时发生互相推诿、无人负责的局面。可见,在L4级别下自动驾驶车辆生产商(包括系统提供商)应当承担更重的注意义务与责任,对其技术质量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深圳条例虽然引入了L4级别自动驾驶技术,但驾驶员行为规范及权利义务模式仍然停留在L3级别,导致技术与法律某种程度上的脱节。
2.可供选择的法律方案
在我国未来的《道路交通法》修订中,应根据不同技术级别的特征进行驾驶行为规范的妥适规定,可以考虑如下三种方案:
(1)分别针对L3、L4级别规定不同的行为规范和权利义务类型。针对L3级别设定生产商的环境监控义务与驾驶员的接管义务,针对L4级别设定生产商的环境监控义务与最小风险管理义务,此种安排的核心原理是根据不同技术级别的特征确定谁能最有效地控制交通安全风险,一旦确定后就排除其他主体的风险管控责任,以免出现因多个风险管控主体导致权限重叠和责任空挡。此种方案区分不同技术级别进行清晰的权责界定,但缺陷有二:一是要求清晰界定不同技术级别,因而对于处于技术级别过渡阶段的车辆可能存在解释适用上的困难;二是自动驾驶技术处于不断升级革新之中,如果自动驾驶商业应用跳跃L3级别进入L4级别,则L3级别的规定就面临过时与虚置。
(2)鉴于技术上对L3级别人机切换的安全性存疑,可以考虑在立法上直接跳跃或淡化对L3技术级别的规制,直接规定L4技术级别的交通行为规范与权利义务,对标最先进自动驾驶技术与法律解决方案。此种方案显然以L4级别自动驾驶技术的安全性与适用性得到产业验证为前提,但技术发展仍然面临一定开放性与不确定性。
(3)参考上述美国《车辆自动驾驶操作法案》建议将自动驾驶车辆或系统生产商、供应商作为驾驶人的立法方案,将人机协作切换问题纳入既有的法律框架内解决。既然自动驾驶模式下自动驾驶供应商是交通法上的驾驶人,那么其必须承担交通法上的注意义务,直至驾驶模式状态结束,切换为人类驾驶员驾驶模式。因此,人类驾驶员在自动驾驶模式下不需要保持警觉义务,只须在系统提示或自动驾驶模式结束时及时介入接管即可。即使人类驾驶员未及时接管也无需就因此引发的交通事故承担交通法上的责任,但不影响其交通法以外的其他法律责任的承担。由于此时仍是自动驾驶供应商在驾驶,为了避免事故发生,其应在技术上采取最小风险管理措施,例如减速、驶离道路或在安全地带停车。这就在自动驾驶技术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须趋向L4、L5级别的技术水平。此种方案基于不同的事前规制思路,也将提供不同的事后规制与责任模式选择:将生产商(包括供应商)纳入交通行为法规制范围,不仅可以追究其产品责任,也可以追究其交通过失责任,显然对其施加了更重的注意义务与责任,须考量保障交通安全与促进产业技术革新之间的平衡。
我国究竟采取何种自动驾驶模式的驾驶人定位及交通行为法规范方案,是自动驾驶商业应用法律准入面临的具有挑战性的路径选择问题,需要在综合平衡自动驾驶技术创新与交通参与人法益保护的基础上,根据立法时机与自动驾驶技术的发展水平做出妥当的立法决策。若L4级别自动驾驶成熟度在更广泛的测试与示范应用中得到进一步提升与验证,则第二种方案对标最先进自动驾驶技术与法律解决方案,直接规定L4技术级别的交通行为规范与权利义务,有利于维护法的安定性,在立法上更具科学性、前沿性。
综上,虽然目前自动驾驶技术尚无法消除开放道路复杂性所带来的所有交通风险,例如存在极端天气、罕见、突发交通形势等系统边界情形,但这并不应成为自动驾驶技术立法准入的障碍。随着自动驾驶L3级别技术的逐步成熟,有必要在产品准入法与交通行为法中引入自动驾驶技术:在产品准入法层面,需要引入自动驾驶技术功能性概念并建立动态的、细化的准入标准,不仅须注重自动驾驶车辆出厂时的系统安全性等静态标准,更须注重对自动驾驶进行全生命周期的过程性监管与动态准入,施加生产商或系统供应商的网络安全维护义务、算法更新义务;在交通行为法方面,需要根据自动驾驶技术的特征对驾驶人进行正确的法律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环境警觉义务、接管义务、最小风险管理义务等行为规范的创设与调整,既为自动驾驶商业应用提供妥适的事前规制框架,也为事故损害的发生提供事后规制及追责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