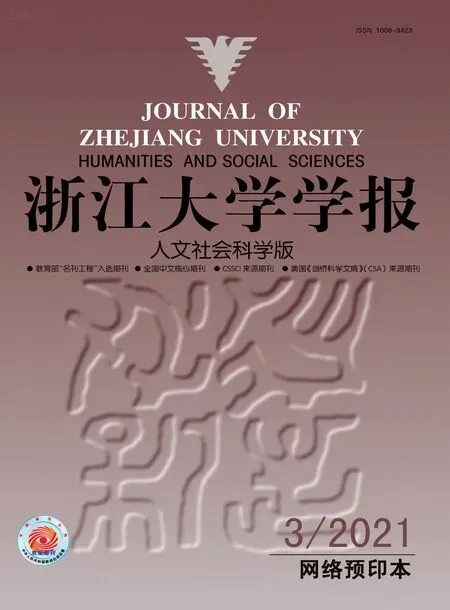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规范内涵
朱晓峰
(中央财经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人格权编中明确规定自由概念的条款有三个:一个是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该款规定了人身自由概念;另外两个是第一千零三条和第一千零一十一条,规定了行动自由概念。从这两个概念在《民法典》体系中的具体位置来看,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人身自由是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并非具体人格权[1]17;而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的行动自由则是具体人格权。行动自由往往表现为身体移动的自由,因此在《民法典》的权利规范体系上被纳入身体权框架[2]138,但是鉴于行动自由强调的重点在于自然人对其身体行动的自主决定权不受外界干预,因此我国学理上认为可以扩张解释其内涵而将从事特定活动的自由也纳入第一千零三条规定的行动自由范畴[3]93。亦即言,在人身自由和行动自由的规范关系界定上,应当将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行动自由与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予以明确区分,以便在统一的人格权概念体系下界定《民法典》中人身自由的内涵与规范边界,从而为一般人格权条款的具体适用奠定基础。
一、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理论争议与法典选择
在《民法典》之前,尽管学理上不乏批评之声,但我国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的一般性制定法如《侵权责任法》始终没有出现关于自由或者人格自由等更具有一般意义的概念[4]90。相较而言,《妇女权益保障法》(1992 年)第三十四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 年)第二十五条、《国家赔偿法》(1994 年)第三条、《劳动法》(1994 年)第三十二条、《执业医师法》(1998 年)第四十条、《婚姻法》(2001 年)第十一条等明确规定了自然人的“人身自由”受法律保护。在这些具体的制定法中,人身自由无一例外地都是作为具体人格权而被规定和保护的[5]70。对此,实践中有法院在判决书中明确表示,“人身自由是指身体活动的自由,即可以通过人的自主意志控制肢体行为等物理活动上的自由”①详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川01 民终15876 号。。但司法实践也并未完全坚守前述制定法的立场,最高人民法院2001 年发布的司法解释即法释〔2001〕7 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三项即直接规定“人身自由权”并将之与“人格尊严权”并列,共同作为一般人格权对待[6]26。2017 年的《民法总则》虽然没有如法释〔2001〕7 号一样径直规定“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权”,但其将“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并列规定在第一百零九条,并置于第五章“民事权利”之首[7]257。这实质上是将之前制定法中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对待[8]750。由此导致的问题是,《民法典》究竟应如何对待人身自由?
(一)《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学理分歧
对此,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学理上存在不同意见。
人身自由否定论认为,人身自由是一种具体人格权,若将之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会导致一般人格权的涵摄能力降低,无益于法律创制一般人格权规则之立法目的的实现[9]49。徐国栋教授主编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即没有明确宣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10]83。
人身自由肯定论认为,宪法第三十七条以及《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等均已使用人身自由概念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表述,基于现行法秩序之外在概念体系一致性的考虑,人格权编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概念表述应与之保持一致。
折中论认为,考虑到人身自由概念固有的缺陷以及我国现有法律体系中的制定法传统,人格权编对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应予宣示,但应当用其他更一般性的概念取代人身自由概念,以确保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开放性和价值基础彼此之间的合体系性。
折中论在学理上获得了更多的认同。例如,梁慧星先生主编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而被宣示出来的是“自由、安全和人格尊严”[11]44;王利明教授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则是将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规定为“人格尊严、人格平等和人格自由”[12]18;杨立新教授主持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的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分别是“人格尊严、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其中人格尊严构成价值基础的核心,包括保持和发展人格的自由[13]41。显然,折中论所使用的“自由”概念和“人格自由”概念均比肯定论的“人身自由”概念更符合法典外在体系基础概念彼此之间的逻辑规范要求。
(二)立法者的具体选择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的内部稿部分接受了否定论的观点,仅在第七条规定了人格尊严为人格权编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而将人身自由作为具体人格权之一种规定在身体权框架内[14]186。但之后草案的各审稿却再次回到了肯定论的立场而改变了内部稿的规定,重新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并列,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加以规定[15]367。尽管在草案审议过程中,仍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应将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修改为“人格平等、人格自由、人格尊严”,以提高一般人格权规则的涵摄能力[16]42,或者直接规定“民事主体享有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17]378,并且学理上也有观点坚持认为人格权是以人格平等为基点,以人格自由、人格尊严为双内核[18]138,但否定论与折中论的观点均未被最后的《民法典》所接受,《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全盘采纳了肯定论的基本立场[1]17。
事实上,在《民法典》编纂之初,立法者即明确表示:“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针对性的新规定。”[19]3这表明,我国立法者为此次《民法典》的编纂设定了两项基本目标:第一项目标是实现对现有法律规则的科学化、体系化的整理,实现民事立法的科学化、体系化①关于法典编纂的科学性以及法律条文表述技术和规则问题,可参见黄文煌《民法典编纂中的法条表达技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条文的梳理》,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1 期,第122 页。;第二项目标是对现有民事法律规则予以完善,从而及时回应现实生活对制定法提出的要求。就此而言,《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最后选择,即将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本来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直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加以规定,可能会导致原本内涵外延相对比较清晰的人身自由概念以及相应的具体法律规则的理解适用出现混乱。因为同一概念既是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又是具体人格权本身,在理解与适用上难免会出现法律体系自身的违反,这显然与第一项目标并不完全吻合。因此,在《民法典》全面施行的背景下,如何在具体概念的理解与适用上区分《民法典》第一百零九条以及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在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抽象意义上所使用的人身自由与《妇女权益保障法》(2018 年)第三十七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2013 年)第二十七条、《国家赔偿法》(2012 年)第三条、《劳动法》(2018 年)第三十二条、《执业医师法》(2009 年)第四十条等在具体人格权意义上所使用的人身自由,是学说理论与司法实务亟须解决的问题,另外对该问题的解决也可以间接回应立法者编纂《民法典》所追求的科学化与体系化的规范目的。
二、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的界定方式
对《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人身自由”的具体理解,既涉及《民法典》内部概念如人身自由和行动自由、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等概念的规范关系的认定问题,也涉及现行法律外部体系的概念、规则彼此之间的规范关系处理,尤其是与宪法第三十七条的人身自由、第三十八条的人格尊严之间的规范关系处理问题,还涉及以人身自由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的涵摄能力以及与此相关的立法目的的实现问题等,因此应仔细斟酌。
(一)《民法典》颁布后的理论分歧及评析
在《民法典》颁布后,对于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中规定的人身自由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学理上仍存在如下分歧:
一是人身自由误用论。该观点是法典编纂过程中的人身自由否定论的延续,其认为《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将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是一种失误。因为能产生其他人格权益的只能是抽象的人格自由而不是人身自由,后者是具体人格权,包括身体的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或者说人身自由作为一种独立的主观权利、具体人格权,不能成为另一个独立主观权利的渊源[20]76。依据该观点,该款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只能是人格尊严,或者人格尊严所代表的就是一般人格权,人格尊严是一般人格权的代名词。但对如何处理该款规定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关系,该观点并未予以说明。
二是一般性自由论。该观点认为,该款的人身自由既包括身体自由即自然人行动自由不受非法限制、身体不受非法搜查、不受非法逮捕和拘禁等,也包括自然人的自主决定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婚姻自主权等[2]25,是自然人自主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参与各种社会关系、行使其他人身财产权利的基本保障。在该观点内部,又因为对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不同认识而分为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是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并列对待,认为该款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含义非常广泛,所有人格权都以这两种价值为基础,都是这两种价值的具体表现,它们共同构成认定新型人格权益的根本标准,具有权利创设、价值指引和兜底保护等多重功能[1]16-17。该观点将人身自由作为一般性自由对待,并且在规范功能上与人格尊严并列,认为现行法律体系中的其他具体法律规则所使用的人身自由通过该款获得了抽象的一般意义,在理解与适用上能够与人格尊严同等对待。
另一种虽然将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对待[21]33,承认该款已经存在的事实而未如人身自由误用论一样直接否定人身自由的一般人格权属性,但与将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完全并列的观点不同,其并不认为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居于同等地位,于此其又抛开该款的文义而认为人格尊严是自然人行使其他一切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构成其他人格权的渊源性权利[22]71。显然,这一观点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一方面尊重《民法典》的已有规定而认为该款的人身自由构成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又受思想观念史上关于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关系的影响,忽略该款将二者并列规定的作法,认为人格尊严构成所有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只是人格尊严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除前述三种直接讨论《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人身自由概念的内涵外延与性质的理论观点外,学理上还有观点从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规范关系的视角,来讨论作为《民法典》所保护的人格权益的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尤其是人格尊严[23]10-11,但未讨论人身自由本体及其与人格尊严和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的规范关系。
整体而言,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已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共同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予以承认的背景下,在具体理解和适用该款的人身自由概念时,无论是第一种观点所持的误用论,还是无视该款的具体规定而直接以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都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一般性自由论中将《民法典》该款规定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在规范功能上同等对待的观点,在形式上符合该款的文义表述,但缺乏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内在规范关系上的有力论证来证成二者的此种关系,并且也未解决现行法律体系下,在《民法典》一般人格权条款中规定的“人身自由”与在其他制定法中规定的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行动自由”“婚姻自主权”等具体的自由类型在具体适用上的规范关系。相比较而言,一般性自由论中的折中性观点既承认该款规定的人身自由是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又未将之与具有高度抽象意义的人格尊严完全等同对待,更能经受住学理上的诘难。但问题是,该观点亦没有厘定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与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清晰界定该款内部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之间的规范关系,因此对本款规定的人身自由的规范内涵的界定仍有进一步考量的空间。
(二)在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规范关系中确定人身自由
事实上,在《民法典》第一百零九条以及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已经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共同作为民法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予以宣示的背景下,既不能如人身自由误用论一样直接否定或者无视《民法典》的这种规定,否则可能损害制定法本身的权威性;也不能如一般性自由论中的完全同等对待论一样直接从文义出发,将《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两种基本价值并列以观,因为无论是现行法律体系内人身自由既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也作为具体人格权的基本现状,还是已公开的《民法典》颁布前后的立法资料以及《民法典》颁布后对全面理解和实施《民法典》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都没有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前者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沈春耀同志2018 年8 月27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民法典各分编(草案)〉的说明》中即明确指出:“人格权是民事主体对其特定的人格利益享有的权利,关系到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保护人格权、维护人格尊严,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任 务……落实宪法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要求。”[17]2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晨同志2020 年5 月22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的说明》继续维持了前述立场[17]13。后者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 年5 月29 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以及同年6 月16 日发表的《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 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重要文章,即明确指出:“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70 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24]4这些权威性文件所展现出来的基本图像是:人格尊严是《民法典》所保护的人格权的基石所在,具有更基础的价值和地位①关于人格尊严作为《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首要价值的具体论述,可参见王利明《人格尊严:民法典人格权编的首要价值》,载《当代法学》2021 年第1 期,第 3 页。,而人身自由则并未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一图像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的既有规定,特别是与宪法和《民法典》中关于人格尊严和人身自由的具体规定既有相契合的部分,也有迥异的内容,由此直观性地反映了1982 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格尊严、人身自由以来法律实践与学说理论对该规定的继承与发展演进。因此,从法秩序内外在体系融贯的角度来看,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应当将《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规范关系,与宪法第三十七条人身自由条款与第三十八条人格尊严条款联系起来进行体系解释,从而将《民法典》对人格权的保护作为宪法确立的基本价值及一般法律思想在民事领域的具体展开来理解[25]148。
对于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人身自由,我国宪法学理上普遍认为其核心内涵是自然人人身不受非法侵犯、自主支配身体的自由,在外延上第三十七条狭义的人身自由与第三十九条住宅不受侵犯、第四十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共同构成广义的人身自由[26]221。宪法学上的这种广义人身自由论观点与前述民法学上关于《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人身自由属于一般性自由的立场之间并无本质分歧,由此为把《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人身自由理解为一种一般性自由提供了宪法上的论证基础。相比较而言,对于宪法第三十八条的人格尊严及其与第三十七条的人身自由的关系,宪法学理上则存在广泛分歧:
具体的基本权利说认为,根据宪法解释方法,只能将第三十八条作为一个具体的基本权利理解,其与第三十七条的人身自由、第三十九条的住宅不受侵犯、第四十条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并列存在于广义的人身自由规范体系之下[27]79。该观点被认为构成我国当前宪法学理上的多数说[28]37。
内部规范地位统摄说认为,无论从宪法第三十八条所处的位置、规范的表达方式还是立宪修宪的历史来看,“人格尊严并不构成我国宪法上的一项具有根本性的、贯穿整部宪法的价值”[29]53的权利,其目前只是我国宪法上的与人身自由等并列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要使该条规定的人格尊严成为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只能通过修改宪法来完成。
双重规范地位统摄说认为,宪法第三十八条前半段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可以理解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规范性语句,表达了类似于《德国基本法》第1 条第1 款的“人的尊严”那样具有基础性价值的一般法律思想,从而能够作为我国宪法上基本权利体系的出发点和渊源[30]47。
一般人格权说认为,由于人与人格、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存在不同,因此我国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人格尊严”无法与《德国基本法》第1 条第1 款规定的“人的尊严”进行简单类比或等同,该条将人格与尊严放在一起只是为了提高人格权的保护力度,在本质上是一般人格权[31]102。
价值相互构成说认为,从价值上的相互构成与支撑视角来看,在宪法第三十八条的内部关系上,可以以前句统摄后句,形成原则对规则的拘束;在第三十八条的外部关系上,一方面可以以第三十八条的人格尊严作为第三十七条人身自由、第三十九条住宅不受侵犯、第四十条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基础,另一方面人格尊严也可以成为这三个条文规定的基本权利的构成性要素。在此基础上,该说认为人格尊严构成了这些权利的基础[28]37。
可以说,囿于具体的制宪历史背景,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的人格尊严与第三十七条规定的人身自由、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住宅不受侵犯等在立法者初始的设定中都是以具体的基本权利形象出现的。只是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把人格尊严的意涵限定在与侮辱、诽谤等相关的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保护的狭窄范围内已经不能满足现实生活对制定法的需求了,在此背景下学理上希冀通过解释跳出宪法文本的窠臼,从而在更具基础价值的意义上理解人格尊严以有效回应现实生活的要求。因此,除了具体的基本权利说之外,其他观点都希望突破文本的限制而将宪法第三十八条的人格尊严作为一种比第三十七条的人身自由更具有基础性地位的基本权利对待。依据这些观点,无论是将第三十八条的人格尊严作为所有基本权利的渊源而使之成为贯穿现行法秩序的一般法律思想,还是将之作为宪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并通过《民法典》中的人格权一般性保护条款而投射到民事法律关系领域,都可以将第三十七条的人身自由涵摄其中。这种以人格尊严作为现行法秩序的元价值的观念被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的内部稿所接受,其明确以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14]186,没有再像《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一样,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并列,共同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尽管后来立法者为了保持《民法典》概念体系在外在形式上的一致性而再次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并列,共同作为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但前述以人格尊严作为贯穿现行法秩序的一般性法律思想的观点却被立法者在其他场合明白无误地表达出来[17]13,21,这就为围绕人格尊严理解《民法典》中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诸法律价值的规范关系提供了可能。
具体来讲,一方面,《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所使用的人格尊严概念虽然脱胎于宪法,但其内涵实质上已经突破了1982 年宪法制定者通过第三十八条赋予人格尊严的狭窄意涵,而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民法典》的价值基础和贯穿其中的一般法律思想了;另一方面,囿于前见及现行法律规范既有概念的使用传统等因素,更具基础价值的概念如人格自由等未被立法者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而承认,人身自由这一现行法律体系中仅被作为具体权利对待的概念却又被立法者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价值,而与更具基础性价值的人格尊严并列规定,这也是《民法典》颁布之后被人身自由误用论所诟病的关键之所在。在此背景下,若从现行法秩序外在体系的科学性与合体系性视角进行评价,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已经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基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产生的其他人格权益”的背景下,基于对制定法权威的维护和对该条文义的基本解释,一方面应如一般性自由论中的折中观点一样,重新认识现行法律体系下的人身自由概念,并像宪法学理上一样在广义上承认人身自由具有一般人格权的性质,从而在外在体系上和人格尊严并列,共同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另一方面,从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的视角来看,于此亦不能僵化地严守《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文义而认为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是完全并列的、处于同等重要位置的基本价值,否则即会与立法者通过人格尊严创设一般人格权的基本目的相违背。这实质上就要求,在理解《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时,既要承认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也要明确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规范关系,而不把前者作为与后者同等重要的价值基础。或者说在坚持以人格尊严为元价值的前提下[32]126,来理解同样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规范关系及其规范内涵。
事实上,将人格尊严作为法秩序的元价值而以之为基础来理解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格尊严与人格自由的规范关系,进而确定后者的规范内涵,在比较法上亦不乏先例。例如,德国民法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虽然是《德国基本法》第1 条第1 款的“人的尊严”和第2 条第1 款的“人格自由发展”[33]152,但在德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在法律价值体系中并不是并列关系。在《德国基本法》确立的法律价值体系中,人的尊严是整个基本权利体系的基础,是不能触碰的基本权利[34]65,而人格自由发展是以人的尊严的实现为核心目的的重要基本权利。保障人格自由发展,是为了充分实现人的尊严。因此,受人的尊严所内含的相互尊重原则及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所限,人格自由发展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中的自由,要求自然人既对自己负责,也对社会中的其他人负责[35]70。这就表明,德国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即人的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之间的规范关系是:内含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以及自我决定的人格自由发展以人的尊严为基础,保护人格自由发展是为了人的尊严的实现,应当在人的尊严框架下为人格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36]68。这种规范关系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人的尊严除了自然人内外在自由的自主实现外,还包括自然人所担负的社会责任与社会中其他每个人自我的自主实现相统一;另一方面,抽象的人的尊严主要经由人格自由发展来体现,人的尊严为人格自由发展的运用提供正当性说明[37]155-156。同时,考虑到精神性人格自由的内部构造无法为现实生活中的自然人的权利保护请求提供清晰的保护界限,因此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人格自由发展主要指向一般性的行为自由,包括人之行动的所有表现形式或生活领域,构成其他自由权的补充性的一般自由权[38]102。
德国民法上的实践经验表明,将更具有一般性的人格自由放在人的尊严的范畴之下,在人格自由与人的尊严的内在规范关系中来确定人格自由作为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的属性与边界,既可以使人格自由的内涵与行使界限得以确定,亦可以使人的尊严的内涵更为丰富,从而使之摆脱人的尊严无用论者所诟病的人的尊严的空洞性问题[39]170。以此为借鉴,即使宪法第三十七条的人身自由和第三十八条的人格尊严都是具体的基本权利,而不具有《德国基本法》上第1 条第1 款人的尊严和第2 条第1 款人格自由发展在整个法秩序中的价值与规范地位[40]37,但在《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明确予以规定并置于“民事权利”章的首要位置以提纲挈领,作为一般人格权乃至整个民事权利体系的价值基础予以宣示之后,实质上就已经实现了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权利性质和规范地位的转化[41]13,使之成为以《民法典》为核心的整个民事法律体系的价值基础或贯穿其中的一般法律思想,确定了民法保护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基础的民事权益的法律基础。
这样,《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即可被理解为对《民法典》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民法基本价值在人格权领域的进一步宣示和强调[42]106。并且在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内部关系的规范解释上,《民法典》也为把人格尊严理解为一种更具基础性的法律价值而将人身自由作为该基础性价值的具体化提供了可能。事实上,正如学理上有观点已正确指出的那样,人格尊严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但不具有实践指引性的薄概念,虽然不能为具体行动提供具体确定的指引,却可以为之提供正当性论证,因为它在当代社会背景下成为用以论证行为正当性的道德体系和道德话语的核心;与之相比,人身自由是一个在实践中具有世界指向性和实践指引性的厚概念,在指引具体行动的论证中,人格尊严可以为人身自由提供正当性论证,从而为人身自由概念使用边界的确定提供道德上的支持[43]169-170。当然,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这种厚概念与薄概念之间在实践和体系论证上存在的规范关系,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人格尊严的内涵,克服人格尊严抽象性、普遍性所导致的空洞和不确定的问题[39]170。
因此,基于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在理解上的正当性论证关系,并且结合我国现行法一直以来在具体人格权意义上使用人身自由的传统,可以将《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人身自由理解为:自然人以彼此承认和相互尊重为基础而排除他人干扰发展其人格个性的、对自身紧密人格领域的自主和自我决定权[44]43。这意味着,《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人身自由,首先是以人格尊严为基础,强调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与尊重;其次,人身自由的核心在于个体的自主和自我决定自由,这显然并非狭义的身体行动自由,而是包括个体依据自主意志选择并依此行为的所有自由的表现形式;再次,人身自由以自然人彼此之间的相互承认和尊重为前提,因此相应的自由表现形式是对自然人自身人格发展而言关系紧密的领域,由此将自由的界限与对他人的承认和尊重联系起来,防止因为对过于宽泛的自由的保护而侵入他人的核心利益范围;最后,人身自由强调自然人对自身人格发展的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性也具有绝对权所具备的消极防御属性,即对于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他人负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以人身自由的这些特性为依据,可以将那些未被《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一款明确承认为具体人格权而需要通过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纳入民法保护范畴的其他人格利益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直接以人身自由为正当性论证基础而无须回溯至作为元价值的人格尊严的人格利益,如意志自由、性自主权、生育自主权、离线权以及其他以人格自由发展为要旨的一般性自由;第二种是无法通过人身自由而需要直接以人格尊严作为正当性论证基础的人格利益,如个人信用、人格形象的统一性、敏感个人信息、仪式行为的可尊重性等;第三种是需要将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结合起来共同作为相应人格利益被纳入一般人格权保护范畴的正当性论证基础,如生命自主权以及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等[45]113。对于已被《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一款明确承认且在人格权编被详细规定的具体人格权类型,通常情形下无须再通过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宣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来论证其被民法保护的正当性问题,如宪法第三十七条人身自由的核心内容即身体行动自由以及第三十八条人格尊严的主要关注对象即名誉权、隐私权等。亦即,虽然这些具体人格权是从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中发展出来的,但在制定法已经将之作为具体人格权明确规定下来之后,若再将之纳入以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条款的涵摄范畴,即会导致规范适用的混乱,与立法者通过第九百九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区分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格权保护规则的立法目的相悖。
三、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的主要表现形式
从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规范关系来确定《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人身自由的内涵,将人身自由理解为自然人对自身紧密人格领域的自主和自我决定权,具体应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具体把握其涵摄范围。
(一)人身自由与行动自由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不包括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规定的行动自由。该条的行动自由即身体行动自由,主要是自然人依据自主意志自由支配外在身体运动的权利。在《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将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规定以前,我国现行法中对身体行动自由的制定法表述是“人身自由”[5]70。虽然学理上有采扩张解释方法以扩展“人身自由”概念内涵的观点[46]10,但制定法中的人身自由依然是作为具体人格权出现并始终以行动自由为核心指向。制定法的这种传统对《民法典》人格权编相应概念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及第一千零一十一条用“行动自由”取代“人身自由”概念作为之前身体行动自由这一具体人格权在制定法上的表述。显然,这里概念使用上的变化主要是为了《民法典》外在概念体系的合逻辑性,并不是为了赋予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行动自由以新的内涵。《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的“行动自由”实际上就是《民法总则》第一百零九条颁布之前各制定法规定的“人身自由”所指向的身体行动自由,亦即司法实践中法院所普遍理解的“可以通过人的自主意志控制肢体行为等物理活动上的自由”。
由于作为具体人格权的“行动自由”已为《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所规定,所以在解释论上,不宜再将“行动自由”纳入《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的涵摄范畴。这种解释既为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在案件审理中所支持,在比较法上亦有迹可循。
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在审理一般人格权的案件中明确指出,侵害一般人格权的,一方面要构成对自然人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的侵害,另一方面还不得构成对具体人格权的侵害①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01 民终355 号,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浙杭民终字第1901 号。。亦即言,若构成具体人格权侵犯的,则不构成一般人格权侵犯。这显然是将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理解为并列的关系而非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基于同样的考虑,若符合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行动自由涵摄要件的,则不宜将之再纳入以人身自由为价值基础的一般人格权的涵摄范畴。
在比较法上,《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明确规定“自由”受法律保护,另外司法实践以《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的“其他权利”和《德国基本法》的基本权利条款而发展出来的一般人格权规则,也保护以人格自由发展为基础的人格利益。对于《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规定的包括自由在内的具体人格法益与可以涵摄一般性自由的一般人格权之间的规范关系,德国学理上认为这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包含关系,不是母权利或渊源性权利与派生权利之间的关系,而是并列的合作关系[47]20。一般而言,《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中作为典型人格法益而被明确规定下来的“自由”与行为自由同义[48]16,或者更确切地说,该自由就是身体行动自由[49]466,它并不包括经济拓展能力,也不包括人格的自由发展,因为前者属于竞争法的调整范畴,而后者则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调整领域[50]90-91。
将身体行动自由纳入《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行动自由”而非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人身自由”的涵摄范畴,意味着因非法拘捕和监禁等方式限制和剥夺行为自由的,如顾客被怀疑在商店行窃而被控制②参见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佛中法民一终字第307 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2)海民初字第1704 号。、自然人被非法监禁于监狱中或者精神病院③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9)沪一中民一(民)终字第246 号。等等,一般来说均属于依《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而非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调整的对象。当然,在司法实践的个案判断中还应当结合其他主、客观要素进行具体分析。例如,对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我国学理上通常认为,对身体行动自由的侵害行为,应当区别不同的侵权人而在过错程度上有所区别;对精神活动自由的侵害,则不再考虑过失,仅以故意为限[5]70。与之相比,在德国法中,同样的错误监禁,却可能因行为人的过错不同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例如,医生因错误鉴定某精神正常的人为精神病人,导致此人被关进精神病院而丧失行动自由,如果医生鉴定时存在故意,则构成对身体行动自由的侵害,属于《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明确规定的“自由”的涵摄范畴;如果医生的主观状态为过失,则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调整范畴①参见 Hager J.,“Das Recht der unerlaubten Handlungen,”im Beckmann R.M.,Klinck F.&Busche J.et al.(eds.),Johannes 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mit Einführungsgesetz und Nebengesetzen:Eckpfeiler des Zivilrechts,Berlin:Sellier-de Gruyter,2011,S.92。对此也有不同的司法实践,如丹麦法院就以侵害自由权为由,判决具有过失的医生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具体可参见 Bar C.,Gemeineuropäisches Deliktsrecht,Bd. 2,München:C. H. Beck,1999,S.90。。在其他场合,如行为人因过错导致交通事故引起交通堵塞等,对受影响的当事人而言,这属于一般生活风险,并不会存在任何受法律保护的自由被侵害而导致侵权法上的义务发生;但如果该交通堵塞是故意引起的,则构成对受影响之当事人身体行动自由的限制②参见Medicus D. & Lorenz S.,Schuldrecht Ⅱ:Besonderer Teil,München:C. H. Beck,2014,S. 466。拉伦茨教授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此类事件中当事人的身体行动自由并未受到侵害,因为被阻碍的仅是车辆的正常行驶,即使是故意导致的交通堵塞,亦不存在对身体行动自由的侵犯,受影响人也不能依据第823 条第1 款主张侵权法上的救济,对此具体可参见Larenz K. & Canaris C. W.,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Besonderer Teil 2,München:C. H. Beck,1994,S. 386。福克斯教授与拉伦茨教授持同一观点,参见Fuchs M.,Deliktsrecht,Berlin:Springer,2009,S.17。哈格尔教授则支持梅迪库斯教授的观点 ,具体参见 Hager J.,“Das Recht der unerlaubten Handlungen,”im Beckmann R. M.,Klinck F. &Busche J. et al.(eds.),Johannes 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mit Einführungsgesetz und Nebengesetzen:Eckpfeiler des Zivilrechts,Berlin:Sellier-de Gruyter,2011,S.92。。德国法上之所以区分故意和过失,从而将两种不同的过错行为分别纳入具体人格权和一般人格权的调整范畴,是因为前者的保护界限相对清晰确定,在判断责任成立时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受害人可以获得更充分的保护;而后者则因为保护界限并不确定,需要法官在个案中平衡考量各种冲突的法益以确定责任成立和相应的责任承担,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受害人是否可以获得法律上的保护需通过利益权衡来确定。这种区分保护的思路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一般人格权规则和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的具体人格权规则的实践适用中也值得借鉴。虽然《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规定除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之外,其他侵害人格权益的民事责任都由法官在综合考量制定法明确列举出来的因素的基础上权衡认定[1]47,但是,相比较于内涵外延更不确定的一般人格权而言,具体人格权受法律保护的界限更清晰,即使法官有自由裁量权,这种权力也会更多地受限于具体人格权的明确保护边界。亦即,在行为人为故意时,通过作为具体人格权的《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的行动自由更能充分地救济受害人;相应地,在行为人为过失时,通过作为一般人格权的《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人身自由而给予法官以充分的自由裁量空间,可以在各种法益的保护之间取得平衡。
(二)人身自由与意志自由
在《民法典》第一百零九条将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予以规定前,对于规定在各特别法中的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是否包括身体行动自由之外的其他自由,我国学理上即存在争议。否定论认为,人身自由仅指自然人的身体行动自由,意志自由等不在人身自由的涵摄范畴[51]175。肯定论则认为,人身自由不仅包括身体行动自由,也包括意志自由,但对具体的意志自由范围则存在不同认识,存在着表意自由论、自主思维论和自主决定论等分歧[5]70。其中,表意自由论认为,人身自由包括意思表示的自由,而意思表示地自由是指自然人自由的决定为或者不为意思表示及决定意思表示的具体内容[52]238。自主思维论认为,自然人享有精神自由权,有权自由支配自身内在的思维活动[46]10。自主决定论认为,自然人享有意志自由,有自主思维并做出决定[53]201。
相较于否定论而言,尽管肯定论在将意志自由纳入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范畴内的具体界限上存在分歧,但其将意志自由纳入人身自由的范畴更具合理性。这是因为:意志自由与行动自由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行动自由的核心在于自然人可以自主支配其身体以离开某特定空间而不受限制①参 见 Hager J.,“Das Recht der unerlaubten Handlungen,”im Beckmann R. M.,Klinck F. & Busche J. et al.(eds.),Johannes von Staudingers Kommentar zum Bürgerlichen Gesetzbuch mit Einführungsgesetz und Nebengesetzen:Eckpfeiler des Zivilrechts,Berlin:Sellier-de Gruyter,2011,S.91-92。但是,希腊法院的判决表明,阻碍某人进入某空间或者使用某公益物,亦属对身体行动自由的侵犯,具体可参见Bar C.,Gemeineuropäisches Deliktsrecht,Bd.2,München:C.H.Beck,1999,S.89。,自然人自由支配其身体的前提在于其享有意志自由,享有意志自由的自然人可以依自主意志为或不为意思表示并决定意思表示的内容。亦即,意志自由到身体行动自由的过程是自然人将主观意志或思维见之于客观行动的过程。在此意义上,意志自由与行动自由共同构成完整的身体自由[5]70。当然,将意志自由纳入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范畴之内,确实面临着权利规则和法律体系构造层面的双重难题。
就权利规则构造而言,正如前面表意自由论、自主思维论和自主决定论在具体认定意志自由内涵时存在分歧那样,意志自由的内部构造并不清晰,无法为相应的权利保护请求提供明确的法律保护界限,所以要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则来保护意志自由存在困难[54]197。相比较而言,行动自由的内涵相对清晰明确,可以满足法律规则适用确定性、可预见性的要求。
就法律体系构造而言,由于意志自由具有高度模糊性和广泛包容性,学理上有观点认为,应将意思决定自由、思想自由、表达自由、信仰自由、创造自由权以及性自主权等均纳入意志自由的范畴[12]133。但如果将这些自由均纳入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范畴,不但可能会导致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功能和规范适用规则上的混乱[55]49,还可能破坏民法体系内部财产性民事权利与人身性民事权利体系结构的分工与安排[44]43,使民法典的体系构造缺乏科学性。
因此,将意志自由纳入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范畴所遭遇的两个难题若解决不当,将会导致人身自由的涵摄范畴过于广泛,不但违背立法者保护自由的意旨,尤为重要的是还可能导致行为人动辄得咎,造成对整个社会所普遍珍视的一般行为自由的戕害[56]21。所以,讨论是否将意志自由纳入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人身自由范畴亦即《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涵摄范畴,亦必须在重视和回应这两个问题的前提下展开。
首先,权利规则构造论的质疑在将人身自由作为具体人格权对待时确实存在。因为权利规则要求权利本身具有相对清晰的内涵外延以确保权利行使界限的明确性,从而实现法律规则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但与具体权利规则不同,一般人格权并非典型权利,其本质上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束”[57]401,“具有秩序功能的上位概念”[58]336,或是一项“框架性权利”[47]20。这就意味着在一般人格权的框架结构下,法官在个案审理中可以依据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法律价值进行利益衡量,从而决定优先保护何种人格利益[59]8-9。而将意志自由纳入人身自由的涵摄范畴,只是为法官在具体案件中通过《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确立的一般人格权条款进行利益衡量提供更充分的正当性说明依据。至于以人身自由等价值为基础的一般人格权在个案适用中的具体界限在哪里,还需法官在个案中结合具体情况予以确定。就此而言,权利规则论的质疑在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时可能并没有适用空间。
其次,无论是将人身自由作为具体人格权对待,还是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对待,对法律体系构造论的质疑都应认真对待。事实上,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下:
一方面,宪法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适用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宪法基本权利包括宪法一般人格权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宪法基本权利没有经过民法表达是不能受到民法保护的[60]6。而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只能由民法规范予以调整,宪法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可以经由民法上的一般条款进入民事领域,但进入民事领域的宪法权利规范应是适用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对于适用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宪法权利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①关于言论自由的最新讨论,可参见左亦鲁《从自由到平等:美国言论自由的现代转型》,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1 期,第152 页以下。、投票自由、表达自由等,即不能通过民法一般条款或民法一般人格权规则进入民事领域[5]70。基于同样的考虑,这部分内容也应当从纳入人身自由涵摄范畴的意志自由中排除出去,不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涵摄领域。
另一方面,在民法体系内部,虽然民事权利本质上与民事主体的人格本身均存在联系,但不同的权利类型与人格本身的关系在紧密程度上并不相同。在《民法典》体系内部,对于与人格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格权的享有和保护而言,依据《民法典》第九百八十九条规定,可以适用人格权编确立的包括一般人格权规则在内的权利行使和保护规则;对于与人格关系相对比较密切的自然人因婚姻家庭关系等产生的身份权利的保护,依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一条,在婚姻家庭编等没有特别规定时可以参照适用人格权编关于人格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对于与人格关系最不密切的财产权而言,仅得依据财产权规则如合同编或物权编确立的权利行使和保护规则调整,原则上不得依据人格权规则进行保护。因此,如果不将纳入人身自由范畴的意志自由限制在与人格关系密切的人身领域,那么就可能造成《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确立的一般人格权规则的适用领域过度扩张,破坏《民法典》民事权利结构的体系安排[44]43,与立法者希冀的民法典的体系性、科学性目的相违背。例如,对于受害人因欺诈、胁迫而做出订立合同、签订遗嘱或缔结婚姻的意思表示,原则上仅得通过合同编、继承编和婚姻家庭编的规则予以解决。只有那些无法通过其他规则调整而同时又与人格本身关系密切的意志自由,才能纳入《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人身自由的涵摄范畴,如在他人居住的地方书写有警告和威胁含义的语言②参见贵州省安顺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2)安市民终字第115 号。,即可构成对他人受人格权编调整的自由的侵犯。另外,《民通意见》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盗用、假冒他人名义,以函电等方式进行欺骗或者愚弄他人,并使其人身财产利益受损的,应属于对他人意志自由的侵犯[6]26,在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调整范畴内。
最后,实践中还应区分愚弄与戏谑,防止保护自由的同时构成对自由的戕害。我国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为:“戏谑之言系属法外空间,不得为民法所调整,否则容易剥夺公民之人格自由,使公民在社会生活中陷于动辄得咎的境地。”③参见四川省犍为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川1123 民初492 号。该观点值得肯定。事实上,在德国法上,以威胁、强制或者欺骗形式侵犯意志自由而被纳入《德国民法典》第823 条第1 款“自由”范畴的,亦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限制而仅在例外情形下被允许[49]466。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并不以物理强制为必要,通过欺诈或胁迫的方式使某人不敢离开某处,亦构成对行动自由的侵害,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的涵摄范畴,而非侵害意志自由,不属于《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人身自由的涵摄范畴。另外,以欺诈、胁迫等方式影响他人意思决定或对其身心加以威胁并造成相应损害者,虽可能不构成对行动自由的侵犯,但仍有可能侵犯其他具体人格法益,例如逼婚,就构成对婚姻自由的侵犯,属于《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的调整范畴,不宜将之认定为意志自由被侵犯[61]112,从而纳入人身自由的涵摄范畴并通过《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进行调整。
(三)人身自由与其他自由
一般认为,作为具体人格权的人身自由内含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但如果将人身自由作为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予以规定,是不是还须将其内涵限定在狭义的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范畴内,仍需斟酌。
从目的解释的视角来看,《民法典》承认并明确规定一般人格权条款的核心目的在于克服具体人格权规则涵摄能力之不足,为现代社会背景下具体人的人格利益的充分保护提供制定法依据[36]61。因此,如果依然从具体人格权意义上来理解作为一般人格权之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就会不当地限制一般人格权规则即《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涵摄能力,无助于立法目的的实现。
从历史解释的视角来看,即使在将人身自由作为具体人格权对待的法律实践运用和法学理论探讨中,人身自由也从未被完全限制在狭义的身体行动自由和有限的意志自由范围内。事实上,以最高人民法院为代表的司法实践普遍倾向于通过扩张解释的方法扩展人身自由的适用范围。我国学理上对这种立场亦持肯定态度。例如,在刘某诉某乒乓球俱乐部等以错误医学鉴定影响其运动生涯案中,原告仅十四岁,曾在全国性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冠军,引起好几家培养单位的关注,由于被告率先录取了原告,原告只能放弃其他深造机会。嗣后,原告在入学体检时被初步诊断为存在不适于高强度训练的疾病,被告遂以此为由决定让原告离队。原告不服并另行委托第三方权威机构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原告身体健康,并不存在影响高强度训练的疾病。但被告仍坚持之前的决定,拒绝让原告归队训练,原告为此只能回原籍高中就读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总第29 辑),(北京)时事出版社2000 年版,第64 页。。在我国学理上看来,本案中被告的行为导致原告丧失了进入特定领域发展的机会,客观上可能导致原告人生轨迹发生改变,使其无法按照个人自主意志发展完善其人格并最终实现人格尊严,因此可以纳入一般人格权的调整范畴。对此,也有法院在判决中指出:“一般人格权是指具有高度概括性的以民事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权利,具有补充功能,对于侵害人格独立、人格自由、人格尊严的行为,不能以侵害其他具体人格权的名义进行法律保护的,应认定为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②参见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鄂08 民终113 号。亦即,司法实践和学理为提高一般人格权的涵摄能力而往往使用更抽象的人格自由概念作为一般人格权的正当性论证基础。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突破之前的制定法规定,而将人身自由作为与人格尊严并列的更具抽象意义的基本价值加以规定时,实质上即意味着其也可以与《德国基本法》第2 条第1 款的人格自由发展做出同样的解释,包括人之行动的所有表现形式,因此可以成为其他具体自由的补充[38]102。
同样,以人格尊严的实现为目的而将《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人身自由扩展至人之行动的所有表现形式或生活领域,意味着对人身自由的扩张解释必须与人格尊严结合起来[37]155-156,人格尊严并非单纯是扩展人身自由的审查标准,还可以为把人身自由扩展至人之行动的所有表现形式提供正当性说明。这也就意味着,以包括人之行动的所有表现形式或生活领域的人身自由作为《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一般人格权的价值基础,实际上使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涵摄能力实质性地提高了。由此,在冒名顶替他人上学并使被冒名者丧失受教育机会③参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鄂01 民终355 号。、身份信息被冒用并被税务机关等列入黑名单④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沪0112 民初665 号。等案件中,实质上都可以通过《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进行调整。
通过强调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的内在规范关系而将人身自由扩展至人之行动的所有表现形式或生活领域,表明《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人身自由并不是封闭的系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僵化概念,而是向丰富变化的现实生活完全开放的抽象价值,可以将那些因时代背景变化而产生的新型自由纳入进来,从而提高一般人格权规则的涵摄能力[62]44。这也意味着,在数字时代,以这种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为基础的一般人格权规则,不仅可以为个人信息、数据等尚未被权利化但又与自然人人格密切相关的利益提供更为充分的保护[45]113,还可以为其他更广泛意义上的以人格尊严的实现为目的的人的自由提供一般性的保护基础。例如,劳动者因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而既可能使其工作适应工作时间灵活化的需求,也可能因这种新技术被用人单位滥用而付出代价。因为数字技术在劳动领域的运用首先会带来工作与生活界限的破坏,用人单位会通过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召唤那些正处于休息时间的劳动者,使工作强度和绩效压力本来就已经很大的劳动者的负担进一步加重[63]92,导致劳动者身体健康方面的风险[64]13-23。在权利论者看来,“劳动权是人的一项权利,并且是一项人权。劳动要合乎人性的要求,要有利于人性的发展”[65]185。这就要求数字化背景下,法律应关注劳动者享有的正常休息的权利,该项权利的实现要求劳动者在工作时间之外不被用人单位随意打扰,或者在其被打扰时有权不做出回应,如在非工作时间有权不回复工作邮件或者对工作指示不做出回应而没有不利后果。而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劳动者在休息时间享有的依个人意志自主安排生活、全面发展人格并享有生活安宁不被侵扰的人格利益,在用人单位通过数字技术侵扰而劳动者不能通过劳动法的特别规定取得救济时,可以通过《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获得保护[66]47。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作为一般人格权价值基础的人身自由在概念使用上虽存在不足,但通过目的解释、历史解释及体系解释等解释方法的综合运用,仍然可以在现行民事法律体系中通过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内在规范关系而将人身自由的内涵予以确定,使之在与《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的行动自由相互区分的基础之上,成为可以涵摄人之行为的所有表现形式或生活领域的补充性的一般性自由。在具体适用上,《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条第二款的人身自由构成其他具体的自由形式如《民法典》第一千零三条、第一千零一十一条的行动自由及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第一款的婚姻自由的补充,从而为现实生活中以人格尊严的实现为目的的人的自由的保护提供法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