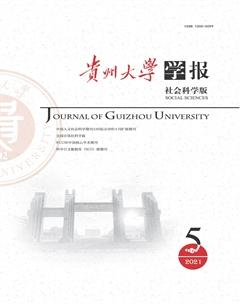从福岛核废水排海事件看国际法的现实障碍与未来走向
摘要:日本政府福岛核废水排海决策及未来排海行为涉嫌违反国际法。国际法却无力阻止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体现国际法实施面临现实障碍:一方面,国际法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另一方面,国际违法行为的认定及国际法的强制实施都非易事。然而,国际法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人类命运共同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国际核安全法律体系日臻完善,国际核安全法的约束力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中国应推动国际社会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国际核安全法律体系,加强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促使日本遵守国际法。
关键词:国际核安全法;福岛核事故;海洋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D9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5-0111-05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在两年后把福岛核电站事故产生的100多万吨核废水排入太平洋,整个排放过程将持续30年。该决策引起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国际法学者依据国际公约剖析其违法性并提出建设性意见,敦促日本政府放弃核废水排海计划,防止造成国际海洋污染灾难①。 但迄今未能改变日本政府核废水排海决策,体现国际法实施面临的现实困境,值得深入研究。
一、福岛核废水排海事件的违法性
日本政府福岛核废水排海决策的违法性与未来核废水排海行为的违法性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必须结合国际法进行具体分析[7]。
首先,日本政府福岛核废水排海决策涉嫌违反国际法规定的程序。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缔约国,日本负有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海洋环境污染,确保国内环境污染事件不对其他国家管辖海域或公海造成污染②。 因核废水排海将增加海洋环境污染的风险,日本应“用公认的科学方法观察、测算、估计和分析海洋环境污染的危险或影响”,公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还应提前将核废水排海计划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国家③。 但日本迄今未履行公约规定的程序性义务。日本政府将核废水排海的决策程序缺乏公开性、透明性和民主性,涉嫌违反《公约》规定的程序性义务。
其次,日本福岛核废水未来排海行为的违法性可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方面,日本有义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参见《国海洋公约公约》第194条。]。 判断日本是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标准为是否存在更优的替代方案。鉴于地层注入、蒸汽释放、氢气释放和地下掩埋方案能更有效地降低污染风险[8],而日本政府执意选择核废水排海方案,极大地增加了国际海洋环境严重损害的风险,这证明日本政府并未“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海洋环境污染。日本政府明确承认其决策是基于便捷性和经济性,而非基于科学性和安全性,这也表明核废水排海并非最优选择。因此,福岛核废水排海行为违反《公约》以及国际辐射防护的基本法律原则。另一方面,未来福岛核废水排海行动必须达到安全排放标准。国际核废水安全排放标准可参照《公约》和《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确定。《公约》要求各国制定法律、规章和措施以防止和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其效力应不低于全球性规则和标准[参见《国海洋公约公约》第207条、第210条、第213条和第216条。], 这得到相关国际公约的肯定。例如《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规定了允许倾倒的废物及其最低豁免浓度。日本未来排海的核废水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其一,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高于国内法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设定的安全排放标准,则必然属于违法行为。其二,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低于相关安全排放标准,则须在坚持公开性、透明性和民主性的前提下通过核查监督机制予以确认,日本政府还应及时更新核废水排海计划实施情況、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与应急准备方案,否则仍属违法行为。
二、从福岛核废水排海事件看国际法的现实障碍
国际法不能使日本收回核废水排海的决策,无力阻止日本核废水排海事件的发生,无权对日本违法行为进行惩罚,体现出国际法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现实障碍。
1.国际法并未得到严格遵守
首先,国际社会不能以日本违反相关程序性法而迫使日本政府放弃福岛核废水排海决策,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国际法的性质决定的。国际法是调整平等国际法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各种规范,其约束力来源于各国意志的协调或协议[9]。当今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超国家实体。根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的原则,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其他国家身上,迫使其他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其次,国际法是建立在国家主权原则基础之上的。任何国家都拥有在其境内利用核能的权利,承担核安全治理责任与国际协作义务。但国际核安全法主要通过国家来实施:国家是核安全监管的首要责任主体,对外参与国际核安全公约,履行国际法律义务;对内建立核安全法律体系,履行国内治理责任[10]207 。对于可能产生的跨界影响,国家承担预防、通知、协商和谈判的责任,但其国家主权必须得到充分尊重[11]。
最后,国家的国内和国际核安全义务并不平衡。国家首先是承担着维护本国人民生命财产与环境安全的责任,其次是防止可能产生跨界损害的对外责任。二者发生矛盾时,国家可能会选择牺牲国际核安全义务。虽然日本政府一再强调核废水达到可饮用的程度,但却拒绝自己饮用或排放在日本境内[12],就是因为日本国内和国际核安全义务的不平衡性。日本政府将国际核安全义务置于次要地位,为确保国内核安全而不负责任地选择将核废水排海。
2.国际违法行为的认定障碍重重
从国际法角度认定日本排污行为的违法性并不容易。首先,国际核安全公约为框架性原则和义务。核安全公约确立了安全优先原则、国际合作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等框架性原则和义务,其中大部分缺乏明确性,仅为国际核安全治理提供了激励机制,国家在核安全监管方面仍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其次,国际核安全公约仍不完善,存在概念不清、权利义务不明确等问题。例如《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对“及早通报义务”缺乏界定,对通报时间、内容和方式、违约责任以及协调机制语焉不详;《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中“倾倒”“放射性废物”等核心概念模糊,严重影响公约的实效性。
再次,国际核安全标准缺乏核查机制。国际核安全标准体现国际核安全防护的最高水平,是核安全领域的指导性法律文件[10]189-202,但缺乏国际核查机制。国际核安全标准的应用及安全咨询评审的实施完全取决于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没有核查权,仅有权将安全标准适用于其职能工作,或应当事国请求而适用于根据双(多)边协议而开展的工作[参见《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第3条。]。因此,即使最终主张成立国际核查工作组也只能以“合作倡议”形式并遵循国际合作原则[7]。
3.国际法的强制实施面临困境周边国家无权针对日本核废水排海决策或排海行为采取强制措施,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核安全法的鼓励性质。国际法的强制性是对违法或不法行为的反应,体现在国际法可对国际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对违法成员施加制裁[13]。国际法是否具有强制性取决于国家行为的性质。核能利用活动属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危险活动,核事故所导致的跨界损害并不可归因于国家;即使发生重大核事故并导致跨界损害,国家承担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导致的损害赔偿责任。因此,历史上国际社会多次增加核安全公约强制性的修正案提议都未获得通过,国际核安全法并未确立强制实施机制和惩罚机制[10]335-336。
国际核安全法主要通过国家以己法自律方式自愿实施。因国际核安全公约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标准具有高度科学性、中立性和公信力,国家具有履行国际核安全公约义务的自觉性,主动通过“自我治理、己法自律、自我监督、管促分立、信息公开、公众监督等国内治理机制”确保核安全[10]203。
三、从福岛核废水排海事件看国际法的未来走向
1.人类命运共同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全人类相互依赖性的增强使国际社会共同利益成为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性价值[14]。人类命运共同理念将更加深入人心,推动国家主动遵守国际法,平衡国内和国际核安全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国际核安全治理有助于提高本国核安全水平,推动本国核电发展,从而增加本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一国核安全水平的提高及核电效益的增加可为其他国家提供良好的实践经验、提高民众对本国核安全及核电效益的信心,从而增加其他国家的绝对收益[10]256 。国家遵守国际核安全法还能提高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核安全是核能利用的最高原则,每个国家的核安全都是国际核安全的组成部分,都关系所有核电国家的共同利益;国家通过国际和国内核安全治理提高总体国际核安全水平,从而为国际社会创造更多的安全利益。 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公共利益日益深入人心,即使对本质上属于国家主权范围之内的事项,国家行使主权的方式也将受到限制,国家会更加主动地遵守国际法,平衡国内和国际核安全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
2.国际核安全法律体系日臻完善国际组织和国际司法机构将在国际核安全法律体系的完善、适用和实施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国际司法机构的判例推动了国际法律原则的确立和完善。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确立国家有义务保证境内活动不损害他国环境、人身或财产的原则,成为国际环境法的基石[参见1941年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1949年科孚海峡案、1957年拉努湖仲裁案和1974年核试验案都承认国家不得允许其领土被用于有损于他国权利的行为。]。 国际法院在“使用核武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咨询意见强调,国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进行的活动不损害他国环境的义务已成为国际环境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参见The 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Advisory Opinion of 8 July 1996 I.C.J。]。 聯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和《预防危险活动的跨界损害的条款草案》确立的国家责任与核安全领域的国家责任高度一致。国家责任条款草案具有习惯国际法的效力,也是未来国际核安全治理的法律基础[15]。
国际核安全标准将与国家核安全标准更加有效地衔接,共同规范和确保核安全。国家立法将更加主动地采纳国际核安全标准,使其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标准[16]。国际原子能机构将更积极地履行推广核安全标准的职责,通过提供同行评审服务,提高核安全标准的适用性;更加重视国际核安全协作,增加核安全公约的普遍性,推广核安全标准和良好实践,提高国际核安全水平[17]。
3.国际核安全法的约束力显著增强国际协作机制和多元主体将发挥更加积极的监督作用,国际核安全法的实施将得到显著增强。
首先,国际核安全协作机制的地位更加凸显。国际原子能机构推进国际合作,制定规则,提供同行评审服务,构建全球核安全知识网络,是国际核安全协作的枢纽。核安全峰会和国际核能监管机构协会等多边协作平台推动国际共识与合作协议的形成[18]。正式机制和非正式机制共同作用,推进国内核安全治理,提高国际条约的约束力,促进国际核安全法的有效实施[10]245。其次,国内外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日益重要。“国际法的原则及内容越来越朝着国际民主化、平等化的方向发展。”[19]国家、国际组织、公益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更加积极主动地监督国家履行国际义务。各国核安全监管机构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国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提供同行评审服务,提升核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和专业性;国内外专家参与决策过程,提供专业意见[10]315; 联合国、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国内外社会组织和个人形成国际和国内舆论压力,是对现代政府违法行为的不容忽视的制裁[20], 这都促使国家遵守国际法。
最后,信息公开制度与公众参与制度是多元主体监督的前提。核安全监管机构应完善公众参与制度,确保信息透明度和公开性;核安全决策应保障民众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否决权;核应急处理过程应保证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制度将确保多元主体的监督权,推动国际核安全法的实施。
四、结论
中国应推动国际社会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善国际核安全法律体系,加强多元主体的监督作用,促使日本遵守国际法。中国可通过缔约方会议机制讨论日本国家报告,也可提议召开缔约方特别会议[参见《核安全公约》第20条、第23条。], 要求日本对核废水排海问题做出解释;中国还可以探讨诉诸国际司法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可行性。然而,鉴于国际核安全法律制度的鼓励性质,中国更应在维护国家主权的基础上以国际原子能机构为主要平台帮助日本进行核安全能力建设:敦促日本实现核能促进机构和核安全监管机构的职能分开,确保核安全监管机构的独立性;支持日本加强核安全文化建设;敦促日本贯彻核安全优先原则,放弃核废水排海决策,科学处理事故反应堆退役工作。这是从根本上克服国际法的现实障碍、妥善处理福岛核事故、确保国际核安全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黄惠康,日本核废水排海的四大悖论[N].解放军报,2021-04-25(4).
[2]高之国,钱江涛.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涉及的国际法原则和问题[A]//北京:中国海洋法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论文集,2020:621-631.
[3]高之国,钱江涛.《对日核污染水排海可打法律组合拳[N].环球时报,2021-04-20(14).
[4]廖丽.日本处置核废水必须符合国际法[N].光明日报,2021-04-28(11).
[5]苏金远.日本核废水排入海决定有违国际法理[N].解放军报,2021-04-29(4).
[6]GAO Zhiguo.New Collaborative Path to Tackle Japans Nuclear-Contaminated Wastewater Challenge[EB/OL].(2021-04-12)[2021-05-18].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4/1222534.shtml.
[7]郭冉.日本福島核废水排海的违法性以及对策[EB/OL].(2021-05-02)[2021-05-18].https://www.sohu.com/a/464262550_100001695.
[8]BROWN A.About that tritiated water: who will decide and when?[EB/OL].(2018-06-05)[2021-05-18].https://www.japantimes.co.jp/opinion/2018/06/05/commentary/japan-commentary/tritiated-water-will-decide/.
[9]杨泽伟.国际法[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4-9.
[10]郭冉.国际法视阈下美国核安全法律制度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
[11]RAO P S.First Report on Prevention of Transboundary Damage from Hazardous Activities(A/CN.4/487/Add.1)[EB/OL].(1998-04-3)[2021-05-18].https://undocs.org/A/CN.4/487/Add.1.
[12]NEWS K.Deputy PM Aso Repeats Claim That Treated Fukushima Water is Good to Drink[EB/OL].(2021-04-16)[2021-05-18].https://english.kyodonews.net/news/2021/04/ccdf91e0cdde-aso-repeats-claim-that-treated-fukushima-water-is-good-to-drink.html.
[13]吴嘉生.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之研析[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16.
[14]高岚君.国际法的价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138.
[15]赵洲.国际法视野下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J].现代法学,2011(4): 149-161.
[16]陈刚.国际原子能法[M].北京: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2:38-40.
[17]胡锦涛.深化合作提高核安全水平[EB/OL].(2012-03-27)[2021-05-18].http://www.gov.cn/ldhd/2012-03/27/content_2101050.html.
[18]刘宏松.国际防扩散体系中的非正式机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47.
[19]杨泽伟.国际法析论[M].第三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8.
[20]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M].周启朋,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76-277.
(责任编辑:蒲应秋)
收稿日期:2020-06-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诉讼语境下南海诸岛领土主权证据适用实证研究”(20AGJ004)。
作者简介:
郭 冉,男,河南南阳人,博士,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核安全法、国际海洋法。
①例如黄惠康的《日本核废水排海的四大悖论》[1];高之国,钱江涛的《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涉及的国际法原则和问题》[2]621-631;高之国,钱江涛的《对日核污染水排海可打法律组合拳》[3];廖丽的《日本处置核废水必须符合国际法》[4];苏金远的《日本核废水入海决定有违国际法理》[5];Gao Zhiguo.“New Collaborative Path to Tackle Japans Nuclear-Contaminated Wastewater Challenge”(Global Times,30 April 2021,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04/1222534.shtml)[6]。
②参见《联合国海洋公约》第192条、第194条。
③参见《联合国海洋公约》第204条、第205条和第206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