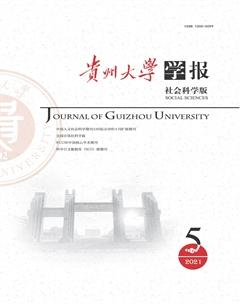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模式案例比较及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卿定文 王玉婷
摘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我国贫困程度最深、扶贫攻克难度最大的地区,其扶贫模式和成效、防止返贫状况等备受关注。对于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来说,在由扶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历史起点上,总结典型扶贫模式的经验,给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一是要坚持地区差异性发展,二是要加强地区资金整合与利用,三是要打好政策措施“组合拳”,四是要推进地区协同协作发展,建立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接续发展机制体制。
关键词:乡村振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典型扶贫模式;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21)05-0089-07
一、相关研究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2011年我国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划定了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要求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力度,增强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着力解决发展问题,以改变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面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精准扶贫政策持续推进,至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 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其中,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扶贫攻坚的重要战场,解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问题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持续攻克的重点任务,其所取得的成就也尤为显著,为区域性整体贫困的解决、绝对贫困的消除,贡献了巨大力量。但当前我国仍然面临着相对贫困、多维性贫困及返贫危机等问题。对此,需要不断深入了解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总结过去的扶贫经验,对比分析其典型扶贫模式,以切实巩固扶贫攻坚成果,保障扶贫成效的持续性,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自我国明确划定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我国学界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主要集中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针对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地域特点[2-3]、贫困影响因素[4-5]、扶贫攻坚效果[6-7]、扶贫方式问题和解决对策[8-9]、经验启示[10]、连片开发与跨区治理[11-12]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微观层面,针对我国某一特定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种扶贫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如比较分析吕梁市三种典型扶贫模式[13],对比云南深度贫困地区五大典型产业扶贫模式[14],等等;或者对不同地区的同种扶贫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如比较分析不同地区金融扶贫模式、产业扶贫模式等的异同[15-16]。随着扶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接续推动扶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性、方法举措[17-18]等方面,也日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内容。这些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也有很多需要深化的空间:一是大多成果以单个地区或单一扶贫模式进行研究,缺乏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整体性、多样性和实践性方面进行分析;二是我国已经进入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交汇期,需要进一步结合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进行研究。基于此,本文就在对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探寻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助力我国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
二、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实际情况分析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的连片特困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四个地州这14个地区[19],主要集中在我国中西部地区,与我国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区及边疆地区高度吻合,多处于省市边缘地带,以山区居多,自然生态环境相对原始朴实,经济基础薄弱,交通、水利、教育、卫生等基础公共服务建设比较滞后等等。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地势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并逐级下降,自然环境差异大,各地区生活方式截然不同,造成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原因、发展情况也不尽相同。因此,深入了解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实际情况,总结好扶贫经验,推进这些地区持续发展,为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服务。本文以六盘山区陕西省陇县、乌蒙山区贵州省六盘水市、大别山区安徽省六安市、藏区四川省甘孜州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综合考察其实际情况,对比分析其选择和创新扶贫模式的现实依据,以深入了解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取得重大扶贫成果的客观原因,这对推动乡村振兴与扶贫攻坚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六盘山区陕西省陇县
陇县地处六盘山区渭北高原西部边缘地带,与千阳县、宝鸡市陈仓区和甘肃清水、张家川、华亭、崇信、灵台五县毗邻;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起伏递减,山岭重叠、沟壑纵横;四季分明,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水系繁多错杂,流量较大,号称关中的“水龙头”;动植物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盛产牛乳、苹果、核桃、香菇及蜂蜜等农产品。陇县位于关中平原城市群,是宝鸡副中心城市、陕甘宁三省交通要塞和边贸重镇,占地面积2 27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7.1 377万人,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98.66亿元,三大产业发展良好,产业结构比为21.940.038.10。陇县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立足地区要素禀赋,挖掘特色资源,以产业扶贫为根本抓手创造了“1265”菜单式产业扶贫模式——编制一张菜单、打造“双百”基地、做大做强奶山羊、苹果、核桃、烤烟、食用菌和中蜂六大特色产业板块、推进旅游、就业、光伏、电商、生态五大新型业态,走出了陇县特色产业扶贫新模式,带动了陇县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整体性脱贫。
2.乌蒙山区贵州省六盘水市
六盘水市位于贵州西部乌蒙山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以丘陵和喀斯特地貌为主;拥有煤、铁、锰、锌、玄武岩等矿产资源;气候凉爽适宜,素有“中国凉都”之称;生态旅游资源丰富,有瀑布、溶洞、峡谷、温泉等天然景观,植物品种繁多,农作物丰富,盛产猕猴桃、刺梨、茶叶、食用菌、中药材、石斛等农副产品。六盘水市处于川滇黔桂四省结合部,总面积9 914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58万人,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 339.62亿元,三大产业结构相对稳定,分别占比为12.744.842.5。其基于优势自然条件,坚持问题导向,创造性地提出了“三變+生态旅游”扶贫政策,以政府为主导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集中资源、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将扶贫资金、农户资源变成资产整合入股旅游业,确保农户可获得定期分红,给予农户一定的土地、房屋、木林等租金补贴以维持基本生活,并推行景区就业、务工或者开展生态农庄等旅游新业态,激发了农民的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了农户通过旅游产业实现脱贫增收。
3.大别山区安徽省六安市
六安市位于安徽省西部、长江与淮河两河之间,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呈梯形状分布,以山地、丘陵、平原为主;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全区河流众多;生态环境优良,自然资源丰富,盛产油、茶、麻、桑、水产、板栗、油茶、毛竹、中药材、食用菌等多种农副产品。六安市是大别山区域的中心城市、省会合肥经济圈副中心城市、长三角产业转移辐射城市和国家级陆路交通枢纽城市,总面积15 451.2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87.9万人,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1 669.5亿元,三大产业结构为14.336.349.4,第三产业占比较大。在我国金融扶贫政策的指导下,六安市根据现实情况,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机构为服务主体,创造了大量新型金融扶贫产品,创新了金融服务方式,如扶贫小额信贷、“劝耕贷”业务、“拎包银行”服务及扶贫保险等等,形成了“1+1+N”多元金融扶贫模式,加强了贫困地区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为贫困户提供贷款担保和支持其特色产业发展,促使六安市扶贫攻坚取得重大成果。
4.藏区四川省甘孜州
甘孜州地处四川省西部、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域差异显著,呈现出北高南低、中部突起、东南缘深切、山河相间等特点;气温较低、冬季较长、降水量少,日照充足;是长江和黄河两大流域的水源涵养地,“中华水塔”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物多样性强,植被资源丰富,矿产资源众多;盛产苹果、石榴、板栗、花椒、古藏茶、油桐、杜仲、红樱桃、芜根等农作物;总面积15.3万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09.7万人,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410.61亿元,三大产业结构为19.625.754.7,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基于自然地理特征,甘孜州农作物产量不高,交通不便,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成为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为改变贫困面貌、提高农作物产量、推动农产品外销、促进经济发展,甘孜州采取了“互联网+科技+扶贫”模式,从强化人才服务体系、打造产业示范引领、构建服务平台体系、壮大产业基地园地四个方面入手,贯彻落实“三区”(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科技人才专项、“龙头企业+”“农业科技园区+”等科技精准扶贫方式,建设优势特色产业示范基地和农业科技园区,搭建“四川科技扶贫在线”甘孜分平台,发挥科技创新驱动力量,促使科技扶贫成效最大限度化,推动甘孜州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
三、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典型扶贫模式的比较
由于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自然环境、发展程度和人文习俗的差异性,各地区自身实际情况不尽相同,扶贫措施也截然不同。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针对自身情况实施精准扶贫,创造了许多典型扶贫模式,如陇县“1265”菜单式产业扶贫模式、六盘水市“三变+生态旅游”扶贫模式、六安市“1+1+N”多元金融扶贫模式、甘孜州“互联网+科技+扶贫”模式,等等。同时,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又有其共性特征:多处于省市交界处,地形主要以山地、高原和荒漠为主,产业单一粗放,多以农业、牧业和矿产开采加工业为主,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等等。因此,典型扶贫模式又具有借鉴意义。对典型扶贫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总结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扶贫经验,为保障地区可持续发展开辟新道路,有效巩固扶贫攻坚成果,使之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效衔接。
1.依托力量比较分析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由于各自面临的实际情况不同,各地区的扶贫模式不尽相同,其依托力量也有区别。陕西省陇县“1265”菜单式产业扶贫模式,以政府为主导来编制扶贫菜单,依托企业、产业基地、贫困户等多方面力量进行合作,打造六大特色产业模块。贵州省六盘水市“三变+生态旅游”扶贫模式,以生态自然资源为基本条件,通过政府、景区、旅游开发公司、贫困户间的相互合作,共同开发生态旅游资源,推进景区就业、务工或者开展生态农庄等旅游新业态。安徽省六安市“1+1+N”多元金融扶贫模式,主要以金融机构及其网点为依托力量,加强金融网点建设,打造新型金融扶贫产品和服务,延伸金融服务领域。四川省甘孜州“互联网+科技+扶贫”模式,依靠科学技术,以科研机构与科技扶贫产业示范基地为主要依托力量,创建和完善“四川科技扶贫在线”平台,提供专家服务、技术供给、产业信息、供销对接等相关服务,组织科技下乡、技术培训等科技扶贫活动,动员科技人员深入贫困村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建立科技扶贫产业示范基地,培育壮大地区特色农业产业。
2.扶贫机制比较分析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模式迥乎不同,其扶贫运行机制也大不相同。陕西省陇县通过扶贫产业菜单,让贫困户自主“点菜”,以龙头企业、合作社、园区等为主体,通过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园区扶持、就业务工、技术支持等方式,将选择同样“菜品”的贫困户吸纳到产业扶贫基地中,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或园区)+基地+贫困户”的全产业链带动模式,建立紧密的生产利益联结机制,使大产业与小家庭融合对接,降低贫困户独户生产的风险与压力。贵州省六盘水市以政府牵头,进行“三变”改革,将土地、木林、房屋等资源、闲散资金及扶贫资金整合入股旅游公司,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生产运行模式,统筹合力开发旅游资源,并辐射影响其他乡镇,共同合作打造农家乐、农家住宿等旅游业态和生态农业,建设特色景区及民族村寨,实现联村镇发展,形成“村村一产业,寨寨有风光”的产业循环发展道路。在“1+1+N”多元金融扶贫模式下,安徽省六安市以政策性、商业性和合作性金融机构为服务主体,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以“金融机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N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运行方式,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户提供不同的新型金融扶貧产品与服务。四川省甘孜州采取“互联网+科技(+龙头企业)+示范基地+农户”生产协作模式,政府牵手科研机构,组织“科技进藏区”“科技扶贫万里行”“送科技下乡”等科技扶贫活动,打造和完善州、县级“四川科技扶贫在线”扶贫平台,构建扁平化专家服务模式,建设科技扶贫产业示范与服务基地,给予贫困户生产发展以技术支持。
3.耦合程度比较分析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相对贫困人口数量多,贫困深度广,致贫原因多元,单一扶贫模式难以解决多维度贫困问题,必须使主导扶贫模式联合其他扶贫模式共同发力。陕西省陇县“1265”菜单式产业扶贫模式,基于贫困户自身能力与现实需要,依托六大特色优势产业,编制种植、养殖、就业、生态多项产业“菜单”,并涵盖道路建设、安全饮水、环境整治和校安工程四类基建以及健康、教育、社保兜底重点项目“菜单”,涉及扶贫攻坚的多方面内容,与其他扶贫模式耦合程度较强。贵州省六盘水市“三变+生态旅游”扶贫模式,以绿色发展为导向,将生态环境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统筹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以生态旅游业带动其他产业发展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在教育、健康等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稍有欠缺,与其他扶贫模式耦合程度相对较弱。安徽省六安市“1+1+N”多元金融扶贫模式,坚持“户贷、户用、户还”原则,做到“应贷尽贷”,通过多元化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户提供适量资金支持,为产业、文化、教育、健康等综合扶贫提供最优化、精准化的资源支持与配置,与其他综合扶贫模式的耦合程度相对较强。四川省甘孜州科技扶贫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通过专家对接、科技下乡、免费技术培训等方式对贫困户进行技术指导,确保贫困户养殖种植、产品销售等技术服务需求能得到有效解决,提升贫困户的科学文化素养,与产业、教育扶贫耦合衔接较强,但是较少涉及健康、基建等方面内容,与其他扶贫模式耦合程度相对较低。
4.风险防控比较分析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工程,也是深得民心的德政工程。但实施过程中由于涉及面宽,工作量大,资金使用多,项目分布广,利益平衡难度大,不确定因素多,各种风险也蕴含其中。”[20]尤其是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必须增强扶贫模式风险防控能力。“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21],但是其经济属性导致扶贫面临着市场风险。为降低价格波动等市场风险,陕西省陇县“1265”菜单式产业扶贫模式,以龙头企业、园区、合作社等为主体,通过入股分红、土地流转、园区扶持、就业务工、技术支持等方式,将贫困户镶嵌到全产业链发展中,增强小农户生产经营与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生态扶贫作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与扶贫攻坚“双赢”的新道路,也有可能引发生态环境风险。贵州省六盘水市在持续推进“三变+生态旅游”扶贫模式的过程中,深入推动“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战略行动,加强生态环保领域的监督执纪问责,保障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有机统一。金融扶贫在为扶贫攻坚带来大量资金的同时,隐藏着较大风险,尤其是扶贫小额信贷,极易造成逾期与坏账风险。为规避风险,安徽省六安市“1+1+N”多元金融扶贫模式,在坚持“户贷、户用、户还”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多途径金融诚信宣传;加强预警防控,对信贷到期数据进行跟踪,建立收回台账,及时掌握贷款到期信息;规范扶贫小额贷款发放与管理,加强小额扶贫资金催收力度,以增强风险防控能力。科技扶贫相对而言风险较低,但倘若贫困户掌握运用生产技术不过关,也会导致技术风险。四川省甘孜州“互联网+科技+扶贫”模式,通过省县“四川科技扶贫在线”网络服务平台,为贫困户提供农业技术指导服务,且积极组织科技人员下乡举办科技培训班,大规模建设科技扶贫产业基地,以规避贫困户因技术掌握不过关所導致的风险。
四、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模式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我国扶贫攻坚任务最为艰巨的地区,在扶贫攻坚过程中创新了多种扶贫模式,取得了扶贫攻坚的巨大成果,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前,我国扶贫攻坚已经取得全面胜利,工作重心开始逐步由扶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如何推进扶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成为当前解决好“三农”问题、提亮全面小康成色、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任务。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密不可分,扶贫攻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为乡村振兴的持续推进奠定了物质基础;乡村振兴是对扶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发展,两者统一于推进“三农”问题的解决。因此,通过对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典型扶贫模式的比较分析,总结扶贫经验,对我国持续巩固扶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价值和启示。
1.坚持地区差异性发展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涵盖我国大部分贫困地区,纵横跨度大,自然环境差异大,发展情况截然不同,区域特色差别大,必须聚焦地区实际情况、自然资源及生产要素等各方面情况,把握地区特色与差异,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发展特色产业,不宜跟风效仿。虽然当前扶贫攻坚任务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但我国乡村地域广阔,发展程度不一,地区特色与差异性大,接续做好乡村振兴工作,也同样需要坚持地区差异性发展。由于乡村还承载着自身的地域历史文化价值和“乡愁”,同质化发展必然会导致乡村历史文化的消殆,村民归属感的弱化以及乡村特色的破坏。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充分体现农村特点,注意乡土味道,保留乡村风貌,留得住青山绿水,记得住乡愁”[22]。因此,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地区差异性发展,其主旨在于聚焦地区特色,需要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各地“三农”发展的实际困难与问题,找出制约地区“三农”发展的客观因素,明确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与期盼;抓住地区特色与优势,掌握市场需求,把握发展动向,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发挥其带动作用和辐射效应,打造适宜地区发展的产业新模式;加强对乡村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加大乡村特色文化的扶持力度,让乡村文化承载“乡愁”,助推乡村振兴。在顺应乡村特色发展、保留乡村原始自然风貌的基础上,加快完善电力、交通、水利、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和相应配套设施建设,助力地区特色发展,释放地区特色的最大效益,避免千村一面。
2.加强地区涉农资金整合与利用
资金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物质基础,优化扶贫与涉农资金的管理与配置、提高资金使用率,是扶持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造血”能力,切实推进扶贫攻坚进程,保障精准扶贫成效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强化扶贫资金监管,确保把钱用到刀刃上”[1]。同样,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需要加强涉农资金整合与利用,构建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扶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推动“三农”工作重心的转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中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进一步完善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长效机制”,支持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用于农业农村设施建设之中;“支持以市场化方式设立乡村振兴基金,撬动金融资本、社会力量参与,重点支持乡村产业发展”[23];建立规范的涉农资金整合管理平台,优化涉农资金管理体系;将涉农资金整合审批权下放到县级政府,明确统筹整合、管理使用资金的责任主体,让县级地方政府自主合理安排涉农资金;继续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保单质押贷款等贷款业务,开发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保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搭建资金整合使用管理监督平台,开展相关监督检查活动,建立省級统一考核、评价监管体系,加强法纪约束与责任追究力度,避免涉农资金的滥用占用;实施“保险+期货”金融服务模式,增强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3.打好政策措施“组合拳”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诱因复杂多变,贫困户往往因不同不利因素叠加致贫或返贫,仅仅只是通过传统“输血”型或单一扶贫方式,难以解决贫困户贫困问题。对此,贫困地区要实现自我调节与发展,必须“采取超常举措,拿出过硬办法,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用一套政策组合拳,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24],即要求打好扶贫攻坚“组合拳”。同样,“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政策衔接,要总结脱贫攻坚成功经验,参照脱贫攻坚相关政策与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乡村振兴的政策与工作协调机制”[25]。打好乡村振兴政策措施“组合拳”就必须:聚焦优势特色产业,盘活各类资产资源,进一步贯彻落实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政策措施,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与发展多元融合新业态;完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快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保障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现实需求;构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体系,坚持“防治结合”原则,实施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协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物质奖励机制与晋升制度,鼓励基层人才扎根农村,大力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加快实现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完善农村治理政策与制度,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农村治理机制,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坚持农村自治、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加强农村普法守法教育,提高农民法律意识。
4.推进地区协同协作发展
我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处于省市边界地区,与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区及国家主体功能区等区域的划分高度吻合,因此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不仅仅涉及经济发展问题,还关乎革命文化建设、少数民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安定等综合性问题,只靠县市级行政力量难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必须跳出行政区域界线,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协作发展,才能实现整体扶贫效益的集约化、规模化与最优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亦需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26]。“乡村振兴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各地的起点不尽相同:既有较好发展基础的东部地区,也有拥有一定发展基础的中部地区,还有刚刚摆脱绝对贫困的脱贫地区。”[27]为巩固拓展扶贫攻坚成果、适应我国各地区现实需要,必须深化东西部协同协作,聚焦协作地区发展优势,建立东西部经济资源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机制,实现资源要素有效对接;强化协作保障机制,进一步推进各地乡村振兴协作互动;“落实好‘东部企业+西部资源‘东部市场+西部产品‘东部总部+西部基地‘东部研发+西部制造的东西合作模式,共同打造东西部协作升级版,助推乡村振兴东西协助高质量发展。”[27]同时,要加快地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破除妨碍城乡发展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推动构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平等交换的体制机制,实现城乡优势互补。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02-26(2).
[2]肖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贫困空间特征及精准扶贫研究[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9.
[3]王宝,高峰,李恒吉.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区空间特征及致贫机理[J].开发研究,2016(6):59-64.
[4]张梦楠.河北省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致贫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D].石家庄:河北地质大学,2017.
[5]李贝,李海鹏.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湖北恩施州龙凤镇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61-67+134.
[6]冯朝睿.后精准扶贫时代云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多中心协同反贫困治理效果评价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0(7):135-146.
[7]付玲,朱洪波.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政策效果研究——精准扶贫视角[J].中国集体经济,2017(28):127-128.
[8]陶少华.集中连片特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困境与实践路径——基于重庆民族地区的调查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8(38):59-63.
[9]孔令英,郑涛,刘追.集中连片民族特困地区精准扶贫项目实践困境与原因阐释——基于南疆地区S县W村的项目案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7(10):35-43.
[10]高虹,王佳楠,吴比,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精准扶贫的经验总结及脱贫启示[J].农村金融研究,2019(5):17-22.
[11]王友云,向芳青.连片民族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协同扶贫合约制治理模式探讨——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06-112.
[12]赵作权,赵璐,陈芳.建立跨区域扶贫开发一体化体制[N].中国科学报,2017-05-08(7).
[13]郭冠男.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多种模式决胜脱贫攻坚——以吕梁为案例[J].中国经贸导刊,2020(6):32-35.
[14]陈忠言.产业扶贫典型模式的比较研究——基于云南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的实践[J].兰州学刊,2019(5):161-175.
[15]付李濤.我国连片贫困地区金融扶贫问题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6.
[16]汪年逸.特色产业扶贫模式比较研究[D].蚌埠市:安徽财经大学,2018.
[17]牛胜强.深度贫困地区推动两大战略有效衔接的使命任务及重点领域[J/OL].当代经济管理,2021(4):1-8.[2021- 04-12].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210401.1346.003.html.
[18]尹业兴,贾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设计[J].农业经济,2021(3):37-39.
[19]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J].老区建设,2011(23):12-18.
[20]石平.精准扶贫工作的风险防控[J].当代县域经济,2017(9):13-17.
[21]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 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J].党建,2018(11):4-6.
[22]习近平在云南考察工作时强调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J].云岭先锋,2015(2):4-5.
[2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N].人民日报,2021-02-22(1).
[24]习近平.抓住机遇立足优势积极作为系统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J].党建,2015(6):1.
[25]何绍辉.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大抓手[DB/OL].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20-06-08)[2021-04-12].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20/0608/c40531-31738293.html.
[26]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J].中国民族,2021(4):1.
[27]雷明.协同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选择[J].中国报道,2021(3):38-41.
(责任编辑:王勤美)
收稿日期:2021-05-1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体系构建研究”(16BKS024);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治理的实践路径及现实意义研究”(19WTB06)。
作者简介:
卿定文,男,湖南新化人,博士,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王玉婷,女,广东化州人,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