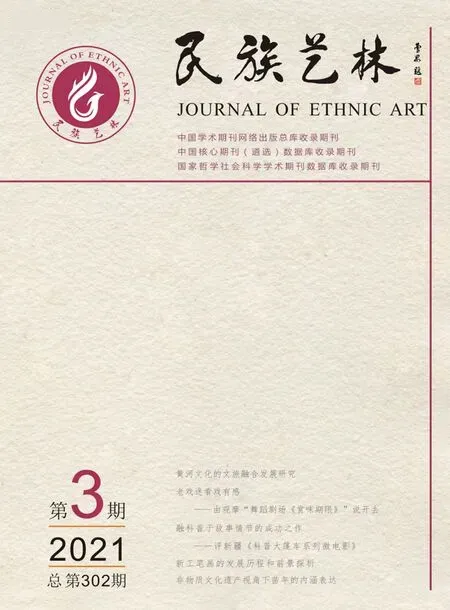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苗年的内涵表达
彭兰燕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40)
一、引言
每逢佳节,各地各民族都在其地域内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庆祝节日。而今发现,不管是中秋、端午、春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还是傣族泼水节、彝族火把节、苗族苗年节、台江姊妹节、布依族三月三等各少数民族的节日,在国家意识、文化洗礼、商业诉求、媒介技术等现代力量的介入下,大多发展为了由吃、玩、娱为核心的旅游节日。苗年尤其如此,苗年自2000 年始(2001 年未举办),雷山县政府便将其作为重点资源进行打造,已连续举办“苗年文化节”20 年,进而“苗年文化节”被塑造为黔东南的一张闻名世界的旅游名片,其节日的仪式性、狂欢性和符号性都呈现出被放大的状态。然而,不可忽视的是,节日正是因其固有的各种仪式活动,使人们在节日中感受到的狂欢和节日文化中展现的可区别各民族特色的符号得以共同构建成一个具有宏大叙事的时空,要研究这一宏大叙事的内在含义,则要从三个层面去进行剖析。目前,已有研究中多从社会历史变迁、民俗文化保护的层面对苗年传统节日活动的微观层面进行分析,尚缺乏由仪式、狂欢和符号三个层面去深入分析其内涵,而此三个层面是与节日内涵息息相关的,因此,从这三个层面去分析有利于更好地把握节日文化存在的意义,也能更有利于从非遗保护的视角去探寻节日文化的内在意义,从而引导相关部门在进行节日文化资源的开发时,能够更加尊重和保护节日文化,让节日文化的内涵滋养节日文化,保其本真。
二、非遗“苗年”的仪式表达
仪式是传统节日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是一种具备理解、界定、阐释和分析特定含义的广阔空间和维度,既是一种认知的体现,也是一种具体的实践行为。它与节日相辅相成,赋予传统节日以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仪式是一个包含丰富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实践的象征体系,是一种文化建构起来的象征交流的系统[1]。”作为一种文化表现,仪式具有象征意义。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在《戏剧、田野与象征》一书中,提出了“社会剧”(Social drama)的概念,尤其强调仪式的表演性和象征性。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释》中将仪式称为一种“文化表演”(Cultural Performances)。这种文化表演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也更适用于今天的现状,尤其是当曾经的仪式在旅游的带动下已然成为一场场文化表演的时候。不难发现,节日总是与一定的民俗现象紧密相连,它借助于仪式化的各种活动对既定文化系统的内涵价值观给予生动的再现和强调。节日中的仪式,是由不断重复的程式化的动作构成,不断重复着既定的固有内容,正是这种程式化的仪式表演,不仅是节日活动有序进行所遵循的“串联单”,而且是承载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动态载体,更是成为某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文化相区别的象征符号。
仪式在节日之中的呈现一般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节日的各种外在形式与物化的载体;二是这种仪式所包含的精神文化内涵。首先,作为节日的外在形式或者物化载体而言,仪式是通过特定的程式、方式或者行动来为某个节日钉上标签。显然,几乎所有的节日都有其别具一格的庆祝仪式,例如中秋节吃月饼、春节的挂春联,苗族过苗年的斗牛、傣族泼水节的泼水等都让人不假思索地就知道是代表哪一个民族的哪一个节日,尤其是少数民族所有的节日活动因其独一无二而更具区别性,类似于这些的仪式活动就是节日的物化载体。其次,作为节日精神文化内涵的载体而言,仪式是承载着民族集体意识的,也正是这种集体意识使得仪式的象征意义能够通过这种集体记忆的形式跨越时空传承。杜克海姆曾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提出,节日仪式能唤醒这种集体意识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民族情感,因为节日仪式所具有的感召力和生命力,能够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人都被当下的参与感、崇敬感或者欢悦感所深深打动,从而从内心深处在这种年年岁岁的固定节日仪式中重温自己和本民族群体之间的认同感。
苗年具有的神秘性与丰富性共存的诸多仪式活动成为游客们纷至沓来的理由之一。具体而言,举办苗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叫“忌年”,苗语称“勤仰”。如十月初五的辰日过年,则从初五起到初七止,不准挑水劈柴、扫地割草,也不准往外倒水,不准互相串门。第4 天后,房族中的一男孩便到自己的叔伯家去玩,称为“踩年”,苗语叫“腾仰”,必须送一碗糯米饭、一条鱼或者一只鸡腿,然后才互相串门。过节第3 天的午日(十月初七),天一亮,男人们争先到井边烧香烧纸,然后挑被称为金水银水的泉水回家做饭,掐食祭祖,然后才恢复正常的挑水、泼水和扫地。人们认为午日这天早上积肥最好,男人们要到村旁去拾猪粪、狗粪暂时存放起来。有的地区则认为十月午日是传统的嫁娶吉日,不少男女青年在这天举行婚礼。第二阶段从十月初八到初十的未、申、酉3 日,叫“游年”,苗语称“游仰”。一种形式是大芦笙队到客村去吹奏,吹奏者身穿青布衣服,开胸对扣,头包青色包头帕。宾主比赛吹笙后,十月初十的酉日,主人为大芦笙队的客人饯行,并送给一条猪腿或一定数量的牛肉带回村。明年的这个时候,今天的主人又变成了客人,双方礼尚往来,友谊长存。有的地区过苗年3 天后,各村寨分别举行芦笙舞会,甲寨3 天,乙寨3 天,丙寨、丁寨再接着来。最热闹的要算第二天,第三天为尾声。另一种形式是男青年到别村去找姑娘对歌,在村旁谈情说爱。第三阶段叫“刹年”,苗语称“刹仰”。即十月十一到十三日的戌、亥、子3 日,是部分地区过苗年的高潮。相邻村寨的苗族人集中到一个芦笙场跳舞,铜鼓也被抬到场地中央悬挂起来,人们随着乐声鼓点翩翩起舞。跳芦笙舞的最后一天,客方的小伙对姑娘们吹起讨花带的芦笙曲。每个跳舞的姑娘都要将事先准备好的花带送给吹笙的小伙,否则会被认为是手艺不佳或懒惰。姑娘们把一条条美丽的花带拴到小伙们的芦笙上,花带寓含着姑娘们的深情,哪位小伙得到的花带多,人们便会发出由衷的欢呼声。傍晚,人们纷纷散场,互相把客人招呼到自己家里,共度佳节。如果大家觉得还不过瘾,可再增加一天,苗语叫“加仰”。

图1 祭祀前的准备——吟唱苗族古歌

图2 苗年期间的苗家姑妈回娘家
从以上三个阶段可以看出,不管是严谨肃穆的祭祀活动,还是自由热闹的娱乐性活动,都有特定的仪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一个完整的节日就是由一系列完整的仪式构建的。因此,“过苗年”也可以说就是“过仪式”,其包含的是生活的仪式、祭祀的仪式、服饰的仪式、交往的仪式和娱乐的仪式等等。所有的仪式都具备着极强的象征意义,包括:对祖先艰苦生活的追思(在苗年期间多食用糯食)、文化秩序的构建(通过祭祀确立与神、鬼的关系,通过走亲串寨确立与他人的社会关系)、对本民族历史的铭记(每逢节日必穿盛装)、对生活的热爱(节日期间各种娱乐活动的进行)。这些仪式都历经了千年的传承和发展,承载的是苗家人丰富而沉甸甸的民族文化情感,已经成为苗族文化的独特象征。
与许多传统的节日仪式被简化而呈现碎片化不同,苗年的节日仪式作为体现苗年文化的重要部分,不但没有因旅游开发而被简化,反而更加注重所有的细节,将其完整地展示出来,所以在实质上其仪式感是被加强的。此外,当地民族群众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的民族所有的文化独特性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益,因此更加重视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如今在全球化、多样化的时代中,文化的独特性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性,通过特定的仪式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归属感十分必要,有必要强化传统节俗内涵丰富、形式生动的节日仪式,从而增进民族的文化认同与促进民族情感升温,从而巩固民族凝聚力。
三、非遗“苗年”的狂欢表达
苏联学者米哈伊尔·巴赫金在系统研究中世纪以来的“狂欢节”文化以及对拉伯雷的作品进行细致而具体的分析后得出了独特的“狂欢化”理论。为了避免被认为是“理论泛化”的滥用,有必要在此说明为什么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能够使用在本文研究节日民俗之中。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理论”的背景是在欧洲大肆兴起“狂欢节”之下提出的,这种狂欢是建立在人们举行各种狂欢仪式活动时所感受到的放松,从本质上看,其实就是中世纪民众借以得到尽情放松的节日,是当时他们对等级社会的一种不满,而这狂欢节是此种等级社会之下的民众的“安全阀”。此外,在巴赫金的研究中,中世纪所有狂欢节庆式的庆贺活动被统称为“狂欢式”,这种狂欢式是狂欢节的仪式活动,属于一种民俗文化存在,该理念萌芽于这一民俗活动的研究之中,因此也能适用于本文对苗年节中狂欢文化的论述。
狂欢节是一种“非官方的民间诙谐文化”,其最鲜明的特征即是暂时消解社会等级壁垒,全民参与,甚至是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也屈尊混入贩夫走卒的低俗嬉笑之中。在狂欢仪式中,等级、权威概念消失[2]。进而,巴赫金提出,从深层的社会含义而言,“狂欢节不是艺术的演出形式,而是生活本身的形式”,并且是“生活本身在狂欢节上表演”[3]。由此看出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是一种源于生活本身中呈现出的各种欢娱形式,是在某一时空里人们所显示出的无阶级的平等的一种共享欢乐的状态,是强调生活中的狂欢,而不是被演出的狂欢。学者鄢鸣对巴赫金笔下的狂欢的认识是:“这种狂欢是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一种全情参与的活动,具有全民性、颠覆性、狎昵性等特点。”[4]但是对于今天的狂欢活动所体现的狂欢特点,笔者更宁愿将其中的“狎昵性”变换为“娱乐性”,因为就巴赫金所描述的中世纪的狂欢节多具有宗教意味,用“狎昵”一词代表亲昵而不庄重则很贴切,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所举行的这些以推动文化旅游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节日庆典活动中,宗教的含义已经十分淡化了,许多节日的祭祀意味也变得越发浅薄,更多的是体现为娱乐的一面。因此,笔者将现如今的节日狂欢的特点概括为“全民性、颠覆性和娱乐性”。不管是在中世纪还是在今天,“狂欢”的实质都是人们借用各种形式给予自己放浪形骸的机会和暂避现实重重压力的机会。而节日就是这么一把解锁狂欢的钥匙,也是最常见的被用来作为举行某种狂欢的筹码。节日一般都具有浓厚的“呼朋唤友齐聚一堂”的共享性,加上节日中不可或缺的各种仪式活动和节日内容,节日民俗与狂欢的直面相撞,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同时也唤醒人们内心潜藏的潜意识。伴随节日氛围的越渐浓烈,一些非理性的潜意识就被激发出来,容易让人在此环境之下开始对自我和对世界有一种新的认知,更加勇敢地去追求被世俗压抑之下的真我,从而敢于宣泄自己的各种情绪,使节日的“欢娱”变成“狂欢”。这种在“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一派欢庆中所迸发的激情和热情将节日民俗的狂欢色彩展现得淋漓尽致。“狂欢节实际上已成为那些不复独立存在的民间节日形式的储存器[5]。”显然,追求欢乐是全人类的天性,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特权,不同民族,不同国家都有许多形式各异的狂欢活动,不管是国外盛行的慕尼黑啤酒节、美国的火人节、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节等,还是我国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还是本文的苗年节都是最好的例证。

图3 丹寨王家村苗族苗年打糍粑
苗年节作为一项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几千年的传承中,依靠代代相传而逐渐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庆祝机制。它的“狂欢”特点同样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全民性。在少数民族节日中,全民性指的是同过苗年的苗族以及前往参与的游客,在苗年节期间,整个雷山的苗族群众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其狂欢的全民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同村同寨间的狂欢。在过苗年时有一个“扫寨”的习俗,即在苗年第1 天,同村的邻里之间的苗族群众会相互邀请去自己家一边喝酒吃饭,一边唱歌聊天,这一种方式十分有助于同村同寨的苗族群众维护彼此间的关系;二是不同村寨间苗族人民的狂欢。在苗年期间,不同的村寨之间相互协商好举办踩芦笙、唱歌、斗牛的时间,一个村寨一个村寨轮流着举行各种娱乐活动,以便于每一个村寨举行活动时都可以互相前往参加,这一方式是用狂欢的形式将不同村寨不同支系的苗族人维系在一起,有利于民族情感的升温;三是青年男女间的狂欢。在苗年期间,一方面会举行“游方”的活动,这是为未婚的男女青年提供彼此认识的活动,是雷山苗家人传统的恋爱方式,是未婚男女青年们主动追求爱情自由的体现,年轻人聚在一起对歌聊天,是心的狂欢;另一方面,苗族人喜欢将喜事集中在苗年期间举办,尤其是喜酒集中在苗年期间举办,苗家人的婚宴所体现的是有情人之间的狂欢。
其次是颠覆性。巴赫金笔下的狂欢节颠覆的是社会的阶级等级秩序,是民众得以在狂欢节中享受到平等和无压力的生活。与之不同的是雷山苗年节的举办是为了在农闲时节庆祝丰收,因此,其颠覆性在于想要摆脱远古时期食不果腹以及辛勤劳作的日常生活,能够在节日期间享受到丰收的喜悦和悠然自得的生活。
最后是娱乐性。巴赫金认为节日是一种区别于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是“非常态”的时空。苗年也是属于“非常态”的时空,苗年对于苗族人民而言是在每一年的特定时间举行的节日,而对于非苗族的人来说更是一种“非常态”的体验,当这种节日与“非常态”的狂欢结合,这种节日的狂欢形式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宣泄情感的场景,从而节日也自然地渗透着不同于平常的严肃性,人们也更加注重能否体验到娱乐的放松感。此外,在苗年中进行的诸多活动也都是让参与者能够放松的,例如斗牛、斗鸟系列或者踩芦笙舞等都是娱乐性较高的节日活动。

图4 苗年斗牛

图5 踩芦笙舞
四、非遗“苗年”的符号表达
节日符号作为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在特定时日集中展现该民族相关文化元素集合的最佳载体,能较充分地表达该民族的文化色彩,由此形成一种众人皆知的符号,从而该符号就能起到代表这个民族的作用,而节日里的符号元素则包括仪式、服饰、节日美食、歌舞等,这些符号元素在节日中被集中地展现出来,正是这些符号元素凸显出正在进行的是什么节日,这便是节日作为一种符号,对于民族文化的意义。苗年作为苗族一年一度中最重要的节日,被认为是苗族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之一,对于苗年而言,其节日符号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与农业自然规律的契合。苗族的诸多节日都是与农业自然规律相契合的,什么时候该劳作,什么时候该休息,都在年复一年的岁月中找寻到最恰当的时机,并且通过这种岁时节日来规制自己的生产生活的秩序,让个体的生命也能在其中得到秩序化。苗年的时间没有固定的日子,是“活路头”每一年根据整个村寨的农业生产情况进行推算的日子决定的,因此,这一节日的过节时间也就充分地体现了整个过节地区的农闲时间的正式到来。此外,苗年大多在农历十月进行,而这一时期属于冬季,遵循农业“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这一段时间属于农闲时节,也恰是庆祝一年丰收的好日子。苗年虽然历经了上千年岁月的洗涤,却仍然能够代代相传至今,其不仅是体现苗家人生活智慧的方式,而且更是苗族同胞们借助特殊时间去完整记忆祖辈们所生活的点点滴滴的方式,从而体现自己作为一个文化体的存在。
其二,是原始崇拜和宗教禁忌观念的存储器。原始崇拜源于早期人类对于某一对象的“无知”和“畏惧”而产生的一种情感寄托。苗族也是很典型的起源于农业文明的民族,苗族祖先们最开始崇拜的对象就是自然,例如苗族服饰图案上随处可见的各种植物花鸟的纹案。此外,苗族也在岁月的积淀中出现了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苗年就能充分地体现这种祖先崇拜,在苗年期间,祭祀祖先是一件重要并且严肃的事情,例如在过苗年的第1天晚饭时,要先将糯米酒、鱼等食物留给祖先,进行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后,一家人才可以动筷子吃饭,以此表达对祖先们的缅怀和感恩祖先们对他们的护佑。此外,崇拜也就会导致禁忌观念的产生,在苗年期间要注意的禁忌也有许多,例如不能在未对祖先进行祭祀前食用饭菜,就是祖先崇拜导致的禁忌观念出现的体现。由此来看,原始崇拜正是通过制度化了的节日祭祀仪式或禁忌,符号化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图6 苗族“嘎闹”支系的百鸟衣服饰
其三,是民族身份的典型表达。苗年作为苗族独一无二的一种民族文化习俗,是极具唯一性的,从而能成为苗族身份的一个显著象征。苗年对于民族身份的肯定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众所周知,苗族历来有“百苗”之称,是支系繁多的民族。在不同区域的不同支系的苗族,有不同的过节时间,过节方式也存在差别,因此可以就此进行简单的支系分类。另一方面,苗年是苗族独一无二的节日,因此能够作为是否是苗族人的一个象征。很显然,苗年和苗族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牢固的联系,提到苗族就会想到苗年的热闹,提到苗年就会想到苗族的生活智慧。
五、总结
节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只有真正的认识其中的内涵意义,才能切实地理解其珍贵所在。苗年来源于生活,其内涵亦表现的是苗族人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不管是“仪式性”“狂欢性”还是“符号性”,都无不体现苗族文化的精妙,并且通过“苗年”年复一年地举办,让一代代苗族人都能从中体会先辈们的智慧,以及在仪式活动中享受狂欢、在狂欢中感受民族文化的记忆,从而更好地认同本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文化身份,形成良性的代际互动,推动苗族文化的传承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