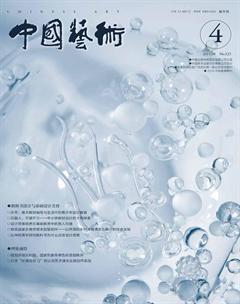“时间—影像”的共时与重构
程艺


摘要:全球化的景观时代是一个不断被视觉技术挟制的过程,全控式的社会处境既已成为现实,当代繁复芜杂的视觉图像悄无声息地重塑和设计着人类视觉神经的感知,我们生活在图像的欲望中,被围观、被侵占、被统辖,我们生活的情境已然成为资本共谋的实践场域。影像作为视听之物和感官场域,如何冲破“景观”的层层包围已成为难题,我们又如何来反思后现代美学语境在当下依然有其效用和机会?媒体、广告、流量、社交网络充斥在当下的社会中,整个社会的中心都围绕着肆虐的消费主义,人的理性似乎在现代社会中缺席。在全球经济结构崩塌、文化颓败,一切都被大数据计算的当下,我们应该生产出新的知识、图像带领人类进入“负熵”[1]时刻,建构人类新思维。
关键词:“时间—影像” 德勒兹 后现代
从柏拉图(Plato)的“洞穴寓言”到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拟像”,影像在不同学科的语境中有着不同的阐述路径。无论是作为权利、欲望的投射还是大众消费,影像都已经成为时间的栅格,成为人类时代的缩影。当初从影像获得的想象力和感召力已经丧失,我们需要的似乎只有欲望。
一、影像是什么?
影像(image)一词在英文和法文中的意义丰富,它既可以指称客体的形象,又可以是形象在意识中的投射。当影像指向他或它之时,需要另一个他或它来补足自身。“Image”是一种质料,是介于主体和客体间的物质。在吉尔·路易·勒内·德勒兹(Gilles Louis Rene Deleuze)看来,事物的世界乃是一种绝对的运动影像,这里已经是一种“元电影”(metacinema)。在此所呈现的图景是所有的事物,以及其所有的面,受到着来自外部的作用,同时以其所有的面,对接受的外部作用做出反作用的回应。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创造进化论》中表述概念“电影幻觉”:一个运动或一个无人称的、统一的、抽象的、不可见的或不可知觉的时间,它存在于机器中,人们“通过”这个机器来展示画面。柏格森将机器记录的瞬间对现实的映射认知为最新的幻觉,一种错误的感知。《物质与记忆》中,柏格森通过绵延(duration)对整体的敞开性和对系统物质的改变来进一步把握对运动、感知和时间的认知。我们注意到,伯格森的理论和现象学的论述在某些方面是前电影的条件。[2]但当电影把目光对准现实中的事物时,它所描述的世界就是一种自身的影像,影像运动间产生的知觉就是来自拍摄者对世界的知觉,而不是柏格森所说的“电影幻觉”,更不是不可见和不可知的。这种运动带来的感知更接近感知物。影像的自身就是物质,并没有藏在机器背后。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在《影像论》中立足于现象学“本质直观”的理念来展开对影像的思考。他以看到桌子上的白纸为例区分出两种存在: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白纸的客观存在并不会因为主观意愿而存在或消失,它是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留存于我们大脑中的“影像”是一种自为的存在,无论我们是否一直观看白纸,它都会存在。但影像与实物间存在着“本质同一性”,不具备“存在统一性”。白纸在人脑中的客观外在及其真实存在方式是一致的,而人脑中对白纸的影像意识和白纸在桌子上的存在方式是有区别的。一个是意识的存在,一个是真实的存在。萨特对于影像的研究可总结为“影像并非是一个物”,影像和知觉有着本质差别,知觉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的,而影像是内在的、主观的存在。影像“是一种意识的状态”,它和思维无关,但会影响思维活动。无论是作为事物本身的形象,还是作为大脑里的拟像,它们如何在电影影像里得到关联,这也成为德勒兹电影理论中论述的重要问题。而作为艺术家、创作者、导演,如何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改造和变异,让其成为现实世界中的真实感知,也是不同时代要探讨的重要命题。
深受萨特早期作品影响的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对形象、叙事、神话等概念的系统阐述,提出了电影“影像时刻”的不可编码性。罗兰·巴特提出,电影只有在停止播放时才能显现出意义。如何获得电影的意义,如何超越电影的影像性,是需要观看者与电影文本在特定语境之中相遇、转化的,是一种超越个人经验和感知功能的存在。获得电影的意义是观看者的一个内在性行为,这种抵抗行为避免了被社会系统整合的可能,从内在超越客观世界的理解。而我们对于他人的理解和获得都只是个人获得快感的行为。“看电影”本身对于罗兰·巴特来说是一个动作,是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运动的一个方式。他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将繁复多变的图像艺术语言简单划分为“能指—所指”的符号分析是无力的。电影内的影像与文本之间相互建构,而观众是在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体验中把握图像文本的“不可明说物”,从而获得从属于私人的感知意义。在《明室》中,罗兰·巴特对于电影的意识形态潜能予以更有力的论述:“图像赋予我生机,我也赋予图像以生命……我和图像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切冒险的来源。”他指出意识形态在电影的图像文本间有更清晰的显露方式,也借用对意识形态的读解和揭露,为电影文本的阐释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径。
德勒兹以柏格森的三本著作《时间与自由意志》(Time and Free Will)、《材料与记忆》(Matter and Memory)与《创造进化论》(Creation Evolutln)中的影像理论为基础,先后在1983年与1985年完成了自己影像理论著作《电影Ⅰ:运动—影像》与《电影Ⅱ:时间—影像》(简称“电影”系列)。他打破了克里斯蒂安·麦茨(Christian Metz)的电影符号学研究,直接深入影像内部,突破了电影叙事和电影意义的厚重围墙。各个时期对影像理论批判的学科如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社会学等,在德勒兹的研究理论中都成为牵绊和束缚。他哲学式的解构影像创造了属于电影本体的概念。“电影”系列谈的是电影吗?电影这个媒介似乎无法涵蓋德勒兹在两本著作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他所谈论的是电影作为影像的电影,所论述的影像又是来源于作为媒介的电影。德勒兹在主体客体、人与世界的范畴之外,论证电影与影像作为第三政体[3]的存在。电影影像是与宇宙影像、生命影像同时存在的。“电影—影像”是对人类本体意义存在之上研究出的新的思想路径,是人与宇宙、思维与影像多重意识的循环往返。德勒兹电影文本的关键是关于“晶体—影像”与其潜在的关系,在“晶体—影像”内部是多种感知动态交换的晶体结构,是多种二元体此消彼长、相互建构的晶体模式,“现实与潜在”“过去与将来”“虚幻与实在”不断在一个最小时间内部循环创造影像的联结和转化。“镜像”和“胚胎”是引发视觉与知觉运动的两种意象形比喻,二者在影像内部打开了身体脱离物理经验的内在动态。“晶体—影像”作为时间记忆最小的循环模式,同时也完成了生命、宇宙、电影三个主体间的循环。这种所谓的世界影像[4]也是德勒兹最初在文本中提到关于“image”的理解,是最初的影像。
二、运动影像的组合关系
无论在柏格森还是德勒兹的观念中,“影像”是无任何符号指涉含义的客体,也并非唯物主义者为区别于“意识”而对立的“物质”。某种程度上,它和尼采思想中的“力”有潜在关联。德勒兹认为“质—力量”与人物和物本身相关,与事物状态和起因有关。影像中的物本身涉及自身并构成事物状态的被表现体,而它们的起因也只涉及自身,构成事物的状态。这种“力”既是实体又是虚幻,看似缥缈又穿插在所有的实体以及生命之中。“力”不是绝对的一元,也否定一切的二元对立。这也契合德勒兹反对一切只针对影像内在意义的解读,我们要从内部与外部、整体与全体、主观与客观、多维度多路径进入电影之中,打破一切中心权力所展开的论述。影像的生成来自人的感知和时代语境的相遇,它的存在是现实和再现的循环,是我们目光投向世界又返回大脑的再现。在德勒兹眼中,事物的世界已经是一幅运动的影像,“元电影”是早于任何影像的存在。运动着的事物接受各个事物的作用,同时反作用于其他事物,这种绝对运动是事物间作用与反作用形成的。柏格森关于“宇宙普遍性变动”的概念阐释是德勒兹提出“运动—影像”的奠基。当“我”沉浸在“世界影像”中,“我”会不断从世界中获得“感知”,这便让多种形态的影像在体内生成,从而“我”生成的“感知”也持续感知世界,这是德勒兹思考影像的起点。
德勒兹借用查尔斯·S.皮尔士(Charles S.Peirce)的符号三分法来构建“感知—运动图示”(Sensory-motor Situations)。皮尔士符号学理论不同于弗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先验结构,“索绪尔的符号学严格限定在语言符号的范畴之内,其符号的所指并不指向实在之物,而是指向物之概念”,但皮尔士并没有被困在语言系统内部,而是直接跳出语言符号,其参照的是来自人类世界的现实物。相比索绪尔,皮尔士的符号学理论更为开放和人性化,其为德勒兹提出的“感知—影像”“情感—影像”“动作—影像”的层级递进提供了理论样本。
皮尔士符号学的理论根基是他提出的三个“普遍范畴”(universal categories):“一级存在”(firstness)、“二级存在”(secondness)、“三级存在”(thirdness)。所谓“一级存在”,主要指涉的是自我的存在,皮尔士又称其为“感觉状态”(qualities of impression),这种存在是不依赖于任何事物的存在。“二级存在”是关于时空的经验,牵扯到事物与事物互相作用的感知关系。而“三级存在”是一种“中介”“再现”,是一级和二级发生关系的场所和媒介。这三种级别的区分是皮尔士哲学思想的基本范畴,德勒兹也在此基础上提出“感知”“情感”“动作”影像的互生关系。如果比对二者的思想脉络,我们可以把德勒兹所认知的人的思维和情感当作“一级存在”,[5]它是理性思考的独立体,是“情感—影像”。现实世界是“二级存在”,它对于人类来讲是外部存在,人的思维和情感通过感知外部和客观世界从而有了自身的判断和行动。“动作—影像”也是基于此而生效的,它是通过人的判断对外部世界的回应。而在“三级存在”的作用之下,人基于实践有了全新的认知和思考,从而对世界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体会和认知,是意义的来源,也是因为在感知和情感双重作用下,最终形成“动作—影像”。
“感知—影像”“情感—影像”“动作—影像”三种影像组合成“感觉—运动组合”。德勒兹把世界的蜷曲化和动作相联系。蜷曲化来自函数概念,蜷曲本身包含着无穷的变异和曲度。而当世界“运动—影像”和作为人的思维的生命影像相互感知和作用之时,世界会发生“曲度”,延展出新的视域,从而在其新的视听系统中建构和再生。[6]动作和感知像是天平的两端,在相互感知中的延迟期是动作产生感知的间隙。[7]感知联系着动作,动作引发行为。间隙生成的延迟感不仅是感知和动作的一个平面,同时在中间还有作为“情感—影像”的推动。在三者的组合关系中,感知的抉择、动作的延迟和情感的推动是生成“电影时间”的主要步骤,也是将电影化身为精神思维的前提准备。[8]这也更系统地论证了德勒兹关于“这是无数的运动影像所组成的没有中心的宇宙中形成的不确定的中心”。
三、从“运动—影像”到“时间—影像”
在“运动—影像”向“时间—影像”的推演转化过程中,传统的“动作—影像”已经在精神感知的影响情景中瓦解,但其生成的一种纯粹的视听情境,是一种关于视听情景的纯描述状态。关于从动作到时间的转化过程,德勒兹在访谈中阐述得十分清晰:“电影,首先是运动—影像:那里并没有一种‘报告介乎影像与运动之间,电影创造了影像的自动运动。接着,当电影做出它的康德革命时,也就是当它终止,让时间附属于运动时,当它将运动创作成一种独立时间时(造假运动作为时间报告的临现)。那么电影影像便成为时间—影像,一种影像的自我时间化。”德勒兹把“时间—影像”大范圍的出现,归因于二战后人类机体感知的转移。
二战引发了人类集体感知系统和思维方式的巨变。二战之前,电影始终是依照传统的以日常生活为主的动作逻辑式的作品形态。二战之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德国新表现主义等风格的出现,使得全球电影生态进入“时间—影像”的视听情景中,从视听语言到观众的观看感也都被深刻地改变了。电影视听关系出现“反逻辑”“反常规”的剪切方式,人物的运动状态进入非理性的逻辑运转模式。电影中的人物进入彷徨、间隔、阴郁的状态,电影的叙事脉络也从线性开始瓦解。二战后的电影叙事更多地趋于分散、间离的方向。这种运动的间隔、人物的彷徨、叙事的间离、视听的搅拌成为德勒兹在阐述电影进入“感知—影像”的例证。时间脱离“运动—影像”和叙事的逻辑发展,一种真正意义的“时间”被电影剥离出来,并抛向电影银幕前的观众。
电影告别叙事,人类从沉浸式的观影体验进入完全颠覆的视听体系中,观看过程中会生成全新的感知和思维。值得深究的是,当灾难给人类历史带来巨变,如何对新的世界、新的理性、新的艺术做出合理的判断?“运动—影像”“时间—影像”两条感知脉络中,自始至终都会根植于人类面对世界遭遇的具体境遇之中。在意大利早期新现实主义的影片中,米开朗琪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已经开始把镜头聚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沉闷时间。从他的《蚀》开始,影片多次对人情的淡漠和空间的空旷进行镜头描摹,从而瓦解掉人物动作带来的连续感知,凸显了物理空间上的感受。而在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影片中,对于真实场景和设计场景的融合是他带给观众最重要的感知时刻,观众会被真实的场景和日常生活的镜头变化所迷惑,费里尼消除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也同时融合了观众与场景的差别。
人们正在面对一个迷惑的局面,对视听情景的转变和替代,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和无法界定性。人物在散乱、失序、颠倒的非线性叙事和任意空间的关系中,无法真正区分和辨认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虚幻的,而自身的心理经验和身体经验也重新打混搅拌。在琐碎的镜头下,日常的真实被一种无法界定的影像带来的真实所替代。纯视听情境制造了极端的主客观关系和心理、身体的感知系统,由它们产生的视听符号彼此不断生成、交流,并在未知的时刻相互转移。法国新浪潮电影运动沿袭了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道路,從代表人物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处女作《精疲力竭》和之后的《狂人皮埃罗》的镜头语言整体来看,都是“毫无目的性”的混乱镜头,正是因为整体性的混乱从而打造出更加纯粹的视听语言。在《激情》中,戈达尔对于感知“运动—影像”的厌弃已经上升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为了增加间离效果,除了在镜头语言上增加更多暴力式的分切和剪辑,在人物设置上也设计了女主角的口吃和老板的咳嗽。德勒兹的“时间—影像”概念在于时间与影像的全新联结方式,对影像的挖掘从运动维度推进至时间维度。
四、“晶体—影像”——现实和潜在
电影不只是镜头的延续和发展,它连接的是与世界相关的图像世界。电影不断在世界和影像间扩充彼此的循环系统,“运动—影像”向“时间—影像”转化中的感知关系并未消亡殆尽,它一直作为一种封闭的物质存在于第一维度之中,而脱离了运动逻辑的时间具有不可辨识性,是存在于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幻间的。曾经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预感说“一种摄影机—意识不再由它能够跟踪或完成的运动来界定,而是由它能够进入的心理关系来界定”。时间的真正属性在于“循环”。影像中的现在与潜在是相互促发和暗示的,没有绝对的现在,没有成不了“现在”的潜在,所有的现在都会成为过去,所有的潜在也都会成为现在。潜在会在某个时刻替换掉正在发生的现在,现在必然会成为过去,以便新的现在到来。所有影像都是由现在和潜在一起构成的,它的内部贯穿了现在、潜在和过去的时间线。
柏格森认为:“我们的现实生活,随着时间的变化,会增添一种潜在生活,一种镜像。因此,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都有两面:它既是现实的,又是潜在的,一面是感知,一面是回忆。能意识到其现在感知和回忆连续分解的人类似于自动扮演角色,倾听和观看自己表演的演员。”“晶体—影像”是“镜子”和“种子”,它在电影的叙述当中会随时启动观众自然的生成现实、想象关系的互动机制。对于“晶体—影像”的形态,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理解为开启人们内在感知系统相互作用的动态装置,一种脱离物理身体经验的内在动态。随之我们进入一种权利关系式的观看,“镜子”的意象使我们的观看处于两面影像的中端,我们观察着真实与想象的边界,“种子”使我们把它内化在镜头某个地点中。这种差异化的动态成功抵消了直接的再现和被围困在时间内部的叙事关系。
人们在“晶体—影像”中可以看到时间本身,现实和潜在于晶体容器中相互循环和指涉,形成影像本身最小的循环。而根据柏格森《材料与记忆》中的“时间圆锥体”推论出,现实和潜在的最小循环是最容易让人获得临时感知的,而关于潜在的潜在则需要调动过去进入更深层的循环内部。我们可以把现实和潜在当作推动异质流逝的力量,一个面向未来,一个面向过去。在晶体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时间的永恒,它是地理概念中的“多层化”,每一次呈现都意味着把时间压缩到时间内部,就像层岩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分裂、增生。费里尼的《八部半》、维姆·文德斯(Wim Wenders)的《事物的状态》都揭示了“种子”和地点的关联,它们是如何成为剧中的电影,在剧中发生从而再指涉回影片本身的发生关系。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思考成为景观的影像和现实本身的关系。
《公民凯恩》中由若干个证人的“回忆—影像”镜头去拼凑故事线索,这些属于回忆的时区被连续地集结成属于过去的“现在”。诚然,这些过去的时区都反映着当时的事件,每个时区的部分记忆都或多或少地还原了凯恩之死的线索。在每个时区当中都隐藏着柏格森所指称的“闪光点”,这个点成为展开凯恩生活的所有“记忆—影像”,从这些记忆时区挖掘出来的影像都是用来重构属于过去的“现在”。但在这个时区的记忆又不同于纯粹的“回忆—影像”,因为纯粹的过去不能置换为属于当下的“现在”,它仍是属于封闭的回忆。这种回忆本身和电影中那些证人一样,充当一个尖点重新跳进回忆的时区内。电影中有关凯恩妻子的故事情节,所使用的长镜头是对于过去时区的全面打开。这时的苏珊已游离于现实世界,她的思维已经回到过去,此时的影像时间已经全面脱离了运动关系,而是让运动隶属于时间。
五、“时间—影像”的共时与重构
德勒兹通过《电影Ⅰ:运动—影像》《电影Ⅱ:时间—影像》揭示了电影的“时间”从“运动—影像”的关系中脱离,并进一步求证人类对呈现影像主体的理解的变化。德勒兹十分明确地在《电影Ⅰ:运动—影像》中告诉读者,这并非是关于电影史的研究。在面对二战毁灭性打击后的重要历史时期,德勒兹对影像学的分析更多地带有一些伦理学的意味。他把电影中的物质客体和电影本身当作研究中被描述的对象,其实更多的是描述自身。[9]他认为电影是一种言语行为,展示的是一种心智质料[10]。电影利用自身的言语,描述构建电影本身的“对象”,从而生成一套完整的“心理机制”,即具有自身逻辑的精神自动装置[11],也具备某种语言的可陈述性。描述的即是一种人在经历过后的感知结果[12]——对物的感知,对宇宙的感知。电影中的整体是完整的经验主体,是人展示出的情感质料。我们从《电影Ⅰ:运动—影像》总结出“运动—影像”同时承载着运动物体的位移动态过程和所有感知运动物体的共同性质——纯粹运动。纯粹运动关乎整个宇宙物质的本质性运动,然后在双重的感知运动作用下,我们才对“感知—影像”“动情—影像”“思维—影像”等有了内化的感受。电影作为一种动态媒介,开辟了我们心灵去往宇宙万象的途径,而在和宇宙这个巨大的影像库相遇后,我们会把产生的感知拍摄成影像展示出来。
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当时间从运动过程中转向和断裂,“时间—影像”将会展示出什么样的形态和表征,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力量?德勒兹在围绕整个“时间—影像”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在戈达尔等人的现代电影中,“直接时间”早已转变成若干种物质存在于电影中,各种视觉材料被打乱、推进、延迟、粉碎、破坏、重组,属于异质的“直接时间”被一次次地叠加和抵消,视听影像已不再是一个整体,它成为可以被随意暴力拆解的组合。但在不断被推进的、复杂的、异质的影像空间中,政治与社会、男性与女性、真实和虚幻与现实毗邻,所有要素和符号共同“钩联”出巨大的网络。现代世界变幻莫测,巨变中隐藏着巨量的话语和信息,巨量的信息阻碍了人类与真实世界联结的通道,超越了心理个体,也使得外部整体被撕裂成碎片。如今各种信息在我们“内部”形成各异的图像,它们利用自身的无效性侵袭了我们的精神思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现实中找到有效的信息来源。
法国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人物戈达尔,在他的早期作品《精疲力尽》《狂人皮埃罗》中,男主人公都以“浪荡者”的人设出现,他们没有羞耻心和道德观念。如《精疲力尽》中男主人公米歇尔不停地偷盗,不断进行毫无头绪的冒险,嘲弄一切,这些“浪荡者”不再对影像中的情境产生过多深入的反應。这是“动作—影像”无法延续感知活动的全面失效,“动作—影像”不再通过情景产生“感知—影像”,而是转换成一种纯视听的情境。那么脱离了运动的纯视听影像在时间的绵延中又再次被谁连接?德勒兹在《电影Ⅱ:时间—影像》中谈到“任何影像的连续都形成一个序列并向一种反射它的类别转换,这就是从一个类别向另一个确定力量变化的类别过渡”。这种连续的影像序列相互连接和构建,在戈达尔的电影中尤为常见。异质图像、人物姿态、场景颜色等都在符合反射条件时构成一种类别。这种有断续的序列组合连接而成的影像时间线是横向发展的。那么在《周末》中,用来反射幻想、暴力、癫狂的感知类别,又会形成另一条更高阶层的力量序列,两条序列相互交织重叠,如《自画像》的绘画类别、《芳名卡门》的音乐类别,两条序列共时延展合并,聚集了两种不同的“时间—影像”。
被聚合和共时的纯粹时间,它们化身于各种形态的符号和画面中。在戈达尔的影片中,这些画面看似被暴力地切分和剪辑,但它们永远不是孤立的。在非理性剪辑和随意融合画面的转场过程中,“感知”与“运动”已全然脱离。它们化身为对光、音乐、物的纯粹感知,与它们相联系的是更虚幻的精神和深邃的思想。看到森林会联想到自由,这已不是线性发展的连续感知,而是产生感知后与精神思维的循环,二者在一个不可识别的尖点相互创生和发展。“时间—影像”创生出的“精神符号”储存在“晶体—影像”中,每一个“晶体—影像”中的小循环都在为之后的循环铺垫,是被识别的基础。运动关系在电影中中断,而继续在“晶体—影像”中循环。
在二战前的经典电影中,两条序列犹如两条坐标贯穿于观看者的大脑之中,影像画面之间彼此连续、相似、牵引、对抗地横向延伸,而被安置、剪辑好的图像画面会自然地生成概念和思维。这种作为概念的整体也不断被外化,最终形成观看者的自我意识。这个影像整体的内部是不断由两股力量驱动而带来变化的,“运动—影像”的延伸和经剪辑后生成的概念搅拌着电影内部和外部,形成两种精神符号,它们二者间呈螺旋上升状,无法断裂。
在现代电影中,以戈达尔为例,剪辑的失效造成精神、思维无法连续和快速生成,蒙太奇成为经典电影生成精神符号的刽子手,造成了整体内化的中断。来自不同时空的脱节影像被安置在前后,彼此间相互抗争和拒斥,这是属于戈达尔电影中特殊的剪辑和衔接方式。似乎这些图像没有理由具有延续和内化的功能,更丧失了与电影整体的关系。但属于影像的自我意识并非全然消失,反而每个时区、序列的图像都有了意识,这是相对于经典电影中欧几里德坐标的崩塌。戈达尔的影片中已没有相对完整的影像整体的内外运动,因为聚合被打乱、共时被重组,而被构建出的是不受约束、肆意发展的内部和外部的对立。断裂的内部如何维系一个外部整体,整体又如何使得内部拥有理性的秩序,这是独属于戈达尔作品的不可公度性。德勒兹说:“直接时间—影像的精神符号是不连贯影像间的(但总是重新衔接的)非理性分切和不可整体化。人们可以轻易地接触外在或内在,因为它们是非理性分切这条界线的两个方面,这条界线也不再是它们之中任何连续的组成部分,它只作为一个必须会为自己提供一个内在的自主的外在出现。”
注释:
[1]原本负熵(negentropic)只是指植物的生长过程,斯蒂格勒将其改为“negantropic”,旨在说明人类外在器官化的学习过程。他认为此处的“学习”可以等同为福柯所说的“规训”。对于现在的社交网络平台,斯蒂格勒认为则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其本身的知识。
[2]柏格森认为影像的总体即物质,且将其与运动画上等号,变动成为影像的特性,是影像与一切生成事物结合的结果。“比精神上的再现多一点,但比物质物体少一点。”影像存在于一切正常知觉之前也独立于所有感知主体之外。
[3]德勒兹区分了“运动—影像”中的三大政体(regime):世界影像、生命影像、电影影像。作为第三政体的电影影像,其感知方式不在于客体世界,也不在于生命本身,而是在于其自身——摄影机的感知。
[4]在《运动—影像》中,德勒兹把世界中的呈现物(what appears)的整体集合称为影像。认为这些影像不过只是宇宙广袤中繁生的调整,每一个影像都是“借由所有组成部分”作用于其他影像并呼应着其他影像。这就是宇宙影像,或者称为世界影像。
[5]德勒兹借鉴了美国符号学专家皮尔士的逻辑学和符号学的“三度”理论。而这三度在德勒兹的“运动—影像”符号分类中分别对应感知、动情、动作三大范畴。
[6]德勒兹认为当“运动—影像”与世界中不确定性中心即有生命影像相互联结时,世界发生了曲度的变化,形成新的界域,且围绕着中心而发生新的组织关系。
[7]德勒兹认为“感知—影像”是引发人物动作的基础,而动作则是一种综合,蕴含着感知与动情,“动情—影像”则起到了中介作用,将感知延伸到动作。
[8]德勒兹在《运动—影像》通过结合摄影机运动机能和皮尔士的符号学,把电影看作自动装置。又在《时间—影像》中,将影像与符号、身体与思维、感知与记忆推向更为无限广阔的维度。他认为电影装置的根本意义在于机器意识:非人。
[9]德勒兹认为电影不是一种语言,而是语言可陈述物的一种视觉质料。
[10]德勒兹在《时间—影像》中把电影形容为一种言语行为。它用来展示心智质料。这种心智质料如同一种预含物、一个条件、一个必然对应物,言语行为通过它建构自己的“对象”。
[11]语言通过意义单位和操作这个精神自动装置提取语言。
[12]当语言获得“心智质料”或可以被陈述时,它便把它们变成不再由影像和符号表达的纯语言学意义上的再描述。
参考文献:
[1]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
[2]德勒兹.电影Ⅰ:动作—影像[M].黄建宏,译.台北:远流出版社,2003.
[3]德勒兹.电影Ⅱ:时间—影像[M].谢强,蔡若明,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
[4]德勒兹,迦塔利.什么是哲学[M].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
[5]德勒兹.康德与伯格森解读[M].张宇凌,关群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6]德勒兹.尼采与哲学[M].周颖,刘玉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7]萨特.影像论[M].魏金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8]柏格森.材料与记忆[M].肖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9]德波.景观社会[M].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10]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2.迷失方向[M].赵和平,印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
[11]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M].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