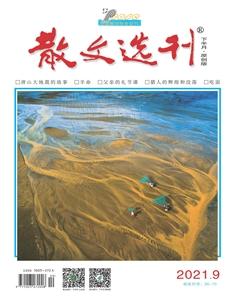同志们
段兵胜

清明节前回乡下,村里儿时玩伴大春跟我讲了个故事。
他说,隔壁村“同志们”是个老革命。这位老革命没读多少书,是佃农家庭出身,用大春的话说,叫“根正苗红”。他长得一副憨厚相,吃得苦,干劲足,不到30岁就当上了乡里的干部。但他讲话的水平一直没有练出来,一开口就是“同志们”,然后如“鸭子囫囵大螺蛳”一样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几句大实话,一点官威也没有,所以大家都叫他“同志们”。不打紧的会议,台上的人在讲话,他坐在台下,半分钟不到就打起呼噜。
虽然如此,“同志们”在我们这一带依然有口碑,他这个老党员,从不搞特殊,长期走村串户工作,不坐公车,忙起来甚至不分日夜。他还练成了个特异功能,边走路边睡觉,但总走不到沟里,撞不到田坑。
大春说,“同志们”儿子也是党员,也吃“国家粮”,不过不是靠“同志们”吃上国家粮的。他高中毕业后,表现突出,先是被推荐到村里当团支部书记,然后进入乡电影队放电影,接着自己考进了大学,最后进了黄石的一家钢厂搞政工。遗憾的是,政工搞得好好的,厂里要改制,要分流突围。他想,留下来的人都应该是技术精英,要靠那些种子选手发愤图强重整雄风,于是主动“下海”了。这时候,“同志们”也没为儿子的事去开个后门,他总是对儿孙说,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是好汉。
“同志们”退休后也不闲着,帮助他们村里修桥、补路、打水泥、晒场、搞文化活动室建设。有心人算了下,这些年来,他为村里出的钱,大约10万元。但是他对穿衣打扮不讲究,没见穿几件新衣服,夏天穿出来的衣服,白汗衫,大黄裤衩,老伴都给打了补丁。特别是吃饭,“同志们”看到桌上了撒了一粒饭,也要捡到嘴里去。有一次,他筷子夹一粒花生米,中途花生米掉落,从桌子上蹦到水泥地上,他从地上捡起来,将花生米上的红衣搓掉,然后将洁白的花生米放进了嘴里。
“同志们”的老伴先他离世了,儿子儿媳从城里回到乡下照顾他。好冷的冬天哟,儿媳用温水给他洗衣裳,他看见后责怪儿媳浪费:“我一个月用不了你一天的电。”气得儿媳摔了衣服起身回城。儿子也埋怨老父:“我们从来也不花您一分钱,您那么多钱也花不完,退一万步说,就是钱不够花,我们给钱您花,这冷的天,您何必要儿媳浸着冷水给您洗衣服啊?”“同志们”说:“不是钱的事,你妈一直是冷水洗衣服。”儿子生气归生气,服侍归服侍。孙子听妈妈说这事后打圆场:“老了,随他。”这孙子刚读完博士,在老爸的劝说下,舍弃了大城市和发达城市的多个高薪工作诱惑,回到父亲曾经上班的钢厂搞技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到哪都是工作,家乡更加親切。
我见大春讲到这里停顿了下来,就问:“大春,后来呢?”
大春说没完,故事的高潮部分,是在今年。春节前,“同志们”的儿子要贴春联。“同志们”不让贴,90岁的他可能有了要离开世上的预感。大年初二的晚上,一群村里的侄子侄孙来看他,陪他吃饭,他罕见地喝了一点酒,然后让儿子打开抽屉拿出存折交代后事,说反正儿孙现在生活也不缺钱,他只存了这么多钱,是办后事用的,乡里乡亲来帮忙,不要亏待了人家。儿子看见存折上只有39000元钱。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怎么只有这么点钱,他家又没花父亲的钱,依他的估算,这些年的退休金,加起来至少应该在100万以上才对。
他还在疑惑呢,只听见“同志们”对他说:“我走后,政府应该要发一笔丧葬费和抚恤金,应该还不少,这笔钱就捐出来,用于革命旧址保护和革命文物征集吧。”
第二天一早,“同志们”真的走了。
我听完故事,好久没有说话,和大春告别时在心里决定,我一定要到这位老党员、老革命“同志们”的墓前祭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