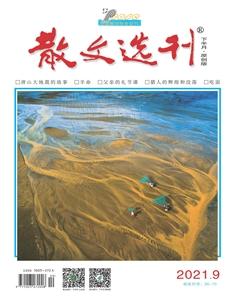父亲
韩琨瑶

父亲是一位地质工作者,他们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山越多、越险、越闭塞的地方,就是他们要去工作的地方。
逢暑假,妈妈便带着我和弟弟去寻父亲。父亲的单位夹在大山的中间,我们乘坐着解放牌汽车在崎岖的山路上转晕了头,才看到山坳里的一大片青砖楼房。车子在那幢略高些的房前停下来,司机跑进去连叫了几声“韩工”,才见父亲不紧不慢地走出来。他蓬松着头,满脸胡子拉碴,又黑又瘦,像山中烧炭的老农,怎么看父亲也不像是个工程师。走进父亲房里,我们看到满屋的零乱,一大摊铺开的绘图纸,纸上精致的标志以及密密麻麻像机器印制的细线,这才意识到,父亲真的不一般!
父亲的地质队离家二百余公里,那时交通不方便,父亲每年只在我们寒暑假期间回来。
每次听说他要回家,我和弟弟都很欣喜,整天地盼着。等他拎着大包小包走进家门时,我们却又很惶恐,一来可能是由于很久没看到父亲;二来呢,是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的缘故!每每这时,我和弟弟总躲进内屋悄悄偷窥父亲,而父亲总是不慌不忙地打开黑皮包,頭也不抬地喊:“树红!树昆!过来拿你们的东西。”这句话是我们一年中最感到惊喜的。我俩会丢掉羞怯争先恐后地凑上去。父亲翻了翻,拿出两个铁壳文具盒和绘图铅笔,分我们一人一份(那时绿颜色的这种绘图铅笔最好了,使劲儿削都不断头),又摸出一些糖果给我们。我和弟弟拿着糖果去四合院中吃,左邻右舍的小朋友羡慕地望着我们,分享着我们有个当工人的父亲的快乐。
第二日,我们就再也快乐不起来了。因为父亲开始查问我们的学习,检查我们的考试成绩,并为我们制订假期学习计划。计划很紧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由他带领,到房后的田问路上跑步,做早操。热了便回屋去洗脸(那时父亲总会用手摸我们的头看是否淌汗了,如淌就算锻炼好了,没有,还得再跑一下),然后拿着语文课本去朗读,读声要洪亮,吐字要清晰。读一个半钟头,回到老屋对面的小砖房里写假期作业。有时一进去,我和弟弟如释重负,把门倒关了耍闹,听到父亲脚步声,又赶紧鸦雀无声地做作业。就这样,一天天把假期度完。
于是,我们便盼着父亲快走。父亲走了,妈妈就会放我们去“小白房子”用弹弓打谷雀子,或是到“机械闸”下的沟里摸鱼。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一天天长大。父亲照常每个假期回来帮我们补习功课。读完小学五年级,我和弟弟以优异的成绩考进陆一中。但父亲丝毫没有放松对我们的严格管教,每每送我们到校,都严肃叮嘱:“学习最重要,你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读好书。”
初二时,父亲发现我们英语成绩不太理想,便试着辅导我们。但他学的是俄语,只好以百倍的毅力,坚持自学英语。“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辅导下,我们英语水平逐渐提高。
六年的中学生活转瞬即逝,我和弟弟考取省内重点大学,父亲的教诲常响在耳边。我和弟弟的大学生活极其勤俭。冬天穿着父亲寄给我们那种他登山穿的“翻毛皮鞋”,戴着妈妈织的毛线手套。大学四年,父亲每隔一周便要寄封信给我们,信封是父亲用很厚的牛皮纸做的,沉甸甸的,有时一拆开里面还会掉出几张十元的钞票来。信上写的是些鼓励我们加倍努力的话。字里行间,折射着父亲望子成龙的心愿。父亲每次到学校看我们,都身着蓝布工作服,肩挎帆布包,手捏长把黑雨伞,还刻意把胡须剃得很干净。找到我们后,带我们到学校附近的小馆子坐下,点几个我们喜欢吃的菜。父亲默默地低着头,一个劲儿夹菜给我们。吃完了,他又唠叨些专心学习之类的话,然后便径自去了。
四年后,我们步人社会。分工作时父亲根本不考虑走关系的事,他郑重地说:“我这辈子是不求人的,不会走后门,凡事你们多靠自己。什么工作都是人做的,重要的是把每件事情做好,接下去该走什么样的路,自己选择。”于是,我们被分到最基层山乡农村工作,每日里上山下村串户,田边地角踏遍,真是好辛苦好累。有时几个月回家一次,晒得脸皮黑里泛着红光。但父亲并不同情我们,他写信说:“这正是锻炼你们吃苦耐劳的好机会,你们年轻,不吃点儿苦怎么行!我五十多岁了还不照样在登山,每天还要走几十公里山路!”我们听了,纵有千苦万苦也难张口了,渐渐地,习惯了基层生活。我每日除了工作还背着画夹,去画一些松林村落、鸟石山水。仔细观察和体验农民的生活,感受他们的质朴和憨实,细细品味那份浓浓的乡情。随着我们的成家立业,渐渐懂得了父亲的话。知道现在我们拥有的一颗完整独立、忘我的事业心和那种对待困难的坚强毅力是与父亲长期的谆谆教诲分不开的。我们没有了对家的依恋,我们对事业一往情深,我们耳中无时无刻不在响着父亲的声音:“你们少操心家事,努力干好工作是大事。”
终于有一天,父亲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带着颇具荣耀的无数荣誉证书,永远回来了!这个工程师,除了铺盖行李,就带回一大箱存书和绘图工具,加上一捆他认为能留做纪念的得意之作——大大小小的图纸。父亲开始闲下来,闲下来的他不知所措,做什么呢?他不擅长闲暇度日。我们开始教他钓鱼,这个时候,父亲好像个孩子,不时地对我们问这问那,我们心中不禁暗暗好笑。我们的子女也围着父亲一个劲儿地喊着“爷爷、爷爷”,而父亲却又重复着原先教育我们的方法去教育他们。有时一个小学三年级的数学题会弄得他头脑发涨,但他总不肯认输。他两鬓斑白,行动渐渐迟缓。他真的老了!当我们去上班,他会装得很平静地问一句:“几时回来?”再也没有了那些极其严厉教训人的词句了。
我们现在已成父亲,在重复父亲原来教育我们的样子,这是多么神圣而神奇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