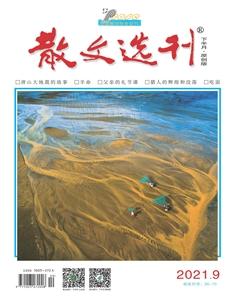消失的一星期
朱未

毫无征兆,在一个周日的早上,我开始腹痛。
这天,如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完后,我坐在沙发上准备吃爱人烤的面包。这时,腹痛开始了。我想,或许是饿了,或是岔气,吃完早饭也许就恢复了。然而,饭后疼痛加剧,那是一种肺部以下、腹腔中间位置的疼痛,痛感呈环状,放射到后背。于是,在冬季一个暖阳杲杲的日子,我踩着香樟树黑色的果子,佝偻着走进了医院。
经过问讯、触摸、验血与CT检查,被告知得了急性胰腺炎,需住院治疗。疫情期间,住院须先做核酸检测,所以,当天只能在门诊挂水,一直到深夜一点。从星期一的早上开始住,彼时,我并不清楚要在医院里度过几个白昼与夜晚。
病房号711,和爱人开玩笑说,我住进了便利店。病房三人一间,一位43岁的大哥早我一天人院,他与我是同样的病症,不过我是初次发作,而他却因为急性胰腺炎第七次入院。听到他报出的数字,我惊讶不已,他是到底放肆自我到了何种程度才会如此反复地进出医院。大哥说他每隔一两年就会发作一次,人院、治疗、恢复,继续酒肉生活,如此循环往复,不加节制。
“我现在喝一碗白粥,感觉都是最香的。”他从昨天开始就没有吃东西了。
住院第一天,身体处于余痛的振动之中,护士通过机器设定流速,我被24小时不间断地注射药物。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天,我的身体被禁锢在床上,不能自由活动,我肉眼所见的世界是病房,四肢所能控制的区域是病床。手臂的疼痛是隐隐约约的,又是永不停息的,每一滴药水的滴落,带来一段阵痛。到后来,血管受到不间断的冲刷刺激,肿胀起来,胳膊比原来胖出许多,像一条饱满的牛蛙腿。
戳入手臂的针头,像是闪着寒光的铁链,被囚禁在病房的时间,仿佛几个世纪那样无聊而漫长。我打开手机,可有可无地回复几条消息,一只手举着手机,不一会儿就累得放弃。药水和营养液不停地流人体内,让我得以存活下去。每天,不同的护士来给我注射和换药,我不能做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我活着,然而,仅仅是活着而已。
住院前三天,我不可以喝水、不可以吃东西。前两天,疼痛覆盖了一切的欲念,因为有输液的加持,感觉不到饥饿,我甚至忘记了人类还需要吃饭这个事实。第三天,身体渐感舒适,干裂的嘴唇就像龟裂的土地,渴望着甘霖降世,想吃东西的欲望复苏了。爱人切了几片黄瓜给我擦拭嘴唇,我贪婪地把黄瓜含在嘴里吮吸,如此甘甜、如此美味,仿佛三万六千个毛孔都吃了人参果。那一刻,黄瓜的汁液就是最好的玉液琼浆。第四天,医生开了一罐营养粉,用温水搅匀,乳白色的液体,真正的可以浸润口腔直通腹部的液体,小时候,喝豆奶粉之类的固体饮料我会吐,而此时,杯中美好的营养粉,是如此的动人。第五天,护士在住院牌饮食那一栏,贴上了四个字:清淡流食。这意味着我可以吃食物了,我终于理解了同病房那位大哥对白粥的渴望。
住院期间所要忍受的痛苦,可不仅仅是胳膊的肿胀和腹部的饥饿,还有屋内环绕的无休止的呼噜声。那位大哥的父亲六十多岁,五短身材,头大脸圆,一副憨厚朴实的样子,然而他的呼噜声并不朴实。他鼾声如雷,一旦开始,一刻不停。他睡着时,张着嘴巴,大口吸进氧气,大口排出二氧化碳,各个音阶的声音从他口腔和鼻腔喷涌而出,那鼾声轰轰隆隆,势不可挡,就像拖拉机驶过夜晚寂静的街道。
住院一周,我摆脱了社会所赋予我的一切角色。不再是一名文学工作者,不必处理琐屑的工作,不须回复那么多的微信群消息。疾病成了最好的防火墙,把社会关系挡在了墙的另一面。医院外的世界运转良好,我参与或是不参与,都是无足轻重的。诗人穆旦写过:“你给我丰富和丰富的痛苦。”正如每一枚硬币都有两面,这一周,我胳膊疼痛、饥肠辘辘,身心却获得了清风徐来一般的平静。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生病會让一个人明白,只有存在本身才是存在的意义所在,存在之外的种种不过是存在的附加而已。那些天里,“想到故我与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人难为情”,夜晚从7楼的窗户眺望这座城市,那楼房里的点点星火是如此温暖而温情。
住院一周,我所经历的那些琐碎,仿佛光束中飞舞的尘埃,细微而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