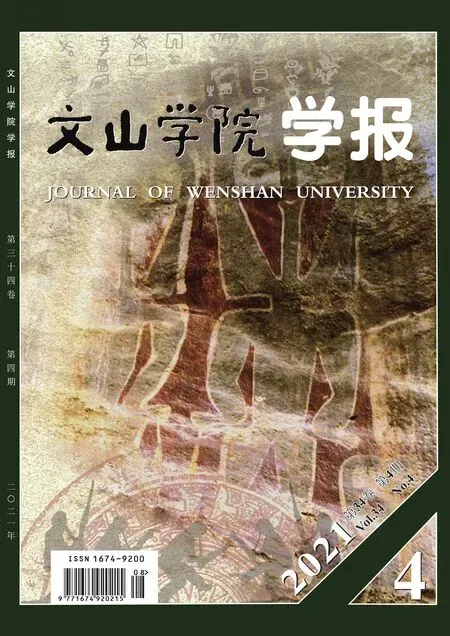工商人类学视角下明清洱海地区历史开发与环境变迁
刘 黎
(曲靖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一、工商人类学与民族地区环境问题
在工商人类学中,文化具有核心作用和意义,“文化,有利于规定个人应当做什么,为了生存在其生活环境中,需要文化进行跨代沟通。……文化允许行为创造和约束。”[1]这涉及到工商人类学中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组织文化,“解释文化的关键步骤,是确定组织倡导的重大价值。”[2]任何文化都要依赖于一个组织为载体,形成组织文化和组织行为,二者共同影响施加作用于组织团体本身。“从管理来看,随着人们参与一整套共同的准则和价值观,他们会最大程度地与管理者进行基础合作的。结果,通过帮助组织成员间建立和维持有效的工作关系,文化能够最大程度地加强内部组织整合。一旦个人主动了解文化的准则和价值观并将其内化,直接的监督会变得不重要,因为共享的准则和价值观会控制个人行为并激励员工。”[2]在本文案例资料中,白族即是一个组织团体,白族文化是一种组织文化。文化是一种复合多元的事物,白族在其形成过程中融合了洱海周边众多的族群,其最终文化也是多元的,吸收的中原儒家农耕文化,在其族群演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清王朝政府把腹地富余人口引向边疆垦殖,缓解人多地少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然地理环境相对优越、农耕文化厚重的大理地区成为王朝政府发展农业经济的重点对象。在大规模无序的开发下,大理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本文借用工商人类学组织文化与组织行为的理论在历史检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尝试解读分析在白族组织中,如何适应、约束和改观在社会历史大背景变迁下所产生的新环境、新事物,使其在自然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中形成一个平衡局面,以促进白族组织团体的和谐发展。这就涉及到白族组织团体内部的组织文化和个体组织行为对文化、技术与制度三要素的看法,组织的有效凝聚与运转有赖于对不同文化因素的管理和调和。技术和制度,在人类学意义上,也是文化的衍生意义事物。在一个组织内部,制度是一种原则规范,技术是一种发展手段,二者最终都将由文化因素融合进组织团体的个体,即内化,使其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并长期坚守而不改变,这其中既牵涉到国家、政府和社区的整体管理,即组织文化的倡导,又是白族内部个体组织行为的认识、体验和内化,二者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二、案例资料:对大理白族明清以来农业开发史的历史考察及田野调查
笔者以云南大理白族为调查研究对象,大理地处滇中,白族占到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强。大理地区明清以来移民涌入及农业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遭到过度的开发和利用。
(一)历史检视
朱元璋荡平盘踞云南的元王朝残余势力后留沐英镇守云南(其后代世袭镇守云南),洪武十九年沐英上奏朱元璋:“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待。”[3]2709次年,朱元璋令沐英等“自永宁至大理,每六十里设一堡,置军屯田。”[3]2805明代末年,洱海地区的耕地已由明初的2.8万顷增加至5万多顷,扩大了近一倍,历史上素称干旱的云南县,亦一变而为“云南熟,大理足”的富饶沃壤之乡。[4]“清代中叶……在人口总量上,连续突破2亿、3亿、4亿大关,到1851年达到4.3亿,在110年间增长了2.9亿,超过了以往所有历史时期的增长量,形成庞大的人口基数。”[5]清廷积极制定政策应对人口增长压力,“……各省凡有可耕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6]清代内地人口迁入云南、贵州和四川西部的人口在300~400万之间。[7]到清末云南人口已达1250万人[8],而明末云南人口仅为147万人[9]。清代为降低水位,扩大洱海出水口,保护洱海周围的农田不被淹没,“……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浚,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余亩,……”[10]大量人口迁入,而土地开垦的有限性决定了这种办法为必然趋势,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努力挖掘可利用之资源。
大理地区是滇西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在明清云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大理府的人口仅为5.2万人,而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则骤然增至56万人,1830年为59万人。[11]869-8761713年,大理地区人口密度为2.89人,1830年为44.27人,增长了15倍。笔者以1827年为基准,云南布政司的田亩为92 887顷,夏税为240 548石,丁税为203 831两,大理府的田亩为10 884顷,夏税为25 272石,丁税为28 272两,[11]893大理府在云南21个主要的府厅级行政单位中,上述三项分别占全省的12%、11%和14%,仅次于云南府,可见农业经济开发力度之大。长时段无序的开发下,诸多的生态环境问题显现出来。明李元阳《大理府志》记载,“府西为点苍山,东为叶榆泽,山之十八溪东注于泽,灌溉之利,……百年之内,沃土变为沙石……。”[12]106邓川州横江堤,“……永乐间同知李福修筑。堤阔可容牛一架为准,近年豪右侵占,仅容水流而已。……”[12]108过度改变径流、湖泊等的自然补偿形式,导致其自我调节功能逐步衰退或丧失,灾害和纠纷的背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如洱海西部水土流失的严重现象。
(二)现状
笔者对喜洲镇六个典型的白族村庄进行调查走访。喜洲镇位于洱海西部,平地和缓坡约占30%,山地约占70%,呈缓坡形长条状,是数条河流冲积形成的冲积扇地形。由于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冲积扇和沙坝逐步被开垦利用。周城村是喜洲镇最大的白族自然村,周边几个村子分别为桃源村、波罗滂村(上关村)、仁和村、仁里邑村、河矣城村。6个被调查村庄的人口与耕地面积现状如表1所示。

表1 6个村庄人口与耕地面积现状①
从表1可看出,这一区域水田面积都比较大,且大部分村庄水田面积都大于旱地面积,周城村因所处地形影响较为特殊,故水田面积和旱地面积相当,且人均耕地面积都偏小,典型的人多地少。这些水田有一部分分布于苍山山麓处,距离洱海较远的缓坡型台地上,随着气候的负面发展,苍山山麓处流下的溪水干涸后,就无法通过自然补给的方式进行灌溉,灌溉较为困难,从村中年老之人口中访知,这些水田的灌溉用人背水实现或引用附近山涧处龙潭水,为此附近数个村子经常在插秧季节发生为争水的械斗事件。当地农民在缓慢地时间变化中觉察到了气候变暖的趋势,稻谷收割季节明显提前。还有一些山涧龙潭也已经干涸消失。
除了洱海周围地区,如弥渡县在明朝时期修建了著名的水利设施——地龙,这些水利设施是在人地矛盾及水源供需矛盾下建设的。弥渡地区历史上降水量就属于干旱型,明代曾发生数次载入史册的大旱,嘉靖年间3次、万历年间1次、崇祯年间1次。这是一种人地矛盾与气候因果关系的恶性循环。人口增加伴随的土地开垦及其附属农业设施的过度发展,从笔者调查走访的区域已经看到对洱海周围区域的局部环境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三、案例解读:文化与技术、制度的辩证关系
(一)技术停滞下文化对“无序”制度的失控
人口、制度、文化与技术是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四个主要因素。随着劳动技术不断发明和应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与改造能力不断增强,社会制度不断得以发展健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开发力度就不断增强。生态文明是一个动态概念,包括人、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环境,类似于人与人之间形成的道德伦理系统,过度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开发,就会导致这个动态的系统失衡。大理地区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区,白族的形成最晚当不迟于南诏政权统治末期,白族形成过程中受到了中原儒家文明的巨大影响。明清王朝均以大一统的姿态出现,通过政治军事手段进一步促进了云南边疆与内地的联系。明代中国腹地的移民改变了云南的人口结构,清代进一步扩大了这种趋势。在前述部分业已论述了大理地区明清以来农业发展的状况及其影响,文化、技术与制度三者的平衡关系因为人口的剧增而被打破,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发展。
当然这不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明清两代开发云南边疆所取得的成果进行否定,而是后历史时期的总结与反思。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状况,需要用客观的历史眼光进行审视。大理地区明清以来王朝政府进行农业开发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的蔓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时段理论”认为,长时段历史对社会发展存在着决定性作用,是一种结构的存在——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等因素,它们会促进或者阻碍历史发展。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个文明所具有的稳定性与韧性,是一种结构的存在。制度和技术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变化。在一定时段内,人口、制度与技术能相对平衡的相互发挥作用,在自然生态环境承受的范围内对其进行开发利用。制度与技术的物质性决定了它们具有超前性,换言之,是一种不稳定性,在巨大的物质利益与生存压力下,文化理想性的约束对制度与技术会发生“失控”的状况,大理地区特别是清代开发与移民达到了顶峰,从上述论述中耕地、水利设施建设及后果可看到这一景象。笔者走访调查中大理州洱源县铁甲村的乡规(道光十五年所立碑记):“… …河边柳茨,绿御水灾,不得口行砍伐;山地栽松,以期成材,连根拔取… …不许仍蹈前辙。… …所有规条开列于后:… …一遇有松菌,只得抓取松毛,倘盗砍枝叶,罚银五两;一查获盗砍河埂柳茨, 罚银五两… …”。②这既是文化意识的体现,也是制度的作用。但在物质成就的吸引下,这种文化意识的理想性被掩盖,制度的约束亦慢慢失去作用。笔者走访时,当地村民都说那是老一辈人的规定,社会环境发生改变,部分规定已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一个较为剧烈的开发周期后,由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剧变,人们集体意识到自然环境过度开发的恶果,社会会产生一种保护自然环境的传统文化意识的回归,笔者在走访洱海西部喜洲镇上关村(波罗滂村)看到村规民约中有“滥捕滥捞不下海,滥砍滥伐不上山”“天龙洞水人人夸,村后苍山树满报,村前洱海鱼戏水”的提法,周边几个村寨也有类似的提法、宣传与号召。在这种文化意识的推动下,环境保护制度推行起来较为容易,因为这是民众心中的一种共鸣。这种现象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普遍存在,故保护乡村或社区文化,尤其是在如同大理这样白族聚居地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尤为重要。同时,利用或者发明一些新的技术替代对自然生态环境有危害的旧的技术。
技术与制度是推动获取物质成就的巨大推力,当然这背后是文化的凝聚与感染所致。但当人口的繁衍增长超过现有生产条件时,为养活更多的人口,在传统农业生产背景下,开荒是必然的选择。因为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在公元前1世纪时,粮食平均亩产约为100斤,到南宋时期,平均亩产量为200斤,高产地区为1000斤左右,接近现代水平。[13]此后再无新的突破。制度因素对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有一个明显加强的过程,农业生产技术在一个时段内长期保持在一定水平范围内而无新的突破,人口却是不断剧增,在这样的情况下,制度会超越起源于文化的意识范围,鼓励开垦土地。前述中明清两代由于内地人口的压力,向边疆移民,大理地区人口与农业的发展是其表现。对此,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依靠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如粮食的亩产量,以养活更多的人口。而不是无限制的开垦山地。笔者走访喜洲镇的六个白族村庄看到水田面积大于旱地面积,因为引进了现代的大型电力灌溉设备。以往,因为水利纠纷而发生械斗,背后实质是已超越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开垦山地,导致山区涵养蓄水能力下降,森林被砍伐,地表水蒸气减少,影响年降水量,继而影响到整个区域生态小环境的良性循环。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中叶以来传统中国人口剧增,但这种剧增人口密度分布不均,腹地人口密度大,而幅员辽阔的边疆地区却人口稀疏。腹地人口剧增,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渐突出,成为社会治理的重大问题,社会潜伏着一股危机。在这种社会危机态势下,王朝政府采取了一种务实的态度,把腹地富余人口引向边疆地区垦殖。人口涌入大理地区在内的云南高原之际,同时也是中原儒家农耕文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清廷王朝政府自上而下有政治目的的大力宣扬儒家文化,政府倡导主办学校,进行王道教化;二是移民进入带去的农耕技术。大理白族在其形成过程中就不断吸入中原农耕文化,这样外来移民在农耕文化传统和技术角度上没有太大的文化隔阂,二者共同促进了大理地区农业经济的开发,表现为土地大规模的开垦和水利建设事业的发展。但王朝政府总体上没有规划和控制人口迁入,经历长时段大规模农业经济开发,自然生态环境呈现恶化发展趋势。在这其中,技术、制度与文化扮演着主导角色,人口不断剧增,技术发展在一个时间段内长期保持均衡水平,即停滞不前,而外部因素(压力、新事物、新环境等)又不断变化时,制度变迁会超越文化的约束步伐,通过制度的实施缓解或者遏制环境因素所带来的压力。文化对本质源自于己的制度变迁发生了“失控”效应。
(二)制度“校正”与文化“救赎”的意义
在美国“西进运动”中,制度变迁、文化传统与技术条件扮演着重要角色,三者互为内在条件,促成了在美国历史上发展的重要地位。其中,备受关注的便是其中关于制度变迁在美国“西进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制度变迁研究中,凡勃伦认为环境对制度有决定作用,诺思用物质动机和精神动机解释制度变迁的内在关系,格雷夫认为文化信息的差异导致制度变迁。笔者借鉴上述三位学者关于制度变迁理论的框架,认为明清以来大理地区农业经济开发过度导致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发展的三个主导因素是环境、动机和文化。
环境变迁必然引起制度的变迁。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国家腹地人口剧增,人地矛盾突出,在这样的社会危机下,王朝政府在稳定对云南边疆的政治统治后,大规模引导富余人口向大理地区在内的云南边疆地区移民垦殖,以缓解内地人口压力,应对社会危机。因为中国传统国家王朝政府有引导狭乡之民移往宽乡的传统国策;民众的动机是经济物质的获取,在农耕文化发达的中国传统社会,土地对于农民是至关重要的。在这场移民垦殖运动中,王朝政府对环境变化所做出的制度安排呈现为无规划的状态,因为中国传统国家以政治大一统见长,而技术因素发展滞后,因此王朝政府不能形成也不能对全局移民数量做出技术数目控制,对大理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未能统计估算,人口过度迁入,对山地、水资源、森林等过度开发导致对生态环境产生破坏。经历一个过度开发区后,国家、民众两端皆意识到了环境破坏的后果,因为这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和民众生存。在后历史时期,从国家层面而言,是一种制度“校正”,对民众而言是一种文化的“回归”,在这两者的改观中,国家与民众两头以经济物质动机为主导改观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精神追求动机。
综上所述,在技术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制度会超越文化的约束力,缓解现实压力,这种制度安排并非是文化理性的选择,即表现为对制度的失控。当外部环境和技术因素发生改观,制度安排会得到校正,文化再次回归到约束制度与技术的轨道,这最终表现为一种文化的“救赎”。因为文化、制度与技术三者因素中,制度与技术在本质上均是一种文化的衍生物,只不过制度与技术在表象上表现为物质现象,文化则是一种精神现象。据此,笔者通过对大理地区农业经济开发及自然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及对水土流失较为严重的洱海西部喜洲镇6个白族村庄的实地调查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大背景下,文化、技术与制度在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中,文化居于核心地位,制度与技术处于两翼地位。文化需要制度与技术的辅助,否则是为无源之水。制度与技术需要文化对其物质“戾气”的抚慰。同时,文化、技术与制度的关系变动又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因素既包括物质的方面(现实压力、技术条件、制度变迁等)和精神的方面(传统、观念、习俗等),因此,在工商人类学视角下,这即是管理与调控组织文化的过程,组织如何处理物质与精神二者所产生的矛盾,使其在一个组织内协调发展,共同引领组织的和谐发展。组织如何倡导主流文化或者观念,用何种方法使其得到组织内个体的共鸣,达到在个体心中的内化,自觉遵守这种文化的倡导。当然,组织中个体的思想或意识也会影响组织文化的走向,这需要组织正确地看待与处理,二者互为影响。在本文中,这即是组织(国家、政府和社区或乡村)如何进行环境保护的倡导,得到民众的普遍回应与支持和理解,民众也可通过非官方组织进行环境保护的诉求,二者彼此达到调和平衡,文化、技术与制度三者在这样的大框架下不会偏离轨道。所以,保护发展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对保护民族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条重要的社会发展路径;现代的技术、制度与传统的文化没有绝对对立的界限,技术发展与制度变迁想要的是什么?最终可归结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精神“救赎”,制度和技术最终升华为一种文化的存在。自然生态环境是一种缓慢变迁的结构,如同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所蕴含的深意一般,王朝的衰败在一种不知不觉的状态中业已走向灭亡的道路,不论后来的崇祯皇帝如何励精图治终究踏不过那个死弯。一味地以制度与技术“高歌猛进”,以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让文化的精神力量置于边缘地位,忽视自然生态环境这种缓慢的恶化,其后果将是一条毁灭的死胡同。
四、结论
通过对大理地区明清以来自然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考察和田野调查,以工商人类学的组织文化和组织行为为引导理论,分析白族组织团体在大环境变迁下,王朝政府所做出的制度安排,即引导富余人口进入大理地区开垦,这种无序的制度安排导致了生态环境恶化,在后历史时期,伴随着技术因素的发展,表现为一种制度的校正和文化的回归。在这其中,组织团体,即国家、政府和社区(乡村)的主导力量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和“美丽乡村”建设在民众中引起了共鸣,组织团体中个体组织行为受到了这种组织文化强有力的吸引,前述提到的诸多乡村(社区)中宣传保护环境的口号即是表现。文明的发展不是一种物质成就的归结,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精神的“救赎”。回望美国“西进运动”中,在文化上是一种“天定命运”的宣扬,制度上的安排则是不断地为工业化进行铺垫发展,这实在是依赖于对技术的发展,而缺乏对技术的辩证看待,把自然生态环境置于人和文化的对立面,美国“西进运动”的成果是一种“物质文明”的成功,而不是“精神文明”的胜利。在文化意义上不是精神的救赎,是一种文化的工具论。文化与技术、制度的辩证关系是一种文化的精神救赎,而不是物质欲望无限制的扩张,文化被作为一种工具应用到促进技术与制度的发展中去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
注释:
① 实地调查数据。
② 笔者调查走访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