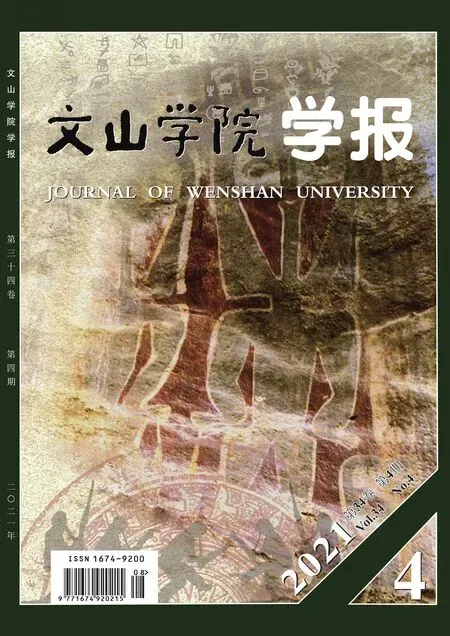崇儒重道与文化象征:清代云贵地区的学宫
杨永福
(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贵州 遵义 563006)
学宫,又称孔庙、文庙。而称“文庙”,是相对“武庙(关、岳庙)”而言。明清一般称为“文庙”,所谓“天下文庙,惟论传道以列位次”[1]。学宫,实际上是庙、学两部分的合体,庙即孔庙、文庙,是祭祀先师孔子及其弟子的场所,学即儒学(所谓官学),乃教授生徒、培育封建人才的学府。二者相邻而建,合为一个整体,可以追溯至唐代。唐玄宗开元年间,追封孔子为“文宣王”,明确规定各地的官学须建立孔子庙,于是便出现了孔子庙与官学相互结合的建筑体制。
明清之际,学宫承载着多重功能,即学宫是开展祭拜“至圣先师”孔子等活动的场所,也是儒学教官衙署所在之地,地方官员向当地绅民定期集中宣讲《圣谕广训》等文告的地方。一般而言,只要创设了儒学(府、州、县学及卫学、提举司学),均要修建学宫,换言之,学宫是当地开展学校教育、传播儒学文化的中心,是地方治理过程中文化软实力的集中显现。儒学在清代的西南边疆得到了很大发展,学宫亦随之得到较大范围的建设,学宫所承载的文化权威及内涵在西南边疆社会治理中得到了较好的彰显。
一、“崇儒重道”:明清文教治理云贵地区的思想
云贵地区儒学的开设和学宫建设,与明清王朝“崇儒重道”治理方略的实力推行密不可分。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即提出:“治天下当先其重且急者,而后及其轻且缓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给而民生遂,教化行而习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2]他说:“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3]在统治者看来,西南边疆民族众多,乃是“荒服之区,蛮夷之地”“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西南边疆是明代土司制度实施的重要地区,如何将土司子弟培养为忠顺于朝廷的、对封建礼教有认同感的群体,更好地实现“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明统治者认为,必须要通过学校教育这一途径。在明军平定云南后,朱元璋即下令:云南各“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风俗”[4]。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六月壬申,户部知印张永清言:“云南、四川诸处边夷之地,民皆啰啰,朝廷与以世袭土官,于三纲五常之道懵焉莫知,宜设学校以教其子弟。”朱元璋深以为然,谕礼部曰:“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5]
清统治者继承了明朝重视教育的做法。康熙曾说:“朕惟至治之世,不专以法令为事,而以教化为先。……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事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6]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在《御制学校论》中指出:“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尚在教化。以先学校者,教化所从出,将以纳民于轨物者也。……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教化之原。欲敦教化,而兴起学校者,其道安在?在各其本,而不求其末,尚其实,而不务其华。”[7]认为“国家化民成俗之本,不可一日废者,学校是也”[8]41,故“天子重道,崇师儒,尊先圣”[8]20。因此,从最高统治者到地方官吏,都把兴办学校、端正士习、教化民风,在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传播儒家道德礼教和价值观念作为治理地方的重要方略,“从来地方之治,在风俗;风俗之厚,在教化;教化之兴,在诗书;其所以鼓舞而作新之者,是又在上之人加之意耳”[9]。“学校之设,择秀民众处其中,而以《六经》之道训而迪之。盖欲其明大伦,崇正学、悖治体,探化原以成君子之行,以备公卿百执事之选,以收正朝廷治天下之功。而人才之威衰,俗化之厚薄,恒于是乎?实系治道之最先且急者”[8]19。
在清政府的重视下,云贵地区的儒学教育得到了较大发展。据《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统计,到清末新式学堂建立以前,云南的官学在明代72所的基础上增加到101所,其中有府学14所、州学29所、县学34所、厅学12所和提举司学3所,以及光绪八年添设定有学额而未建孔庙的厅学、县学10所。至清末贵州全省共有官学69所,其中:府学12所,直隶厅学3所,直隶州学1所,厅学6所,州学13所,县学34所[8]19-43。
二、“崇儒重道”之践行:清代云南边疆的学宫建设
清初云贵各地恢复重建儒学的过程中,学宫建设是一项重要的内容。没有学宫,儒学便失去了物化的载体和依托。因而各地方官始终把重建、扩建和完善各级原有学宫作为其发展官学的重要措施,亦将学宫建设视为自己任内的重要政绩,他们或捐出俸禄、或劝地方士绅捐资,完备规制,改善条件,使学宫成为当地儒学发展的标志。
从学宫的建设情形,可以反映出清代云贵官学建设的基本情况。下面以云南各地学宫的建设为例加以阐述。
表1统计的学宫数量为101所(含迄至光绪八年仍没有建立学宫的官学),与前面提及的清代云南101所官学这个数字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反映出明清时期云南学校建设一个比较完整的概貌。由其中可得出以下几点基本的认识:

表1 元明清时期云南各地所建学宫简表
第一,根据表中统计,建于元代、明代续修并继续发挥作用的学宫有10所,约占总数的9.9%;迄至光绪八年仍没有建立学宫的官学共10所,占总数的9.9%;建于明代的共有62所,约占总数的62.4%;清代新建的学宫有19所,约占总数的17.8%。表明云南的大多数官学及学宫在明代就已建设,部分官学甚至在元代就已经设立了。这些官学覆盖了清代云南所有的经制府、州、厅、县,以及作为特殊行政机构的提举司辖区,也就是说举凡设立行政机构的地区,均设立了官学。
第二,由表中所载学宫分布看,表明由明至清云南官学有很大的扩展。明代建设(包括元代建设并在明代继续发挥作用)的官学共有72所,主要分布在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府、州,而从滇西北、滇南到滇东南的沿边弧形地带还没有设立官学。到了清代,随着朝廷在边疆民族地区改土设流,以及政治、军事控制的进一步加强,此种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前代未设府学的滇西北、滇南普洱以及滇东南广南、开化等偏远民族聚居地区第一次设立了官学,表明清代云南官学的地域分布较明代是大为扩展了。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殊的行政辖区,如三个盐井(黑盐井、琅盐井、白盐井)提举司辖区,依然建设儒学,修建学宫。而且,建学的时间均在明代。反映出明清政府在教育制度的推行方面,并没有因为此类地区非经制府州县,而有遗漏。进一步表明,明清中央政府对在西南边疆推行教育是十分重视的,而地方政府亦不遗余力地执行朝廷既定的教育政策。
第四,比较突出的一点是,自明至清,云南地方政府十分重视学宫的建设,各地历任官员可以说是前后相继、修建不绝。试举数例:
临安府学宫。元至元二十二年,宣抚使张立道建。泰定二年,佥事杨祚增建。至正十年,平章汪惟勤继修。明洪武十六年设儒学,庙因之。二十年,通判许莘重修,规制始宏敞。宣德间,知府赖瑛建尊经阁。天顺六年,知府王佐筑杏坛、射圃。成化四年,知府周瑛凿泮池。十五年,副使何纯、知府薛昌重修。弘治九年,副使李孟晊、知府陈盛置乐器。十二年,副使王一言、知府王资良凿泮池。嘉靖十年,副使戴书建启圣祠。二十年,副使蒋宗鲁建名宦、乡贤祠。万历三年,知府昌应时建云路坊。三十年,教授胡金耀造祭器。三十四年,地震倾圮,巡按周懋相会巡抚陈用宾、分巡参议康梦相重修。崇祯十六年,知府丁序琨、知州刘僖重修,悉毁于兵。清康熙十二年,知府程应熊修建尊经阁、明伦堂。二十二年,知府黄明重修于东庑瓦砾中,见石摹圣像,恭移于尊经阁。二十九年,升川东道知府黄明、同署府事丁炜、知州朱翰春始铸祭器。五十一年,知州祝宏移建斋宿亭。五十三年,知州陈肇奎修泮池。雍正四年,知府栗尔璋建太和元气坊。十年,知府石去浮、知州夏治源、教授夏冕同郡绅萧大成捐置乐、舞器。乾隆十六年,学正杨元亨同绅士修泮池。二十九年,教授董聪同绅士建礼门、义路、石坊。三十七年,知府永慧、知县周鑑同绅士重修大成门。四十三年,知府盛林基同绅士重修洙泗渊源坊。五十年,知府何敏、知县周恭先同绅士重建棂星门。五十七年,总镇定柱复杏坛旧址,知府张玉树同绅士重建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坊,圣域由兹坊,贤关近仰坊,清泮池,侵占复旧规。六十年,知府江濬源同绅士于泮池周围绕以垣墙,竖圣域、贤关二坊。匾额内外,焕然一新。嘉庆九年,江濬源复建大成殿。十五年,知府王善垲率绅耆重建崇圣祠。十八年,知府何南钰建大成门,金声、玉振门。道光二年,绅士等复建斋房。规制宏敞,金碧壮丽,甲于全滇。光绪六年,邑绅刘鸿阳、刘家祥倡建思乐亭于泮池之中央,并修补碑亭、棂星门、围墙。[10]
元江直隶州学宫。明洪武二十六年建。嘉靖四十年,迁于府治北。万历二十五年,土舍那天祐重修。夷中向学者鲜,诸生多以临安府属人充之,教官亦侨寓临城。天启三年,始建元江学署于建水州左,以为师生讲习之所。清顺治十六年,改土设流,学署迁于府城内。岁久多毁。康熙九年,知府潘士秀建大成门。二十六年,副将毛来凤、知府纪振乾、通判陈大受、教授丁炽南相继重修。二十九年,知府单世、教授施发甲凿泮池。四十二年,知府李赞元建尊经阁。五十年,知府章履成修建大殿及两庑。五十二年,教授张凤鸣、陈冏伯建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斋及居仁、由义二坊。雍正六年,知府迟维玺、教授杨薫增筑月台,置祭器、乐器、演习乐舞。九年,知府祝宏、教授杨薫改建棂星门、石牌坊,增建月台石栏杆。乾隆十一年,知府董廷扬、教授陶以敬倡捐重修。十九年,提学沈慰祖、布政使阿兰泰、知府张钧率各官捐俸,及绅士董修。二十二年,教授张维灿重修崇圣祠、大成门、龙阶。三十五年,改府为州,庙学仍旧。嘉庆九年,署州欧阳道瀛、学正汤国侯率绅士重修两庑。二十一年,署州刘继柱、学正张含英率绅士新建木坊。同治三年,游击舒世泰拆毁尊经阁、大成殿及两庑。光绪九年,官绅请款捐赀重修。[10]
黑盐井直隶提举司学宫。明万历四十五年,永宁府署井事韦宪文卜建。天启二年,署提举马良德详照各省盐司事例,建学设官。六年,署同知吴思温重建。崇祯十三年,署通判曾曰琥重修。清康熙三十八年,提举沈懋价重修。乾隆十二年,署提举孙嵩拓地建崇圣祠,设乐舞,置乐器。十九年,提举邱兆熊重修大成殿及两庑。三十年,提举黄辅重修大成门、钟鼓亭,建礼门、义路坊。咸丰元年,大成殿灾,提举刘廷谔同井绅武康臣重修。九年,杜文秀之变,复毁于兵。同治十年,提举郭时郁筹款修葺。七月,龙沟河蛟泛,淹没大成殿一角及东西庑。光绪七年,提举萧培基筹款重建大成殿、东西庑及照壁。[10]
各地官员对学宫的修建如此重视,原因在于清代是把发展教育作为考核当地官员的重要内容。当然,各地方官员基本上都出身于科甲正途,对教育在促进当地社会发展,教化地方民风方面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地方官员对落实教育政策可谓不遗余力,每到一地任职,都把举办学校教育、建设学宫作为自己任内的重要政绩,学宫也就成为当地儒学发展的重要标志。
第五,迤西地区如大理府、永昌府、普洱府等地的很多学宫,包括黑盐井直隶提举司学宫、琅盐井提举司学宫,在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的战乱中遭受兵燹损毁严重,但在当地官府的重视下,大部分均在战后得以修复,继续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清代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在云贵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和执行。
三、文化象征:云贵地区学宫的规制与内涵
(一)学宫的建筑规制
清代,对各地文庙、学宫的规制,以及内部供奉、礼器、祭祀的程式等都作了统一的要求,“直省、府、厅、州、县文庙规制,供奉、礼器、乐舞暨崇圣祠祭品,”同于太学,因此,“学宫规制,各府州县相同”[11]。换言之,从国家层面对学宫的规制有着统一的要求,但在规模上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国家、府、州、县级,其相应的规模和标准也有所区别。有的认为,国家级的学宫大成殿面阔九间,府、州级的面阔七间,县级学宫的大成殿为面阔五间。也有的学者认为,大成殿的建制主要取决于修建资金的多少,而同地方官学设置地的行政级别没有太大的关系。时人也指出:“邑必有学,学必有先师之庙,其制之隆庳广狭华朴则视邑之大小,物力之丰啬,人文之雅陋以为之差。”[12]
具体来看,学宫其内部建筑,主要由两大建筑群组成,一是以大成殿(或称为先师殿、先师庙、圣殿、至圣殿等)为核心的建筑群,包括大成殿、东西两庑与崇圣祠,合称文庙,其功能主要在于祭祀先师、春秋释奠、朔望行礼。其中大成殿的地位最为突出,处于中心,建筑规模亦最大。一是以明伦堂为核心的建筑群,主要有明伦堂、尊经阁、斋舍号房、教官廨署等,其功能主要是教授、管理生徒的学习,也承担部分礼仪职能,如乡饮酒礼就是在明伦堂举行的。此外,还有一系列处于附属地位的建筑,如下马碑、照壁、泮池、棂星门、大成门、乡贤祠、名宦祠、忠义孝悌祠、节孝祠、文昌阁、魁星阁、敬一亭、土地祠、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坊等。这些建筑在学宫中都有着自身的地位和象征意义,因而在排列上有着一定的规则,并非随意安放。根据大成殿(庙)和明伦堂(学)的相对位置,云贵地区学宫的建筑格局大体有三类:一是左庙右学,明伦堂位于大成殿的西边,此种格局同于京师的国子监;二是左学右庙,即明伦堂位于大成殿的东边;三是前庙后学,明伦堂位于大成殿的后方。
学宫中的各种建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附丽而形成,并被统治者赋予不同的功能和象征意味。兹举数例:
下马碑:立于学宫前,书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其意在于维护文庙的庄严与神圣。康熙二十九年议准:“学宫关系文教,凡官民等经过者皆下车马,并禁于学宫内放马污践。”[13]5
泮池:进入棂星门,内有半圆形水池,“泮即半,意为东西门以南通水,以北无水,不同于天子制度”[14]。春秋时期,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曰泮宫。童子入学谓之入泮。泮池之上建单孔石桥,又名“状元桥”,以供行走。
大成殿:乃学宫中的主体建筑,祭拜孔子之所,四配十二哲陪祀于其中。由于是学宫之主体建筑,最为高大宏阔。殿内悬挂有从康熙帝到宣统帝所颁御书匾额:万世师表、生民未有、与天地参、圣集大成、圣协时中、德齐帱载、圣神天纵、斯文在兹、位育中和。
崇圣祠、乡贤祠、名宦祠:明嘉靖九年,诏令天下各学于大成殿后建立启圣祠,祭祀孔子之父叔梁纥。清雍正元年,封孔子先世五代王爵,更名启圣祠为崇圣祠。名宦祠祭祀曾任职于当地并有功德于民的官员,而乡贤祠则祭祀以文章或者品行著称于世的当地名贤。
忠义孝弟祠、节孝祠:两祠从清雍正二年以后奉令修建于学校的,前者祭祀当地的忠臣义士孝子顺孙,后者则祀守节的妇女。两祠在学宫中的位置并非固定,有些地方节孝祠建在学宫之外,但均属于学宫整体象征的一部分。
(二)学宫内部陈设
1.殿庑供奉的先贤排位及顺序
乾隆六年礼部议准:“学宫从祀先贤、先儒神位次序,以京师太学成式通行直省府、州、县。遵照书题,按东西先后次序安设。”[13]6由此可见,学宫内祭祀先贤、先儒的位次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
大成殿正殿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居中、南向。两旁配以复圣颜子(左)、宗圣曾子(右)、述圣子思子(左)、亚圣孟子(右),面东西向。又次为十二哲,东列先贤闵子损、冉子雍、端木子赐、仲子由、卜子商、有子若,皆西向;西列先贤冉子耕、宰子予、冉子求、言子偃、颛孙子师、朱子熹,皆东向。
东庑则祭祀蘧瑷、冉季、公良儒、罕父黑、郑国、叔仲曾、颜何、乐克正、周敦颐、程颢、邵雍等先贤三十九人,以及先儒谷梁赤、后仓、董仲舒、杜子春、范宁、韩愈、范仲淹、张栻、真德秀、赵复、吴澄、王守仁、汤彬、陆贽等二十五人。
西庑祭祀先贤林放、宓不齐、公哲哀、高柴、樊须、公孙龙、秦商、颜高、石作蜀、后处、句井疆、县成、公祖句兹、狄黑、左丘明、公孙丑、张载、程颐等三十八人,先儒则有公羊高、孔安国、毛苌、诸葛亮、王通、司马光、欧阳修、胡安国、吕祖谦、陆九渊、魏了翁、陈献章、刘宗周等二十五人。①
2.礼器、乐器与祝章
礼器。举行祭祀时,需要摆放各种祭品,于是就需要相应的礼器。据道光《开化府志·庙学》记载,当时开化府学宫使用的礼器有:“豋一、铏十七、簠十七、簋十七、云雷尊一、牺尊一、象尊一、壶尊六、爵盏四十九”,均为铜器;“笾一百五十、豆一百五十、篚盒十七、牲俎十七、祝板二”,分别用竹、木制成。
乐器。学宫承担着教化地方的重大职责,因此当举行春、秋大祭时,必定要举行歌舞活动,则乐器就必不可少。据记载,这些乐器种类很多,“金之属有编钟、有镛;石之属有编磬;丝之属有琴、瑟;竹之属有排箫、有笛、有篪、有管;匏之属有笙;土之属有埙;革之属有鼖鼓、有楹鼓、有足鼓、有搏拊、有相鼓、有鼗鼓、有提鼓;木之属有柷、有敔、有拍板;舞之器有籥、有翟。引乐之器曰麾,引舞之器曰节。”[15]各地儒学在实际操作中,使用的乐器种类及数量或有差别。据道光《开化府志·庙学》记载,当时开化府学宫使用的乐舞器具有大麾幡一、小麾幡一、金钟十六、玉磬十六、特钟一、特磬一、启柷一、止敔一、悬鼓二、搏拊二、琴二、瑟二、排箫二、笙二、箫二、笛二、埙二、篪二、节二、羽籥二十四、干戚四、龙伞一、凤扇二。
同时,清廷为了显示祭祀活动的庄严宏大,专门制作有祝祷之词和乐章、伴舞。顺治十三年,颁国子监文庙大成乐章,康熙八年改章名“和”为“平”,称中和韶乐。五十五年奏定平字乐章,通行赞唱。雍正二年,令阙里司乐选工付太常演习、订正,转相传授,以达于直省各学。乾隆八年,照康熙间用“平”字撰乐谱十二章,颁于各学。[15]每次大祭,整个仪式分为迎神、初献、亚献、终献、彻馔、送神六个环节,哪个环节伴舞、哪个环节不伴舞,都有明确的规定,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
(三)学宫的文化意蕴
清代官方十分重视学宫建设及修缮,“学宫之地,圣贤灵爽所依,不惟丁祭宜修治肃清,即平时尤宜洒扫净洁。”[10]鄂尔泰·丁祭教“地方风化,起于学宫,官司职守,莫先祭祀。”[10]陈宏谋·整饬学宫丁祭檄
通过学宫这一物化的建筑群,体现出这样一些文化意味:一是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大成殿是整个学宫建筑群的核心,也是规模最大、修饰最为华丽的建筑,整体呈现中轴连线,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布局严谨的特点。二是浓厚的儒学气息。学宫作为儒学的物化载体,是地方崇儒重道的标志,又是当地儒学文化传承的辐射源。它将地方文官集团、当地文化精英和平民阶层以一种强有力的可以感触得到的规范化、制度化方式整合在一起,为官府向民众传达国家意志和主流话语(如朔望齐集宣讲活动)提供了极佳的场所。三是主流文化价值的彰显。在这里,孔子作为统治者倡导的文化权威被置于中心的地位,历代先贤先儒也有属于自己的位次,当地有名望的乡贤、有功德的官员,甚而地方忠孝节义、贞节烈妇都能“刊刻姓名于其上”,被后人所观瞻。这样的传播形式,无疑对当地乡民形成视觉上和心理层面的强烈冲击,对当地社会而言成为一种显著的价值导向。
在清代地方层面,学宫与社稷坛、先农坛、风云雷雨坛等共同构成了国家祭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礼仪体系传承的物化象征。从诸多地方志书的相关记载来看,云贵地区县一级行政治所,均修筑有社稷坛、先农坛等建筑,这体现了国家权力在边疆民族地区渗透的力度。清政府如此重视学宫的建设与维护,目的在于通过对孔子的尊崇和文庙的维护而实力推行教化,体现“怀柔远人”的基本思想,在多民族的西南边疆达到“建学校以化夷”的终极目的。学宫建筑庄重、朴实、肃穆,具有深厚的文化意味,可以使得当地的民众面对它们时肃然起敬,更重要的是位列其中的这些人物及他们的德行与事迹,可以让人产生敬仰和向往,从而产生强大的激励与引领的作用,这样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邹鲁回忆自己早年的经历曾说过:“自从我会走以后,我的母亲有了空闲,从不同意我到热闹的地方去,却常常引我到隔壁的孔子庙玩耍……小时候在那儿耍,不知不觉中一定会产生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母亲又把她所知道的关于圣贤豪杰的故事,讲给我听,勉励我效法圣贤豪杰;并且常说做圣贤豪杰,并不是一桩难事,只要好好读书敦品。”[16]通过文庙中的各类建筑及其象征,清统治者倡导、鼓励的品德与行为得到了集中的表扬和彰显,在多民族地区明白无误地确立了一种文化价值导向。这就是历代皇朝中央一直倡导的儒家“教化”,即“以王权为中心的政治系统,通过宣讲、表彰、学校教育以及各种祭祀等方式,将王权主义的价值体系灌入人们的意识之中”[17]。有论者认为,在各朝各代的更迭中,清帝国构建的儒家教化运动可称之为典范,其时,“儒家教化”不仅是“一个文明化进程”,也是“延伸清帝国统治的手段”[18]。这应该就是清帝国在云贵地区不遗余力地建设并维护学宫地位的根本原因。
注释:
① 先贤排位及顺序见道光《开化府志》卷6《学校·庙学》,部分研究者结果与此不同。
——凤羽文庙大成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