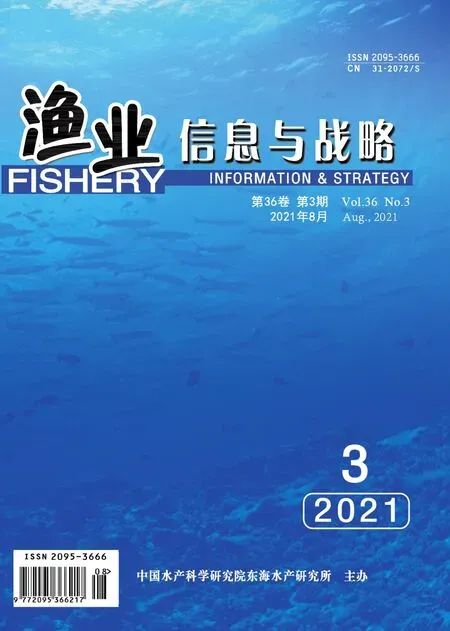新西兰渔业发展概况及对中国渔业发展的启示
张馨月,刘 勤
(1.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1306;2.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东海水产研究所,上海 200090)
新西兰位于太平洋的西南角,除两个较小的离岛外,还包括两个主要岛屿(北岛和南岛)。其海岸线长达15 100 km,专属经济区面积位居世界第四,达到130×104km2。在新西兰海域中已被发现的海洋物种超过16 000种,其中商业捕捞对象有130种。近年来,新西兰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乳制品出口规模位居世界前五位。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新西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1]。
新西兰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其水产品被出口到世界各地,年均出口额达14×108新元(1新元≈4.512 7元)。水产品出口贸易为新西兰经济做出了贡献,新西兰约有95%的商业捕捞产品和75%的水产养殖产品用于出口[2]。
近年来,中新两国在海洋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和新西兰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入,开展了多领域、多行业的交流与合作[5]。渔业是两国合作的“排头兵”,中新两国应携手合作,抓住机遇,充分利用中新自贸协定升级的有利条件,探索两国渔业合作新领域。
1 新西兰渔业发展现状
1.1 渔业资源
新西兰在渔业资源开发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专属经济区海域内沿岸大陆架的浅海区面积较小,深海区面积较大,渔业资源相当丰富,生长着上千种鱼类,其中可以商业捕捞的鱼类数量达上百种,年可捕捞量约50×104t。新西兰每年商业性捕捞和养殖的鱼类、贝类产量为60×104~65×104t,其中超过半数供出口[17]。新西兰主要渔业资源有7种:鲷(Sparidae)、大西洋胸棘鲷(Hoplostethus atlanticus)、黑鳍蛇鲭(Thyrsitoides marleyi)、鲣(Katsuwonus pelamis)、金枪鱼(Tuna)、红拟褐鳕(Pseudophycis bachus)和新西兰双柔鱼(Nototodarus sloani)。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具有“公共财产”属性,因而政府在平衡不同经济主体的捕捞竞争和渔业资源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新西兰渔业的重要特征是渔获物中高值资源较多,个体大,天然苗种数量多,自然繁殖的群体数量大于捕捞和自然死亡的数量,资源处于良性循环中[19]。
1.2 渔业类型
新西兰渔业主要分为深海渔业、近海有鳍鱼类渔业、近海贝类渔业和远洋渔业[1]。
深海渔业是指在离岸12~200 n mile的海域内从事深海鱼类捕捞作业。其最常见的捕捞方式是拖网捕捞[1]。
近海有鳍鱼类渔业通常以小型渔船为主,使用拖网、围网等进行捕捞作业[1]。这种渔业生产主要集中在近岸海域,特别是在奥克兰和南岛东海岸地区[1]。
近海贝类渔业根据目标渔获物的不同生态特征,而使用不同渔具或捕捞方式,例如人工潜水采捕鲍鱼。与新西兰大多数商业渔业一样,近海贝类渔业通过配额管理制度(quota management system,QMS)进行产量控制,每年政府相关部门会确定其总可捕捞量(total allowable catch,TAC),以保障贝类资源的可持续开发[1]。
远洋渔业作业范围包括新西兰专属经济区、公海等海域,主要集中在太平洋。该渔业类型使用渔具种类较多,其中最常见的是围网,也包括其他渔具,例如用于捕捞特定物种[1]的延绳钓等。
1.3 渔船数量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的渔业统计数据显示,新西兰专属经济区海域的渔业资源状况有所好转,新西兰国内的渔船规模持续扩大[1]。新西兰国内的一些渔业公司为了扩大生产和完成捕捞配额,租用外国渔船的数量有所增加。1998年以来,新西兰国内船队的捕捞量已达到总捕捞量的63%以上,作业方式主要是拖网和延绳钓。新西兰渔业法规中没有限制双拖网作业,但为了保护资源,相关管理部门划定了拖网渔船作业禁渔区,并规定拖网网目尺寸不得小于100 mm。新西兰渔业部门将200 n mile专属经济区划分为10个管理区,各管理区严格实施网目尺寸限制和鱼类捕捞限额。另外,所有在新西兰注册的总长大于21 m的渔船,生产期间都应向渔业控制中心报告每日的船位和渔获量[10]。
据统计[1],1978年,在新西兰注册登记的渔船数量约为5 000艘,船长多在23 m以下。大部分渔船为个体渔民所有,每艘船船员数量一般不超过4人,平均每航次作业时间为2~3天。近年来,近海渔船数量有所下降,但船长23~27 m的大型深水围网渔业作业渔船数量不断增加。表1是1995—2017年新西兰渔船总数量,从表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来,除2012年外,渔船数量呈持续下降的趋势。

表1 1995—2017年新西兰渔船总数量Tab.1 Number of fishing vessels in New Zealand during 1995—2017 (艘)
1.4 捕捞产量
新西兰的海洋捕捞业和水产养殖业都很发达,大约有2万人从事渔业捕捞和水产养殖相关工作。新西兰90%以上的水产品产量来源于捕捞业,其国内三大企业水产品产量占到全国总产量的40%~50%。除了捕捞水产品以外,近年来新西兰养殖水产品产量也逐渐成规模。2018年6月,新西兰初级产业部相关研究报告显示,预计到2022年6月,新西兰水产品出口额将从18×108新元上升至21×108新元。表2为2008—2017年新西兰海洋捕捞产量,从表中可以发现,新西兰海洋捕捞产量偶有波动,但都维持在420 000 t以上。

表2 2008—2017年新西兰海洋捕捞产量Tab.2 Total capture production for New Zealand during 2008—2017 (t)
1.5 水产品加工与流通
新西兰渔业公司主要从事水产品的捕捞、加工和销售,其中Sealord公司最具有代表性。Sealord公司是南半球最大的综合深海渔业公司之一,在新西兰拥有1 000多名员工,在海外拥有240名员工,其主捕四十多种深海鱼类,这些鱼类大多生活在新西兰周边海域,以天然饵料为食,90%的渔获量以各种冷冻形式出口到40个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Sealord公司还向一些企业销售冰鲜鱼,这些企业随后以自有品牌对产品进行再加工,供当地消费和出口。随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打破了水产品销售在时空的限制,Sealord公司正努力开拓电子商务渠道进行水产品销售。
1.6 渔业捕捞配额管理制度
渔业捕捞配额管理制度是当前国际渔业管理的主流模式,新西兰是第一个将配额管理制度应用于多鱼种渔业的国家[1]。捕捞配额管理制度是依据各种渔业资源的最大可捕量,并根据捕捞能力合理分配渔获量份额的一种管理方式[1]。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是,改变了过去渔业资源管理普遍采取的限制渔船数量、设置禁渔区和禁渔期等被动式管理方式[13]。
新西兰捕捞配额管理制度的成功离不开公权力强有力的管理支撑。许可准入制度的落实,需要在多种措施全力配合下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果。具体应从渔场、准入人员和许可证3个方面去落实捕捞准入制度,更大限度地对渔民、渔船、渔具做出相应的限制。新西兰不断完善渔业法律法规,将捕捞许可证和捕捞配额联系到一起,同时还逐步放开对配额权转让的限制[13]。
1.7 对外渔业合作
新西兰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因此,该国政府十分关心外贸政策的制定和对外经济关系的发展。例如:2000年新西兰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为期5年的渔业合作协定[12]。
新西兰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重要的合作伙伴,在两国水产品贸易中,新西兰水产品对中国的出口远远大于来自中国的进口。2008年新西兰与中国签订了贸易协议,成为第一个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发达国家。中国现已成为新西兰最重要也是发展速度最快的贸易伙伴之一。
目前,新西兰是中国第五大水产品供应国,很多新西兰企业都与中国企业在水产品加工领域建立了合作关系,一些新西兰水产品还以中国为基地,加工后进一步出口到其他国家。新西兰已将中国视为水产品出口的战略性目标市场,随着中新水产品进口关税的降低,预期其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水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2 渔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尽管新西兰在渔业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但在发展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
2.1 非商业捕捞区渔业活动对渔业资源造成破坏
海洋是新西兰人生活的重要载体,既是娱乐的场所,也是食物和收入的来源。其国际贸易依赖航运,水产品贸易仍将是新西兰和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的重点领域之一。2018年,根据新西兰官方信息,曝光了一组海洋捕捞业的照片和视频,这些照片和视频揭露了新西兰渔船在生产过程中捕捞了诸多濒危珍稀海洋生物,随后,很多研究学者就此展开了相关研究,新西兰政府对非商业捕捞区渔业活动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9]。
2.2 渔业作业方式对海洋生态造成负面影响
使用拖网等渔具用以捕获海底贝类或深海鱼类,是一种较为经济可行的渔业作业方式,但这种方式却常常对海底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威胁。尽管此类渔业作业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从1995年开始,人们才关注并注意研究此类渔业作业方式可能产生的影响。新西兰渔业部非常关注海底作业对各类海域、大陆坡与深海环境的影响,并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最终与国际社会共同研究得出共识:海底作业会极大地损害底栖生物的寿命,并最终对整体海洋生态造成负面影响[16]。
2.3 渔具渔法有待改进
船只使用的延绳钓、拖网和刺网是海鸟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海鸟通常被诱饵和捕获的鱼所吸引,而捕捞活动中使用的延绳钓、拖网和刺网等渔具可能会伤害、捕获或杀死它们。为了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减少意外捕获海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人类与海鸟和平共存的必要条件。新西兰渔业部部长要求制定减少意外捕获海鸟的措施,对可能引发海鸟危险的所有渔业行为发布政府公告。
2.4 新冠肺炎疫情对渔业出口造成巨大冲击
根据新西兰渔业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是新西兰活龙虾(red swamp crayfish)的主要出口市场,占总出口量的98%~99%。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国经销商取消从新西兰进口的订单,导致新西兰出口商150~180 t的活龙虾滞销。除中国外,美国、日本和欧洲的需求量也在大幅缩减,尤其是随着全球航空运力下降,新西兰水产品的出口遭遇了空前的打击。
高档海产品销量也持续低迷,截至2020年9月底,新西兰最大的渔业公司之一——Sanford公司的冷冻品库存量从8 300 t增至12 000 t,银鳕鱼、帝王鲑和贻贝等高端产品库存量甚至翻了一倍,货值高达7 500×104新元。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新西兰的水产品出口商受到了巨大冲击,企业和政府应调整战略以应对疫情。
3 新西兰渔业发展的积极措施
渔业在新西兰经济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近年来新西兰渔业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离不开新西兰政府在渔业发展中适时推进的一系列应对措施。
3.1 依托先进科学技术,加强对渔业活动的监控力度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已制定计划将使用先进科学技术来提高获取渔业相关信息的质量和数量,加强对商业捕鱼活动的监控。数字监控项目是用于跟踪、报告和监控商业捕鱼活动的数字系统,可以提供更准确和最新的信息,以更好地为政府和渔业决策提供信息,同时有利于可持续渔业的发展[11]。
3.2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坚持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新西兰渔业的长期目标兼顾经济利益和环境可持续性,并体现在政府的《2030年海洋渔业战略计划》中。该战略计划的长期目标是“新西兰人在环境限制内最大程度地利用渔业来获得收益”。新西兰政府通过监测海上服务船只的运动轨迹(误差不超过1 n mile)来对海底作业渔船进行管理和控制,并通过科学家为其设计的空间模型来预测各类海底作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可以预见的是,新西兰政府将与更大范围海洋生态的利益相关者和管理机构进行互动并进行磋商,继而寻求一种综合的、多部门的生态管理机制[16]。
3.3 减少意外捕获海鸟,重视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底层和中层延绳钓渔业中,应该要求加重钓线,提高钓钩沉降率,降低海鸟捕获的可能性。需要紧急研究更有效的措施,减少海鸟与拖网和刺网的交互作用[20]。同时尽可能减少能成为海鸟饵料的鱼屑,否则将吸引海鸟,增加海鸟尾随的数量。对于濒危的种类,拯救每只海鸟的意义都很重大。尽管意外捕获的海鸟数目不多,但所有船队合起来捕获的海鸟总数非常庞大,因此要让船员提高警惕,通过适当的处置措施,增加海鸟被误捕后的生存机会[11]。
3.4 及时调整水产品出口贸易战略措施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新西兰诸多渔业公司带来了新的挑战。疫情暴发后,政府和企业出台多种举措。政府方面,新西兰渔业部部长斯图尔特·纳什已同意增殖放流一定数量的龙虾,将一部分龙虾配额转入下一捕捞季;企业方面,不断适应新的市场环境,积极拓展零售业务。以Sanford为例,该公司将长尾鳕作为一款零售热销产品,其产量的增长使公司再次专注于大宗商品线的开发;贻贝产品因太过依赖餐饮渠道,从2021年起,相关渔业公司已针对贻贝开发新产品和市场渠道。
4 启示与思考
新西兰是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国家,自1972年中新两国建交以来,经贸、文化等关系一直稳定、健康的发展。长期以来,中新两国的贸易规模一直稳步增长[3],了解新西兰渔业发展方向,借鉴新西兰渔业的先进发展经验,对于促进中国渔业向生态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4.1 加强政策扶持,尽快引入捕捞配额管理制度
在新西兰的渔业管理实践中,采取了各个鱼种和渔业种类分开管理的配额管理制度,有效遏制了渔业资源的衰退。中国也有必要尽快引入这一制度,逐步开展针对重点品种和海域的捕捞限额制度[21],以完善现行的渔业捕捞配额管理制度。捕捞配额管理制度要想得到有效实施,就必须通过有限的准入和其他措施充分配合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具体可从捕捞准入制度、配额分配机制、放开对配额权转让的限制和完善监管机制四方面入手[13]。
4.2 加强渔业合作,增强信息交流
近年来,中国水产养殖业和加工业以其固有的特点和优势迅速发展,在这一方面,有必要扩大对新西兰的水产品出口,并与新西兰建立合作关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需要加深中新两国工商界之间的相互了解,探索合作领域,拓宽交流范围,共谋和谐发展,深化务实合作,共创互利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