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山铸铜 博赡通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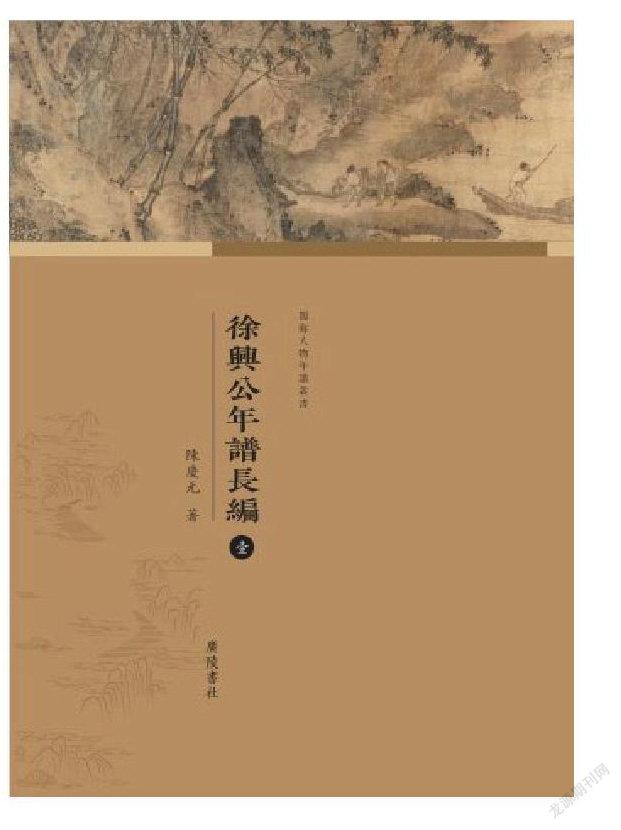
陈未鹏, 文学博士,《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审。
晚明闽中文学的成绩令人瞩目。《明史·文苑传》云:“闽中诗文,自林鸿、高棅后,阅百余年,善夫继之。迨万历中年,曹学佺、徐辈继起,谢肇淛、邓原岳和之,风雅复振焉。”①结合历史语境,“风雅复振”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晚明闽中诗文名家辈出,如曹学佺、徐、谢肇淛、邓原岳等,他们的创作成就突出,在诗坛上具有较高地位;二是晚明闽中诗文踵武优秀的地域诗歌传统,再现了二百余年前洪武永乐闽中诗派先驱当代的盛况;三是晚明闽中诗文高举“风雅”之帜,力矫诗坛“正声久不作,蛙鼓杂天籁”②之弊,在诗坛上别具一格,深具地域色彩并雄踞一方,推动了晚明诗歌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晚明闽中文学实有深入研究之必要。
晚明闽中文坛具有代表性的文人之一是徐。徐(1570—1642),字惟起,又字兴公,闽县(今福州)人,著有《鳌峰集》《红雨楼集·鳌峰文集》《笔精》《榕阴新检》等数十种,藏书数万卷,多秘本、善本。徐又是著名的诗人。钱谦益云:“兴公(兴公,徐字)博学工文,善草隶书,万历间与曹能始(能始,曹学佺字)狎,主闽中词盟,后进皆称‘兴公诗派。”③徐以布衣之身,主盟闽中文坛长达三十余年,其为人、为学当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但长期以来,对于晚明闽中文学的重要作家如谢肇淛、徐、曹学佺等人的认识还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如前引《明史·文苑传》之语,虽然敏锐指出晚明闽中文学的风雅复振,然而万历年中,在闽中首倡风雅者,是曹学佺、徐,还是谢肇淛、邓原岳、徐熥?这就涉及作家行年、经历、交谊、作品系年等方面的研究。应当说,近年来晚明文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基础文献的考订、辨别、整理仍是深入研究的前提。
因此,陈庆元先生《徐兴公年谱长编》(下文简称《徐谱》)的出版,对于推动晚明闽中文学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年谱之体,仿于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④知人论世,是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非知人论世,则不足以深入理解诗歌和诗人。而年谱,正是知人论世之学。知其人,论其世,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但也是相当艰难的工作。年谱的撰述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只是简单的以事系年的工作。一部好的年谱不仅要全面反映谱主一生的行事与境遇,对于谱主的经历与作品有清晰的系年;还要对谱主的行谊交游有广泛的考察,对当时的社会空间与文学环境有精要的展现。《徐谱》即是这样的一部著作,其搜罗宏富、考订精细、去取谨严,徐的家世、生平、创作、交游和成就,晚明闽中文学兴起的背景,其文学的主张与发展的盛况,均在这部160万字的厚重著作里得到准确、细致、清晰的描绘。就年谱的特色与价值而言,我以为《徐谱》有以下三个突出之处。
一、扎实的文献考证与深厚的学术积累
陈庆元先生早年致力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出版有《中古文学论稿》(1992)等论著,卓然名家。20世纪90年代,他开始潜心于福建地域文学之研究,于1996年出版《福建文学发展史》。《福建文学发展史》的写作颇下了一番“采山铸铜”之工。他说:“笔者撰著《福建文学发展史》时,不免涉及作家的生平事迹,涉及作家的生卒年。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他人的现成成果,然后注明出处。笔者在撰著时,给自己订下一条规矩,尽可能读别集,在读别集时,也读总集,同时注意方志和各种杂著的材料;如果自己看到的材料有限,不能下结论,才对他人的成果进行判断,决定取舍。”⑤陈先生的研究一贯重视原始文献。研究立足一手文献,比起“辗转摘抄”当然来得辛苦,文献的收集、整理、解读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出成果也相对较慢。但只有立足一手文献所得之成果,才不会蹈袭前人、拾人牙慧,才不会以讹传讹、贻误他人。如徐之生卒年,有许多著作和研究论文沿袭旧说,做出错误的判断。而陈先生则依据徐本人的《鳌峰集》和徐友曹学佺《挽徐兴公》诗,考订出徐生于隆庆四年(1570),卒于崇祯十五年(1642),当为定论。徐生卒年的确定,明确了徐是晚明诗人而非遗民诗人的身份,这是厘清晚明闽中风雅倡导者的前后次序和相互关系的关键性一步。
关于徐之生卒年问题,他所引证的并不限于上述材料。书中前后所引,生年部分有:
1.《鳌峰集》卷十六《甲辰元日》:“人生七十老如何,怜我今年一半过。”
2.《鰲峰集》卷二十《丙辰元日》:“四十俄然又七龄。”
3. 《鳌峰集》卷首张燮《寿徐兴公先生六十一序》:“君揽癸在隆庆庚午年。”
4. 曹学佺《三山耆社诗敬述·附记》:“徐兴公乡宾年六十八,予学佺为最少云。值社芝山之龙首亭,自不佞始,愿与诸公岁岁续兹盟焉。崇祯丁丑八月之十三。”按:丁丑,崇祯十年(1637),徐此年六十八,逆推,生于隆庆四年(1570)。
5. 徐《寄苏霞公》:“岁月如流,人生易老,犬马齿今已七十,桑榆景迫,百务俱废,老树婆娑,生意顿尽矣……己卯七月。”按:己卯,崇祯十二年(1639),此年七十,逆推,生于隆庆四年(1570)。
《徐谱》还根据相关文献,考订出徐出生日为七月初二,并驳《荆山徐氏谱》、郭柏苍《竹间十日话》之误。关于徐卒年,《徐谱》不仅举曹学佺作于壬午冬的《挽徐兴公》诗为直接证据,还详考徐于崇祯十三年(1640)后的活动与作品,力证卒于崇祯十二年(1639)说之误,也举崇祯十五年(1642)后曹学佺、陈衎等人悼念徐的多首诗作证,明徐卒于顺治二年(1645)说之误。可以说,《徐谱》考证、辨析和解决了许多学界之前尚存在疑义的问题,凭借的并不是孤立的材料。《徐谱》用丰富的文献支撑形成博证,使得其所得之结论可靠确凿。《四库全书总目》评价顾炎武《日知录》言:“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⑥移之评《徐谱》之考证,亦可成立。
《徐谱》引据浩繁、博赡通贯,当归功于陈先生充分的文献准备工作。《徐谱》从酝酿到最终完成,垂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他念兹在兹,以傅斯年所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做了大量基础性的文献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文献收集的范围包括谱主的所有著作、谱主父兄子孙的著作、谱主文友的著作。徐著作宏富,但布衣一生,文献散佚严重。徐之亲友著作也不易寻访。多年来,陈先生旁搜远绍,或往返于海峡两岸,或探寻于京沪苏豫等地,或借助师友同道,远求于美国、日本,得到许多珍贵的刊本、稿本、钞本,这其中之艱辛隐约数语不足以道之。正是二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寻访,使《徐谱》的撰述有了丰富的文献支撑。以此为基础,他对文献进行了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就徐一人,即搜集了大量的佚诗佚文,点校出版了徐《鳌峰集》(广陵书社2012年版),发表《徐著述编年考证》(《文献》2007年第4期)、《徐年表》(《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徐的荔奴轩及〈荔奴述〉》(《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第4期)、《徐生平分期研究》(《闽江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徐的〈红云约〉和红云诗社》(《上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徐生卒时间详考——兼论作家生卒的考证方法》(《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徐尺牍稿本考论》(《文献》2017年第2期)、《徐兴公“编集”理论与实践》(《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徐修志实践及其理论》(《闽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等论文。对谱主父兄子孙,文友中的何乔远、徐熥、郑怀魁、谢肇淛、许獬、张燮、曹学佺、蔡复一、林古度、张于垒等人,也作有年谱或年表并发表,对谢肇淛、徐熥、曹学佺、张燮、崔世召等人还发表有著作考证,诗文研究等方面的论文。宋代苏轼在《稼说》一文里说,富人的庄稼长得好,是因为富人“田美而多”且“食足而有余”,田美而多,所以地力得以更休;食足有余,故能耕种及时、收获从容。苏轼用富人之稼譬喻学者为学。《徐谱》构建在深厚的学术积累之上,所以其举重若轻、不蹈空论,凡所创见均有坚实的文献基础和周详的逻辑思辨,可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二、网状的研究格局与丰富的全景再现
《徐谱·前言》说:“当下某些年谱是‘线性的,或只有‘独干而缺枝少叶式的年谱。‘线性的、‘独干式的年谱只关注谱主,不大注意周边的人物;本谱则是‘网状的、‘发散式的,与谱主交游的人物多达千人、酬倡作品数千篇,本谱尽可能‘一网打尽。涉及的人物尽可能考其字号、里籍、生卒年、生平仕宦及著述,尤其注重描述与谱主的交往。”⑦《徐谱》的网状研究格局有多个方面的体现。
首先,《徐谱》不限于为徐一人作年谱,而是将晚明闽中文学的代表人物,如谢肇淛、徐熥、曹学佺、林古度等一并纳入叙述,同时与谱主关系密切的邓原岳、陈价夫、陈荐夫、董应举、陈一元、陈鸿、崔世召等人的事迹也多有载记。徐一生亲友、交游,远近数百人之多,《徐谱》尽可能地考其字号、里籍、仕历、著作以及与谱主的关系等;可考其生卒年者,也作简要考证。可以说,《徐谱》以徐为中心线索,贯串起晚明闽中文学人物群体,从而串珠成线、织线成网。这些人物的事迹、作品互相交错,构成了晚明闽中文学丰富的网状图景。
其次,《徐谱》的体例也体现为网状结构。《徐谱》的正文以年月为序纪事系文,而附录有十种之多,皆事关谱主生平事迹:一是荆山徐氏世系图;二是历代徐传记;三是徐文集佚文辑录(徐佚诗,陈教授也已辑录,见《鳌峰集》附录);四是著述编年考证;五是芝社社集表;六是红云社社集表;七是纂修志书表;八是辑录校梓旧籍表;九是辑录校梓亲友著作表;十是徐八论:父亲兄弟与子孙、生平三个时期、《鳌峰集》与“兴公诗派”、诗歌理论与评论、纂修志书及其理论与方法、旧籍整理的实践与主张、编辑审订亲友诗文集、徐尺牍之讨论。附录之四以下七种,以专题编排,与正文及《鳌峰集》相互发明,相映成辉,一如“网络”之纵横交错,将徐这个人物全面立体地加以展现。
再次,《徐谱》以幅员辽阔、历史绵长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作为大背景,是中国文学时空交织网络下的节点呈现。《福建文学发展史》是“试图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来描述福建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探讨它的发展规律和特点”,⑧《徐谱》也是以中国文学为背景的地域文学研究著作。近年来,地域文学的研究蔚然兴起,在理论探讨、个案研究和地域文学史的撰述上均有较丰富的成果。地域文学研究的兴起是中国文学研究细化和深化的必然结果。所谓细化,不是旧有论述的篇幅扩大,而是在时代变迁、社会环境、文学思潮、作家生活经历、传播接受等方面研究的基础上,再加上地域自然与文化环境的因素,对作家和作品做“地域性”的考察。所谓深化,则不限于针对中国文学研究未遑涉及的二三流作家的史料打捞,而是一种破除遮蔽的重新论述,对以往研究中相对被忽略的作家作品的价值重估。《徐谱》的写作一方面概括凝练了徐及晚明闽中诗派的地域性,述及多个徐参与的地域文学社团,如芝山社、红云社、避暑会、泊台社、耆社等,并考察了“晋安七子”“兴公诗派”的成员构成,对闽中诗人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和知识多所引证注释,对前人论述晚明闽中文学地域性特征的文献参考征引。另一方面又论从史出,用大量的文献史料展现了闽中诗派之不染楚氛、尽涤时趋、不流浮响俗调的独特价值。
《徐谱》的网状研究格局取得了“全景再现”的良好效果。徐博闻多识,著作涉及文学、方志学、目录版本学、书法绘画及自然科学等方面;还喜购书、抄书,是著名的藏书家。《徐谱》多角度立体呈现了徐这个博洽人物的“全景”。徐是晚明闽中文学活动的关键人物,参与多个文学社团,主盟闽中诗坛,后进皆称“兴公诗派”。《徐谱》以徐为中心,以点带面,再现了晚明闽中文学发展的全景。而《徐谱》对徐及晚明闽中文学的地域特色的挖掘和考察,突显出闽中地域文学的独特性,打破了关于晚明文学公安、竟陵“楚风”一统天下的单调刻板印象,还原了晚明文学“全景”的斑斓色彩。
三、清晰的问题意识与内在的情感投注
《徐谱·前言》说:“年谱的写作,通过史料辨析,既可以颠覆传统的结论,也可以发现新问题并加以分析解决。”⑨的确,《徐谱》的撰述有着清晰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一种质疑的习惯,在对史料的搜集、叩问与辨析中发现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问题意识”还是一种思考的方法,以问题意识整理、排列、比较后的文献史料呈现为有意义的知识,从而帮助我们立体化地思考“有意义的知识”与一些更大的关怀之间的联系。
具体到年谱的撰述。年谱的撰述很容易犯史料堆积的弊病,而在“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散乱的史料有了统率,就能在学术莽原上排兵布阵、开疆拓土。《徐谱》的搜罗史料、参互考订、断定事实、编比成书,就是为了解决问题。如前面提到的徐生卒年问题,《徐谱》通过缜密的考证辨析,厘清了这个问题,借由问题的解决,梳理了晚明闽中诗坛诗人谱系结构。不限于此,《徐谱》还解决了荆山徐氏家族由商而儒,徐氏家族文学,兴公体,徐书信体散文,兴公诗话与诗学批评,徐藏书,徐纂修方志,徐校辑旧籍、编集,徐与叶向高、谢肇淛、曹学佺诗歌风格的异同,闽中诗人与江浙诗人的交往,闽中与闽南诗人的互动等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有大有小,但无论大小,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都成为学术研究进一步前行的阶梯。
陈先生之所以能提出并解决这些问题,则与他的文献功夫密切相关。有一段时间,学界流行“宏大话语”,对于史料考证有所轻视。然而胡适曾说“但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胡适一生治学,可谓“开山辟地,大刀阔斧”,但胡适也有《章实斋年谱》这样细致的著作,“虽是一时高兴之作,他却也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⑩《徐谱》所下的也是绣花般的文献功夫。陈先生立足原始文献,并得益于扎实的文献考证和深厚的学术积累,所以能在原始文献的整理与比对中独立思考、纠正讹误,发现并解决许多具有原创意义的问题。也正因为强烈清晰的问题意识,所以他对文献史料的关注与运用,是贯通的立体的网状的研究格局,也因此使得文献史料在去取提炼之间有丰富的全景再现。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名为“年谱长编”,实际上是资料编年与考论结合,将编年、考证、论述熔汇于一书,在年谱撰著理论和体例上有独特的贡献。章学诚言:“今之学者虽趋风气,竞尚考订,多非心得,然知求实而不蹈于虚,犹愈于掉虚文而不复知实学也。”?如果考订之学,不能有所为而作,而区区于细微琐细的补苴襞绩、考订名物、纂辑比类,则无所谓之学也。《徐谱》的“问题意识”在于将这些考订与“更大的关怀”联系在一起。更大的关怀既有对晚明文学发展面貌的地域性部分的强调,也有对年谱写作的理论和体例的重新审视。这种重新审视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一种自然而然又不得不然的创新。《徐谱》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根本,去取之意与编次之例皆根据实际需要裁定,所以“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自然在撰述的理论和体例上要有所突破;反过来,理论和体例的突破,使得《徐谱》的撰述更加自在无碍,最终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
年谱的写作一如通史,“非学问足以該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可谓难矣。陈先生积数十年之功,研究地方文献文学,学问该通;《徐谱》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可谓熔铸。然而《徐谱》之所以能有这样的规模与成绩,与他内在的情感投注,也是分不开的。
通常情况下,学术研究倡导冷静客观的态度,避免情感的过度介入。然而,问题意识的背后其实也隐含着研究者的学术趣味。多年来,陈先生对晚明闽中文学倾注了许多的精力。这是学术荒原的召唤,也是乡邦文献的情感驱使。写作《徐谱》期间,陈先生曾多次实地寻访徐的往踪旧迹。如徐曾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游福安,万历四十八年(1620)往福安修县志,陈先生也曾专程沿着徐的福安路线,一一踏访。那次的福安之行,地方友人提供了罕见的石刻照片,再次印证了文献中徐的福安经历。实物与遗文相互参证,真可谓对“二重证据法”的身体力行。然而就实际而言,徐提及的福安胜迹大多数都历经变迁,哪怕没有“被西风吹尽,了无陈迹”,也只是略存大概而已。古人游踪依稀、陈迹斑驳,犹且心心念之、杖履及之;这既源于文化精神的自觉接续,也来自思想情感的深沉认同。
当然,情感驱动下的学术研究,并不意味着以情夺人、放弃严密的科学论证,而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坚持。那些熙熙攘攘的热闹和走马灯式的时髦,对于内心有坚定持守的人而言,不过如过眼云烟。章学诚说:“天下至理,多自从容不迫处得之;矜心欲有所为,往往不如初志。”?捧读《徐谱》,写作者那种从容不迫、不忘初志的坚持跃然纸上。《徐谱·后记》说这部年谱前后做了二十年,“十九年前尚在壮岁,满头乌发,如今头颅发白,癯然老翁”,?此语让我想起了孔夫子的“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我曾为其中之境界不胜兴感。而读毕《徐谱》,意犹未尽,所以热切期盼陈先生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他规划中的《徐兴公尺牍编年笺证》《徐兴公研究》《徐熥集编年校笺》等著作,如此,则必将更进一步嘉惠学林、垂范后来。
注释:
① 张廷玉:《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四文苑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57页。
② 谢肇淛:《读闽诗三首》其二,《小草斋集》,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99页。
③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34页。
④ 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章学诚遗书》卷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⑤ 陈庆元:《明代作家徐?生卒年详考——兼谈作家生卒年考证方法》,《文学遗产》2011年第2期。
⑥? 《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029,448页。
⑦⑨ 陈庆元:《徐兴公年谱长编·前言》,广陵书社2020年版,第6页。
⑧ 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后记》,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32页。
⑩ 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页。
? 章学诚:《答沈枫墀论学》,《章学诚遗书》卷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5页。
? 章学诚:《答客问上》,《章学诚遗书》卷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 章学诚:《家书一》,《章学诚遗书》卷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 陈庆元:《徐兴公年谱长编》,广陵书社2020年版,第2001页。
(责任编辑:斯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