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灵中心”到“庙宇中心”的转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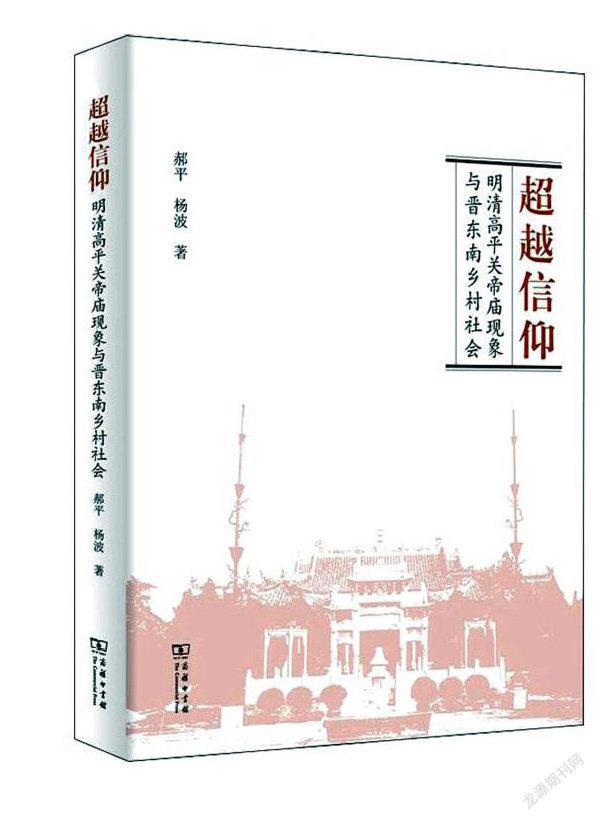
刘永祥,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所副教授。
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视域观察,关公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都无可置疑地占有一席之地。如若将目光聚焦到民间信仰或乡村社会,其重要性则会更加凸显,这从曾经出现的“村村都有关帝庙”的普遍现象中即可明白看出。当关公以庙宇的形式成为乡村组成部分后,就逐渐超越信仰和文化层面,转而成为关涉乡村经济、生活、习俗等各个层面的社会实体,在某些地域甚至成为凝聚整个乡村的中心。因此,研究这一极具文明特色的历史现象,显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学界以往将关注点放在了关公从人到神再到圣的形象转变过程,以及秉持“以神灵为中心”的思路,研究其在信仰和文化层面所产生的影响。最近十余年,研究者虽也开始关注关帝庙的庙宇属性及其在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但所涉及的庙宇数量及地域范围相当零散,严重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郝平和杨波所著的《超越信仰:明清高平关帝庙现象与晋东南乡村社会》,首次尝试“以庙宇为中心”对高平县域内数百个关帝庙展开整体性考察,使学界对于关帝庙现象的认知不再停留在大而化之、模糊不清、充满想象、似是而非的印象层面,其学术特色鲜明,学术路径独特。本文拟对此展开论述,不当之处,尚祈方家见教。
一、突破信仰尺度:以乡村视野对关帝庙现象展开整体性建构
学术研究的创新与推进大致来源于视野、方法和材料等层面,而视野的转换常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有时甚至居于中心地位,尤其对于那些已经明显进入瓶颈期的研究领域来说更是如此。著者开篇即指出:“本书不同于一般的关公信仰、关公崇拜或关公文化的研究,也与通常意义上的民间信仰研究大异其趣……是对于特定历史时期和区域范围内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的综合剖析。”①如果从其所提到的信仰或文化层面加以观察的话,关公研究确实已经成果累累,所剩空间不多,不论是关公形象的变化,还是其所担负的神灵功能,抑或关公戏曲的流传等,均已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历史面貌,即便是从民俗学和人类学角度对关帝庙在现实生活中的意义追寻也已取得较大进展。由此观之,对于关公在中国的研究必须突破信仰和文化尺度,才有可能取得新的进展,亦即必须实现视野(路径)的转换:由“神灵中心”转向“庙宇中心”。
秉持以庙宇为中心的研究旨趣,绝非意味着降低关公作为神灵面相的重要性。相反,关公信仰是中国关帝庙现象的文化源头,忽略这一点,所有论述也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学理依据。但是,关公信仰及其文化自形成后长期存在,不仅它本身的内涵和外延在历史演进中层层叠加,呈现出时代的差异性,而且当抽象的信仰和文化转换为关帝庙这种外在的、具体的形式后,它的发展就增加了一条新的实体路径,而这两条路径既互相依存又互相区别。精神层面的关公更多体现的是国家和儒学的意志,实体层面的关帝庙则更多体现的是乡村大众的需求。如果一味从信仰出发,所描绘的面貌只能是一般意义或者抽象意义上的,与乡村中的实际情况有时会产生较大的疏离。“无论是从实地调查中的感受来看还是从碑文来看,村民们所在乎的似乎更多的是庙宇的建筑是否完备(庙貌),而不是其中的神灵是谁,是神灵塑像是否精美,而不在乎这个塑像是谁。毫无疑问,凡庙皆有神,而且神灵总是居于庙宇核心的位置,但是对于民间庙宇来说,这并不意味着神灵就是庙宇最核心的内容。”②这是相当有见识的看法,它提醒人们注意,关公作为神灵是一回事,关帝庙作为庙宇则是另一回事,两者间存有差别。时代越往后,关公作为神灵的一面越弱化,作为庙宇的一面越突出。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在为什么修建关帝庙这一问题上,不论是古代儒生还是当代学者,大都从信仰层面论证其修建的合理性,却忽略了另一个重要现象:当修建关帝庙在区域乡村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后,其行为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小传统,不再需要在碑文中专门论证修建的合理性,这从侧面折射出“关帝庙作为庙宇的属性越来越超过关公神灵本身”。③换言之,从国家视野和信仰层面考察,神灵是关公研究的核心,但从乡村和社会层面考察,庙宇则是关公研究的核心。由此观之,本书实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是它对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大的贡献所在。
当视野从神灵转向庙宇、从精神转向社会后,其背后所隐藏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经济网络等都渐次浮现出来,进而构成一幅以关帝庙为中心的区域乡村社会图景。“在这个意义上的社庙绝不仅仅是一个信仰活动的场所,庙是乡村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一个缩影和集中体现。关帝庙是最典型的代表。”④关帝庙是一座衙门,是基层政府的议事厅;关帝庙是一个社民权利和义务的确认地;关帝庙是一座法庭,是乡村调解纠纷的地方;关帝庙是一个新闻通讯社和学校,是乡村的信息中心和教化中心;关帝庙是一处市场,乡村庙会常常在庙宇附近举办;关帝庙是一所医院和心理诊所,人们在这里寻求心理的慰藉;关帝庙是一间剧场,几乎有庙就有戏台……关帝庙是区域乡村各类场所的集合地,几乎涉及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绝非单纯的信仰和文化范畴所能涵括。故此,著者所探讨的诸多议题在在充满着新意。比如,关帝庙所承载的乡村治理功能,以往就很少被论及,或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抽象论述层次。该著则通过对禁约碑和诉讼碑的发掘和解读,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并明确指出:“庙宇是村社治理的核心,它是村社组织的具体的活动空间。”⑤饶有趣味的是,关帝庙在村社管理中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关帝庙在村庄中的位置和地位,而与关公信仰本身没有太大关系。在处理村内及村际纠纷等事务方面,关帝庙扮演着重要角色,关公作为神灵则已悄然隐退,这两类功能显然应该进行认真区分。这也再次提示我们,从乡村视角对庙宇展开研究是一条亟待深入的学术路径,庙宇与村庄的关系为研究的核心。
关帝庙对区域乡村社会生活的复杂涉入,决定了此项看似很具体的研究必须采取整体的考察方法,也就是所谓“整体史”的方法。就研究方法来说,虽然整体史的提法很早就已出现,但始终备受质疑,尤其是能否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整体研究。事实上,越是宏观研究越应慎重采取整体史提法,越是具体研究越应采取整体史视野。该著之所以新意迭出,正是因为突破了单纯信仰和文化层面的考察,转向以庙宇为中心,“以关帝庙为基本地理标识将乡村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关帝庙有关系的现象贯穿起来进行研究”,⑥从文化、社会和经济等多个角度,对关帝庙在高平乡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影响,给予了全面、细致的考察。同时,由于关帝庙现象在中国的广泛性,此项研究就突破了區域史的范畴,具有了普遍性的方法论意义。
二、回归实证史学:对关帝庙碑刻史料的充分收集与解读
自20世纪初“新史学”倡导关注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伊始,跨学科治史就成为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思路。改革开放后,学术思想迎来大解放,史学研究越来越强调对其他学科的借鉴,大有不采取跨学科方法则不足以谈史学研究的趋势。诚然,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本身带有很强的复杂性和延展性,适当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也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跨学科之间的整合是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稍不留神就会流于概念的套用,而所谓借鉴的意义也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在历史事实层面的建构尚未完成之前,妄谈跨学科方法恐怕并不可取,起码存在相当的风险。如果从学科属性上讲,历史上出现的关帝庙现象具有跨学科的鲜明特点,可以从不同学科视角予以解读,但这种解读必须建立在基本事实清楚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著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关帝庙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它可以也应该被抽象为某种哲学或社会科学理论,但它首先是一种历史现象”。⑦那么,关帝庙在乡村的基本事实是否已经得到系统梳理了呢?
如果从民间信仰或民俗文化层面来说,关帝庙的整体面貌已经比较清晰,但从关帝庙在乡村的实际影响来说,历史场景还相当模糊。其核心原因在于史料发掘的停滞。尽管傅斯年所言“史学就是史料学”有其偏颇之处,但历史学的根基无疑正在于史料的发掘、整理与阐释。在史学高度发达的当今,是否占有新史料几乎成为评判学术优劣的核心标准,而新史料的批量发现则常常意味着新领域的开拓。关公研究之所以进入瓶颈期,正因为对地方志或文集等严重缺少细节的传统文献史料的过度依赖,“未能找到一处像高平关帝庙这样集中而典型的区域个案,没有进行大量的实地田野调查,没有对一个区域的民间文献做集中的整理和研究,没有真正深入到关帝庙的历史现场之中”。⑧因此,坚持由史料出发进行相对纯粹的历史学梳理,是符合关帝庙与乡村这一选题研究现状的。只有类似的基础研究扩展到足够的时空范围以后,进一步的整体描绘才有可能接近历史本真。否则,所刻画的关帝庙在乡村的场景只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建构,带有较大的想象成分。事实上,以往研究者对于关帝庙在乡村的多面影响未必没有认识,只是受史料所限,无法在细节上予以深描。著者则秉持回归实证史学的基本理念,在大量占有与高平地区关帝庙有关的碑刻史料、口述史料,以及文献史料等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上,将“‘印象转化为经过史学实证的、具有丰富内涵的、丰满的、多层次的历史事实——关帝庙现象”。⑨
高平地区现存关帝庙共有200多处,涉及400多个村庄,而著者所采取的田野调查原则是逐村逐庙,“调查以村庄为基本单元,以庙宇为基本单位,以碑刻为史料重点,将碑刻文献归户到村庄庙宇之中,将庙宇放到村庄环境之中,将村庄放到高平地区的区域社会背景之中”。⑩这项工作足足花费了5年之久,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著者对于庙宇碑刻史料的运用更为全面,可谓细致入微,主要表现在将碑刻落款和捐款题名纳入研究范畴,作为揭示关帝庙在乡村社会和经济层面所发挥影响的关键史料。这种对史料的新解读,实则仍来源于研究视野上从“以神灵为中心”到“以庙宇为中心”的转向,或者说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当然,其也折射出与人类学重在追寻意义的解释路径的区别。
史料搜集的详尽以及解读的细致入微,在关帝庙的学术推进方面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显著效果。其一,通过大量细节的展示厘清了关帝庙在高平地区乡村社会的实际运作模式,特别是以往十分模糊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方面。诸如关帝庙的管理组织、管理制度、经济来源以及与工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都得到较为清晰的梳理。最典型的例子是,揭示出关帝会这一专门的关帝庙管理组织的存在方式以及与村社的区别,包括是否自愿参加、身份获得方式、参与人数规模、集体协商程度等。11而且,相关史实的披露也能丰富对区域乡村结构的认识,如关帝庙修建主体的变化(从家庙到社庙)即能折射出治理结构的变化;借贷、经营矿产、出租房屋等比较罕见的经费来源等,同样能反映乡村经济层面的多样性。其二,新史料的发现深化了对关公信仰层面的认知,丰富了以往单纯从国家和儒学层面的解读思路,增添了更多的底层社会色彩。比如,在关帝庙名称上,民间命名有时按方位,有时按功能,而且带有突出的口语化和随意性特点,像“关爷庙”就比“关帝庙”更为流行,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存在着一整套的制度性规范来对名称进行约束……而这一切在传统社会中几乎都不存在,至少相关的规范非常少,程度也很弱”。12再如,多神崇拜是中国民间信仰的最大特点,而在众多神灵中,关公常常居于非常显赫的中心地位。著者对高平地区关帝庙的神灵体系作了详细的梳理,涉及文昌、奶奶、二郎、鲁班、大王、玉皇、佛、老君等众多神灵,充分折射出民间关公信仰的复杂性。其三,提供了许多高平地区独有的特殊案例,既彰显出地域特色,也为将来更大范围地对比研究奠定基础。比如,西沙院就出现“庙称炎帝,而社称关帝”的奇特现象——通常情况下,同一个社庙选用的神灵文化符号是一致的,而西沙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炎帝是高平特别是西沙院所在小区域内最具影响力的信仰类型,以炎帝来作为庙的名称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关帝信仰所承载的信义精神是村社组织建立过程最需要的伦理价值,因此以关帝来作为社的名字更为合理”。13类似特殊案例提醒人们在进行一般性叙述时,必须充分留意区域乡村信仰结构中的历史叠加现象,也再次印证“以庙宇为中心”路径的重要性。
三、改善失语状况:以关帝庙为中心刻画乡村普通人群的行为
中国的史书编纂从一开始就高居庙堂之上,两汉之后更与君主政治紧密连为一体,“资治通鉴”成为其主要功能,最能反映这一点的莫过于官方史学的高度发达。史学的贵族化和政治化趋势使得正统史学独占鳌头,而且充满对普通民众的规训味道。清末梁启超等新史家曾斥之为“君史”,转而以西方文明史学为蓝本倡导“民史”书写,尽管这是服从于政治变革的宣传口号,但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中国传统史学“重政治轻社会”的弊端,亦即忽略乡村社会尤其是普通人的生活情形。此后百余年间逐渐发展壮大的社会史(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一直在努力改变上述失语状况,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不过,其在史料运用层面仍主要聚焦于政府档案、地方志和文集,所呈现的是由地方中高级士大夫描绘出的场景,虽未必失真,却难以触及最底层的人群生态。近些年,学者日益关注民间碑刻和文书史料正是对这一薄弱点的弥补。就关公研究来说,以往秉持“以神灵为中心”的研究大多关注信仰层面,忽略了背后“人”的行为。由于关帝庙多由乡村自发修建,并日益具备了社庙性质,成为各类场所的集合体,因此恰能反映普通人群的生活情形。著者尝试以碑刻史料为线索,揭示“隐藏在庄严肃穆的庙貌后面的具体的人的行為”,14常能发前人所未发。兹略举几例。
关帝庙碑文大都出自儒生之手,碑文内容主要反映这部分人的思想,也因此备受研究者重视,而不太起眼的题名则常常被忽略,殊不知看似枯燥的名单恰能折射基层乡村的知识分子构成及其生态。“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在民间社会活动着的底层士大夫群体大概都包括一些怎样的人,这些人中除了郭嗣焕中了进士,可以算中层知识分子外,其他人都是底层知识分子。他们的主体是由庠生、贡生等组成的,真正的举人和进士很少。”15这一论断大致能反映出县域范围内知识分子的群体构成。碑文虽大多出自底层儒生之手,但从内容中仍能窥测村民对关公文化的认知。比如,作为一项重要的关帝庙习俗,搭戏台唱戏并非单纯承载酬神功能,还有对外宣传、对内教化以及村际交往等社会功能。对于很多村民来说,娱乐功能甚至居于首位。可以说,时代越往后,信仰之上被附加的其他功能越多。而且,由于唱戏的娱乐功能日益凸显,其与关公信仰之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紧张关系。儒生在撰写戏楼修建碑文时,常常将戏曲看作嬉戏,认为有“侮圣”之嫌,并对戏台建筑规格超过关帝大殿的做法予以批评。类似碑文足以反衬村民对修庙唱戏的热情在某些时间节点显然要高于神灵本身。这种外在形式掩盖内在意义的习俗现象,在当下乡村仍大范围存在。事实上,从碑刻史料中可以发现很多与以往想象大不相同的乡村群体行为,而这才是村民关公信仰的真实状态。神像与庙宇的序列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许多碑刻史料显示:“在正式修建庙宇之前,创建庙宇的位置上就有神像或者神龛。在这些例子中神像的存在是先于庙宇创建的,庙宇实际上是从一个小的神像或者神龛发展而来。在庙宇创建之前,在这个空间上就已經存在着围绕神像或神龛而展开的烧香膜拜活动。”16这与通常想象的先修庙后塑像的情况有重大差异,提示了庙宇创建的另一条途径,即从神龛神像逐步扩大演变而来。
再者,区域乡村的各类人群几乎都与关帝庙产生联系,以往受关注最多的当推商人,大致沿着关公忠义精神与商人先义后利理念相契合的思路展开探讨。高平地区的碑刻史料同样能够印证上述观点,甚至在某些碑文中出现了“商贾依仁义以取钱财”的特殊表述,明确将商人与关帝庙联系在一起。17除此之外,从繁复的关帝庙碑刻史料中还可以勾勒出其他相关人群的具体行为,尽管数量不多却弥足珍贵,如工匠、乐户、医生等。关于捐工和管饭的记载,则涉及关帝庙修建的每一个环节,再现了充满生活气息的历史现场。最具创新价值的是关于女性关公信仰的记载。民间一直流传女性不拜关公的说法,但从高平地区发现的碑刻史料来看,这种说法恐怕未必确切。传统女性在社会中缺乏独立性,其身份需要通过丈夫家族来确认,因此捐款名单中她们的名字直接附在丈夫或儿子后面,但女性名字单独出现以及女性集中捐款的情况并不少见,足以证明在某些历史时期“女性充分地参与到了村庄关帝庙的活动之中,但是参与又有所限制,她们没有捐物也没有捐工表明她们对于具体的庙宇修建活动是无法参与的”,18也证明女性存在着超出家庭范围之外的社会活动。捐款中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由女性组成的“会”的组织,也为传统社会女性组织的普遍存在提供了好的例证。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结 语
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往往比较具体,甚至有琐碎之嫌,近年来也因此受到某些批评,被指为事实详尽而意义不足,如时兴的乡村研究几乎呈遍地开花的格局,但最终结论常常趋同。此种批评自有其道理,当微观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后,理应期待宏大叙事的出现或终极意义的追寻,但因此判定微观研究不再有价值则显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更何况,当下的微观研究其实不是太多,而是仍嫌太少,应该继续“碎片化”才能保证宏大叙事不至于出现重大偏差或流于想象。《超越信仰:明清高平关帝庙现象与晋东南乡村社会》正是将目光聚焦到高平地区的关帝庙这一实体,借助田野调查和民间文献等第一手新史料,详尽梳理了关帝庙在区域乡村的实际影响,成功实现了从“以神灵为中心”到“以庙宇为中心”的转向,开辟了一条民间信仰研究的新路径。我们甚至可以大胆预测这将是未来的趋势,在特定学术范畴内具有了范式意义。其所揭示的诸多细节或特例,也再次提示了继续推进微观研究的重要性。当然,方法论层面的整体视野同样必不可少。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15161718 郝平、杨波:《超越信仰:明清高平关帝庙现象与晋东南乡村社会》,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82,165—166,277,188,12,281,9,4,11,160,79,164,277,131,123—124,255,136页。
(责任编辑:李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