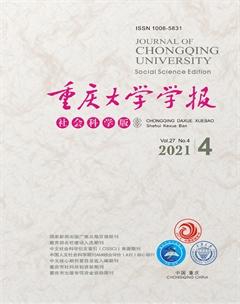德润四海
朱舸 李广良
摘要: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董仲舒;大一统;汉朝儒学思想;汉朝治边思想;汉武帝边疆经略;夷夏之变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4-0083-09
汉初及至武帝时四夷的威胁(尤其是匈奴)一直是国家生死存亡的首要大事,在对付夷狄的策略上,大臣们积极出谋划策。高祖时期,关内侯刘敬主张与匈奴和亲,用结亲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缓解国家危机。但和亲“缓胜”的政策并非长久之计。“文景之治”财富的积累,使国家实力进一步增强,武帝锐意对外用兵,开疆拓土的同时,大力实施文化征服。董仲舒的夷夏论与“大一统”学说为汉武帝实施文化征服提供了理论支持。但北方匈奴兵威日盛,匈强汉弱的悬殊局面难以迅速改变。董仲舒的夷夏论与“大一统”学说难以在汉匈战争中发挥作用;在与西域诸国的交流中,使用外交策略获得很大成功;在东夷朝鲜的征服中,军事武力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董仲舒思想的正确性在东、西、北方的征服中尚未能有机会进行验证,但在汉武帝开拓与经营“西南夷”
“西南夷”一词出于《史记 · 西南夷列传》,指当时生活于西南地区众多少数民族,即今川滇黔三省及甘肃南部的各少数民族。 的过程中,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指导思想。
一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兼并战争持续不断,道德的持续滑落使得焦虑的孔子希望通过记载历史整顿天下纲纪,重构社会秩序。基于这一目的,孔子著《春秋》,于隐微细密处书写大义,试图对现实政治生活和威权势力施以干预,“正是非,故长于治人”[1]36。其中,对于夷狄,孔子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通过教化,夷狄的文化程度可达到华夏族的水平。事实上,由于动乱,春秋时期,孔子思想并未展现出实际效用。及至战国,尽管诸国更是“争于气力”[2],但儒家政治的“合法性”确逐渐体现出来,对于国家治理,儒家显然胜过其他诸子学派。秦亡汉立,空缺的国家意识形态急需确立,“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春秋》受命所致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3]2504-2510。董仲舒的话展现出了孔子之后,儒学《春秋》一脉的文化功能。汉武帝在文景之治国家财富迅猛攒聚的背景下,北攘匈奴的同时希望“德润四海”。董仲舒在强权君主面前主动导引政治走向,发挥《春秋》夷夏观的进步观点,提出“四方不能往,则不全于王”[1]289。四方歸服,成为君主称王的必要条件。可知董仲舒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1]32,即是在儒学“屈君”之内而“伸君”。也就是说,“伸君”与“屈君”并不是水火不容,儒家经义赋予“天”成为最高价值本体,且通过天人感应,这一交互性的关系使得这一学说体系富有张力。在孔子的学说体系内,认同夷狄具备礼义的可能性。董仲舒欲使汉帝国“罢黜百家”,使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就要发展儒学令其具备强势(主动)能力,“《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责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而王道终矣”[3]2502-2503。可知,此乃董仲舒在承继《公羊传》华夷之辨的基础上所作的发挥。《公羊传》认为,中国之所以与夷狄有区别,在于能实行儒教伦理。董仲舒认同《公羊传》的夷夏之别论,但对《公羊传》的观点作了修正,他认为虽然夷夏有别,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夷夏也会“互变”,而“天”下“大一统”则是夷夏观念淡化的基本前提。普天之下,无分夷夏,都可以通过儒学进行教化。汉武帝外征四夷,拓展帝国版图,“四海”的范围不断扩大。而如何教化,即成为关乎天下的重要问题。董仲舒充分发挥《春秋》大义,试图对武帝时期的四海产生影响,发挥《春秋》教化功能。他努力把儒学提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以夏变夷”在理论上完成建构,真正使《春秋》经义能够得到国家层面的肯定,倡导“儒学官学化运动”[4]。
《春秋》传授至董仲舒时,他将公羊学中夷夏观发扬光大,使之成功匹配汉帝国经略边疆的实际需要,在此基础上,提出“大一统”的策略,这成为董仲舒政治哲学的核心和关键,“《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3]2523。指出儒家与“大一统”的直接关系。
随着汉武帝时期“天下”观念的进步,边疆地区的范围向外延伸,董仲舒的以儒学令蛮夷更化的思想便在西南夷地区发挥其经世效用。
董仲舒的“春秋”学不仅仅是理论,在汉武帝开疆拓土的政治实践上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结合汉武帝时期的史实可发现,汉武帝北攘匈奴时,董仲舒夷夏观与当时朝廷主流观点并不一致。而在征服南越时,《汉书》云:“南越已平”[5]3859。《史记》亦书“汉既灭越”[6],“平”“灭”即武力征服南越之义。汉武帝在攻伐匈奴、降服南越的过程中,董仲舒思想终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事实上,汉武帝对“四夷”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历史上“四夷”多笼统地称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至汉代,四夷概念相对具体,分别为:第一类以匈奴为代表,汉朝的策略为力战;第二类为出于联合抗击匈奴的目的,以西域、东胡为代表;第三类为继承前朝版图的基础上,对不进行朝贡的地区施以影响(军事为主),以朝鲜、百越为代表;第四类最为特殊,它从未对中原王朝形成军事威胁,地理位置在汉初极为重要且陌生,以西南夷为代表。在“四夷”内部的实力比较上,匈奴实力最强,“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7]3815。汉武帝时期“四夷”开拓的史实,在《史记》《汉书》中多有(列)传记载。“从公元前135年至前119年,主要的精力用在对付匈奴的威胁方面”[8]。汉初七十余年间四位帝王在匈奴战事上的忍辱含耻,至汉武帝时,以军事手段为主导破除匈奴威胁。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没有在匈奴战事上得到展现。也就是说,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夷夏观并没有在国家对外开拓疆土(匈奴)方面发挥实际效用,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批评董仲舒“犹复欲守旧文,颇增其约”[7]3831,认为董仲舒不了解匈奴人桀骜性格,其言论“未合于当时”[7]3831。那么要证明董氏“大一统”思想与边疆经略的关系,研究视角只能往其他地域进行延伸。李大龙在《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中提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汉武帝‘大一统思想在建元六年(前135年)第二次出兵调节百越之间矛盾时已经形成,其核心内容即是‘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9]。汉武帝所谓“汉为天下宗……天子诛而不伐”[10],更多的是调停战事之义,即“安”。二是“董仲舒对‘大一统的思想阐述只不过是对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进一步细化,替汉武帝进行系统论证……董仲舒对《春秋公羊传》中‘大一统的重新阐释即是迎合了汉武帝的这一需要”[9],关于李大龙的这一观点,除了治思想史的思路以外,史书上也多有记载:“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民用凋敝,奸轨不禁。时少能以化治称者,惟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公孙弘、倪宽,居官可纪。三人皆儒者,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数谢病去,弘、宽至三公。”(《汉书·循吏传》)以经术润饰吏事,其实并不包括董仲舒。“董仲舒为人廉直。是时方外攘四夷,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史记·儒林列传》)。如果说董仲舒认为公孙弘阿谀逢迎以身居高位的观点不客观,那么我们排除经师之间的互相倾轧的可能性,非儒者的汲黯评价公孙弘的话就更为可信。汲黯“面触(公孙)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汉书·张冯汲郑传》)。 李大龙坚守班固立论,将董仲舒与其他经师看为一类,同以经术迎合君主的意图,或有谬误。参见:《汉书》卷五十九《循吏传》,第3623-3624页;《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3128页; 《汉书》卷二十《张冯汲郑传》,第2319页。。由于以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治理方案“只有理想性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提高可操作性、现实可能性和有效性”[11]。汉儒发展至董仲舒时,汉武帝初登帝位,面对天下治理,选择国家的指导思想则非常谨慎。国家的行动须正义理由,汉武帝引用孟子“天子讨而不伐”[12],寻求出师的正义。董仲舒的治“夷”思想在经营“百越”方面也未能体现出来,“大行曰:‘所为来者,诛王。王头至,不战而殒,利莫大焉。……诏罢两将军兵”[5]3861。可以看出,汉武帝在调停“百越”时的治理思想只是口头上宣传,言不符实,除了纯粹的战事外,没有实际的政治操作,董仲舒思想也未能得到实施。秦时李斯提出“地无四方,民无异国”[13]2545的观念,始皇遵之,秦“外攘四夷”[13]2547中徒有兼并战争,国家疆域扩大而没有实施对“夷”的政治治理措施。由此可见,秦、汉迭代,君王的治边思想一脉相承,即:国家实力的增强,用武力对四海(夷狄)之地施以影响,令其臣属中原王朝为第一要义;武帝外征朝鲜,亦重在战事,以及汉朝出于联合围剿匈奴的国家战略极重视西域的开拓等,也说明军事武力对于国家稳定的重要性。
由上可知,汉武帝时期外征“四夷”,在百越、匈奴、朝鲜,西域之地皆无儒家“大一统”的意蕴。除却这些地区,只剩“西南夷”地区了。“四夷”中西南夷实力最弱,汉朝用什么方式“征服”“西南夷”?《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蛮夷虽附阻岩谷,而类有土居,连涉荆、交之区,布护巴、庸之外,不可量极。然其凶勇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为劣焉。”[14]山川阻隔,交通不便,西南夷地区在中原王朝的对外关系中显得无足轻重
余英时在论述汉朝的对外关系时,是以对汉朝的影响力为主要参考标准。他以如下次序排列:匈奴、西域、羌、东胡、乌桓与鲜卑、朝鲜半岛、南方(南越)、东南(闽越)、西南、东地中海地区。西南成为仅次于东地中海地区的末流之列。参见:崔瑞德、鲁惟一主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其在政权组成上,“西南夷君长以百数”[15],百蛮蠢居,部落林立,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独立于中原文化的正统体系之外,所以也未能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秦朝统一后,尽管开凿西南交通要道——五尺道,但并未能将西南夷納入秦统领范围,更没有将中原文化深入到西南夷的民风治理上,西南仍然是一个非常独立的文化区域。至汉代,仍然因为西南夷“远臧温暑毒草之地……屯田守之,费不可胜量”[5]3844。一旦遇到叛乱之事,该地暑热潮湿、毒草丛生,即使拥有杰出的将领也不能施展军事才能。经略西南夷地区对汉朝劳而无功。加之北方匈奴的强大军势,汉朝政权收缩财力,全力应对匈奴。因此,西南夷逐渐消失在中原王朝的考虑之外了。
但,汉武帝时期,西南夷重新提上日程。董仲舒的“德”治思想在国家治理方面终于找到突破口并成功地指导汉武帝征服西南夷,最终实现汉朝的“大一统”。正是汉武帝经略西南夷,董仲舒的儒学“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的“大一统”欲求形成默契配合,使“德润四海”[3]2479完成由理想到现实的跨越。
二
西南夷两次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是由于唐蒙、张骞分别在南越发现枸酱,出访大夏时得知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文翁依《春秋》开创性地于边疆地区进行儒学实践,蜀郡风气大为改变,从此教化盛行,甚至影响汉武帝使之下诏令郡国设置学校,显示了儒学教化的作用。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在番禺初见枸酱,得知枸酱这种珍奇美味由蜀郡生产后,经夜郎的牂柯江运送至南粤。唐蒙遂上书汉武帝,希望凭借夜郎的兵力制服南粤,进而开拓西南夷。于是皇帝命唐蒙拜见夜郎侯多同,遂开通了夜郎的道路。徐复观在其《两汉思想史》中,将董仲舒的《贤良对策》与《春秋繁露》分而视之。作为《春秋繁露》的拔萃,“《贤良对策》则以现实政治问题为主,他的天的哲学,在力求简括中反退居不太重要的地位”[16]。对策之年发生于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正值开拓西南夷,《贤良对策》中记载了董仲舒对汉武帝的提醒: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3]2511
此时汉朝与夜郎等地尚属盟约关系。董仲舒所谓夜郎等地对汉朝的悦服归心实际上只是政权名义上的归属。不过,董仲舒已在此提醒汉武帝在扩张疆域的同时要注意将恩德广施到百姓身上。董仲舒的这一在对策中的建议,与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后续事件合拍。汉朝将夜郎和其周边小国的所在地合并为犍为郡。设置犍为郡之后,汉王朝征调巴蜀郡的士兵修筑僰道到牂柯江的道路。据《史记》载,当时经朝廷批准动用巴、蜀二郡千余人,唐蒙又擅自多征士兵万余人以进行水路运输补给,并以军法处死违令的首领,使得巴、蜀二郡人心中引起惊恐,酿起大骚乱。汉武帝得知此事后,便派司马相如为特使,谴责唐蒙的过激处罚,司马相如作《喻巴蜀檄》。在这篇檄文中,司马相如说明汉朝开拓西南夷的真实意图,即“存抚天下,辑安中国” [17]3044,批評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17]3044-3045,并对巴蜀民众进行安抚。文章以稳定民心为起始,委婉地告诉巴蜀群众,开发西南这件事本身并无错,不该抵制,“当行者或亡逃自残杀,亦非人臣之节也”[17]3045。司马相如描述士兵血战北疆的场景,劝诫巴蜀臣民应当以国事为重:
夫边郡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弛,荷兵而走,流汗相属,惟恐居后,触白刃,冒流矢,义不反顾,计不旋踵,人怀怒心,如报私仇。彼岂乐死恶生,非编列之民,而与巴蜀异主哉?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而乐尽人臣之道也……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今奉币役至南夷,即自贼杀,或亡逃抵诛,身死无名,谥为至愚,耻及父母,为天下笑……(汉武帝)故遣信使,晓谕百姓以发卒之事,因数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方今田时,重烦百姓,已亲见近县,恐远所溪谷山泽之民不遍闻,檄到,亟下县道,咸谕陛下意,唯毋忽也。[17]3045-3046
可知,汉武帝在平定巴蜀时,遇叛乱不是军队镇压,而是派儒生(司马相如)为特使前往安抚,且晓以大义,认为应征民众的逃亡与叛乱是父兄教导不严而导致的不知羞耻、风俗不淳。儒生为改变这一乱象,责怪掌管教化的三老与孝悌不教诲之过,正值耕种时节,特别慎重考虑不去烦劳百姓。汉武帝德化百姓的檄文正是依据董仲舒“道不平,德不温,则众不亲安;众不亲安,则离散不群;离散不群,则不全于君”[1]290 “百姓不安,则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1]319的思想为基础而发布的。通过将檄文快速下发各县以表明皇帝心意。德治的结果是巴蜀最终归顺汉朝,蜀变服而巴化俗。汉武帝晚年下《轮台诏》宣布停止自元光二年(前133年)以来一直奉行不移的武力绥服匈奴政策,证明了仅有武力和战争是不足以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治“心”。
开通西南夷成为武帝朝极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为此,国家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当唐蒙已经打通僰道到牂柯江的道路后,便着手继续开通西南夷的道路。广征巴、蜀、广汉三郡的士卒数万人修筑道路。两年时间,耗费数以亿计,士卒多劳累至死。结果耗时五年却始终未见成效,引得朝野一片反对之声。许多朝廷大臣认为通西南夷之事于国家不利。如朝廷重臣公孙弘即多次上书汉武帝建议罢修西南夷道,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18]。公孙弘认为经略西南夷地区对汉朝劳而无功,认为西南边疆各族对于国家来说,并无实际价值,国家应当保护民力,继续汉初的固有政策,使西南夷处于化外之地。汉朝的真正敌人是匈奴,国家应当收缩财力,全力北攻匈奴。尽管如此,由于外交的畅顺,经略西南夷的进程得以顺利推进,邛、莋之君听说南夷已与汉朝建交,便自愿归顺汉朝,成为汉朝的臣国,请求给他们置吏。这一化外之地所发生的变化,为汉朝平定西南夷提供了良机。司马相如为蜀郡人,他比朝廷大臣更了解西南夷的实际情况。司马相如应汉武帝询问,认为虽然汉初四代帝王皆弃此地,但由于这些夷族靠近蜀郡,秦时已置为郡县,具备开拓、经营的良好条件。汉武帝遂“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5]3839。相如出使入其地后,“罢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17]2583 。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归来,上书汉武帝描述其在大夏国见蜀布、邛竹杖。“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19]。因与匈奴的战事激烈,汉帝国收紧势力一致北进。而司马相如经营西南夷,“三年于兹,而功不竞,士卒劳倦,万民不赡;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业”[17]2583。在众朝臣的反对下,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秋,罢西南夷”[20]。及与匈奴战事稍歇,汉武帝再度将经营西南夷地区放到重要日程之上。
自公元前130年夜郎归附,至公元前109年滇王降,汉朝赐滇王印,置益州郡,至此,西南夷全部归附,至明帝立修通永昌道,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南方古道得以全线贯通。整体来看汉朝在西南夷地区“博恩远施,远抚长驾”,相继建郡置吏,减轻赋税,施恩布德,并不断传播中原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移民屯垦,凿渠修路,汉朝对西南夷的开拓与经营,促进了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汉朝经营西南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董仲舒的“大一统”德治思想。
不同于匈奴,较之于兵戎,董仲舒“德润四海”的策略更适合于西南诸夷。司马相如劝谕巴蜀显示了汉朝“德”治的成功,但属于非兵戎成功的个案,尚未提升到理论高度,至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则完全是董仲舒“德润四海”的“大一统”思想的成功。
董仲舒从《诗经》天下观出发,参照《尚书·禹贡》的五服系统,在承继汉初以来“和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大一统”和夷夏一家的四夷治理路径。董仲舒《春秋繁露》之《楚庄王第一》中举晋讨伐鲜虞之事证明“《春秋》贤而举之,以为天下法,曰礼而信……今我君臣同姓适女,女无良心,礼以不答。有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1]6-7的正确性。董仲舒通过主张君主应对仰慕和遵守华夏礼仪文化的民族加以褒奖和肯定,同时对于不愿亲近,不愿归化的夷狄也应以仁爱之心对待。董仲舒这一“《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1]95的从变而移诠释策略,使得华夷之别超越了先秦时期的地域之分,将二者之间的划分界限确立为是否有礼,“在战国向秦汉的历史大转折中赢得了诠释的空间,顺应了当时中华民族由分裂逐步走向统一的历史潮流,并成为汉初经学之核心”[21]。汉武帝想要通过风俗教化的力量来实现“德润四海”[3]2497,那么“远夷之君,内而不外”[1]281的华夷一体观念就要内嵌心中,“对四夷也讲仁爱,这是先秦思想家没有提出过的认识,是中国古代民族观的一次飞跃”[22]。
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以德治为主,以法治为辅,德治不及时,动以兵戎。在经营西南夷的过程中,汉武帝遵循这一原则,汉兵所至之地,布以仁义,宣传礼义,顺应人心,民皆归服。而在“德”治遭遇挫折时,不得已发兵动以武力。如汉武帝派遣使者欲通身毒国,后因滇、夜郎等国阻拦,汉武帝便发兵降服。类似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皆在迫不得已之时。汉武帝开始认识到西南夷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南夷对于汉朝天下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西南夷地区是西汉王朝与身毒(印度)、西域商贸往来的重要交通线路,是关系国家强盛的重要区域。尽管西南夷文化落后,但“故关守永昌,肇自远离,启土立人”[14],进行儒学教化,实施仁政,相继建郡置吏,尊重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习俗,任用原少数民族的首领,遵循汉夷共治的原则;减轻赋税,进行移民,汉夷杂处,文化融合,中原文化与生产技术伴随官治和移民也传播到西南地区。
当西南夷诸国臣服于汉朝之后,帝国的治边思想真正展现出儒学的经世一面。 既然“中民”与“四海”的夷狄之民已无二异,那么夷人之性就等同于中民之性。而董仲舒认为中民之性又是可教化、待教化的。这样汉朝经略西南夷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董仲舒的教化路径。教化在西南夷地区的实践即汉族移民迁入与派遣官吏。中原居民向西南移民主要与屯田政策有关。“(赵充国)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23],这一屯田政策先是在西北地区取得成功,后来在汉朝开拓西南夷地區面对因路途遥远,供给供应不足和蛮夷数次侵扰的难题时,也推行这一政策。“当是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散币于邛僰以集之。数岁道不通,蛮夷因以数攻,吏发兵诛之。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东至沧海之郡,人徙之费拟于南夷”[24]。这些汉族移民将收获的谷物交给当地的郡县官吏,满足官吏、驻军与修筑道路民众的需要。通过官吏发给的凭证,这些汉族移民到府库中领取钱财。自此之后,有不少内地的地主与商人招募一大批汉族农民到西南夷地区屯垦,这一政策没有因以后的朝代更迭而废除。西汉至武帝时,对西南夷地区的文化有影响力的,除了屯田的移民外,西汉时汉族移入西南夷地区移民的还包括遭贬黜的“奸豪”一类。“晋宁,本益州也。元鼎初属牂柯、越雟。汉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汉乃徙死罪及奸豪实之”[25]393-394。吕不韦家族即属其中,据孙盛《蜀世谱》载:“初,秦徙吕不韦子弟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曰不韦县。”[26]吕不韦门下食客众多,知识分子群聚。即使是历经秦汉之间的朝代更替与百余年的风云变幻,这一群体的文化依然延续。汉武帝又令其他宗族徙至此地,“孝武帝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溪,置雟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25]427。通过这些举措,至汉武帝时,西汉政权便让汉族文化通过民间传播的方式在西南夷地区开始深度地影响当地文化,这样就与官吏的“以儒为教”策略形成了良好的互补。
西南地区民族众多,对于如何处理好封建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缓和民族矛盾,是西汉政权继开发、移民之后开展经营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董仲舒认为“为人臣者……受命宣恩,辅成君子,所以助化也”[1]459。以汉族为主的地方官吏在促进西南地区的文化中起了重要作用。虽然汉武帝时期西南夷诸郡官吏史料缺乏,但结合整个两汉西南地区的吏治来看,“从北向南,整个西南地区,始终奉行北人治南地,分区推进”[27]。这便意味着在广汉、巴、蜀三郡的郡守大都来自北方中原,而上述三郡南部的西南夷诸郡(犍为、牂柯、益州、永昌、越嶲)郡守大都来自北方地区(广汉、巴、蜀)。这些西南夷诸郡郡守掌管司法、部分行政。官吏们在力推儒学传播、劝民农桑、检举郡奸等方面所取得的功绩,使西南地区纳入汉朝疆域,儒学得到传播与弘扬,而西南夷“至今成都焉”[14]。正是董仲舒所提倡的夷夏趋同论,“对武帝北攘匈奴,南服南越,开疆拓土,但对于归附者率予以优渥的处理,不能说没有发生影响。而中国之所谓民族主义,不同于西方与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相通的民族主义,其根源在此”[28]。
综上所述,由于与匈奴的战事激烈,汉王朝难以有多余军队与财力对西南夷进行强有力的武力征伐,因此儒学的功用便展示出来。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和夷夏观内蕴与汉武帝的一统思想形成默契。对西南夷的开拓与经营,正是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儒学的治边成果,西南夷从此纳入中原文化系统,实现了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汉武帝之后“大一统”观念继续进一步在西南夷传播,推进了汉、夷民族的进一步融合。
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成功,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巨大成功,是西汉初期推广儒学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证明了儒学与历史进步的合理性。汉王朝在秦代的基础上又对“西南夷”地区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经略与开发,并逐渐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民族治理思想和政策。以至于后来萧望之运用董仲舒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的问题。从此,儒学正式受到国家推崇,儒学独尊的局面因此形成。
参考文献:
[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445.
[3]班固.董仲舒传(卷五十六)[M]//汉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4]余治平.唯天为大:建基于信念本体的董仲舒哲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72.
[5]班固.西南夷朝鲜两粤传(卷九十五)[M]//汉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6]司马迁.大宛列传(卷六十三)[M]//史記.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3170.
[7]班固.匈奴传(卷九十四下)[M]//汉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8]崔瑞德,鲁惟一.剑桥秦汉中国史[M].杨品泉,张书生,陈高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80.
[9]李大龙.汉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及实践[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38-49.
[10]班固.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上(卷三十四上)[M]//汉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2787.
[11]余治平.“荀子入秦”:何以成为一个文化事件?——儒者直面法家治理的精神体验与思想评判[J].孔子研究,2019(6):5-18.
[12]焦循.孟子正义[M].沈文倬,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841.
[13]司马迁.李斯列传(卷八十七)[M]//史记.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14]范晔.南蛮西南夷列传(卷七十六)[M]//后汉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2860.
[15]司马迁.西南夷列传(卷五十六)[M]//史记.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2997.
[1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393.
[17]司马迁.司马相如列传(卷一百一十七)[M]//史记.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18]司马迁.平津侯主父列传(卷一百一十二)[M]//史记.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2950.
[19]司马迁.西南夷列传(卷一百一十六)[M]//史记.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2995.
[20]班固.武帝纪(卷六)[M]//汉书.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171
[21]干春松.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的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公羊学的探究[J].衡水学院学报,2018:4:24-38.
[22]刘宝才.华夷之辩与中华各民族认同互动[N].中国文化报,2014-05-01.
[23]班固.赵充国辛庆忌传(卷六十九)[M]//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2989.
[24]司马迁.平准书(卷三十)[M]//史记.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 1421.
[25]常璩.南中志(卷四)[M]//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84.
[26]陈寿.蜀志·吕凯(卷四十三)[M]//三国志.裴松之,注.二十四史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3:1047.
[27]黎小龙.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89-94.
[28]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册)[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336.
Morality embellishing the surrounding territory: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great unification” and Emperor Wudis theory of “southwest Yi”
ZHU Ge, LI Guangliang
(Institute for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P. R.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 Confucianism and politics developed independently and merged into the pulse of the same era. As the “Confucianist school” in this period, Dong Zhongshu made great efforts to transform Confucianism and make it a practical ideology for the society and the state. His theory of “great unification” met the need of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 to “run the world with virtue”, thus completing the transition of Confucianism from top to bottom. However, due to the Han-Xiongnu War, Dong Zhongshu had no chance to put his ideas to good use in Xiongnu. Because of the foundation laid by Tang Meng road-cutting and Zhang Qians investigation, Emperor Wudi of the Han Dynasty was determined to develop and manage the southwest Yi. Due to the special geographical position,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he southwest Yi was the weakest among the “Four Yi”, and it would not pose a threat to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y. When the Han Dynasty concentrated its troops in the northern border counties, it was impossible to attack the southwest Yi as Xiongnu did. It provided space for the Han Dynasty to popularize Dong Zhongshus idea of “great unifi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Confucian thought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oad, the placement of officials and immigration. The first successful practice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in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Yi-Xia was to manage the southwest Y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i people in the southwest established the authentic status of Confucianism. Dong Zhongshus thought of “great unification” became the dominant thought of the following dynasties,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handling of ethnic relations, strengthening national unity, and developing national economy and culture.
Key words: Dong Zhongshu; great unification; confucianism in the Han Dynasty; the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frontier in the Han Dynasty; Han Dynasty Emperor Wudis theory of frontier; the change of Yi-Xia
(责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