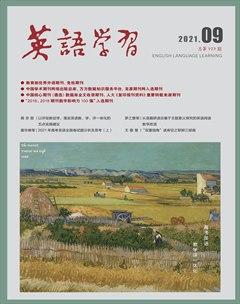“双重视角”读库切之耶稣三部曲
摘 要:本文借用库切本人文学评论中所提倡的“双重视角”审读他最近10年间出版的耶稣三部曲,即《耶稣的童年》《耶稣的学生时代》《耶稣之死》,分析库切是如何在文本创作中通过人物塑造,与卡夫卡的《变形记》、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进行复调式对话的。其对话主题主要从三个方面展现:一是后现代人类生存的异化孤寂感;二是存在的人性价值核心;三是人生的试错过程与美的复杂性。文章主旨在于探讨库切文本中深层的后现代社群哲学思考。
关键词: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双重视角; 复调
从《耶稣的童年》到《耶稣的学生时代》,再到《耶稣之死》,以每隔三年创作一本的速度,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在2020年年初完成并出版了他的耶稣三部曲。这三本小说以儿童大卫作为中心人物。故事的叙述者是西蒙,其主要任务是照顾大卫这个没有父母、不知道来自何处、与他非亲非故的男孩,从幼儿时期开始直到大卫10岁患奇怪病症去世。三部小说使用第三人称视角,通过“他,西蒙(He, Simon)”的叙述 ,表达了库切对孩童教育的关切和对人类处境的思考。
库切的小说一般外在声音都比较简洁温和,而内在的声音则更深刻、更具有反思性。这套耶稣三部曲更是深刻蕴含了库切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虑。库切本人一直强调视角叠加的效能,这一点在《双重视角》这部文集的名称选择上就可以得到佐证。本来一本文集只需要收录研究者自己的论文,但是库切却邀请自己昔日的学生兼同事大卫·阿特维尔参与这本书的写作,就他曾写过的8篇文章进行相关访谈。通过这样的方式,读者得以了解关于贝克特、互惠诗学、大众文化、句法、卡夫卡、自传与告白、淫秽与审查制度、南非作家这8个主题的两种视角及观点。书名的选择表达了库切对待文学研究(也包括文学创作)的态度:尽可能以更多的视角来全方面展现真相。
在《双重视角》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节中,库切曾说:“在所有这些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叙述者准备好了担当问询者与被问询者的角色,线索指向了一种真相,这种真相质疑和复杂化了坦白者声称的真相),我们看到的(我现在推测)是一种幻灭,一种对这样拐弯抹角从谎言中挤出真相的方法的厌烦……”(Coetzee, 1992)。那么库切是怎样寻找关于教育的真相呢?本文也将采用双重视角,从文本的外在声音出发,寻找库切的内在声音,看库切怎样在他的耶稣三部曲中与他所欣赏的作家——卡夫卡、塞万提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进行对话,并邀请读者思考儿童的教育发展与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
对话卡夫卡
小说中的少年大卫是一个挑战世俗的孩子。他的与众不同让他无法适应传统的学校教育,不能被周围的人所理解,教育机关决定把他送到问题儿童学校接受特殊的教育。孤儿感(孤独感)是他一直摆脱不开的阴影。这种与众不同与卡夫卡《变形记》里面的格里高尔有相似之处,一个是外形的异化,一个是想法的异化。当个体与众不同的时候,他的境遇如何?大卫又像卡夫卡《城堡》中的K:没有身份,没有亲人,没有理解他的朋友,像一只迷途的羔羊,面对着对他充满敌意的村庄,城堡当局对他也没有任何信任。在《耶稣之死》中,库切用的比喻是“世界就是一个大监狱”(Coetzee, 2020),最后连大卫喜欢的羔羊也被他所宠爱的狼犬吃掉了。
库切与卡夫卡作品人物的相似性与关联性,首先源于两位作者经历的相似。库切和卡夫卡一样都是生活在一种不能融入主流的、疏离的状态中的人,也都曾经历语言选择的煎熬。卡夫卡出生于捷克的布拉格,又是成长于一个讲德语的犹太家庭的奥地利人。他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犹太人,甚至有很长的时间排斥犹太文化。他与父亲相处并不融洽,在用德语教学的学校学习,一直处于身份认同的迷惘中。而库切作为出生在南非的白人,家里主要说英语。因为经济原因,他和家人一直在更换住所。1949年时库切9岁,他一家搬到伍斯特,这是他第一次接触以南非荷兰语为主的社区。在学校的操场上和街道上,他遇到说着不同类型南非荷兰语的孩子。虽然他的姓氏——“库切”是一个典型的南非荷兰语的姓氏,但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南非白人。在学校里,他是唯一一个通过学院双语考试的学生,对语言的使用一直非常敏感。这两位作家对语言的敏感与不安感受也反映在他们敏锐的社会观察与描写中。他们的独特视角造成了特殊的美学视角——假想的极端状态,要么是成为变形的甲虫,要么是成为救世主般的少年大卫。
他们作品中的主人公一直在反思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格里高尔是家里唯一的养家糊口者,他努力工作以维系家人的生活。尽管变成了甲壳虫,格里高尔还思考着如何能上班赚钱,资助妹妹学习弹钢琴。但是,当他以甲壳虫的形象出现在周围人的面前时,他的境遇大变:老板被吓走,他所关心的家人竟然希望他最好不存在。其实除了身体的异形,他还是原来的那个他,能听懂周围人的话,但是其他人听不懂他的话,也不理解他,这种痛苦、被抛弃的感觉是令人绝望的。《耶稣之死》中的大卫同样也有着不被理解的苦楚。尽管有西蒙和伊妮丝的照顾,他一直觉得自己是孤儿,竟希望能在孤儿院里找到自我。他帮助孤儿院的球队踢球,和一些常人眼中的不良少年打交道,与德米特里这个人们眼中的杀人犯保持密切关系。这些都是他的照顾者——西蒙和伊妮丝,所不能理解的。小说中,西蒙一直试图理解大卫,他努力相信大卫说自己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这样的想法。他在《耶稣之死》中一直尝试弄清楚大卫要带来的讯息,但是到了小说的结尾,他仍旧没有问清楚大卫的讯息是什么。这也给读者一个思考的空间和想象的可能,大卫的讯息是不是与爱有关呢?
这些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也是作者自我情感与命运的投射。卡夫卡和库切笔下的人物心中都充满着爱。格里高尔想着帮助家人;大卫想着帮助周围的人,特别是孤儿院的孩子们。而他们的死亡蕴含着创作者的悲观情结。人可以心中充满爱,但是很多时候人是不被理解的,人面临的是没有出路的未来和绝望的生存境遇。因为缺少同行者,他们不得不孤军奋战。“我们都是孤儿,因为从最深的层次讲,我们都是独处于世(Coetzee,2020)。”这是库切在耶穌三部曲中发出的哀叹。其实人都害怕自己是孤独的,而比这还可怕的是有人根本不敢往这个方向想,也根本找不到自己。所以到最后,作者只能为他们安排了死亡的结局,这表现了作者对济世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的无奈。对作者而言,世界让人失望,生命充满了无解的悖论。就如同《堂吉诃德》结尾,希望纠正世界错误的主人公悲伤地回家,他意识到自己不是英雄,而且世界上已经不会再有英雄存在。尽管处于暮年的库切希望像“西班牙老人”(堂吉诃德)那样思考,但是最后,他还是在《耶稣之死》中结束了大卫的生命。
对话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说:“人生的舞台上也是如此。有人做皇帝,有人做教皇;反正戏里的角色样样都有。他们活了一辈子,演完这出戏,死神剥掉各种角色的戏装,大家在坟墓里也都是一样的了。”桑丘说:“这个比喻好!可是并不新鲜,我听到过好多次了。这就像一盘棋的比喻。下棋的时候,每个棋子有它的用处,下完棋就都混在一起,装在一个口袋里,好比人活了一辈子,都埋进坟墓一样(塞万提斯,2003)。”库切本人是《堂吉诃德》的书迷。他曾经在演讲中多次提到儿童时代读少儿版《堂吉诃德》对他产生的深远影响。儿时的他曾经认为堂吉诃德是一个真正存在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在《青春》中,他曾介绍自己在大学时代如何尝试创作一部《堂吉诃德》的诗剧,但是年轻的他没有完成,因为那个时候这位西班牙老人离他太远了,他无法从他的角度思考(Coetzee, 2003)。但是希望与塞万提斯对话的念头没有消失,暮年的库切通过耶稣三部曲再次尝试塞万提斯式的思考,以至于耶稣三部曲中第三部《耶稣之死》的首版发行语言是西班牙语。
塞万提斯的作品对于库切成长的重要性在《耶稣的童年》中是这样体现的:大卫学习西班牙语的方式就是通过熟读少儿版《堂吉诃德》这一本书。尽管伊妮丝和学校的教师都不喜欢大卫读这本书,但是西蒙重视这本书的意义,并引导大卫阅读。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蒙可以被看作是堂吉诃德的翻版,他相信个体的努力与梦想的价值。西蒙曾对大卫解释说:“我们有两种看世界的眼睛,一种是堂吉诃德的眼睛,一种是桑丘的眼睛。对堂吉诃德来说,这是他要战胜的巨人。对桑丘来说,这只是一座磨坊。我们大部分人——也许你不在内,但我们大多数人——都同意桑丘的看法,认为这是磨坊(Coetzee, 2013)。”现实的生活可能就如同磨坊里的日子,日复一日地充满了辛劳,且没有任何新意,但是西蒙希望大卫理解堂吉诃德的骑士精神,带着为他人奉献之心,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在《耶稣之死》中,少儿版《堂吉诃德》同样也是小说中的重要元素:大卫在医院里,多次在原版堂吉诃德的基础之上,改编并讲述他的“大卫版堂吉诃德”,这种创作方式也展现了作者对《堂吉诃德》原文本的新颖思考。小说中,西蒙也担心大卫陷入《堂吉诃德》太深,所以警告他堂吉诃德代表的是一个虚幻的世界,这本书最后被烧掉了。但是大卫反驳西蒙说,如果书真的被烧掉了,那后来的人们怎么读到这本书的呢?西蒙对大卫的回答感到既困惑又自豪,“困惑的原因是他无法在辩论中说服一个十岁的孩子;感到自豪的原因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可以如此巧妙地将他一局。他告诉自己,这孩子可能是懒惰的,这孩子可能是傲慢的,但这孩子至少不是愚蠢的(Coetzee,2020)。”
像塞万提斯一样,西蒙对他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充满尊重和共情。比如,在《耶稣的童年》中,在码头工人达戈在发薪日抢了出纳的钱箱之后,西蒙对大卫解释达戈抢钱的原因可能是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因为人的天性都是想得到比自己该得到的更多。“达戈想要被赞扬,想得到一枚奖章 ……我们没有给他梦想中的奖章,这时候他就拿钱来代替了。他拿了他认为跟他劳动价值相当的钱(Ceotzee, 2013)。”男孩接着问,为什么不满足达戈的欲望,给他一枚他想得到的奖章?西蒙耐心地告诉大卫,如果那样,那奖章就一文不值了,因为奖章是挣来的。他希望大卫理解收获是需要先付出的,事物的价值在于人类为之所付出的努力。
西蒙是一个持之以恒的教育者,他将这种价值观念实践于对大卫的养育之中。有一段時间,大卫喜欢收集各种物品,包括各种废物,比如鹅卵石、松果、枯萎的花、骨头、硬壳,还有一小堆瓷片和一些废金属。西蒙认为这些废物该扔掉,但是大卫说那是他抢救下来的东西,所以不能扔,西蒙则尊重他的想法。关于钱的价值,大卫曾经问西蒙:如果人们想要硬币,为什么不直接到造币厂去拿?西蒙给大卫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必为了挣钱而工作,如果造币厂直接把钱发给我们每一个人,那钱就没有任何价值了(Coetzee, 2013)。”也就是说,钱和奖章一样,它们的真正价值在于每个个体为之付出的努力。不论是对待大卫还是对待抢钱的达戈,还是堂吉诃德,他都在努力理解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性。
西蒙对于人性的了解非常透彻,正如他在向大卫解释工人达戈抢钱的原因时说道:“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愿意相信自己与众不同,我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愿意相信这一点。但是严格说来,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个个都与众不同,那就不存在与众不同这一说了。但我们还是相信自己(Coetzee, 2013)。”那么,人们如何能够相信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呢?答案是:像堂吉诃德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坚持自己的理想。在一般人看来,堂吉诃德不切实际的骑士精神可能是可笑的,他把妓女当作贵妇,把客栈想象为城堡,说风车是巨人怪物,羊群是军队……但是在塞万提斯或者库切看来,存在的意义在于人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争取,珍视自己的荣誉,肯为他人牺牲,同时也给他人信任。在耶稣三部曲中,大卫也是同样一种类型的人,为了孤儿院的孩子们,离开西蒙,加入这个集体,并深深地影响着每一个和他打交道的孩子。西蒙是自始至终对大卫一如既往充满信任的人,这应该是大卫短暂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不论是自己的行事,还是对大卫的教育,西蒙一直保持他的这种宽容理解的理念,显示着库切对人物的创作态度,亦如塞万提斯创作他笔下的堂吉诃德。
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
关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互文性对话,在库切1994年出版的《彼得堡的大师》里就已经有所体现。在那部小说中,库切采用第三人称形式,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由他想象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小说的内容看似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生平,但是其中许多内容并非史实,而更多的是库切本人对自己中年丧子经历的回忆和思考。这些内容在文本中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形成了多层次的互文。从外表看,读者听到的似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而实际上还有库切内在的声音,这种多层次的众声喧哗和错综复杂的文本互涉时隐时现。在《耶稣的学生时代》中,读者没有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但是会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一位重要人物,那就是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被指控杀父的儿子。该书中还有其他读起来让人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名字,比如被刻画成善良人物的“天使”般的阿辽沙等。
严格说来,在《耶稣的学生时代》中,德米特里不是主人公,他是一个杀人犯——杀死了校长的妻子;在《耶稣之死》中,他也不是主人公,只是一个把大卫当成神一样对待的信徒式人物。为什么说德米特里这个人物在小说中能挑战读者的现有观念呢?笔者认为,德米特里这个人物名字的选择对于库切而言不是偶然的。从某种角度讲,库切是在以复调的形式,通过德米特里这个人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他的作品进行呼应与对话。不论是在文学创作中,还是在学术研究中,库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复调研究都是非常重视的。库切的论文集《陌生人的海岸》中曾收录了一篇介绍巴赫金如何用复调理论来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论文。他认为,“复调小说”的理论是巴赫金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提出的一种文本分析理论,认为对话概念的优势在于没有主导的、中心权威的意识,因此不会有任何一方声称是真理或权威,有的只是争论的声音与对话。 在《耶稣的学生时代》中,库切也采用了这样的方式讨论德米特里的罪行,近乎中立地描述人们围绕德米特里杀人案发出的各种声音与反应。
一方面,所有人都认定德米特里杀人是犯罪行为,但是关于他杀人的原因,不同人的理解是不同的。小说中大多数的人物并不知道德米特里与受害者早有私情。他们以为这是一场爱而不得的犯罪,但是西蒙是唯一了解内情的人。德米特里给西蒙讲述了他是如何与安娜互相爱慕,偷偷见面约会的。然而,跟着西蒙一起了解实情的读者大多不能接受这样的反差:明明安娜在情感上和身体上都已经接受了德米特里,为什么他要杀死女神一般美丽的安娜呢?德米特里这样向西蒙描述他对安娜的感觉:“她是美女,真正的美丽,实实在在,从里到外。如果把她拥入怀中,我应该感到非常自豪。但是我不是的,我感到羞耻。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丑陋、危险且无知的蠢物根本配不上她……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彻底地不对劲。美女和野兽(Coetzee, 2016)。”在美的面前,德米特里一直存在着丑的自卑。所以,在案发的那一天,与自己的女神在一起的幸福时刻,德米特里突然有了一种想让安娜觉得他是主人的感觉。于是他掐住女神的脖子,想让她知道爱是什么以及到底谁是主人。就这样,他掐死了安娜。这再一次证实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出现的观点——美是如此可怕而神秘的东西,竟然会引发人内心中的兽性。美与丑,爱与恨,是两对极为复杂的对应物。“美这个东西不但可怕,而且神秘。 围绕着这事儿,上帝与魔鬼在那里搏斗,战场便在人们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2004)。”至于谁是罪人这个问题,如果参考《耶稣之死》中德米特里写给西蒙信中的内容,“我们想要的,我们所有人想要的是,敞亮的话语打开禁锢我们的监狱大门,让我们恢复活力。当我说监狱的时候,我并不仅仅指医院的禁闭间,我指的是世界,是整个广阔的世界。从某种角度讲:世界就是一所监狱,你在这座监狱里衰变到驼背,大小便失禁,并最终死亡,然后(如果你相信某些故事,我是不相信)你在某个异国他乡醒来接着接受那严峻的考验(Coetzee, 2020)。”库切所关注的不是人物是否有罪,而是如何摆脱“监狱”窘境。
除了在感受“美”的影响力这一问题上进行对话以外,库切还尝试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进行对话,那就是对人性的表露与基本需求的探究。如果上帝不存在,人什么都会做——当然也会犯错。在耶稣三部曲之中,库切让西蒙一直在重复这个观点:人总会犯错,有的时候人不能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德米特里杀死安娜是犯罪,但如果了解他的行凶细节,我们就会知道他的行为是激情犯罪。当他犯罪时,他没有预料到安娜的死亡。他本人一直是懊悔的,所以他向法庭强调自己是有罪的,要求通过去盐矿做苦力来赎罪。尽管德米特里犯了杀人罪,但是他所在的移民安置地——艾斯特拉达当局——对他的审判结果不是死刑,而是给出另外两个选择,要么是被收到精神病院治疗,要么去盐矿挖盐。德米特里选择需要出苦力的后者来赎罪。德米特里的观点也能体现《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长老提到的一种态度:“包括流刑、苦役在内的处罚——过去还要加以鞭笞——其实并不能使任何人改邪归正”(陀思妥耶夫斯基,2004),真正重要的是犯罪者自己的悔过。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不论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是在《耶稣的学生时代》中,审判的场景总有一些关于无聊看客的描述,他们增添了法庭上是非不分的闹剧感。
在《耶稣的学生时代》中,除了在对德米特里杀人案的讨论中,在其他事例中西蒙也反复对大卫强调:人会犯错,犯错的人也会后悔,因为人都有良知。比如在故事开始处,大卫的一个玩伴本吉用石头打伤了一只鸭子。大卫对此非常愤怒。这时候,西蒙教育大卫要尝试理解本吉,他可能就像其他扔石子的男孩子一样,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的本意不是要杀死鸭子,也没有预测到伤害的后果。当他看到鸭子那么美丽的生命被他的行为毁掉了,他也懊悔和悲伤了,“我們并不总能预测到我们行为的后果——特别是我们还年轻的时候(Coetzee, 2016)。” 西蒙是一个成熟的教育者,他通过多个实例反复教育大卫人性的真相,而且他的观点自始至终一致。打死鸭子的本吉和杀死安娜的德米特里,一个是儿童世界的错误,一个是成人世界的错误——我们会犯错,我们并不是可以完美预测行为后果的神人。是啊,我们都是凡人,凡人都会犯错。如果我们真的领悟到这一点,能够直面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才不会躲避和诡辩,才有改正和进步的可能。
在耶稣三部曲中,有一个情节是许多读者不理解、也是学者在撰文探讨的,那就是西蒙和伊妮丝不是大卫的亲生父母,却如此认真地承担父母的责任。有学者表示,即便是圣母玛利亚也还是耶稣的生身母亲,而虽然故事中的伊妮丝与大卫没有任何血缘联系,她却能坦然接受西蒙的提议,尽职尽责地做大卫的母亲,这与读者常读到的白雪公主或灰姑娘的后妈一定是恶毒的常规情节完全不合拍。如果想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看一下《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长老说的话:“地狱就是‘再也不能爱这样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2004)。”在异化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蜷缩到自己的套子里,不想与外界有更多的接触。但是每个个体的内心深处都会渴望着成为一个有爱的能力的人。从这点来看,抚养大卫成长这件事情本身给了西蒙和伊妮丝施爱的机会,让他们二人从付出与担当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两个成人与儿童大卫之间的关系是互为拯救者。另外,“大卫”这个名字的英文是David,如果词汇溯源,其源头的希伯来语含义是“受热爱的,可爱的,朋友”,与“爱”密切相关。所以,笔者认为在耶稣三部曲中,库切用主人公大卫这个名字看似指涉耶稣,实际意图是提醒读者关注“爱”这个主题。他通过耶稣三部曲所发出的讯息,也与“爱”有关,那便是关注在这个后现代社会里,人类对于“爱”的需求与匮乏。
参考文献
Coetzee, J. M. 1992. Doubling the Point: Essays and Interviews[M]. Ed. David Attwel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etzee, J. M. 1994. The Master of Petersburg[M]. London: Secker and Warburg.
Coetzee, J. M. 2002. Stranger Shores Essays 1986-1999[M]. London: Vintage.
Coetzee, J. M. 2003. Youth[M]. London: Vintage.
Coetzee, J. M. 2013. The Childhood of Jesus[M]. Melbourne: Text Publishing.
Coetzee, J. M. 2016. The Schooldays of Jesus[M]. London: Harvill Secker.
Coetzee, J. M. 2020. The Death of Jesus[M]. London: Harvill Secker.
卡夫卡. 2006.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M]. 谢莹莹, 张荣昌,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塞万提斯. 2003. 堂吉诃德[M]. 杨绛,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 2004. 卡拉马佐夫兄弟[M]. 荣如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王敬慧,伦敦商务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澳研中心执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