黍离之悲:两宋之际一位陕西军人的转战史——以《田成墓志》为中心
胡 坤
(西北大学 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从靖康之变到高宗“中兴”,数年间风云激变,时局急转而下,承平时代的安宁稳定被离乱之世的颠沛流离所取代。影响所及,当然不仅限于赵宋的统治阶层。时代洪流裹挟之下,大多数的普通人既有的生活轨迹亦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被迫与乱世相浮沉,并努力挣扎其中。大时代的宏观视角之下,普通人的个体生命或许微不足道,但于个人而言,生命历程中所有遭遇的纠结与坦然、无奈与称意、困顿与振作,不仅重要而且关键。而关注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又不仅在于对个体生命的关怀,也不仅是回应近年来流行的“眼光向下”研究途径,更是了解一个历史时段乃至一个王朝“底色”的有效切入点。
2009年5月甘肃成县抛沙镇西山脚下出土了一方墓主为田成的墓志铭,这方墓志现移藏于成县博物馆,题作《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志铭》(以下简称《田成墓志》)(1)墓志碑额有隶书“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十二字,碑右上角有残损,碑身中部有铁犁划痕,部分文字有残缺;正文隶书,阶州州学教授杜定撰,知阶州福津县宋懋书,任礼、何宗、杨元广刻;此墓志“岁在乙未”立,且墓志称宋高宗为“今太上皇帝”,则乙未为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墓志首行题“□□□□□□□□□田公墓志铭”。有关该墓志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崔峰,蔡副全:《新发现〈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碑〉及其相关问题考释》,《史学集刊》2013年第2期;蔡副全:《宋〈田成墓志铭〉释注暨田世雄相关碑刻举要》,《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墓主田成字希圣,生于宋哲宗元祐初,本籍渭州(今甘肃平凉)。王韶拓边熙河,田成之父赴狄道(今甘肃临洮)为寨户,遂定居。按照墓志中的说法,田成十五从军,北宋时参加了战青唐、平方腊、援河东等军事行动,又趋赴应天府,奉宋高宗登极。进入南宋后,又历经讨群盗张遇、丁进,平定苗傅、刘正彦等战斗,尝任镇江驻劄御前诸军统制、永兴军路兵马都钤辖。晚年因忤权臣,解军职,闲居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后卒于此。
根据墓志的说法,田成一生的行实几乎就是彼时陕西军人在靖康之变前后最标准的经历,与两宋之际的历史高度吻合,堪称典型样本。且田成卒时已是遥郡刺史,有封爵、食邑,又尝任重要军职,然而其人其事在传世史籍中却无一语提及,多少有些令人不解。从田成晚年的官爵来看,他已经不属于寻常意义的“普通人”概念,但就其出身、经历来看,他也只是南宋建国过程中众多陕西军人的一个缩影。尽管所历之事并不平凡,但其姓字不见于史册,惟赖一方专属于自己的墓志铭为后人所知悉,称其“非常人”恐怕亦与事实不符。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田成墓志》的文本入手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对田成的人生历程展开研究,试图通过这一典型案例从“常人”的视角观察两宋之际跌宕起伏的历史,并探讨大时代洪流之下一个普通人的选择与挣扎,以及在故土难回的情境下怀着怎样的情绪与心情。
一、《田成墓志》与传世史籍的对读
《田成墓志》拓片及录文今已公布(2)墓志拓片见蔡副全:《宋〈田成墓志铭〉释注暨田世雄相关碑刻举要》,录文见前揭文及崔峰,蔡副全:《新发现〈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碑〉及其相关问题考释》,赵逵夫主编《陇南金石校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006-1009页。,然与墓志拓片对照,已有录文的标点与文字存在一些问题,现据墓志拓片并参考已有三篇录文,重新录文、标点并分段如下:
碑额: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
□□□□□□□□□田公墓志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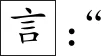
宣和末,朝廷以陕右兵平睦州叛贼方腊,公手斩级三十六,进官升朝。金虏之再至也,公从姚古河东遮寇,会古罢,南关亦失利。公与辛兴宗在隆德府围中,府陷,公阴结民豪韩京图收复。乃以牛车载草,中匿兵,四门齐入,会通衢。纵火取兵,斩虏酋之守者并女真三千余人,城遂复。然时二帝北狩矣。公闻,悲奋感泣,以两旗立左右,率熙河兵及陷散数百人,谓曰:“我辈受国恩几二百年,今运中否,能与我勤王者左,归者右。”左者百余人。公部出济南,说群盗高才、王琪、韩温,合众万余趋应天,奉今太上皇帝登极。





呜呼,年十有□而战立功,瞑且念报君,不忘忠武矣。铭曰:

门生从政郎、阶州州学教授杜定撰。
门生文林郎、知阶州福津县、主管学事劝农□事宋懋书。
岁在乙未。刻者:任礼、何宗、杨元广。
志文首题“□□□□□□□□□田公墓志铭”,所脱九字,可据碑首所题补作“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其下正文首句“□□□□□□□月壬申”,脱年月,《田成墓志》称宋高宗为“今太上皇帝”,且志文后有“岁在乙未”,则宋孝宗时干支为乙未之年为淳熙二年,至于何月则不可知。“武阶太守田侯”,即后文所记田成与夫人刘氏之子田世雄,时为“秉义郎、御前右军同统制兼知阶州”。田成葬地在“西康之西十里西山之下”,西康系同谷县旧称,今甘肃成县。墓志所云葬地与其出土地吻合,在今成县西抛沙镇西山脚下。
田成之父田吉“赴狄道,募为寨户,授田家焉”,后因得疾“不能从军”,“以其田募人代”。狄道为熙州(今甘肃临洮)属县。熙宁五年(1072)王韶拓边熙河,收复其地,遂置熙州[1]9380,田吉大概也是此后不久赴狄道应募为寨户。所谓寨户,是乡兵的一种,宋代史籍载:
乡兵者,籍郡县乡里,及旁塞之民与其丁壮子弟之应募者隶,习武事、备战守;曰义勇,曰弓箭社,曰保毅,曰寨户,曰强人,曰土丁,曰弩手,曰洞丁,曰枪手,曰枪杖手,曰弓箭手,曰勇毅,各因其方之名而名之,通谓之乡兵。[2]468
故《田成墓志》称田吉为“从军”。墓志也反映出寨户还有“授田”,这在宋代史籍中亦能得到印证。如熙宁八年(1075)七月有臣僚上言称:“沿边弓箭手、寨户田土虽有都数,然经略司自来素无拘管顷亩细帐,每有取索,须下城寨,亦恐经久不明。”[1]8680故《田成墓志》记田吉得疾“不能从军”,被迫“以其田募人代”。
“朝廷命熙河帅姚雄经略河外,梁方平监军”,所谓“经略河外”是指元符三年(1100)二月“命熙河兰会路兵马都监兼知河州姚雄统领军马救援青唐”[1]8778之事,是哲宗末至徽宗初年用兵河湟系列军事行动其中之一。此役“吐蕃不留兵守省章,却于峡外平川邀战,雄军既度峡,于是三战三捷,直至青唐”[1]8778,取得重大战果。墓志载田成参加此役年方十五,据墓志田成卒年在“绍兴癸酉三月贰十一日也,年六十有八”,即绍兴二十三年(1153),逆推之,田成十五岁恰是元符三年。墓志与传世史籍所载皆可相互印证。然墓志中提及“皇城使刘仲坚”之人,“梁方平监军”之事,传世史料则未见其载。
“朝廷以陕右兵平睦州叛贼方腊”,与史载“陕西六路汉蕃精兵同时俱南下。辛兴宗、杨惟忠统熙河兵,刘镇统泾原兵,杨可世、赵明统环庆兵,黄迪统鄜延兵,马公直统秦凤兵,翼景统河东兵,刘延庆都统制诸路军马”[1]8802相合。结合墓志后文所载“公与辛兴宗在隆德府围中”及田成劝诫辛兴宗事,可知陕西六路军平方腊时,田成当是熙河兵统帅辛兴宗的部将。“进官升朝”,则是指田成的阶官已升至修武郎(3)据宋代官品令载,武臣“修武郎以上为升朝官”。见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四《职制门一·官品杂压》“官品令”,戴建国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一册,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页。。
“公从姚古河东遮寇,会古罢,南关亦失利”,是指靖康元年(1126)三月,熙河路经略使姚古为河东制置使,“依圣训分遣将兵前去救援太原”[3]330,并收复隆德府(今山西长治),然太原围不解;同年五月再诏姚古与河东制置副使种师中往援太原,种师中战死于榆次(今山西榆次),姚古兵溃盘陀(今山西祁县东南),退保隆德府;[3]356旋即“姚古坐拥兵逗遛,贬为节度副使,安置广州”[4]429,宋廷“诏以解潜”[4]11061代姚古为河东制置使;后“解潜屯兵南关,为粘罕所败,奔于隆德府”[3]385。
墓志言“公与辛兴宗在隆德府围中”,孙觌在靖康中曾为中书舍人,其文集中有一篇题为《勒停人辛兴宗复遥郡防御使隆德府路钤辖》[5]480的制词,似与墓志所记相涉,然史籍所载辛兴宗行实颇粗略,难以比对确定。墓志记隆德府陷而收复事,则未见史载。其后墓志又记:
然时二帝北狩矣。公闻,悲奋感泣,以两旗立左右,率熙河兵及陷散数百人,谓曰:“我辈受国恩几二百年,今运中否,能与我勤王者左,归者右。”
这段记载颇似汉时诛诸吕,太尉周勃入北军行令事:“太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襢,为刘氏左襢。’军中皆左襢为刘氏。”[6]409而田成所为之事,仅此墓志有载,容或有之,然总体而言则“书写”的成分较大。
“公部出济南,说群盗高才、王琪、韩温,合众万余趋应天,奉今太上皇帝登极”事,所言王琪、韩温二人未见史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中则有一段高才的记载,其文曰:“河东军贼高才以二千人归正,出语不逊,王诛之,命右军统制苗傅代领其众。”[7]第1册:64其所云高才身份乃河东军贼,与墓志合,然高才归正时,康王赵构正在济州(今山东巨野),与墓志所云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有异。不过,据田成之妻刘氏的墓志铭所载:“夫人姓刘氏,世居东平,为大族,年十六适田族”,“终于淳熙乙巳八月二十四日,享年七十有四”。(4)田世雄:《宋太宜人刘氏之墓》,拓片及录文见蔡副全《宋〈田成墓志铭〉释注暨田世雄相关碑刻举要》,《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据此可推知刘氏嫁给田成恰在建炎元年(1127),而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与济州又为相邻州府,结合《要录》所记,田成等自河东路渡济河而南,当是先至济州,随后才跟随康王军至应天府。且根据《要录》“河东军贼高才以二千人归正”的说法,墓志中“说群盗”或为不实,而“奉今太上皇帝登极”之语恐怕也难脱“书写”的嫌疑。另外,从《要录》所记苗傅代领高才之众,并结合墓志后文“贼张遇蹂江东,刘光世、苗傅阵九江湖口与战”之载,田成在投奔康王之后,很可能又成为苗傅的部将。
墓志又记败张遇、招丁进、擒刘正彦等事,多与传世史料有相异处,以下一一述之:
张遇“本真定府马军,聚众为盗,号一窝蜂”[7]第1册:189,于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寇江州。守臣承议郎陈彦文视事始十日,固守不下,遇引去。江淮制置使刘光世截其后军,破之”[7]第1册:198。墓志言“贼张遇蹂江东,刘光世、苗傅阵九江湖口与战”,或是《要录》所记“刘光世截其后军”之战。《刘光世家传》亦载湖口之战,然与《要录》所记时间有异,且所记稍详,今将其文迻录如下:
(建炎)二年,群盗一窝蜂张遇掠池州。上幸维扬,除公江淮制置使讨贼。春二月乙亥,赐御笔曰:“见今江口措置最为急务,不可时暂意缓,正籍卿力。未审即日如何施行,仰具措置探报动息,排日奏来。”公自宣化渡绝江,贼已据池阳。公身自抟击,又遣偏裨率水军据团风沙,水陆转战,败贼于九江之湖口。遇解甲,率众来降。[8]卷二
传世史籍中未有苗傅参与此战的记载,据前文所论,墓主田成或是以苗傅部将的身份参与了此次战斗。至于墓志所记田成参战的细节及“光世解佩剑、拊公背”之载,或有夸大的成分。
招丁进事,据《三朝北盟会编》《要录》《宋史》所记,在建炎二年十月[3]865,[7]第1册:281-282,[4]458,以《三朝北盟会编》所记最为原始且详细,载其事云:
丁进复反,率众寇淮西,诏刘正彦帅师讨之。正彦请通直郎刘晏偕行,许之……故晏以赤心骑八百从。逮压贼境,晏知众寡不敌,乃请于正彦曰:“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今贼势甚张,若不以奇计破之,难以力取。请为五色旗帜,俾骑兵八百持一色于山林重复入,皆取后路,前后相继不绝,一色旗尽,即以一色易之,以骇贼心。”正彦然之。贼见官兵累日不绝,旗色各异,谓官军甚众,遂不战而请降,乃分进兵各隶麾下。
其所记丁进“不战而请降”,与墓志所载田成“单骑赴贼营”招降丁进大异。且结合《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所记来看,此时田成似乎又已成为刘正彦的部将。
擒刘正彦事,传世史籍所记略同,以《要录》为详,其文曰:
夜,世忠将至浦城北十里,与傅、正彦遇于渔梁驿。正彦屯溪北,傅屯溪南,跨溪据险设伏,相约为应。世忠率诸军力战,骁将李忠信、赵竭节恃勇陷阵,右军统制官马彦溥驰救,死之。贼乘胜至中军,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正彦望见,失声曰:“吾以为王德,乃韩将军也。”正彦少却,世忠挥兵以进,正彦坠马,世忠生擒之,尽得其金帛子女。[7]第1册374
而墓志有“□功第一”之文,则无法与传世史料相印证。又墓志中明确记田成“从韩世忠受命讨贼”,显见此时田成乃韩世忠所部。
“盖后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荆南王公君瑞也”。据《景定建康志》载:“王玮,字君瑞,绍兴中屡立战功,官至四厢都指挥使。”[9]2037《要录》又载:“代州防御使、荆湖南路马步兵总管王玮为永州防御使,充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荆南府。秦桧之留守临安也,玮为留守司统制,故荐对而命之。”[7]第3册:192王玮知荆南府制词见于王洋《东牟集》[10]442。综前,“王公君瑞”系王玮无疑。
“绍兴辛酉,公以旧忤权臣……遂求补外,居荆南”。绍兴辛酉系绍兴十一年(1141),是年末宋金双方签订了“绍兴和议”,在这个时间点,后文所谓“权臣”,极易联想到时为宰相的秦桧。而所谓“求补外”,从语义而言,在“内”方能补“外”,显然田成此时任职地点应该在临安或附近区域。墓志后文载,田成尝“任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永兴军路兵马都钤辖”。根据田成的经历及当时的局势,所谓“永兴军路兵马都钤辖”的军职,只能存在于绍兴九、十年金人归还河南、陕西地期间。至于“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的军职,据史载:
绍兴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诏:“韩世忠、张俊、岳飞已除枢密使副,其旧领宣抚等司合罢,遇出师临时取旨。逐司见今所管统制、统领官、将副已下,并改充御前统制、统领官、将副等,隶枢密院,仍各带御前字入衔。及令有司铸印,逐一给付。且令依旧驻劄,将来调发,取旨施行。”[1]4016
由此可知,镇江府驻劄御前诸军系从韩世忠淮东宣抚司诸军改编而来,且自绍兴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后才会有墓志所记“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这一军职名。尽管将镇江称之为“内”仍然勉强,但笔者还是倾向于认为田成是解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军职后,闲居荆南府。至于为何选择“居荆南”,则不得而知。
二、《田成墓志》的文本分析与田成的人生历程
前文通过《田成墓志》与传世史籍的对读,可以看到,墓志所叙田成的转战经历,在大的方面与传世史籍所记高度吻合,惟细节之处,或不见于传世史籍所载,或与传世史籍存有牴牾,考虑到墓志与传世史籍叙事的立场、视角,乃至来源的不同,有所差异也在情理之中。不过,结合传世史籍所记,从整体角度重新审视《田成墓志》的文本,仍会发现墓志中存有一些疑问与问题,或者可做进一步的讨论。而在讨论相关问题之前,先对墓志的文本结构作一简单梳理,或有裨于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理解。
《田成墓志》的正文大体可以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序言,交代志文的缘起;第二部分述行实,自“公讳成,字希圣”起,至“公身被二十余创,□功第一”迄;第三部分人物评论及例证,起“公方面美髯”,迄“兴宗大惊谢,愈相重敬”;第四部分起“绍兴辛酉,公以旧忤权臣”,迄“任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永兴军路兵马都钤辖”,部分内容亦属行实范围,然为人物评论及例证隔断,故单列为一部分,或可称之为晚年行实;第五部分叙妻儿之情况;第六部分则为铭文。
明人王衍曾列举墓志铭书法之例曰:
凡墓志铭书法有例,大要十有三事焉:曰讳,曰字,曰姓氏,曰乡邑,曰族出,曰行治,曰履历,曰卒日,曰寿年,曰妻,曰子,曰葬日,曰葬地……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此正例也。其有例所有而不书,例所无而书之者,又其变例,各以其故也。[11]381
以王衍所论比对《田成墓志》,不难发现《田成墓志》“虽序次或有先后”,但大体符合墓志铭“正例”之书法,基本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墓志铭。不过,若以《田成墓志》的细节而观之,不难发现其第二部分述行实,至建炎三年(1129)平定苗刘之变,即戛然而止,后则插入一段人物评论及例证之文,再后所接,便径直跳至“绍兴辛酉”(即绍兴十一年,1141),其中时间间隔达十二年之久。这样的书写方式算不算“变例”呢?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则是,这样的写法背后,是否存在不能与外人道的缘故呢?按照王衍所论的提示,如果墓志铭在书法上出现了“变例”,是应该有“其故”的,至于“其故”为何,则有赖于对墓志文本的细致分析。
这里或可先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将墓志第三部分调整到第四部分之后,即叙述完平定苗刘之变后,接续“绍兴辛酉,公以旧忤权臣”之后的一段文字,而将“公方面美髯”以下文字置于“任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永兴军路兵马都钤辖”之后,那么对于墓志文本而言,到底是对原来表述的提升,还是降低?抑或是没有变化呢?
事实上,经此调整之后的文本,从叙事结构上是更符合“正常”的墓志铭的写法,保证了志主生平事迹的完整性,同时第三部分“公方面美髯”以下文字调整到第四部分“任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永兴军路兵马都钤辖”之后,可对志主生平起到总结、提升的作用,至少在叙事结构上较之原先的写法有所优化。不过,调整之后却也凸显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在叙事中平定苗刘之变与“求补外”之间的时间间隔太过久远,当两段文字接续在一起,难免会给读者以强烈的“跳跃”之感。在此有理由相信,墓志的作者或许正是为了弥补这种“跳跃”之感,从而选择了现在的写法。目前的写法,至少于笔者而言,如果不去刻意分析文本,阅读中所带来的“割裂”之感是非常微弱的,反倒是调整之后的文本所带来的“跳跃”感更为直接且强烈。
如果说墓志的作者是为了弥补叙述的“跳跃”感而采取目前的写法,那么紧接着而来的问题是,建炎三年至绍兴十一年的十二年之间,是因为志主田成的经历中并无值得书写的事迹呢,还是这段时间的事迹不方便书写?答案若是前者,作者选择目前的写法自然是无可奈何的结果,且无可厚非,但若是后者,则需要继续分析其“不方便”的原因何在。
田成的生平事迹唯见此方墓志,传世史籍并无只言片语,要想复原田成在建炎三年至绍兴十一年之间的行实,几无可能。不过,通过其墓志所透露的零星信息,对此问题仍有正面讨论的余地。田成在荆南府闲居时,曾有“吾起身行间,荷恩横列三岁”之语,何谓“横列”呢?现举与田成同时的几通制词为例予以说明。李弥逊《许世安左武大夫和州团练使》制词,其中有“具官某勇冠三军,身鏖百战,用昭显绩,峻阶横列,进职遥团”[12]640之句。岳飞自遥郡观察使晋升为遥郡承宣使,制词有“宣力久劳,战多实著,功加数路,迹扫群凶,遂行横列之迁,兼付承流之寄”[13]1157之语。富平之战中被张浚诛杀的赵哲,后追复亲卫大夫、明州观察使旧官,其制词云:“属权臣之用事,敢专杀以肆威,其还横列之名,仍假廉车之重。”[7]第2册92从前述三例来看,所谓横列,显然是指自遥郡刺史至遥郡承宣使这一阶次,即遥郡官。
田成自言“荷恩横列三岁”,是在绍兴十一年闲居荆南府之后,其卒时为拱卫大夫、康州刺史,属横列最低阶,可知田成自绍兴十一年之后再未升迁。据此逆推三年,其为遥郡刺史当在绍兴八九年之间。武臣晋升遥郡,虽不可与遥郡落阶官升正任相比,但仍不啻为仕途的一道关键门槛。田成起身行伍,又无特殊背景,其晋升为遥郡,当是立有战功。又据墓志所载,田成曾任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永兴军路兵马都钤辖等重要的军职,更可从侧面证明,田成在绍兴年间并非碌碌无所为。
从墓志的记载来看,田成在建炎三年讨平苗刘之变时,即已为韩世忠的部将。而从“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这一军职来看,根据前文所作的考辨,田成在赋闲之前,很可能一直都隶属于韩世忠部。从南宋高宗朝的基本史实出发,绍兴年间,韩世忠部与金、伪齐进行的战斗为数不少,甚至还有名列“中兴十三处战功”的大仪镇之战。如果田成在建炎三年之后一直为韩世忠的部将,他至少应该参加了部分对金、伪齐的战斗,且在战斗中应该有所表现,否则其跻身横列、担任重要军职就无法解释。墓志文本对田成此段经历的缺失,就显得特别意味深长。
另外,《田成墓志》中“绍兴辛酉,公以旧忤权臣,恐中以祸”的说法也颇值得玩味。绍兴十一年之际,朝廷之上能称得上“权臣”的,除了秦桧,再无第二人。田成因何事、何时触犯了秦桧,以至“恐中以祸”,墓志未尝言明,史籍中亦无蛛丝马迹。不过,这里仍可考虑如下两个问题:其一,即以田成最高做到遥郡官而论,其与秦桧的身份、地位相比,其悬隔亦有如云泥,正常情况下,两人似不应有所交集,更遑论作出“忤”的行为;其二,自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朝堂之上风向大变,秦桧的影响力渐次削弱,曾遭受秦桧迫害的臣僚也逐渐回到朝堂,就当时情况而言,被秦桧迫害的历史也变成了一项政治资本,更何况作于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的《田成墓志》,似更有理由将“忤权臣”当作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来书写。
综前所述,墓志书田成“忤权臣”之事,很可能是“书写”的结果,其目的在于抬高田成的政治影响力。不过,似也不能完全排除确有其事的可能,特别是联系到墓志中有关田成在建炎三年至绍兴十一年的行实完全缺失的情况,以及韩世忠在绍兴十一年后被罢兵权的史实,亦与墓志“恐中以祸”的记载暗自相合,其“忤权臣”的说法,也可能并非空穴来风。
尽管《田成墓志》的文本中存在刻意书写、夸大其词、语焉不详等问题,但墓志所记之事大体与传世史籍所载相吻合,其人生经历也基本完整,在此或可根据前文以墓志与传世史籍对读、墓志文本分析的结果,将田成的人生故事略述如下:
田成的先世当是渭州平民,或以务农为业,至其父田吉一代,恰好赶上王韶开边熙河,便应募赴狄道从军,成为宋西北边境上众多寨户的一员,得到政府对寨户的授田,由此在狄道安家守边。然而好景不长,田吉壮年染病,丧失劳动能力,不但难以参加军事行动,连政府的授田亦无法经营,以至于不得不募人代耕,家境也由此每况愈下。田成时年十五,为减少家庭的负担,也为了恢复自家故业,不顾其父反对,毅然从军,投入当地驻军刘仲坚帐下。此时朝廷正用兵河湟,田成随刘仲坚部,在熙河路兵马都监姚雄的指挥下,参加了救援青唐的军事行动。因作战勇敢,由士卒提拔为低级军官。
徽宗宣和末,睦州爆发了方腊起义,为镇压起义,宋廷调集了陕西六路精兵前往东南平叛。田成随熙河兵统帅辛兴宗镇压方腊起义,以战功授修武郎,进入武臣陞朝官的行列。此时宋廷经略燕云失败,金人南侵中原,熙河路经略使姚古被任命为河东制置使,受命救援被金兵围困的太原城,田成作为熙河路的将领自然跟随主将姚古往赴河东。不料姚古兵溃盘陀,旋被贬降,继任的解潜又败于南关,田成等熙河将卒在主将的带领下被迫退保隆德府。隆德府很快亦遭到金人的围攻,田成及辛兴宗等人虽有所抵抗,但终不免于失败,无奈之下田成只得与熙河残兵及周边的溃卒、“群盗”南渡济河,转而向东,来到济州,投奔康王赵构。到达济州后,田成娶了家住东平府的刘氏,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在济州时,康王诛杀了田成他们这支队伍的领头人高才,并将这支队伍拨隶给苗傅,而田成也由此成为苗傅的部将。
不久,田成随着康王赵构的扈从队伍由济州来到应天府,并参加了康王的登基典礼,历史进入了南宋时期,康王便是后来的宋高宗。建炎元年底至二年初,张遇入寇江州,田成跟随刘光世、苗傅等将阻截张遇军,获胜。约在建炎二年之际,田成由苗傅部转隶刘正彦,是年十月,又随刘正彦讨平丁进,丁进在官军的军事压力下投降了朝廷。建炎二、三年间,田成又成为韩世忠的部将,参加了讨平苗刘之变的战斗,且立有战功。自建炎三年之后,田成比较稳定的成为韩世忠的部曲,应该跟随韩世忠部参加了与金、伪齐的战争,因功在绍兴八、九年之际晋升为遥郡刺史。约在绍兴九、十年之时,金人归宋陕西、河南地,田成被任命为永兴军路兵马都钤辖的军职,或恐未尝赴任。
绍兴十一年四月之后,韩世忠淮东宣抚司的军队被改编为镇江府驻劄御前诸军,田成又被授予镇江驻劄御前右军统制。同年,绍兴和议签订,韩世忠被罢兵权,先任枢密使,后赋闲家居,大约在此前后,田成也感受到了政治氛围的紧张,遂求解军职,于荆南府闲居。绍兴二十三年三月,田成卒于荆南府,享年六十八岁。临终前,田成向其子田世雄交代后事,希望死后能归葬祖坟。然而,北宋的陕西故地大都沦陷于金国,且此后田世雄有很长时间都在荆湖、两浙等地任职,未能完成其父的遗愿。直至孝宗淳熙二年,田世雄任阶州知州期间,方将其父灵柩自荆南迁至成州同古县安葬。安葬之处虽非故土,但却是南宋境内离故土最近的地方,且属于北宋时期陕西六路之地,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完成了乃父的遗愿。
三、陕西军人的南迁与故土之思
从靖康之变到南宋重建的一段时间内,有大批北方士庶、军民跟随宋廷南迁,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群体便是陕西籍军人。原因无他,赵宋得以重建并绵延百余年,陕西籍兵将出力最大,亦是偏安政权最为倚重的武装力量。南宋人就曾总结称:“渡江后名将皆西北人。”[14]687而其中又以被时人称之为“西人”的陕西籍武将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如当时号为名将的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吴璘、刘锜、李显忠等,莫不是出身于陕西六路。将帅既多西人,其所领士卒部曲亦以陕西籍为主。时人称扈从高宗南渡“将士多陕西人”[7]第1册:371,刘光世、韩世忠、张俊“三大帅所统颇多西人”[7]第2册:241,刘光世“部曲皆西人”[15]46,四川宣抚司“军士多关中之人”[7]第2册:758,其中“正兵皆西人”[16]卷四。显见陕西籍将帅、士卒于南宋朝廷而言,实为国之干城、邦之柱石。
从前引诸书所记可见,南宋初年陕西籍兵将主要集中在两淮防线刘光世、韩世忠、张俊部,以及川陕防线吴玠、吴璘部。这一现象实则反映了北宋末至南宋初年陕西六路军队两条不同的南迁路线。
北宋时期,陕西便是天下精兵良将荟萃之所,兼之常年与西夏及青唐诸蕃部作战,其军事素质与作战能力更非他处军队所能比拟。北宋时期的陕西军队基本都在陕西境内屯驻、作战,朝廷第一次大规模调动其出陕是宣和末年平定方腊起义之际。随后又因联金灭辽之役,北上伐燕。再后,金军入侵,又先后历经救援河东、勤王京师等大小战役,其中虽多有溃散、战败者,但在宋高宗登极前后,这批离陕军队的残部又在各级将领的带领下,汇聚在宋高宗的周围,形成了南宋最初武装力量的基盘,如刘光世(5)据《宋史》卷三六九《刘光世传》载,北宋末,刘光世随其父刘延庆平方腊、征燕蓟,从范致虚勤王,后“别道趋虢,遂至济州谒康王”,第11478页。、韩世忠(6)据赵雄撰《韩忠武王世忠中兴佐命定国元勋之碑》载,韩世忠先随王禀平方腊,后从征燕山,再从梁方平平定山东诸盗,又“从梁方平防河濬州”,后康王开大元帅府,世忠往从之。见杜大珪编《新刊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上卷一三,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张俊(7)据《宋史》卷三六九《张俊传》载,张俊先从河东制置副使种师中援太原,后“勒兵从信德守臣梁扬祖勤王”,遂归于康王,第11469页。、王德(8)据傅雱撰《宋故清远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充荆湖北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荆南驻劄陇西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一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致仕赠检校少保谥威定王公神道碑》载,王德先从姚古援河东,后从范致虚勤王,康王登极后,“遂引军倍道趋南都”。《王德神道碑》拓片见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3册,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7-58页。,乃至本文的主人公田成等人,皆是在此种情形之下来到了宋高宗的身边。后来南宋两淮防线三大将的军队即是以这批平方腊、援河东、征燕山以及赴京师勤王的出陕军队为基础壮大形成。
至于当时陕西六路境内,尚留屯有大批军队,建炎初年虽亦遭侵陕金军的猛烈攻击,损兵失地,但大体上仍能勉力维持。直至建炎四年(1130),知枢密院事兼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为了缓解宋高宗驻跸之处的军事压力,集结陕西宋军主力挑起了宋金之间的富平会战。由于张浚指挥失当,宋军惨败,一溃千里,陕西之地尽陷于金人。溃散的宋军要么降金,要么退守四川。退守四川的陕西宋军在吴玠、吴璘兄弟的整合之下,渐次形成了后来南宋四川宣抚司的军队,由吴氏兄弟领导。
陕西军人群体的南迁,事实上是时代洪流裹挟之下的无奈之举,其中个人的选择空间微乎其微。无论是后来大批集结于两淮战场,还是川陕战场的南迁陕西军人,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南迁动因的相异。前者因朝廷先期调动出陕,靖康之变历经溃散之后,自然集聚在继承赵宋天下的宋高宗周围,并随之南渡;后者则因战败,故土难守,迫于形势而南退四川。为国而战与背井离乡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这一群体相似的“国”与“家”的记忆。
不过有趣的是,无论传世史籍,还是专属于个人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之类的传记史料,以目前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来看,似乎更多的是在铺叙这群流寓军人的赫赫战功与忠君体国,极少有表现他们怀乡思亲的一面。这其中当然与以“国”为叙事重点的中古古代史学记叙的传统有关,但放在宋金战争的背景之下,北宋已然亡国,大批流寓军人背井离乡、艰苦转战,若说他们没有半点黍离之悲、乡梓之愁,恐怕很难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更有悖于人之常情。就此点而言,《田成墓志》却透露出这位转战南北三十余载陕西老军人的故土之思,则多少显得有些与众不同。
事实上,《田成墓志》中有关田成故土之思并非直接描写,而是借其子田世雄之口来转述,为了利于进一步分析,仍将相关文字迻录如下:
上引文字的叙述重点固然在于“请铭”,但从文章的写作技法而言,作者杜定借田世雄之口,将墓主田成壮士忧国、游子怀乡的形象勾勒出来,虽为不动声色之举,实收先声夺人之用。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墓志后文更多的文字都在铺叙田成的战功,其忧国、体国、为国的一面展露无遗,而怀土思乡的一面却不着一字,墓志起首关于“游子怀乡”的形象便也因此而削弱许多。

正如前文所曾提及,在笔者目前掌握的两宋之际陕西籍军人的行状、神道碑、墓志铭中,无论是如刘光世、韩世忠、吴玠、吴璘等方面大帅,还是如王德、李显忠(9)《李显忠行状》见《名臣碑传琬琰之集》下卷二四《故太尉威武军节度使提举万寿观食邑六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户陇西郡开国公致仕赠开府仪同三司李公行状》。等高级将领,抑或地位低于上述诸人的杨从仪、彭杲(10)彭杲夫妻合葬墓1991年发现于陕西洋县,其墓志铭拓片的局部照片及录文见李烨、周忠庆:《陕西洋县南宋彭杲夫妇墓》,《文物》2007年第8期,第68-70页。《彭杲墓志铭》首行题:“宋故武功大夫、吉州刺史、兴元府驻劄御前都统制致仕彭公事实”。彭杲生于宋钦宗靖康元年,卒于宋光宗绍熙二年,终年六十六岁。等人,几乎看不到怀乡思亲的文字。仅有《李显忠行状》及《杨从仪墓志》中,因李显忠由金投宋致全家被害,而杨从仪则因父母为金人所掳,方在行状、墓志铭中有所提及,且无一例外都在“国”的叙事框架下之下铺陈而来。这里或可举《杨从仪墓志》之例予以说明:
绍兴改元三月,虏自熙河复围凤翔,势益炽。公告二亲曰:“为人之子,非敢蹈于不孝,今城中兵寡,守死无益,不若溃围救援。”即泣别而行……先是,虏耻屡败,遂囚公二亲于青溪寨,公内不自安。二年正月,公乞兵以往,忠烈(吴玠)许公带本部出北山,断虏粮道。行数日,至麻家岭,遇敌接战。翌日至青溪,虏会诸寨兵为援,自辰合战至暮,大破虏众,奉亲以归。(11)袁勃:《宋故和州防御使提举台州崇道观安康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七百户实封一百户杨公墓志铭》,拓片及录文见陈显远编著《汉中碑石》,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18、125-126页。
在上引这段叙事中,杨从仪泣别双亲、双亲被掳、奉亲以归的描写都只是为了凸显墓主的忠义、勇敢,除了“泣别而行”“内不自安”稍涉情感外,并无更多文字予以着墨。显然,这样叙事手法的着眼点仍在于“国”,而并非“家”。对比《田成墓志》的叙述,虽然都属于着眼于“国”的叙事框架,但《田成墓志》至少流露出墓主的乡愁。田成虽死,亦不肯安葬于荆南,纵使千里迢迢,也要埋于近乡之地,他对叶落归根的执念,即便墓志文本书写的隐而不彰,仍可令千年之后的我们读之动容。这或者也是《田成墓志》值得学界重视之处。
四、余语
前文以《田成墓志》的文本为出发点,通过与传世文献的对读、对墓志文本的分析,呈现出两宋之际一位陕西军人的人生历程。综观田成的一生,至少从墓志的文本来看,似乎就是被历史洪流裹挟的一生。父病家贫之时,恰逢朝廷用兵青唐,慷慨从军的表象之下,实则是迫于生计的无奈。之后又在朝廷的调动之下,跟随部队征方腊、援河东,尽管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但在大的局势面前,个人的努力显得如此微不足道。河东的溃败,北宋的覆亡,为国家战斗十数载的田成将何去何从?看似面临选择的田成,其实并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随同溃兵一路向东寻找赵宋的遗孤,不过是一种本能,一种对于“组织”的倚赖罢了。在重新成为赵宋的官军之后,背井离乡的田成靠着他的勇敢,一步步跻身“横列”,可是政治上的波诡云谲却让他在绍兴年间的战斗履历变得一片空白,甚至在专属于他的墓志铭中都不敢多着一字。出于恐惧,在南宋朝廷收兵权的绍兴十一年,田成很“识相”地自解军职,远离政治中心,一路向西,来到荆南府,并在此悠闲地度过了晚年。然而,表面的悠闲却并没有让他真正心安,垂死之际,一再嘱咐自己的儿子:自己这个熙秦人,不能就这样飘零在异乡,不可就地将我安葬,有条件就带我回到故乡,把我安葬在祖宗的身边,没有条件,也要让我尽可能靠近桑梓之地。一生为时代所裹挟的田成,却在临死之际异常执着,如果没有浓烈异常的故土之思,很难想象田成会如此的坚持。
在忠君体国的叙事框架之下,一群远离故土的陕西军人被塑造成转战各地、战功赫赫、国而忘家的“战神”,而在这种宏大叙事之下,却忽略了他们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正常情感。这里或许可以说,幸亏有田成,他的存在让今天的我们得以略窥彼时陕西军人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