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最佳散文奖:加拉巫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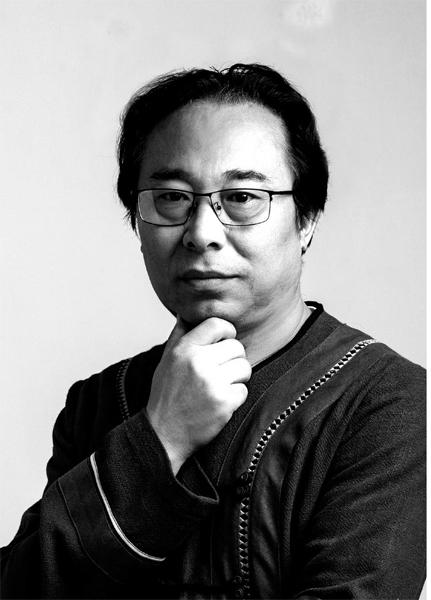
授奖辞
高寒彝区,水冷草枯,只有燕麦迎风生长。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食物,而是天,是信仰,是力量。万物同一。彝人和燕麦,血脉相连。以燕麦之线串起历史与当下,神鬼与人间,加拉巫沙的文字有着燕麦般的纯朴和倔强,亦如大地般厚重隐忍。《燕麦在上》,以一株植物的姿态,在大凉山落地生根,透过燕麦金黄的质地,让人看到一个族群的坚韧、苦难和锋芒。崇山之上,燕麦在上。高高在上。
答辞
吃五谷,生百病。不吃,病未到,人先倒。
彝人偏爱燕麦,乃地理所限。关山万里,道路险阻,土地贫瘠,能喂饱族群的,燕麦有功。古时,战事纷扰,开疆拓土,飞鹰奔犬,充饥的基本上是燕麦碾磨后的炒面。炒面吃个半饱饱,一喝泉水正好好。只消半碗,饱腹感让人舒坦。
在我的母语里,因方言差异,这款饭食多名:“索沫”“哈什”“霍沫”等等,指的都是它。它比晚來的玉米、洋芋、胡豆古老得多。后来者,借的是谐音,一听没啥文化含量。
因偏爱而敬重,因敬重而通达生死。我的族群可能受过贫穷的启示,居然将这款饭食约定成了民俗。譬如,襁褓中的婴儿第一次见天,须调和一碗炒面,在他(她)的唇边沾那么一小点;小儿走亲戚,要背炒面尽孝心;固有一死的那天,灵前要祭祀炒面……再譬如,没人稀罕一枚鸡蛋,可鸡蛋与炒面装在同一袋子里时,鸡蛋的礼仪价值倍增,不再是枚单纯的蛋。类似混江湖,看你跟着哪个混,跟对了,随风随水;跟错了,处处受挫……炒面统领了彝人的所有饭食,它既是彝人物质的生死,精神的来去,能通达生活的任意角落,是彼此心灵的文化依赖。
一个族群不一定天天饮食炒面,但炒面的母体——燕麦必须生长在这个族群的精神疆域里。崇山之下,彝人聚集,抬头仰望。在道德的认知里,彝人放下过所有,却唯独不能放下不负苍天的燕麦。
我该尽我所力,写篇关于燕麦的文章。苍天在上,《燕麦在上》。
《滇池》是我的苍天,让我生起写作的信心;燕麦亦是我的苍天,喂饱了我的肉身。
我有燕麦,滇池有水。这水非同凡响,是云贵高原的圣洁之水,高洁之水。
苍天恩宠,雨露滋润,树木就有念想,多想长成一棵绿盖如阴的大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