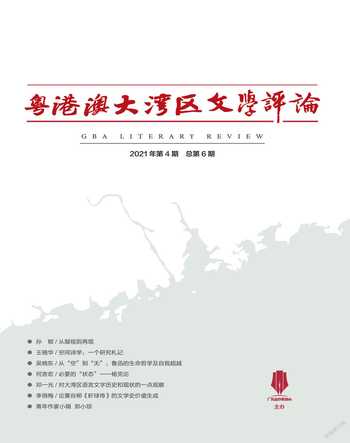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文艺批评的当代化发展
李艳丰
摘要:构建中国化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和批评范式,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经典化与当代化发展,应始终坚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根出发,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创生。应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将其贯注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之中。应立足马魂、中体、西用的原则来建设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实践原则,形成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有传统底蕴又有现代精神的文艺批评话语形态。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当代化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虽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也面临诸多亟待突破和解决的问题。比如,随着消费主义文化发展,低俗的红包式、人情式批评层出不穷,“去批评化”的吹捧式批評,唯西方批评理论话语马首是瞻的文艺批评屡见不鲜。何为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批评?俄国文艺批评家普希金指出:“批评是揭示文学艺术作品的美和缺点的科学。它是以充分理解艺术家或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所遵循的规则、深刻研究典范的作品和积极观察当代突出的现象为基础的。”[1]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文艺的美学与史学之双重标准出发,强调文艺的现实性、艺术性、人民性等多重属性。习近平认为,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2]。可见,文艺批评应通过批评的方式去发掘文艺的价值,进而推动文艺实践的健康发展。如何建构中国化的文艺批评话语体系和批评范式?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地位;要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根之中,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精神、文艺批评话语的辩证融合。唯有如此,才能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摆脱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范式的专断与中国文艺批评的失语问题,真正实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民族性与本土性建构。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作为一种外来的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思想,经过了百年的中国化与当代化发展进程,已经逐渐与中国本土的历史意识、文化心理、审美价值和文艺实践相融合,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的中国化,一方面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现代性发展,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民族性建构,即通过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来接续传统,进而实现中华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资源的现代转化。在此基础上,融合多元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构建本土化、民族化的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体系。要想充分实现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民族化,首先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论与批评话语以及中华美学精神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指导思想,关键就在于它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理论家在不断总结人类优秀文艺遗产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文艺实践创造出来的科学理论,凝聚着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文艺实践、艺术规律与审美意识的真理性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文艺问题时虽然未曾涉及中国传统文艺,但他们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理论出发对社会历史结构和人性精神的思考,使他们的美学理论与文艺思想在知识生产上表现出普遍的求真、求善与求美的历史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来理解人类文化的发展。唯物史观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过去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3]唯物史观“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4]。正是从历史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在反思文艺属性、美学价值与艺术标准等问题时,能始终立足人类优秀文艺实践传统进行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知识生产,在审美、人文与历史的多重维度下构建文艺理论与批评的标准。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艺术起源和艺术感觉的生成时,认为艺术起源于劳动,艺术感觉源于自然的人化,“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这意味着,人类的文艺经验、艺术感觉、美的规律和审美意识乃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淀而成,必须将文艺始终置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之中,在对传统的观照中发掘文艺创作与欣赏的审美规律。马克思在论述文艺的人学属性时,并没有对文艺作抽象的人道主义分析,而是始终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理论视域出发去研究作家、诗人的人学观和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人文内涵。对于传统的文艺作品,马克思强调从历史视域出发,在具体的文化习俗和历史化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与伦理结构之中对其展开美学的分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知识生产逻辑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们对传统文艺的尊重,这也警示我们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思想地基来对待传统文艺。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有艺术观念与审美实践的共通性,都是针对人类历史上优秀文艺作品所展开的社会历史思考以及哲学、伦理和美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有诸多可以融通的地方,可以通过对话、互文阐释的方式,使其在话语交往的历史与逻辑中达成理论话语与批评范式的统一。中国传统文论中关于文艺经世致用、因文明道、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社会历史批评就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文艺作品时,十分强调文艺审美形式中所包蕴的社会历史内容。文艺来源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原则,意味着文艺作品本质上是对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但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文艺并不是客观呈现生活本然面貌的镜子,真正进步的文艺既能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同时也能烛照出艺术家进步的历史理性精神和艺术审美理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主张因文明道、文以载道,只不过马克思主义所谓的“道”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道”,是为人民求解放、求自由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诉求。我们要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歌功颂德、劝百讽一、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政统的“载道”文艺,并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认识论和社会历史批评来对“文以载道”理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总之,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和审美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论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二者的辩证融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典文艺思想给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化提供理论与方法的指导,为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范式的民族性建构提供与时俱进的理论意识与话语内涵。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文艺批评史的写作受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与辩证法的影响,开始逐步摆脱传统文论那种诗文评形式以及考据式整理国故的研究范式,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来书写文学史,比如像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谭丕谟的《中国文学史纲》,吴文祺的《新文学概要》等,均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当时接受的主要是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运用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囫囵吞枣、机械套用的教条主义嫌疑。典型如巴人的《文学读本》,其纲要与内容基本上来自苏联维诺格拉多夫的《新文学教程》。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和机械运用,既不能有效激活传统,也难以推动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民族化、现代化转型。新时期以来,随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论研究的现代化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建设的民族化的多头并进,文艺理论界也开始反思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文艺思想来推动中国文论话语的民族性建构问题。王元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曾指出:“研究中国文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是对中国文论的整理和继承,另一方面是有助于我们考虑怎样建设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5]朱立元先生多次撰文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民族化路径,提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观点对中国传统美学、文艺理论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总结”[6]。在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范式的建构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并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来对接古代文论话语和审美精神,真正推动传统文论与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与民族化建构的历史进程。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美学精神
构建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美学精神,除了要借鉴和吸收世界多元审美文化之外,还要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之中发掘本土化、民族化的审美意识,不断激活传统美学精神,有选择性地继承和转化传统文化中的中华美学精神,使之在当代文艺创作与批评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要在继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来实现传统审美精神的“灵根再植”。要历史、辩证地看待中华美学精神,通过古今对接、古为今用的方式激活美学传统,并使之融入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话语实践之中。唯有不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和养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美学精神,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民族化建构。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弘扬和而不同的中华传统美学精神。“和而不同”出自《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和而不同的意思是不同事物相互聚合、多样统一。《礼记·中庸》言:“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回望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发现,和而不同是人文世界交错和合的文化理想,從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到儒、道、释三家思想在漫长历史中的互渗融合,无不呈现出和而不同、多元宽容的文化精神。刘勰的《文心雕龙》可以说是文化和合的典型代表,“原道”以儒家之道为主,“又兼采道家和其他各家”,崇尚自然取自于道家,《论说》中的崇有贵无、“般若绝境”思想又源自佛家。[7]和而不同是文艺创作与批评的审美组织原则。《文心雕龙·附会》言:“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也。”[8]童庆炳认为刘勰“杂而不越”的思想蕴含着“和而不同”的文艺创作理念。[9]孙过庭《书谱》言:“违而不犯,和而不同”,将和而不同视为书法创作的根本美学原则。正是因为有了和而不同的文化原则与美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融合创生,也才能形成灿烂辉煌的中华美学精神。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继承和弘扬和而不同的美学精神,尊重文艺创作、批评与接受的多元性与差异性,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原则,大胆借鉴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优秀的文艺批评思想与美学资源,以“驱万途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的和合之力,推动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理论与实践的繁荣发展。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弘扬“以美启真”的传统美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追求至真、至诚的审美精神,在漫长的文艺审美实践中形成了“以美启真”的美学传统。庄子言:“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10]荀子在论音乐时指出:“唯乐不可以为伪”,认为音乐是人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不可以虚伪造作。钟嵘在《诗品·序》中批判齐梁时代的文风:“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谨,伤其真美。”[11]提出“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以及自然英旨的思想,[12]强调诗歌创作应追求“真美”,注重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表达自然之真实。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真”并非西方认识论哲学中的真理之“真”,而是偏向于情理的真实,强调人之精神与情感的本真性呈现。宋人沈括曾在《梦溪笔谈·讥谑》中对杜甫诗歌《古柏行》中的诗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作如是批评:“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此亦文章之病也。”[13]沈括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在于他将审美等同于认识,未能领悟到诗歌艺术“以美启真”的美学精神。范温《潜溪诗眼》云:“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丈’……此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大也。”[14]认为诗人通过夸张的手法,既形容古柏之大,又表现出诗人激昂壮阔的心情,虚夸的艺术审美形式中内蕴着诗人的情理之真。纵观中华民族的传统艺术与诗学批评,我们可以发现,中华传统审美中的“求真”,并非西方认识论哲学所确立的逻辑之真,而是蕴藉着天人合一、生生相易、道法自然的存在之真与诗意之真。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继承和弘扬“以美启真”的传统美学精神,立足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美学与史学相统一的方法论立场,既注重科学性,又注重人文性,既强调逻辑性的理性之真,也追求人文世界的审美之真。要在文艺批评中充分实现理性求真之逻辑性与“以美启真”之人文性的辩证融合。唯有如此,才能激活传统批评的美学因子,让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走上理性与感性并举、逻辑与诗性交融的审美批评之路。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弘扬传统现实主义文艺美学精神。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蕴含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突出表现在文艺创作上的“感物”论、文以载道论和以“怨刺”说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感物说最早见于《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15]刘勰言:“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16]钟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17]白居易言:“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18]感物说认为自然环境与社会时代的更替变化影响着创作主体的精神情感以及文学艺术的创作与审美风格,在艺术创作论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精神。文以载道说强调文艺对政治的反映以及对社会的教化功能,从孔子的诗教观,到荀子的明道说,再到刘勰的因文明道思想、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等,形成了“文以载道”的传统美学精神。受封建政治文化与道德伦理等方面的影响,传统的文以载道论表现出诸多理论局限,比如过于追求美政的意识形态目的,提倡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观等。当代中国文论应弘扬文以载道的批评范式,用文艺昌明、贯注、弘扬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之道。“怨刺”说发端于《诗经》:“维是褊心,是以为刺。”(《魏风·葛履》)“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孔子《论语·阳货》提出“诗可以怨”,认为诗歌可以怨刺政治,但又强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与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观。《毛诗序》言“上以风化下,下以风讽上”,肯定文艺的教化功能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白居易《与元九书》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9]提倡讽喻诗,主张“惟歌生病民”(《寄唐生》)、“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认为诗歌应反映国事民瘼。苏轼在《凫绎先生文集序》中赞颜太初诗文“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20]怨刺传统注重文艺的批判性功能与对民生疾苦的人文关怀,表现出中华传统美学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文情怀。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充分尊重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现实主义美学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不断汲取传统现实主义美学精神中的唯物主义思想、朴素的人文主义情怀与批判意识,努力实现传统现实主义美学精神的当代转化与创造性发展。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弘扬传统文论中雄浑、豪放、劲健的崇高美学精神。中国传统美学和文艺理论中虽然没有崇高的美学范畴,但却有与崇高类似和相近的美学精神,比如大、风骨、刚健、雄浑、豪放等。《周易》有言:“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孟子》进一步提出“大”的概念,强调德性与伦理在人性中的崇高表现。《老子》《庄子》等则将“大”视为表现道无穷无尽、阴阳相济的宇宙意识,其主要特征是时间与空间上的无限性,以及人在追求这种无限性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人性精神状态。中国传统文艺审美实践可以说是融合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形成了许多具有中华民族审美特色、表现中华崇高美学精神的诸多概念与话语。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详细论述了“风骨”这一重要的美学范畴,他认为真正的好文章乃是“文明以健”“刚健既实”“风清骨俊、篇体光滑”。所謂“风骨”,就是既要有情志的刚健充实,又要有语言文辞与形式的端庄正直。谢赫《古画品录》谈绘画之六法,其二为“骨法”,称曹不兴画“观其风骨,名岂虚哉!”钟嵘《诗品》言:“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强调诗的“风骨之力”。陈子昂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倡汉魏风骨,认为《咏孤桐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殷璠《河岳英灵集》评陶翰云:“既多兴象,复备风骨”,[21]评高适云:“多胸臆语,兼有风骨”。[22]司空图《诗品》中有“雄浑”“劲健”“豪放”三品,雄浑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荒荒油云,寥寥长风”;劲健者,“喻彼行健,是谓存雄”;豪放者,“天风浪浪,海山苍苍”。严羽《答吴景仙书》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23]沈德潜评杜甫《登楼》诗“气象雄浑,笼盖宇宙”;胡本渊《唐诗近体》言杜甫诗“律法甚细,隐衷极厚,不独以雄浑高阔陵轹千古”。均强调诗文雄浑劲健之风格。中国传统诗文评中的风骨、雄浑、劲健、豪放等概念,蕴藉着中华民族追求至善的道德伦理、崇高的人格力量、刚健的审美理想、敢为天下先的主体意识与英雄主义精神。这种融会在传统审美文化中的崇高美学精神,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重要文化精神力量。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借鉴和弘扬传统文艺批评话语中的崇高美学精神,既要注重发掘具有崇高审美精神的文艺作品,塑造崇高的人文价值与时代精神,又要在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理路中贯注风骨、雄浑、劲健与豪迈之力,让文艺批评话语表现出新时代的崇高精神,形成激越而崇高的批评风格。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充分借鉴和弘扬通变创新的中华传统美学精神。通变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命题,也是文艺创作与批评中的核心概念。《周易·系辞》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生生之谓易”等,强调天地万物之间的会通与变化之道。具体到文艺方面,则表现为文艺创作与批评话语的沿革因创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具体分析了沿革因创、古今会通的辩证关系,提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认为通变的真正意义在于依据时代的变化而推动文艺的变通发展:“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承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4]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唯陈言之务去”的思想。韩愈虽然提倡古文运动,但并不赞同复古与拟古,而是要求“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以古为今用的方式创造性借鉴和发展古文的长处。唐代皎然在《诗式》中言:“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滞曰变。若惟复不变,则限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诗式》卷五《复古通变体》)认为应将继承传统与变革创新结合起来,辩证理解复变之道。纵观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与批评史,虽然不时会出现“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拟古思潮,但会通变革、发展创新的文艺美学精神还是占据着主导地位。通变创新的传统美学精神将历史性传承同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发展结合起来,强调用历史与辩证的眼光看待文艺沿、革、因、创的关系,形成了富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与民族特色的通变创新观。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辩证扬弃通变创新的传统美学精神,要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辨证法思想,理性看待与分析当下的文艺审美现象。对于传统文艺批评话语,我们也要坚持会通与变革的理论立场,不断推动传统文论话语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实践原则
回首20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代性建构,其实是一个民族性逐步流失、西方化的他者现代性逐步浸入的历史化过程。王国维最早援引西方文论的批评范畴,用叔本华、尼采的“悲剧论”阐释《红楼梦》,开创了“以西释中”的文艺批评范式。陈寅恪曾言王国维诗学研究的路径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25]。这种以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为参照系,进而通过比较、借鉴来发展中国文论的思路,成为文艺理论与批评界的普遍共识。西方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在中国当代文艺场的强势介入,虽然拓展了文艺理论的知识谱系与话语边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的现代性进程,但也导致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历史性断裂,以及中国文论民族性、本土性意识的相对缺席。西方文论话语的权力压抑与理论范式的主导,让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界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合法性危机与焦虑意识。20世纪90年代文艺理论与批评界的“失语症”讨论与新世纪以来的“强制阐释”论争,可谓是这种文化合法性危机与焦虑意识的典型表征。曹顺庆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失语症,其病根在于传统文化的巨大断裂,在于长期而持久的文化偏激心态和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26]“强制阐释”论虽以批判西方文论的强行征用理论、主观预设、脱离文本等病症为主,但其话语背后却有着反抗西方文论霸权与构建民族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的理论自觉。建设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应走出西方文论话语霸权与民族文论虚无主义的话语陷阱,重新回归中华传统本根与当代文化现实土壤,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指导之下,充分实现传统文论、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西方文艺思想的辩证融合,形成既具民族性又具世界性的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原则。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话语建设应抛弃唯西学马首是瞻的理论偏至,坚持中西文论话语互文融通、交往互鉴的实践原则。曹顺庆认为:“西方文论的中国化首先强调以中国文论话语、中国学术规则为主,将西方文论化为中国的血肉。而骨骼必须是我们的,必须以中国学术规则来改造西方文论。是中国文论化西方,而不是西方文论化中国。”[27]强调回到中国文化与文论的本根来理解、接受与化用西方文论话语。顾祖钊指出,中西融合的实质不是引进西方文论与简单化用,而是综合创新,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指导下实现的文艺理论的中西融合与综合创造。[28]中西文论与批评话语的互文融通、交往互鉴,一方面是大胆引进各种西方文论话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其进行创造性化用,真正实现中国文论的民族性话语言说方式与文化审美精神同西方文论话语的综合;另一方面就是要超越中国文论话语狭隘的民族化发展路径,在比较鉴别、互文融通中实现民族文论向世界文论话语的转化。刘若愚曾指出其撰写《中国文学理论》之目的“在于提出渊源于悠久而大体上独立发展的中国批评思想传统的各种文学理论,使他们能够与来自其他传统的理论比较,而有助达到一个最后可能的世界性文学理论。”[29]刘若愚以西方理论重构中国传统文论思想的逻辑体系和话语形态,虽有“以西释中”之嫌,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思想的西化阐释,又确实推动了中国传统文论的跨语际、跨文化交流和融通,如詹杭伦所言,刘若愚出于语际之间批评家的位置,“站在发现和建构世界文学理论的角度上”改造艾布拉姆斯的艺术四要素理论来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体系,[30]为中国文论的世界化提供了可资参照的路径。总之,我们既要让西方文论走进来,也要让中国文论走出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西文论话语的交往融通与切磋互鉴,共同推动世界文论话语的总体性建构。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继续坚持传统文论话语和批评范式的现代转换,努力推动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辩证融合。我们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对古代文论中的概念、范畴、运思方式、话语体系及其所映照的民族文化心理进行客观化、具体化与历史化。要用现代的眼光去烛照传统文论,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出发,建构传统文论的思辨性、逻辑性与系统性,实现传统文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要打通古今和中西话语的壁垒与界域,实现古今中西文论话语的比较研究与对话研究,要在恪守中国古代文论的本土性、民族性与异质性的前提之下,实现古今与中西文论话语的融会贯通。要赋予古代文论话语以新的文化语义和时代美学精神,使其能够介入到当代文艺现实之中,成为当代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可资借鉴的话语资源。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与文艺批评实践要有意识地发掘传统文论与批评思想的当代性内涵,在文艺审美鉴赏与文艺批评的话语阐释中不断激活传统文论话语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接续传统文脉、弘扬中华美学精神。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应充分发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理论与传统文论中的批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在评价拉萨尔《济金根》时,均指出了作品所具有的艺术和美学方面的缺陷。如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批判了《济金根》的不足,如形式上应将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艺术冲突缺少悲剧性,“最大的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在人物个性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色”等等。[31]列宁在论述托尔斯泰时,一方面肯定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另一方面又批判托尔斯泰文学中的“托尔斯泰主义”与对恶不抵抗的思想。除了马克思主义經典文艺思想中的批评精神以外,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美刺风戒、“歌诗合为事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也应在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中得到贯注与弘扬。如果没有甄别真假、针砭现实、讽谏丑恶的批评勇气,文艺批评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习近平对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界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认为:“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真正的文艺批评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32]。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要想真正发挥引领文艺精品创作、塑造时代文艺审美风尚、培育积极健康艺术氛围、提升大众审美文化品位等作用,就必须借鉴和弘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批评精神,充分发挥文艺批评家的才识胆力,唯有如此,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才能真正生成介入历史与现实文艺审美活动的精神力量,才能推动当代文艺创作和文化软实力的发展。
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要始终坚持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33]。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在评论作家作品时,始终坚持历史的原则和标准。所谓历史的标准,一方面是要从唯物史观的层面反思作家的历史意识和作品所表现的历史内容,另一方面则要运用正确的历史观对作家作品的历史局限性展开理性的分析与批判。当代中国文艺批评要始终坚持求真的历史理性,对虚无历史、宣扬唯心史观的文艺作品要不遗余力地展开批评,要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要在与时俱进的历史化进程中不断推进文艺创作的历史发展与文艺批评范式的创新变革。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应坚持“人民”的观点与原则。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均强调文艺批评的“人民性”原则,列宁甚至直接指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它必须在群众中间唤起艺术家,并使他们得到发展。”[34]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在贯彻和推动人民性话语的问题上,不仅需要在创作导向上坚持“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的方向,更需要在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情感向度、文艺的现实功能、文艺的评价标准等方面深化人民性话语的内涵。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应坚持“艺术的”“美学的”原则。艺术和美学的原则强调文艺对真、善与美的审美价值追求以及文艺自身的形式法则。文艺作为一种审美的艺术形式,要始终将美的发现、创作与审美精神的传承弘扬作为其终极目的,要以美的艺术形式来实现对真、善与美的价值追求。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实践应以文艺作品的艺术性与审美性为出发点,坚持回到文本场域的审美批评立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与历史相结合、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综合性批评方法,借鉴和弘扬传统文论中的感悟式与诗化批评范式,形成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既有传统意味又有现代精神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与话语形态。
[注释]
[1]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编:《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下),春风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245页。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0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4页。
[5]《“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建立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座谈纪要》,《文史哲》,1983年第1期。
[6]朱立元:《寻找基本观念上的契合点——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民族化的一点思考》,《复旦学报》,1990年第6期。
[7][8][16][2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页、第378页、第414页、第276页。
[9]童庆炳:《“杂而不越”的文化蕴含》,《文艺研究》,2007年第1期。
[10]《庄子》,王先谦集解,方勇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22—323页。
[11][12][17]钟嵘:《诗品》,周振甫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4页、第28页、第15页。
[13]沈括:《梦溪笔谈·讥谑》,施适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50页。
[14]范温:《潜溪诗眼》,见郭绍虞《宋诗话辑佚》(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22页。
[15]《礼记·乐记》,崔高维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18][19][20][23]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10页、第98页、第272页、第430页。
[21][22]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22页、第180页。
[25]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9页。
[26]曹顺庆:《文论失语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27]曹顺庆、邹涛:《从“失语症”到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8]顾祖钊:《中西文论融合与中国文论建设》,《文艺理论与批评》,2005年第2期。
[29][美]劉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版,第3—4页。
[30]詹杭伦:《刘若愚:融合中西诗学之路》,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
[32][33]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9页、第30页。
[34]《列宁论文学与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5页。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艺思想中国化当代化研究”(批准号17ZDA269)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