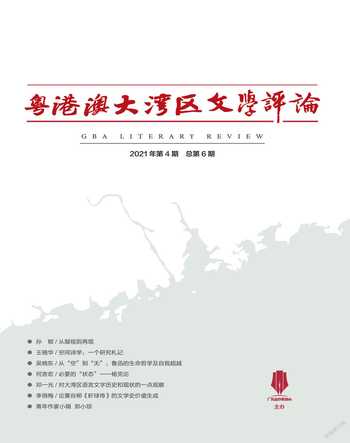左翼导向与市民经验的融合
李俏梅
摘要:《虾球传》是1940年代后期黄谷柳在香港左翼文坛的导引下,调动自己深厚复杂的生活经验写就的一部杰作。它开启了左翼文艺与市民文艺相结合的新路;实现了通俗传奇与骨子里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结合;它的地方风俗画式的写作亦是“左翼——革命文学”的重要遗产,给后来的写作者提供了借鉴。这一文学史价值的生成,一方面有赖于他的个人经验和文学观念,另一方面他既亲近左翼但又尚不属于左翼体系的“中间身份”也让他获得了文学书写的独特视角,从而完成了创作上的综合。《虾球传》是黄谷柳在恰当的时间、地点,顺应文学与历史机缘的结果,具有不可复制性。
关键词:《虾球传》;左翼导向;个人经验;“中间身份”
黄谷柳是岭南文学史上声名卓著的小说家,在香港文学史、岭南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中,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岭南地域文化特征因黄谷柳而在现代文学中得到鲜明表现,而其左翼文艺与市民文艺的结合,通俗传奇与现实精神的兼容则属于开拓性探索。黄谷柳1940年代后期创作的综合意识,和其复杂的经历及与左翼文学契合的文学观相关,但他此时还不属于左翼文学体系,这种“中间身份”让他获得理解左翼文学的独特视角。而当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人”进入新中国的歷史之后,原来的写作路径已难以延续,这一现象颇具有反思之必要。
一、香港左翼文学背景与《虾球传》的生产
黄谷柳传世的作品并不多,尽管也写过一些中短篇小说和剧本,但是一般人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虾球传》。不过,正如林岗等研究者所言,哪怕只有一部《虾球传》,也足以让黄谷柳跻身现代大作家之列。[1]笔者深以为然。黄谷柳是独特的“这一个”作家,他完成了其他作家未能完成的使命,让左翼文学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面孔。
黄谷柳对左翼文学的拓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开启了左翼文艺与市民文艺相结合的新路;第二,实现了通俗传奇与骨子里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结合;第三,地方风俗画式的写作是“左翼——革命文学”的重要遗产,给后来的写作者提供了重要借鉴。黄谷柳之所以能在文学史闪耀自身的才华,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及历史处境相关,在1940年代后期香港,或许只有黄谷柳能够完成这样的创作:是恰当的时间、地点,顺应文学与历史机缘的结果。这一点有点像柯灵眼中的张爱玲:“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2]黄谷柳的文学趣味固然与张爱玲不同,机遇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要理解黄谷柳创作的意义,可能要回到战后香港文学的历史背景。1946年之后,随着抗战结束和内战开始,香港又一次迎来了“南来作家”的高峰时期。除了司马文森、陈残云、黄秋耘、华嘉、卢荻、秦牧、于逢、易巩、黄谷柳等大批寓居广州的作家赴港之外,此时香港还聚集了从桂林、昆明、重庆、上海等地来的一大批文人,包括郭沫若、茅盾、夏衍、胡绳、冯乃超、林默涵、周而复、邵荃麟、葛琴、钟敬文、黄药眠、聂绀弩、胡风等,可以说,此时香港左翼作家阵容强大,创办或复刊的刊物较多。但是,在创作上却处于比较尴尬的状态,大部分作家创作缺乏活力,如郭沫若的《洪波曲》、茅盾的《苏联见闻》、萨空了的《两年的政治犯生活》,这些名家的创作都在回忆过去,似乎已经缺乏书写现实的能力。[3]另外就是开始大力宣扬解放区文学。然而不论是创作还是引进的解放区文学,都不受香港市民读者待见,市场依然被不入流的色情、武侠或其他通俗文学占据。左翼作家看不上这些商业文学,然而巨大的销量却无法被忽视,因为销量不仅关乎经济,更重要的是关涉到左翼文学的“文学大众化”目标的实现。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内战中优势的凸显,一个更远大的任务摆上台面,必须考虑新的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用合适的文学形式来有效影响和教育市民读者,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重要问题。
此时的香港,相对于其他地方不受战争影响,又有相当强大的左翼文学阵营,因此展开这方面的实验是可能的。左翼阵营中的有识之士比如夏衍等人,认为在香港的左翼文学应该向通俗方向转变,并希望在本地的文学工作者接触香港生活,表现此时此地。他对于这个意见的表达是如此迫切,以至于等不及他提议中的“圆桌会议”召开,不惜以戏剧家的笔法“编造”一次座谈会,实际上表达的是他自己的观感和见识,这就是发表在《华商报》1947年元旦的《回顾歉收的一年间——一个文艺工作者的座谈会》一文[4]。
然而写香港本土生活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多数左翼作家对于香港生活的体验并不深入,黄谷柳在这样的时刻“送货上门”,可谓个人与历史的双向选择。夏衍回忆,1947年的秋天,一个“陌生人”来访,一说起来才发现并不陌生,他就是十年前就已经在广州萝岗见过面的黄谷柳,当时的“黄秘书”是广州国民党部队一个校级军官。经历坎坷复杂的人生道路之后,黄谷柳又回到年轻时待过的香港,在极其穷困潦倒中以笔为业,开始写作。他将《虾球传》的第一部《春风秋雨》交给夏衍,夏衍当天晚上看完,认为“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练。”[5]夏衍决定在副刊上连载这部长篇,同时对黄谷柳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就是要按报刊上连载小说的形式,每千字左右截成一小段,每一小段要有引人注目的关节。黄谷柳欣然同意,他表示正要向香港的那些章回小说家学习。
《虾球传》第一部《春风秋雨》自1947年11月14日起在《华商报》连载,至12月28日结束;第二部《白云珠海》连载于《华商报》1948年2月8日至5月20日;第三部《山长水远》连载于《华商报》1948年8月25日至12月30日。《虾球传》连载后,在文坛引起轰动,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1948年当年,第一部《春风秋雨》开始出单行本,到1949年5月已出到第6版,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吴祖光又将它改编成电影,由香港大中华影业公司拍摄,更扩大了其影响。
黄谷柳《虾球传》的成功与左翼文坛的关注和推动是分不开的。如前所述,是夏衍首先看中了作品的价值并予以连载,并对作品的形式提出了要求。作品登载之后,左翼批评界又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对于《虾球传》的讨论,尽管不全是赞扬,但是客观上对于黄谷柳及其《虾球传》的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左翼文艺界此时花那么大功夫推介《虾球传》,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黄谷柳写出了他们所期待的作品。首先它非常富有市民气息。用茅盾的话说就是“虾球那样的流浪儿及其一群伙伴(其中有和虾球一样的扒手, 有大小‘捞家’, 走私商人和投机商人等等),正是香港小市民所熟悉的人物;虾球的倔强和自卫的机智,损人(扒窃)而又被损害被侮辱(受制于比他大的流氓) 的矛盾生活,引起了小市民的赞美与同情,而‘曲折奇离’充满着冒险的与统治阶级所谓法律和社会秩序开玩笑的故事,也满足了小市民的好奇心,让他们得到一种情感上的发泄。这一切,都是《春风秋雨》之所以能够在落后的小市民阶层获得不少读者的重要原因”[6]。而同时《虾球传》又是很“进步”的作品。即使只看第一部《春风秋雨》,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不但表现了虾球本质的善良,同时也暗示他在生活摸索中终将走上光明之路,而对于虾球周围的黑社会人物(大小捞家―流氓) 以及产生和培养这些‘捞家’的社会制度,作者是深致其憎恨的”[7]。而到了第二部《白云珠海》,虾球的目标就已经很明确,离开香港,和牛仔一起去寻找仅仅见过一面的游击队员丁大哥,他心目中“堂堂正正的人”的榜样就是丁大哥;第三部《山长水远》则写虾球经过种种艰辛挫折之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了一名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小鬼”。第四部作者并没有写出,但是题目已经拟好,叫作《日月争光》,将写虾球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的故事。
不能不说这样的内容走向亦与左翼文坛的介入紧密相关。黄谷柳在《答小读者》中说:“事实上,我从人家身上已经学到不少了。在三版《春风秋雨》和二版《白云珠海》中,可以看出我纠正错误的痕迹。”[8]而第三部写虾球投奔游击队,已经有了些概念化的说教,第四部则干脆写不下去了。这些可以说都是特定背景下《虾球传》生产的左翼介入痕迹。但是也正是在左翼文坛的介入下,黄谷柳的《虾球传》完成了将左翼文学的主题与市民文学的趣味相结合起来的历史使命,并且获得了他未曾意料的成功。可以说《虾球传》完美地解决了“将政治正确的‘正规’的内容与‘小市民’的形式衔接起来、让左翼作品在当地文化环境中生‘根’”这一道难题,完成了“夺回大众读者”“夺取黄色堡垒”[9]的艰巨任务,这是它文学史价值的第一要义。
二、个人经验与通俗传奇里的现实主义精神
尽管《虾球传》的出现使左翼文坛看到了以“进步文艺”争取小市民读者的可能,但是《虾球传》仍然并不完全符合自视正统的左翼批评家的要求。比如在讨论过程中适夷就写了多篇文章批评《虾球传》的非现实主义态度(比如太多巧合)和虾球这样的人成为革命者的真实性。他认为小说中虾球走上革命道路是非常偶然的,而在他传奇的经历中他本人也并没有发生真正脱胎换骨的变化。虾球“许多次穷途末路,却从来没有想到过用自己的劳力换饭吃……虾球的全部生活的理想,其中是没有丝毫的劳动观念的”,“抱着这种生活理想的虾球,在性格上是表现出怯懦、卑劣、动摇、矛盾”,“他缺乏一个可能获得思想觉醒和走向不屈斗争的人所必备的性格基础”[10]。 对于适夷的这种“苛评”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但左翼批评家们的确对黄谷柳过多借助旧小说的巧合技巧以及人物的阶级意识不够明确等方面颇有微词。不能不说这些左翼批评家是火眼金睛的,黄谷柳的小说确实很难完全吻合正统的革命理念。一方面他不能,他自己的思想意识还没有那个高度;另一方面,他也不愿。在懂得了一些左翼文学的道理之后,他依然为自己辩解:贴着人物和生活写,写得“恰像他们”,“从精神到行动都要贴近他们”才是最要紧的,“一方面警惕到不把他们写成进步青年,写成见女色无动于衷的清教徒,写成饥不思食渴不思饮的胃病患者,写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观念的烈士;另一方面又提防到不要‘照相式’地把他们的意识面貌原封不动地搬到纸上来。”[11]他是坚持他笔下的生活及人物是吻合他的现实观感和体验的,而这就是一种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小说对虾球及与之发生各种关系的三教九流人物的书写,对于人生、人性以及人情世故的微妙之处的体察,这些内容都是很有现实基础的,它们从黄谷柳半生阅世和阅人的经历而来,是黄谷柳血泪人生的投影和结晶,而这也恰恰是作品最有深度和价值的部分。
夏衍曾经问过黄谷柳:“你生在越南,长在云南河口,为什么能那样熟悉广东下层社会的生活?”黄谷柳回答说:“那主要是因为生活穷困,做过苦力,当过兵,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的缘故。”[12]正因为长期生活于社会的底层,干过多种营生,黄谷柳对于底层穷人的苦难有一种独到的体察。《虾球传》所写的底层人物包括工人、退伍军人、走私客、艇家、扒手、警探、马仔、妓女等。他写这些人物的生活,总是能触及最质感最细节的部分,他的笔说出的是全部黑暗沉重的生存现实,因而具有一种深刻的揭示力量。比如他写虾球。虾球在小说中的起点位置是一个卖面包的小贩。为什么是小贩而不是别的?这在黄谷柳并不是一个随意的安排。他说,在香港这个产业并不发达的殖民地社会里,像虾球这样的少年是欲做产业工人而不得的。“失掉了地的农民及其后裔没有工厂可进,他们多数变成了小贩。中国的小贩之多,已经到了震惊中外政府当局的程度”[13],所以虾球只能在船坞的大门外卖面包求活,而且还活不下去。对于做这个生意的不容易,黄谷柳寫到三点:一是有英国警察的驱赶;二是有其他小贩的低价竞争。小说写牛腩粉摊的生意胜过了虾球,因为“一毫有净粉,二三四毫有牛腩、牛杂粉。”后来白粥摊的生意又抢过了牛腩粉摊,因为“白粥以半毫起计,油条、牛脷、油香饼、松糕也是半毫一件,……工人们有一毫钱就解决早点问题了”[14]。从这些精细的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里贫富的悬殊,普通工人和市民购买力的低下。尽管这样艰难,还有属于黑社会势力之一种的“收规人”要剥削他们。“每个收规人都代表着看不见而感得到的一种可怕势力。人们都情愿每天被这些收规人拿去三毫五毫,或一元八角,买来一天的平安”[15]。黄谷柳能看到表层世界下面的“暗世界”,使他对于穷人受压迫的体察又深了一层。正因为这个社会明的暗的压迫使这些底层人走投无路了,虾球后来成为王狗仔和鳄鱼头的“马仔”,替他们走私扒窃卖命,也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事了。
复杂而坎坷的人生经历不仅使黄谷柳对于苦难有独到的体察和思考,更使他对于各色社会人物的生活、性情、心理以及人情世故的微妙之处有出色的刻画,即使是一些很次要的人物,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比如小说开头对虾球妈妈的描写。虾球妈妈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年轻时丈夫被卖了猪仔流落海外不知去向,大儿子被抓了壮丁,靠在纱厂纺纱的微薄收入养活自己和小儿子虾球。在她觉得虾球不听话的时候,她通常采取的方式是比较粗暴的打骂。小说写她有一个“老毛病”,就是“每一次打他,最初是非常凶狠,但是打了儿子几分钟,自己的手就慢慢软起来,到了最后,她就丢下手下的木棍,自己哭起来了”[16]。小说写出了一个被生活的重压折磨得既脆弱又粗粝的女人。即使是所谓的“反面”人物,小说也写得很生活化。比如写马专员。马专员一面和洪少奶在客厅调情,一面对着在里头忙碌的“鳄鱼头”洪斌大声说话:“喂,老洪,你怎么放客人坐冷板凳?我要到启德机场送朋友去了。”[17]鳄鱼头后来对马专员总结的,明明是“居心可鄙”,却又做得这么“光明磊落”,偷情做官都一样,实在让人恨得咬牙切齿。鳄鱼头也是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但小说把他写得非常真实丰满。鳄鱼头走私,偷窃,勾结官员,以不正当手段捞取大量财富,但从个人能力和心理素质上,小说一点也没贬低他。在作为幕后黑手制造的耸人听闻的窃米事件败露之后,小说写他反应的速度:他以每小时50英里的车速赶回家去,冲进房间,拿出手提皮箧,取出手枪,又迅速冲出去,顾不得下人的追问。此刻他的太太正在赛马场上赌马,他顾不得通知他的太太,“鳄鱼头的汽车比马跑得更快,他在中途换了几次汽车,兜了几个圈子,最后他下了亚娣的艇,叫九叔把艇依着省港内河航道划去。在舱里,他把他身上两杆左轮手枪连子弹皮带解下来,深长地叹了一口气”[18]。而在船行至广州水面时发现异样,一秒钟内他想出上中下三种对策,真可谓干练果敢,反应一流。总之,鳄鱼头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坏人”形象,有丰富的人性内涵。有人说黄谷柳不擅长写人物,其实是不公道的,《虾球传》有名有姓的人物不下二十余个,大多都能给人留下很深印象,显示了很好的写实功力,而写实功力的背后是丰富复杂的生活体验和对于人情世故的通达。也正因为此,评论家袁良骏先生认为很多人其实低估了《虾球传》的文学价值 :“人们在半个世纪中,大抵只把它看成一部通俗的普及读物甚至儿童文学读物,这是很不公正的。事实上,《虾球传》是一部充满传奇色彩的现实主义力作,不仅在香港小说史上,而且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都应给予足够重视。”[19]
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黄谷柳写作一以贯之的精神,传奇只是他的外表。而在1940年代后期写的其他中短篇小说中,他还涉及对一种现实的反映,那就是前国民党军队人员抗战胜利后的出路问题,如他的《王长林》《七十五根扁担》《一直落》,也包括《虾球传》中都有写到。为什么这个实际上在当时已经成了严重社会问题的问题只有黄谷柳等少数作家关注,一方面因为黄谷柳本人有过国军十年的经历,对于自己的同类在为国浴血奋战之后的出路有一种惺惺相惜的关怀;另一方面也是从左翼立场揭露国民政府的冷血和不负责任。而新中国成立之后,书写国民党退伍官兵艰难生存的题材的可能性也丧失了。这大概是导致这一题材较少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表现的原因,但黄谷柳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历史的痕迹。这种现实主义精神也使得他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严峻的环境下,也依然是重体验的。在他1957年以《接班人》为题的中篇里,内容依然是以他在教育领域的观察、采访和体验作为基础的,小说写出了1950年代教育界的一些现状和难题,以及他理想中的教师应该是什么样子,今天读来依然富有启迪意义,并不是简单的假大空文学。为了描写他心目中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他两次去朝鲜进行采访,冒着生命危险在那里待了一年零几个月,直到战争完全结束。在“文革”前他完成了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长篇小说《和平哨兵》,因为多处涉及对彭德怀的描写而自行焚毁[20]。彭德怀1959年即已在“庐山会议”上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头领,“文革”初期又受到残酷迫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是不写或删除这一人物,而是写了之后焚毁,个中意味,不难理解。当然我并不认为黄谷柳是一个超越时代的意识形态局限的人,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历史局限里,但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这种重观察、体验的笨功夫,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
三、“地方风俗画”及其之于“左翼——革命文学”的意义
几乎每一个阅读《虾球传》的人,都很欣赏小说的地方色彩。作为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夏衍最先称道了《春风秋雨》“鲜明的地方色彩”。即使是对《虾球传》有所批评的一些左翼作家,也肯定它在这方面的表现,认为这是小说富有魅力的地方。1980年代以后,对于《虾球传》的地方风格进行深入探讨的文章更多了。张绰在《从文化角度论黄谷柳》中评价《虾球传》“以其鲜明地方色彩的地道‘广味’,获得了被大众认同的审美效果。作品中时常映现出一幅幅四十年代省、港的市井风俗画,突出了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风土人情、世态习俗”[21]。香港文论家颜纯钩也认为“岭南社会生活、 人情风俗、 地理环境以及人伦关系、道德观念的翔实描绘,这个要素,使得他的作品浑然一体,并时而赋予他的作品的人物以独特的意义。”[22]在近期的一篇文章里,赵稀方依然称道:“《虾球传》的成功之处,主要来自其浓郁的地方色彩。《虾球传》有两个主要人物:一是虾球,二是鳄鱼头,他们俩分别代表了香港的底层和黑社会两个领域。虾球、牛仔、亚娣、六姑等人,分别向我们呈现了香港流浪儿、渔家、妓女等底层人的生活方式,鳄鱼头、马专员、洪少奶、蟹王七、王狗仔等人则向我们呈现了黑社会及上层官员的所作所为。”[23]林岗则称,“在1949年前后写作以地域色彩见长的华南作家群里,他最为讀者喜爱,拥有最广泛的读者,而且文学成就首屈一指。”[24]
《虾球传》的地方风味首先表现在对港、粤两地地理生活空间的描绘上。从大的方面来说,小说表现了粤港两地连成一体,易出易入的地形地貌。香港在鸦片战争前原本就是广东宝安的一部分,因此无论在地理还是语言、饮食、风习上都是一体的,香港英属以后,在文化上有了更多西化和殖民化的特点,但从地理上来说依然是一体的,并且直到40年代,两地之间仍然可以自由往来。无论是陆路(如虾球跨过狮子山),还是水路(如鳄鱼头乘小艇逃离香港警方的追捕来到广州黄埔),都十分近便。从小说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到在粤港两地生活多年的黄谷柳,不管是对两地的水陆交通线路,还是香港和广州的城市内部地理都十分熟悉,把黄谷柳所写的关于修顿球场、佐敦道、红磡码头、广州沙溪、鱼嘴、多宝路、黄沙码头、沙河顶、新亚饭店等画面联系起来,基本上可以复原一副粤港两地40年代的历史地图。
《虾球传》地方风味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在于黄谷柳笔下的人物和社会生活世相的描写。比如他写香港的修顿球场,说那是“一个奇异的世界”,一到夜晚,各种各样的人带着各种目的聚集到这里,“儿童、少年、壮丁、少女、少妇……难得看见一个老人。在这里,饥饿的魔鬼跟随者每一个人,追随者人堆中的失败者”[25]。药贩夫妇、扒手、警察、私娼、工人、店员、流浪者……互相窥伺,互为食饵。这是一幅光怪陆离的殖民地底层夜生活图画,非常生动真切。写抗战胜利后的广州,作者写到灰暗的市容,腐臭的河水,像沙丁鱼一样被卡车一车车拖去草草掩埋的死尸,观音山上剪径的土匪,成群的流浪难童,沙溪的赌窟,被强拉的壮丁以及他们的逃亡,退伍后生活无着铤而走险的国民党官兵,和官府勾结的黑恶势力以及贪污腐败的官场,简直是一副四40年代广州和珠三角一带的“浮世绘”。
第三个方面是语言的粤味。总的来说,黄谷柳在小说中的粤语使用还是比较节制的,可说是在主体普通话的前提下恰如其分地夹杂了粤方言,将粤文化的特征和粤语的精华很巧妙地表现出来了。比如人物的命名就很有粤方言色彩。广州人喜欢在人名单字前加“阿”(亚)表示亲切,像“亚娣”“亚喜”“亚佳”“亚笑”“亚炳”等人名即来源于此。人名之外,小说也常常恰到好处地使用一些独特的粤语词汇,如称“钱”为“银纸”,把“谋生”叫作“捞世界”,一起干某种营生叫作“同捞同煲”,“敲诈勒索”叫作“勒收行水”,形容一个人机灵叫“眉精眼企”,要人机智一点叫作“醒定一点”,等等。他也在小说中引用《咸水歌》《粤讴》等粤语民间文学,人物的对话尤其生活化,这些语言上的特色传递了粤地生活气息,甚至使非粤语圈的读者感受到了粤语的独特表现力。而人物内在精神中的粤文化气息也很明显,比如“捞世界”“捞番大世界”就是很多粤人普遍共享的价值观念,在虾球成长的早期,他也是认同这样的观念的,这和环境有关。他拿条火腿回去,屋里的人都称赞“虾球也捞起世界来了!”
近代以来,岭南小说开始兴起,其中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岭南地理民俗,但是像《虾球传》这样将香港、广州及珠三角地区的语言、地理、风俗、人情世态立体地、动态地、原汁原味地端出的实在不多见,可以说是黄谷柳强化了岭南文学的地域文化特色,使岭南文化活色生香地呈现在纸上。而这部小说的“地方风俗画”特征也直接启示了后来的岭南“左翼——革命文学”,欧阳山的《三家巷》,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等革命文学的代表作,无一不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挥洒地方文化书写的魅力,使得这些作品即使是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也依然富有魅力。
余论:《虾球传》的不可再生产性
《虾球传》是黄谷柳在战后香港左翼文化背景下,在左翼文坛的导引下,调动自己深厚复杂的生活经验写就的一部杰作,它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其内容和风格游走于左翼与市民之间,通俗与现实之间,热点与边缘之间。在1940年代后期的香港恐怕也只有黄谷柳这样有复杂经历但又受到左翼影响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而这也是黄谷柳特殊人生阶段的作品,在此之前或之后都难以写出,所以《虾球传》是“天时、地利、人缘”诸因素共同结出的文学之果,具有不可复制性。
首先,不是所有的左翼作家都能写出有市民味的、受市民追捧的文学作品的。这里一方面是生活经验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思想意识的问题。从思想意识的角度看,我们仅仅从1948年间左翼作家阵营对黄谷柳的褒扬及批评中就可以看出问题。以茅盾对《虾球传》的肯定为例:“满足了小市民的好奇心”“在落后的小市民中拥有市场”这类的措辞,字里行间看得出茅盾对于“小市民阶层”其实是有一种倨傲的态度的。这并不是个别现象,不少左翼批评家都流露出这样的态度,因为新文学骨子里是排斥小市民趣味的。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即使是左翼作家的褒奖也透露出他们对于市民文艺过于倨傲和功利化的态度,他们其实看不起“小市民”的。“抱着这样与本地市民阶层相对立、与本地流行文化相对抗的固执而封闭的想法,怎么可能真正有效地融入香港本土语境? 这也同样解释了他们虽然一再提倡走大众化、通俗化道路,但取得的成绩仍旧寥寥可数的原因。就這个层面而论,在内容与形式上都充分照顾到本地特点、‘俯就’于市民读者的《虾球传》,或许也只有当时还未被纳入党组织体制内、尚未成为文化干部、还算是“小市民”一员的黄谷柳才可以为之。”[26]这的确是端的之见,正因为黄谷柳此时并非左翼文学阵营成员,思想观念还没有完全正统化标准化,才可能写出被香港市民喜闻乐见的作品。而以批评态度而言,楼栖对于《虾球传》的苛评或许正说明了他思想的过于僵化,他对虾球“缺乏劳动观念”的否定,他对于小说凭借“偶然”“巧合”手段推动情节的意识形态解读,都说明至少像楼栖这样的作家是无法写出《虾球传》这类作品的。因为这样一来,《虾球传》中的传奇性和娱乐性成分全得去掉,《虾球传》就不是《虾球传》了,也就很难以赢得市民的喜欢了。
第二,从经验的一面看,多数左翼作家在港生活时间不长,对香港市民生活体察不深,缺乏文学感知所必须的基本经验,而黄谷柳则不同,他于1927年来到香港,从事过各种谋生,对底层生活有很深的体验,在香港实在难以维持生活之后,才在亲戚介绍下到广州燕塘陈济棠的部队当兵,并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在庐山暑期训练班集训一周,亲身听取过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报告和讲课。“卢沟桥事变”后即赴抗战前线,是亲历 “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1943年去重庆,1944年任三青团总团宣传处《文化新闻周刊》的总编辑时,因转载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材料被张治中发觉后于1944年12月撤职。抗战胜利后,黄谷柳接任正中书局广州分局业务主任一职,因预感到内战的不可避免,很快辞职并于1946年3月再次回到香港。回到香港,貌似回到原点,但其中过程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对于丰富作品的现实内涵是有益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和左翼人士建立了很深的渊源,他的写作观念与左翼文学观、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亦多有相通之处。比如他说:“那些能够随心所欲控制文字这表现工具的人,大多都是受过高度文化教养的人。他们写出来的东西,即使是小说吧,多数作品都仿佛‘天书’似的难懂。读小说而有读‘天书’之感,作者和读者双方都很不幸。”[27]他出身底层,所受教育程度并不高,所以他天然地认同了文学的“大众化”理想。但此时的黄谷柳又算不上真正的左翼人士,这种“中间身份”使得作品又有许多原生态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确是一个“香港的赵树理”。
而从另一方面看,黄谷柳也只有在这个时段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黄谷柳接触夏衍等左翼人士后,思想迅速发生变化,并于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主动请缨去“十万大山”打游击,迎接南下大军。1950年代初在南方日报社任职记者,此时虽然也写作,但是由于整个文学环境的改变导致写作也发生相应变化。夏衍曾经问起他为什么不把《虾球传》写完?他说:“很奇怪,对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兴趣了。我在朝鲜战场上,看到过不少新的英雄人物,我想通过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28]所以这个时候,他要写的是新时代的“新人”,为了写这部表现新人的巨作投入了数十年的时间,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29]随着1960年代政治气氛变得更加诡谲,出于种种考虑,他焚毁了完成的小说,并留下遗书表明自己的政治清白。当他1970年代末准备重写《和平哨兵》时,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夺去了他的生命。可以看出,进入1950年代以后,黄谷柳所有精力都用于创作“新人”题材的巨作,与原来的《虾球传》不再属于同一风格和体系,尽管在他小说的规划中有个广东籍的战士名叫“夏球”——可以看成“虾球”在新时代的形象延续,但是“虾球”的血脉已中断,永远地留在那个特定的时空之中。
[注释]
[1][24]林岗、张澜:《从黄谷柳的文学足迹看“新人困惑”——读〈黄谷柳朝鲜战地摄影日记〉》,《当代文坛》,2020年第4期。
[2] 柯灵:《遥寄张爱玲》,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附录,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27页。
[3][23]赵稀方:《地方性的分歧——论〈虾球传与经纪日记〉》,《文艺争鸣》,2020年第1期。
[4] 参看周双全:《大陆作家在香港(1945—1949)》,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学位论文, 第31页。参看吕剑:《香港华商报副刊琐忆》,《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2期。
[5][12][28]夏衍:《忆谷柳——重印〈虾球传〉代序》,《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6] [7]茅盾:《关于〈虾球传〉》,初次发表于《文艺报》第4期(1949年),本文引自乐黛云主编:《茅盾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04页、第305页。
[8] [11][13]黄谷柳:《答〈小读者〉》,香港《文汇报》,1948年9月10日,此文收录于《干妈》,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28—231页。
[9][26]谢力哲:《“表现香港”“夺回读者大众”与“夺取黄色堡垒”——论〈虾球传〉之于旅港左翼文坛的意义》,《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8第4期。
[10] 适夷:《虾球是怎样一个人》,香港《青年知识》第36期,1948年8月1日。
[14][15][16][17][18][25]黄谷柳:《虾球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第6页、第4页、第25页、第50页、第16页。
[19] 袁良骏:《重读〈虾球传〉》,《冀东学刊》,1997年第4期。
[20] 黄茵:《再版后记》,见黄谷柳:《虾球传》附录,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21] 張绰:《从文化视角论黄谷柳》,《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
[22] 颜纯钩:《谈〈虾球传〉的艺术特色》,《香港文学》,1986 年第13 期。
[27] 黄谷柳:《我写〈虾球传〉的感想》,香港《大公报》,1949年2月21日。此文收录于《干妈》,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页。
[29] 黄谷柳不顾安危在朝鲜待了一年半时间,记录了一整本日记和照片,19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作为“从旧垒中来”的人遭受沉重的政治压力,但写作的热情一直没有衰落,“文革”风暴之前已经写完30多万字。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