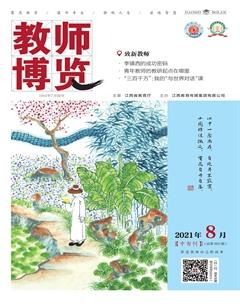人间地耳
项丽敏

惊蛰前夜,一场雨水,后园的地耳苏醒过来。
苏醒过来的地耳紧贴地面,静悄悄地,支棱着耳朵,倾听雨脚落地的声音,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忽而急促热烈,忽而缓慢轻柔,循环往复地敲击。
“嗒!”——泥土之下有了动静,一扇门被轻轻推开。紧接着,更多的门被推开,呼应着来自天空雨水的召唤。
在更深的泥土之下,根茎的吮吸声变得有力,“滋滋滋、滋滋滋”,贪婪又欢喜。在这些声音之外,还有暗流汩汩的涌动声,也来自地下——或许来自近旁的老井——那里有一孔泉眼,干涸了整个冬天,连日雨水的渗透,让它重新丰沛了起来。
老井的水满了,雨也停了。春笋顶开松软的泥土,冒出尖尖的黄脑壳。菜园的豌豆藤又爬上来一大截,就要开花。
苏醒过来的地耳到处漫游,伸向泥土的每一寸缝隙。春天的土地充满了秘密的声响,这是万物的心跳声,只有把耳朵紧贴地面,屏住呼吸,才能听到。
地耳也叫地衣、雨菌子,此外它还有个不太雅的名字——鼻涕菜。我小时候就是这么叫的。大人说,它是雷公打喷嚏时流的鼻涕。“啪!”雷公将一把鼻涕甩下来,落到地上,就长成这“漆黑麻乌”的东西。听起来真有生理的不适。不过好奇的孩子并不管这些,还是蹲下,用手去触摸。孩子的手上有一双眼睛,唯有用手触摸过,才算认识。
近看地耳并非“漆黑麻乌”,而是像海藻一样呈略微透明的黄绿色,软滑柔腻的手感,轻轻一抓就是一大把。
我人生里最早认识的野菜就是地耳。那时我大约五六岁,还没有上学,跟随母亲在她任教的乡村小学生活。离学校不远的河边有一片荒地,放学后,母亲拿着锄头去开荒种菜,我跟在后面,也帮不上什么忙,就蹲在一旁捡小石子玩。
挖好一畦地,母亲见天色还早,就说,我们讨点野菜回去吧。
母亲把挖野菜说成“讨野菜”,仿佛野菜是有人种下的,采挖它们需要取得同意——虽然看不见那个种下它们的人。
河畔到处都是野菜,母亲教我闻它们的味道,告诉我它们的名字,荠菜、苦苦菜、野蒜……但我太小,哪里分得清,在我看来,它们长得都一样。我唯一能分辨的就是鼻涕菜——地耳,唯有它长得与众不同,一旦认识了,就再也不会和别的野菜混淆。
当我认识了这种“雷公鼻涕”的野菜,发现走到哪里都能见到,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也是摔在地耳上。可能是这家伙的恶作剧,让我滑倒的吧。
地耳这东西,“讨”起来容易,洗起来却很麻烦。那么多的细碎泥沙,还有枯草的茎,藏在地耳卷起的耳蜗里,需要极大的耐心,一次一次地淘洗,吃的时候才不至于硌到牙齿。
母亲有洁癖,手脚又慢,每次洗地耳所花的时间,够别人家做一顿饭了。等母亲把加了油盐的炒地耳盛进碗里,招呼我吃饭时,我已经趴在桌子上,嘴角挂着涎水,在饥饿中睡着了。
把地耳吃进嘴里就会明白,为什么把地耳叫作鼻涕菜。那软软滑滑的口感,可真是——唯有鼻涕可比拟。
奇怪的是,这随处可得的地耳,村里却很少有人吃。有来串门的邻居——母亲让我叫她方姨,见我家饭桌上一碗黑乎乎的炒地耳,颇为惊奇地说:“老师怎么吃这个?”
“这是野菜,味道很鲜的。”
“老师是捧公家饭碗的人,还吃这鼻涕糊一样的东西,也太节省了。”
“自己种的菜还没长。”母亲说着,往我碗里拨一筷子炒地耳。
隔天方姨又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布包,搁在锅台上,说:“这个给小鬼吃,小鬼长身体的时候,光吃野菜不行。”村里人把十岁以下的小孩统称为小鬼。
解开布包,原来是鸡蛋,有十几个呢。
母亲赶忙推辞,说不要不要,哪能平白无故要你东西。
“老师你这么见外,是看不起我这个大老粗吧。”方姨嗓门大起来,有些着急上火的样子。
母亲只得收下,嘴里连连道谢。
接下来的几天,母亲就用地耳煮鸡蛋羹吃。往碗里敲进一个鸡蛋,小指在蛋壳底刮一下,让剩余的蛋清流出,加一些水,少量盐,拿筷子在碗里不停搅动,将鸡蛋搅匀。我喜欢听那搅鸡蛋的声音,“嗒嗒嗒,嗒嗒嗒”,像舞台上欢快的舞步,让人兴奋。搅好的鸡蛋浮起一层泡沫,把洗净的地耳放进去,搅匀,入锅蒸。
蒸鸡蛋的声音也是很好听的,“咕嘟咕嘟咕嘟”,光是听着这声音,就觉得又饿又幸福。鸡蛋蒸好了,母亲吩咐我“把勺子拿来”。我赶紧递去勺子,看母亲用勺子在热气弥漫的鸡蛋上划出一个“井”字,滴进几滴酱油,慢慢地,酱油晕开,汤色变红。母亲又放入几粒切碎的葱花,半勺猪油,再倒开水,一碗色泽丰富的地耳鸡蛋羹就上了桌。
此后,隔几天,当我和母亲踩着暮色从河边回来,就会看见有一把菜搁在门口。不用问,准是方姨拿来的。
就这样,母亲和方姨成了朋友。有一次,母亲偏头痛发作,起不了床,还是方姨过来照顾的,从家里做好饭端过来。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没见她爸爸来过?”方姨指着我问。
“她爸爸在外地工作,离这远得很。”
“老师你太不容易了,又要教书又要带小鬼,头疼脑热也没人晓得……”
那天我听到母亲的抽泣声,不知道是因为生病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
春天过去一半,母亲种的韭菜可以吃了,割一把,洗净,切成段,放入地耳快炒,菜出锅时,整个屋子被生猛的香气挤满。到了春末,豌豆荚也鼓起来,摘下豆荚、剥壳,把豌豆和地耳一起煮,起锅时打入蛋花,汤味清甜鲜美。
老家的后园也有地耳,初夏梅雨季,地耳长得尤其水灵,看得人“手痒眼馋”,忍不住就拿了篮子,蹲下去采撷。采得太多吃不掉,母亲就把地耳洗净,摊开在灶头,烤干,拿玻璃瓶储存起来。烤干的地耳蔫头蔫脑,吃的时候用水泡发一下,干地耳遇到水,瞬间就复活。我喜欢吃干地耳炖排骨,吸收了排骨脂肪的地耳滋味肥美,比新鲜的地耳更有嚼劲。当然,如此奢侈的吃法,是成年后才得以嘗试的。
在我成年后,母亲念叨过几次,说要我抽空陪她一起去看看方姨。“那几年多亏她关照,不能一走就忘了人家。”可年复一年,我似乎没有空闲下来的时候,慢慢地,母亲也就不再和我提这事了。
母亲也时常去后园,手里拄着拐杖,用一种静默的语言和地耳对话,又似和地耳一起,倾听那来自泥土之下秘密的声响。母亲已经很多年没有“讨”过地耳了,她的腿脚僵硬得如同老树桩子,再也不能像年轻时那样灵便地蹲下。
有一天,我蹲着“讨”地耳的时候,母亲在旁边突然说:“你还记得方姨吗?听说她得了癌症,已经过世了。”母亲后悔没有能够回到那个村子,去看看方姨。“我们欠她的人情,这辈子恐怕是还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