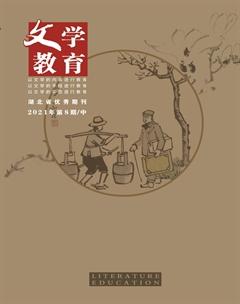论日本女性主义批评先驱驹尺喜美
邹洁 王晓丹
内容摘要:驹尺喜美是日本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之一,其代表作《魔女的逻辑》和《魔女的文学论》开创了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河。驹尺喜美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重新解读日本近现代著名作家夏目漱石和永井荷风的经典作品,揭露男权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扭曲,批判男权制度对女性的压迫。
关键词:女性主义 批评 日本
驹尺喜美是日本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之一,她的很多思想对后来的女性主义批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至今仍焕发着生命力。《魔女的逻辑》[1]和《魔女的文学论》[2]是她主要的代表性著作,开创了日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先河。她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重新解读男性作家的经典作品,批判男权制度对女性的压迫,揭露男权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扭曲。
一.驹尺喜美读夏目漱石的《行人》
在驹尺第一部专著《魔女的理论》的开头提出,男女之间的异性爱应是两性间整体性的交流和融合,以及在此基础上达到的人格的解放和升华。“爱”不仅止于性爱层面,而是双方生命力与生命力的碰撞。而在现实中,两性间却存在巨大的、难以跨越的鸿沟,深陷“爱的缺失”的情感困境。然而在近代以前,这种“爱的缺失”一直停留在实际生活体验的层面,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探讨。驹尺认为近代以来在日本文学领域,对两性间“爱的缺失”有着深切感受的第一人是夏目漱石。
驹尺读漱石的《行人》,感慨于作者由于“爱的缺失”所受伤痛之深。主人公一郎作为一名大学教授,虽然在学校倍受同事、学生的仰慕,但回到家庭却深受夫妻关系不和谐的困扰。他说:“我看到对女人的容貌心满意足的人就很羡慕,看到对女人的肉体心满意足的人也很羡慕。但无论如何,不抓住女人的靈魂即所谓精神,我是不会心满意足的。因此,我从未经历过爱情。”[3]漱石在书中指出世俗婚姻的庸俗,认为这种结合是“不负责任”和“可怕的”。即便是这种世俗婚姻,只要遵从世俗习惯和既成价值观,就能成为大众眼中的“美满家庭”。然而,一郎作为自我觉醒了的新时代知识分子,不能一味顺应这种既成的婚姻模式,对传统婚姻模式抱有怀疑和批判,认为世俗所谓的“美满婚姻”,是在男女双方对心灵的内在交流与契合没有要求的条件下达成的某种契约。一旦某一方产生了这方面的要求,所谓的“美满婚姻”面纱下的种种丑陋不堪就会暴露无疑。《行人》中一郎在婚姻关系中表现出的执拗和阴险,实际上只是想要和妻子进行内心交流欲望之切的体现。他觉得研究妻子的内心比研究学问更重要,这作为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是难能可贵的。“什么钻书本啦,抠心理学啦,我指的不是那种转弯抹角的研究。现在,在我眼前本来是个最亲爱的人,如果不研究这个人的心就坐卧不安。”[4]在漫长的封建传统里,男人关心的不是女人的内心,而是相貌和身体,女人是满足男人审美目光和性欲的存在物。
然而,将女人贬值物化的同时,男人也被切断了通往“爱”的道路。“不管嫁给什么人,出嫁后的女人都会因丈夫而变得邪恶”,一郎的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男权制度下婚姻的本质。首先漱石要表达的是一郎夫妇的婚姻悲剧,而这种悲剧并非个案。其次,在夫妻关系中,丈夫作为压迫者,妻子是被压迫者,妻子在丈夫的压抑下性格扭曲。和一个性格被扭曲了的、丧失人性活力的妻子之间,当然不会有灵魂上的交流,也不可能寻求到真正的幸福,这种认识已经接近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对男权制度下的婚姻的基本认识。漱石未必认识到两性关系背后的性别分工和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也未必对当时出现在日本的、以《青踏》为代表的妇女解放思想十分赞同。然而,《行人》这部作品从对婚姻制度下的夫妻关系这个切入口,可以说触及到了女性主义的核心。
驹尺认为漱石之所以能意识到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得益于日本当时蓬勃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漱石的门生森田草平在明治41年曾和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平塚雷鸟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风波,漱石曾多次牵涉到这场风波中。在两人殉情自杀未遂后,漱石将森田接到自己家,并鼓励他将自己的故事写成小说。明治44年雷鸟创立女性杂志《青踏》,虽无证据表明漱石读过该刊,但从双方前后交往时间,驹尺推测漱石应该受到过该刊的启发,并于明治45年开始创作小说《行人》。如果说修缮寺大患是促使他审视自我的重大契机,那么雷鸟的《青踏》运动则以更直接的方式,使他认识到两性关系的不平等。在《行人》之后的作品《路边草》中,漱石彻底分析了夫妻不和产生的原因,从丈夫的角度描写夫妻各自的利己主义,特别是批判了以社会精英自居的丈夫的自私自利。
驹尺还进一步就两性不平等关系背后的根源进行挖掘,即男人通过独占社会资源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将女性置于被支配的附庸地位;女人在社会中丧失了一切谋生的手段,不得不依附于男人生存。在这种关系中,男人将女人视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对男子而言,妻子一旦沦为日常生活的工具就变得索然无趣,从而通过买春纳妾的方式来弥补内心的空虚。到了现代,虽然已废除了一夫多妻制度,妾不过以婚外情的形式出现,在本质上并无变化。只要女性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的社会构造不变化,两性关系就不会出现本质上的变化。
二.驹尺读永井荷风的作品
另一个受到驹尺高度评价的日本近代作家是永井荷风,甚至把他的文学称为“妇女论的宝库”。驹尺站在女性主义批评的立场上,分析了永井荷风的《比本领》《阿龟竹》《梅雨前后》三部作品,认为荷风通过描写花柳界来打破既有的两性观念,揭露了现有社会秩序下的两性关系及婚姻制度的虚伪。她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进行深入的剖析:
首先,艺妓透视下的女性的独立和自由。《比本领》的女主人公驹代丧夫后回到东京新桥成为艺妓,一天在帝国剧院的走廊偶遇旧好吉冈。当年的吉冈毕业后选择留洋,两人断了联系。现在的吉冈成了一家大公司的营业课长,拥有令人羡慕的地位和财富,已经包养了名为力次的新桥一流女艺人。时隔七年再度相逢,两人之间激情重炽。吉冈提出在镰仓为驹代建一处别墅,让她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出人意料的是,驹代迟迟不给答复。驹代心中有两个理由:一是想要自力更生,不想辞掉艺妓工作,成为某个男人的附庸;二是为了寻求自由。艺妓正因为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秩序之外,因此不受女性行为规范的束缚,获得了妻子所没有的自由。
其次,永井荷风的文学作品最令人惊讶的是对传统意义上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颠覆。以往的文学作品对两性关系的描写大多不自觉地以性神话为前提,将两性的个性倾向与各自的自然性别相联系,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作了明确的界定。如嫉妒、阴险、报复心强等特征,往往被认为是女性气质特点。而在荷风的文学作品中,这些成为男性的气质特点。在《比本领》中,当吉冈得知驹代和演员濑川交往的消息,心里开始筹划对驹代进行报复,偷偷赎下了和驹代在同一家店卖艺的菊千代,借此来羞辱驹代。在《梅雨前后》中,畅销作家清冈得知艺妓君江和其他男人相好的消息,筹划各种卑劣的复仇手段。可以说,男人在感情遭到背叛后对女人实施的报复,是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在实施报复的过程中,男人的卑劣、猥琐和阴暗暴露无疑。
最后,女人被物化不仅是女人的悲剧,更是男人的悲剧。这是因为,女人在被物化后出于本能的自我防卫,很难再对男人付出真情。而男人占据女人身体的同时,渴望灵魂的交流,这是人性的要求。于是,男人不得不為“爱的缺失”感到万分痛苦。如《比本领》中的冈吉在看着驹代的胴体的时候心里不由得想:“如不能在享有此女身体的同时完全占据她的灵魂,就会感到很不爽……真是不可思议。本不该如此……”。《梅雨前后》中,清冈耿耿于怀的是,自己即使提出与君江分手,君江会毫不留恋的离去,很快找到新欢。最终,将女人物化的男人反而被女人抛弃。
驹尺认为永井荷风是当时少见的、具有妇女解放意识的男作家。如《冷笑》中的小山清就是一个妇女解放论者,他同情英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认为“男人做的事女人同样可以做”,日本必须出现这种思想。在这部作品中,荷风对日本存在的艺妓制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认为这是“由德川时代社会道德的欠缺而产生的历史遗物”,“其根本是出自人身买卖的恶习”。他时常对艺妓所受的人格侮辱感到义愤填膺,认为玩弄她们的行为“与色情罪犯的行为如出一辙……如同一群丑陋的怪兽”。驹尺认为荷风与之所以产生共鸣,主要基于两个共同点:一是毫不虚伪的生活态度;二是都被社会抛弃和践踏。可以说,正是由于荷风勇敢地从处于社会上层的家庭中走出来,自甘堕落为一个市井小民,才获得了自下而上的、审查既成社会秩序和社会观念的观察之眼。
如以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史作为参照系来考察驹尺喜美的批评理论,可以发现她深受法国著名女性主义思想家波伏娃的影响。波伏娃认为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男性是主体,女性处于从属地位,是受男性控制和摆布的客体。而驹尺喜美的专著《魔女的理论》《魔女的文学论》都以波伏娃的理论为理论基础。如驹尺从女性视角来考察夏目漱石的文学作品,认为漱石的一些作品明显站在女性角度,对日本女性的生存境况进行了审视,揭示了男权社会的婚姻制度对女性人性的扼杀,并对导致女性不幸的根源——男女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性别分工亦有所触及。
参考文献
[1]駒尺喜美.魔女の論理[M].東京:エポナ出版社,1978
[2]駒尺喜美.魔女の文学論[M].東京:三一書店,1982
[3]夏目漱石.行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26-127
[4]夏目漱石.行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126
基金项目:2018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日本的发展与现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号:18WWB111)。
该文受2019年度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作者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辽宁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