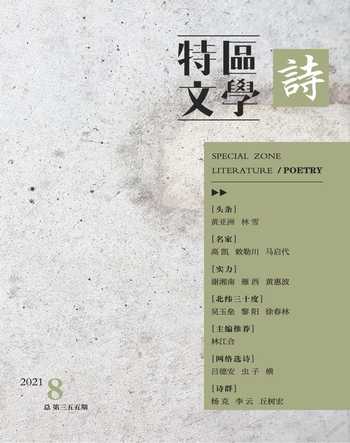十面埋伏
世宾 吴投文 向卫国 周瑟瑟 宫白云 赵思运 高亚斌 徐敬亚 韩庆成 霍俊明
猫
胡 弦
我写作时,
猫正在我的屋顶上走动,
没有一点声响。
当它从高处跳下,落地,
仍然没有声响。
它松开骨骼,轻盈,像一个词
完成了它不可能完成的事,并成功地
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它蹲在墙头、窗台,或椅子上。
它玩弄一个线团,哦,修辞之恋:浪费了
你全部心神的复杂性,看上去,
简单,愉悦,无用。
它喜欢在白天睡大觉,像个它者。
当夜晚来临,世界
被它拉进了放大的瞳孔。
那是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去寻求
新的呈现的世界……
这才是关键:不是我们之所见而是
猫之所见。
不是表达,而是猫那藏起了
所有秘密的呼噜、或喵的一声。
它是这样的存在:不可解。
它是这样的语言:经过,带着沉默,
当你想写下它时,
它就消失了。
诗人简介:
胡弦,诗人、散文家,著有诗集《阵雨》《沙漏》《空楼梯》、散文集《永远无法返乡的人》《蔬菜江湖》等。曾获诗刊社“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称号,《诗刊》《星星》《作品》《芳草》等杂志年度诗歌奖,花地文学榜年度诗歌奖金奖,柔刚诗歌奖,十月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现居南京。
世 宾:语言和写作者的关系
胡弦总能给人带来发现的惊讶,虽然不是豁然开朗地打开一个新的世界的那种发现,或者某种具有强大力量能把人带入新空间的发现,而是一种温婉的、在人们昏昏欲睡的地方轻声地告诉你“你看”的发现;或者在你猜不出木头里藏着什么时,他熟稔削掉那多余的木屑,把一尊佛像呈现给你看的发现。这发现让习惯于肤浅的抒情的诗坛惊叹不已。他的确给语言的发声带来方法—虽然这方法不是很新,但比较管用—他适当地调整发音的位置、歌唱的调子。这位置和调子恰好不会刺激时代敏感的神经,又能舒适地让你看到微风中的火苗—那安全的罩子紧紧地扣在上面。
《猫》这首诗有着胡弦诗歌的特点,在隐秘的关系里,他能简洁抓住事物间的关系,把那隐藏内核—他要揭示的“真相”“真理”呈现出来。同时,他有着恰当的比喻,他能够把理性、感觉—丰富的通感—融为一体,通过准确的意象把他的发现表达出来。猫有如那语言,它在“我”—写作主体之外,它悄无声息,不容易觉察,却从未远离,在屋顶、在墙头、窗台、或椅子上,“完成了它不可能完成的事,并成功地/沒有引起我们的注意。”非常形象地描述出猫在周围出没的样子,也形象地呼应了语言在写作时所存在的状态。我们精心地侍弄着修辞,但猫却当一个玩弄或游戏的线团,“简单,愉悦,无用”。它和写作者的关系就像一个“它者”,但它能给我们带入意外的世界,“那是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去寻求/新的呈现的世界……”。诗人还不仅到此为止,在后面两段,语言的秘密和与主体间的关系又在更深一层得到揭示,“不是我们之所见而是/猫之所见。”“当你想写下它时,/它就消失了。”
这样的诗歌阅读时的确能得到发现的快乐,但这种精致总有点像西湖石一样,或者就像江南的园林一样,或者干脆就像雪糕一样,吃多了总有腻的时候。我能想象胡弦在江南的细雨中,很文化地思考着,捕抓着那蹁跹的意象和事物被削除多余之物之后呈现“真实”的样子时,那喜悦的样子。
吴投文:呼应一个并不确定的答案
胡弦笔下的猫似乎带着诡秘和灵异的气息。实际上,这是诗人在他的观察中带入自我写作情境所形成的结果。在诗人写作时,一只猫在屋顶上走动,无声无息;它从高处跳下,落地,仍然无声无息。它的生活习性是白天睡大觉,而当夜晚来临,它把世界拉进它“放大的瞳孔”,离开我们的视野去寻求“新的呈现的世界”。这些描写细致入微,看起来是写一只猫的活动,却颇切合写作中灵感来临时的状态。对于一位诗人来说,灵感是陌生而亲切的,不期然而来,不期然而去,陌生中带着惊喜,使诗人被唤醒在对世界的奇异发现中。
与一只猫的活动情态相似,灵感亦是“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重塑生命的另一种状态;诗歌写作的实质亦是离开我们的惯常视野,去寻求“新的呈现的世界”。“这才是关键:不是我们之所见而是/猫之所见”,亦可理解为诗歌写作的关键:不是我们之所见,而是诗人之所见。当一首诗完成的时候,灵感就像一只猫一样“带着沉默”消失无形。这样看来,此诗就带有“元诗”的性质,是诗人在“以诗论诗”,是诗人在陈述自己在写作过程中的心理体验。读胡弦的这首诗,我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联想,大概不是无来由的。诗歌写作中的心理状态实际上是不可解的,就像猫“这样的存在:不可解”。用一首诗来呈现这种心理状态,则在不可解中可以落实到写作的具体情境中来,呼应一个并不确定的答案。
胡弦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能力,他往往从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发现人类隐秘的心理状态,并建立某种值得信任的共存关系。另一方面,他也是警惕的,力避诗歌的常规化表述,把他的观察视野建立在坚定的艺术信仰里。显然,这并不矛盾,而是出于一个诗人的敏感,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生活的深层真实。
向卫国:“猫与诗人”—又一种“元诗”写作的范例
在靠近新诗的源头,胡适写过一首《梦与诗》,将诗歌的创造与做梦相比附,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新诗中最早的一首“元诗”。这首《猫》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梦与诗》的升级版,它的主题也可相应地理解为“猫与诗人”。当然,升级的跨度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从1.0直接升级为3.0或者4.0了。
猫在房顶上无声地走动、从高处跳下,“像一个词/完成了它不可能完成的事,并成功地/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猫的动作,类似于一首诗的完成。不仅一首诗悄无声息地完成,本诗还指出了某些完成的细节,增强二者的相似性,强化比喻的效果:猫从房顶跃下,“它松开骨骼”,就好像诗人终于写完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长嘘一口气的感觉。同时,当代诗人几乎一致认为,诗歌的写作和是否最终完成,具有极大的隐秘性,无人可以真的掌握或说出其中的语言奥秘,所以,诗歌写到猫“成功地/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但诗歌写作的隐秘性并不排斥语言的技艺和修辞,它们也总是在隐秘地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这就像猫随时随地“玩弄一个线团”,看似“无用”,却是一种必备的日常功课。
接下来,更深层次的探讨是,猫以悄无声息的行为,“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去寻求/新的呈现的世界”,这正是现代语言哲学关于语言本质的认识。语言(尤其是诗的语言)一经使用,它便离开了使用它的主体,成为另一独立“主体”,它独自去发现世界、创造世界、呈现世界。而另一方面,诗人主体最初的写作意图或思想,却一定程度地被“藏起”甚至完全“消失”。
当代诗中,已有大量关于诗的诗,虽然采用的喻体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诗人自身对诗的认识和理解,比如本栏目曾讨论过的陈先发的《养鹤问题》也是这样的一首诗。不过陈诗偏重于对诗歌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认知,而这一首主要是对诗歌的语言学或纯诗意义上的诗性阐发。此类作品或可视为当代诗歌的一大类型,与偏重于表达具体的社会和生命认知与感受的传统诗歌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
周瑟瑟:南方诗歌美学的建造者
胡弦是南方诗歌美学的建造者,请注意我没有用“江南”一词,我们讲了多年的“江南诗歌”,纤细的、飘忽的、光滑的、女性化的等等美学特质限制了我们对于生活在南方的诗人的写作的想象。显然胡弦并不是这一类型的诗人。他在建造诗歌美学新的屋宇,他在建立属于汉语言诗歌的尊严,他试图确立当代诗歌在现代中国人心里的美学地位。
他的写作比那些既有的传统写作更有创造力,他重新建造了一种新的南方诗歌美学。他建立了一种词与物的逻辑关系,不仅仅是《猫》这首诗,而是他全部的写作,他把词与物的关系重新确立,他给词与物之间留出了一道生命的缝隙。这条缝隙开始是细小的,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个传统写作小富即安的现状中,创造性的耐力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他的诗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具有伸缩性的、弹性的美学在他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呈现。他的诗有语言传统,但又建立在个人现代性感受上,他是那样细微,又是那样开阔,每一首诗都有无限的可能,又适可而止。
他的写作具有很强的分寸感,但又有强烈的原创性。他在词与物中间平衡,他踩在传统与先锋的两端,不时露出诗歌技艺的高难动作,他从没从诗歌技艺上跌落,相反他站得稳稳的,并且形成了他牢固的写作风格—胡弦式的南方诗歌美学。
《猫》是一首关于胡弦写作的“元诗”,以一首诗来阐释诗人的写作,需要特有的精神气息与大胆的构思。显然胡弦炉火纯青,他宁神静气,举重若轻,在一呼一吸中,将人与猫的习性动作融为一体,达到人猫同体的效果。形而上的意义指向与人猫同体的结构漂亮地融合,完成了一首有无限可能的伸缩性、弹跳性极强的杰作。
宫白云:向内伸展的诗
胡弦的诗是向内伸展的诗,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追求一种“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诗歌语言,他“希望在诗歌的深层结构、在诗歌语言内部做一些文章”。所以,他的诗从来都要去到深层去挖掘一些言外之意,就像猫走过去的声音,毫无声响,但是你能感觉它的存在。他诗歌的语言与他的情绪、思想、心灵都是融会贯通的,有种不可言传的玄妙或微妙。胡弦有段话说:“写作,是触摸生活深处那并非人人可及的零散片段,并把那感觉留住。”他的这首《猫》就是如此的效果,他把猫日常的“零散片段”带给他的全部感觉与思考以诗性的方式“留住”了下来。语调幽微,带有冥想的状态,犹如一部缓慢的电影,镜头中那只自得其乐充满了各种情调和美感的猫被缓缓地呈现。看似写猫,实际上是在谈写作的问题,猫的行为喻示着写作者的行为,猫的种种状态启发了诗人的思维,形成了一个个精彩的对写作的提醒,也不仅是因为猫的行为示范了写作,猫的“种种”也让写作变成了人与其它世界保持诗意本性的沟通。这首诗,艺术构成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通过洞察一个猫的日常来感应“写作”之“不可解”的所在,具象而生动,充满了潜意识的色彩。
赵思运:写作的神秘与诱惑
胡弦这首《猫》写得非常机智。它是一首关于诗歌写作的诗歌,带有元诗的特征。整首诗写的是“我”和“猫”的关系。“我”的身份是一个作者,“猫”应该不是写作对象,而是作者的“心像”,或者说,是与作者肉身相伴的灵魂心像,是作者写作行为的伴随者,它更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猫头鹰,每到傍晚就来临。这只猫头鹰就是“智慧”的象征。“它喜欢在白天睡大觉,像个它者。/当夜晚来临,世界/被它拉进了放大的瞳孔。”灵感出没于深夜这一特点,不仅符合浪漫主义诗人的写作习惯,一般的作者大概都有这种体验。在作者苦思冥想的时候,他的精神和灵魂暂时超越了肉身而专注于自身之外的一种洞察。因此,作者的肉身很難感觉到它的存在:猫正在我的屋顶上走动,/没有一点声响。/当它从高处跳下,落地,/仍然没有声响。/它松开骨骼,轻盈,像一个词/完成了它不可能完成的事,并成功地/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猫”(灵感)的视野里,世界永远是新奇的,超出我们的边界去寻求“新的呈现的世界”。它的足迹无处不在,但却又不留痕迹。它的世界“简单,愉悦,无用”,与作者苦心经营的艺术世界(修辞的线团)形成鲜明对比。它的魅力在于,它是“不可解”的,它“经过,带着沉默”。它是不可言说,一旦说出,它即“消失”。
诗人的写作充满着无尽的秘密,像神秘的“猫”眼里的世界。而写作的乐趣大概就在于捕捉这些秘密。这个过程十分艰难,却又充满诱惑,诗歌的魅力盖源于此。
高亚斌:一只猫展现的奥秘
胡弦的《猫》一诗,耐人寻味的是他对诗意的处理方式,显得与众不同。他把诗歌的语境,放置在一个具体的生活场景或生命场景中,放置在对一只猫的日常叙事里。在这里,诗人的“写”和一只猫的活动如此贴近,“猫”作为一个叙事的主体,那么从容自如、毫无顾忌地进入诗歌,“它松开骨骼,轻盈,像一个词”,“它玩弄一个线团”,展示它的“修辞之恋”。
同时,“猫”又是一个叙事客体,承受着诗人和读者的窥视和观察。但它又能够轻而易举地避开了窥视的目光,“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去寻求/新的呈现的世界”,并用沉默拒绝了人的介入和参与。于是,与这个神秘“不可解”的宇宙一样,猫也成为神秘本身,在猫的身上,展现了世界令人着迷的奥秘。
这首诗的魅惑之处,还在于它借助猫的生命活动,完成了对于日常哲理的探询与获得。诗人能够深入到细节,剥开我们寻常的那些可见与不可见,让人遐想无穷。无论是猫在“墙头、窗台,或椅子上”,或是“在白天睡大觉”,与我们对它的了解相比,它的不可知的部分如此莫测,它的确是一个“它者”。
美国诗人桑德堡也写过一首《雾》,与《猫》有着近似的意趣。这启发我们:一首好的诗歌应该存在于动态的不断活动的词语里,哪怕它仅仅只是一只猫,它也是活生生的。
徐敬亚:猫诗之间的木匠手艺
胡木匠做了两把椅子:一把是我,一把是猫。它们怎么合成了一把椅子呢?
先做一个实验:
先删去了第一节的“像一个词”。
又删去了第二节的“哦,修辞之恋”。
再删去第三节的“它是这样的语言”。
删去了诗的暗指,全诗突然静止干净,只剩人与猫。这是一幅寂静的日常画面啊:一个作家在写作,一只猫在跳跃→隐喻的大门关闭了,只留一条微弱的缝,像北岛式的深谜。除非一门心思琢磨语言并极细读的人,或许才能把隐约的线连接起来。
①词、修辞、语言,这三个词太重要了。然而却“缺一亦可”→只要露一个破绽,比如只出现“像一个词”,聪明读者也可以衔接全部对应关系。但埋得有点深,本时代的人们哪有那么多闲情猜测。三处提醒恰好,再多几次,不仅繁复,戏法也就露了。
②如果只有三根绳子,顶多算两把椅子绑在一起,它们之间还缺少凝胶。是一些模糊的、半猫半词的不可解之字语,使猫和语言相互混淆、相互溶解,这的确是一种高超的粘合,语言入诗与猫的“走动、高处跳下、落地、离去……”,出现了猫诗之间的玄妙混血。
③猫是第一显像,必须准确到位:“玩弄线团、放大的瞳孔、呼噜或喵的一声”,都精致,“松开骨骼”写得传神。
这是智慧之诗。就理论深度来说,诗自然无法超越学术论文,甚至不超过一般读者对诗与语言的理解界限。而有了一只猫,平常的诗感立刻生动起来,无限起来。这就是诗的手艺。无论你看到一把椅子还是两把椅子,围观者都不得不赞叹:这位木匠的手艺活儿,真不错!
韩庆成:“猫”的诗学
就带有一些神秘性的智性、思辨类写作而言,《猫》无疑是一首上乘之作。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狭隘的诗学观,我一直不太推崇这样的作品。当然,如果闲来无事,把玩一下也未尝不可,特别是当这是一份工作的时候。
“猫”是“沉默”的,“不可解”的,无来由地出现,无来由地“消失”,悄无声息,神秘莫测,可用以看见,可用以臆想,就算你偶尔听见它发出“呼噜、或喵的一声”,你也无法解读其中的“所有秘密”。“猫”可以指代这样一类事物,也可以指代这样一种“写作”状态,包括“词”的状态,“修辞”的状态,“语言”的状态。在西方诗歌中,“猫”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诗学问题”,如艾略特的“猫”,波德莱尔的“猫”,等等。其中关涉的猫性、人性,乃至神性,已非闲来无事所能把玩。
我对这类诗作的总体感觉,亦如本诗第三段所写:“它蹲在墙头、窗台,或椅子上。/它玩弄一个线团,哦,修辞之恋:浪费了/你全部心神的复杂性,看上去,/简单,愉悦,无用。”
霍俊明:作为精神事件的“元诗”写作
无论是一个静观默想的诗人还是恣意张狂的诗人,如何在别的诗人已经趟过的河水里再次发现隐秘不宣的垫脚石?流行的说法是每一片树叶的正面和反面都已经被诗人和植物学家反复掂量和抒写过了。那么,未被命名的事物还存在吗?诗人如何能继续在惯性写作和写作经验中还在电光石火的瞬间予以新的发现甚至更进一步的拓殖?更多的情况则是,你总会发现你并非是在发现和创造一种事物或者情感、经验,而往往是在互文的意义上复述和语义循环—甚至有时变得像原地打转一样毫無意义。这在成熟性的诗人那里会变得更为焦虑,一首诗的意义在哪里?一首诗和另一首诗有区别吗?
胡弦的写作印证了诗歌是个体精神事件的产物,而具体到《猫》来说这是一首“元诗”。“元诗”即关于诗的诗,关于写作的写作,它往往关涉精神的宣喻,是一种更高层级的精神共同体方式。这一类型的文字是在词语和精神的两个维度同时展开的,不是线性和历史时间的向前或者向后,而是精神维度的垂直向上或者向下。
就胡弦的这首诗来说,“猫”的所有的动作、声音、表情、形态以及不可见事物的猜测都是与“词”的展开、探询以及困惑缠绕在一起的,这是米歇尔·福柯意义上的“词与物”的同时展开、抵牾的过程。明确的“元诗”意识使得这一文本具有经验和超验、可知和不可知融合的视野,诗人保持了对不可见之物以及写作不可解释过程的同步探询,保持了对写作的叹惋和词语命运的困惑以及解惑。
这是词语和世界背后的内在纹理和幽深秘密,它们也如芒刺在一次次让诗人不安,因为伟大的写作既面向了词语的终极挑战又遭受到了时间、存在以及世界的庞大力量的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