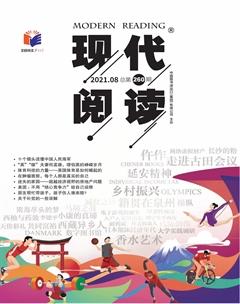迷失的家园


房地产问题在当代中国造成的冲击和影响广泛而深远,仅仅作为单纯的经济问题来讨论似乎是不够的,我们可能也需要引入人文的、社会的和公共政策的视野。
首先,目前大城市的房价是否合理,要从社会心理和人文视角来观照。不同的专家之间有意见分歧,有的认为目前的房价之高已经处于“畸态”,有的则认为房价是城市化、市场化的结果,高房价是正常的。判断一个势态是不是合理,一方面要有实证研究的基础,一方面还要有恰当的判断标准。任何一个势态都有其生成的原因,否则就变得不可思议、无从解释了。
但能够解释势态的原因未必就证明这个势态是合理的。从人文和社会心态的角度看,那么多人集中生活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那么多大学生都有意愿留在大城市,这当然有社会、文化和心理的原因,但这是合理的吗?在大城市中为生存空间而拼命地挣扎,许多人处在非常焦虑的状态中,这是一种好的生活状态吗?当然可以说,谁觉得不好完全可以“逃离北上广”,但我们认真对待过许多人的两难困境吗?
比如,现在我们高校有一些很优秀的博士生就陷入这种困境。他们毕业了有机会留在上海,但压力巨大。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很难买房子安居。房价和个人收入的比例,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大概是大学毕业生起薪的30到40年的年收入。我们当然可以说,博士毕业不必留在大城市,可是我们国家好的研究性大学基本上都位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你的焦虑是你自找的,因为这是现在的新常态,所以就是合理的呢?
房地产价格当然是一个市场问题,但影响市场和价格的不只是经济因素,房价也不只是物质生活的问题,也有公共政策问题。每个国家的房地产发展都是一个发展演化的结果,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一个必经过程,但我们的房价有自己的“特色”。一些地方官员在特定的任期内要做出显赫的政绩,而土地财政能在较短时间内获得很高的财政收入。但土地财政的后果在他们任期之后的长期而复杂的影响可能就被忽视了。所以,在多大程度上我们能说目前的房价是城市化“自然”发展的结果?如果房价的构成要素包含人为的政策,那么对政策的评价就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评价标准本身需要超越经济增長和短期效益的视野,这是需要相关专家学者纳入考虑的问题。
第二,我们对住房需求的理解,也需要超越物质主义的理解。房子到底是一个必需品、商品,还是奢侈品?当我们谈“刚性需求”的时候,我们究竟在谈什么?“刚性需求”似乎是客观的物质需求,但在我看来,所谓“刚性需求”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心性需求”。比如,我们这代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或中期毕业的时候,如果学校分给你一栋筒子楼中的一间房,两个青年教师合住,就相当不错,如果筒子楼中有一个单间分给你一个人,那简直跟现在的豪宅一样,完全满足了“刚性需求”。但在今天,一个年轻教师如果在集体宿舍中有一个单间,会被认为没有达到基本的“刚性”生存条件,在征婚的时候就处在劣势。所谓“刚性需求”或者基本生存条件不只是物质性的,也和社会文化心态有关,“刚性需求”渗入了“心性”的要素。
那么,我们在决定什么是必需品、什么是商品的时候,需要对现代普遍的生存标准有一个清晰的考察和认识,从而形成一个合理的标准。这个标准的设定直接涉及“廉租房”和“经适房”的建设水平。依据这个标准,公共政策的导向应当首先满足作为生存权的基本社会福利,但我们不能说,给你一个“胶囊房”就算满足你的生存权,所以我们需要澄清这个标准。
第三,学区房的需要涉及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其中包括基础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学区房价格的飙升是一个显著趋势,其他许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但在中国,这个问题似乎特别突出。这当然跟我们的教育观念有关系,中国许多家长有一种要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观念。我反复讲过,教育首先不应当只是输赢问题,教育的目标是使一个人健全和幸福,而不是在非常狭隘的功利意义上论输赢。
当然,批评“赢在起跑线上”的观点,主要针对的是“以考分论输赢”的错误导向,而并不是否认教育资源的重要性,也绝不是回避教育资源存在地区差异的事实。对学区房的竞争实际上就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需要反思:其一,这种竞争是有益的市场竞争吗?其二,基础教育资源是否应当作为商品被置于市场竞争之中?
先说第一点。市场竞争使得好学校周边的房价涨到每平方米10万甚至20万这种地步,不仅是疯狂的竞争,而且对社会整体来说是没有收益的竞争。父母都想让子女就读好的学校,抢购好学校附近的住宅,导致优质学校周边的房价飞涨。父母们为此更加辛苦地工作挣钱,来提高自己家庭的购买力,但当众多家庭卷入这场竞争,最终付出的努力会相互抵消,结果仍然只有少数人能进入优质学校,但整个群体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种竞争是合理的吗?在理论上似乎是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却造成了一种荒谬的非理性结果。
再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学区房造成了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就教育而言,一个理想的公平社会应该对所有公民的子女提供基本上同等水平的基础教育资源。也就是说,无论孩子的家庭背景、民族、籍贯和性别等方面有什么差异,他们都应当“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当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完全实现了这种公平的理想,但这并不是放任资源配置不公平的理由。学区房的问题就是基础教育资源的分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屈从于财富的等级结构,形成了一种“富者通赢”的局面。也许,正是由于教育的“起跑线”越来越严重地被财富所扭曲,才会有那么多人为孩子可能“输在起跑线上”而恐慌。
我当然不是主张要回到旧时代的平均主义理念。应对这样的问题,美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沃尔泽提出一种“复合平等”理论,其要点在于:任何一个领域的优势都不应当构成对整个社会资源的垄断。他主张将不同的社会领域尽可能分隔开来,允许每个领域有各自的优胜者,但防止某一个领域的优势越界扩张,延伸为其他领域的支配权。比如,财富的优势应该被限制在商品消费领域。一个富人可以开豪车、穿名牌或者去高级餐馆用餐,享受诸如此类的奢华“消费优势”。但无论他多么富有,也不能用钱来“买官”,因为这就将消费领域的优势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同样,一个政府官员具有政治领域的权力优势,但不能以此免费或低价享受商品和商业服务。在这里,“腐败”的含义就是将权力优势转换为消费优势。
从复合平等的角度来看,基础教育资源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它在本质上不是商品,也不应受到金钱的左右。实际上,免费的义务教育正是一种促进机会平等的制度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钱对教育资源的支配。就近入学的“学区政策”本来也是一种公平措施,但由于优秀师资和学校的地域分布不均,导致对学区房的购买竞争,优秀的公立学校也就变相地成为商品。凡此种种,都会使财富的优势扩张到基础教育领域。
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贫富差异,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更有理由去防止“富者通赢”的格局。时下弥漫的“拜金主义”和“仇富心理”正是对“富者通赢”现实的两种极端反应。所以学区房并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应该单纯交给市场机制来解决,它涉及公共政策,涉及如何更为公平地配置公共资源。
(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作者:刘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