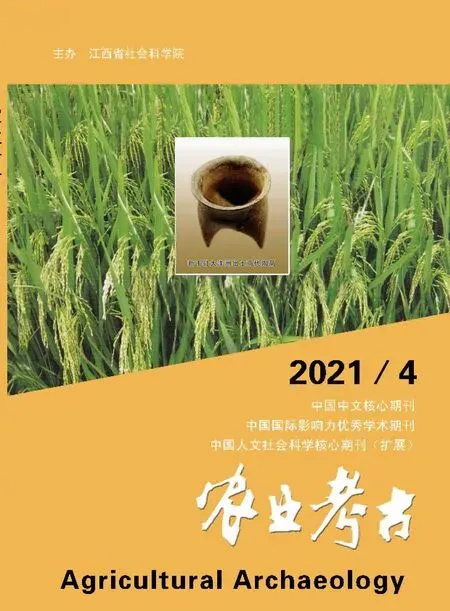战国时期的辨土地与均田赋
查飞能
在《周礼》与先秦诸子著作中,多有周代辨土地、均田赋的记载,内容主要反映各地应贡纳的田赋、物产,这与西周、春秋时期公田共耕制度下田赋征取方式多相违背,却与战国时期授田制背景下田赋征取方式多相符合。在赋税以田亩数量为依据的战国授田制时期,辨土地是较为均匀征取田赋的前提。以往有关周代辨土地的研究,主要围绕《尚书·禹贡》九州土壤展开①,并不能全面反映战国时期的实际情况。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综合分析战国时期的辨土地,并进一步阐述均田赋主张与实践。
一、战国时期的辨土地
自西周晚期宣王“不籍千亩”以来,公田共耕制度至战国时期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阻碍。《吕氏春秋·审分》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注云:“作,为也。迟,徐也。迟用其力而不勤也。”又云:“分地,独也。速,疾也。获稼穑则入己分而有之,各自欲得疾成,无藏匿,无舒迟也。”[1](P431)这反映了公田共耕体制下公田耕作效率低、私田耕作效率高,是战国时期逐步推广实施授田制的直接现实因素。在战国时期授田制下,田赋是农民为国家提供的最主要税种,如何较为均匀地征取田赋是当时社会必须考虑的问题,辨土地就成了实施均田赋的前提工作。
(一)据土壤质地与颜色辨土地
据土壤质地、颜色辨土地,是从大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分辨,主要见于《周礼·职方氏》与《尚书·禹贡》。
《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地”,系统记载九州各区域内作物种植情况,是在辨土地基础上总结的一些“因地制宜”的规律性认识。
据郑玄注,“五种”指黍、稷、菽、麦、稻,“四种”指黍、稷、麦、稻,“三种”指黍、稷、稻[2](P862-863)。《职方氏》因篇章限制未能列出辨土地的具体情况,仅简要记载了各地作物,但也是建立在辨土地基础上的。
在《尚书·禹贡》篇中则详细列举了各州土壤质地、颜色,并进一步划分田地等级,是《职方氏》的细化与丰富:
对比《禹贡》《职方氏》,均有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豫州、雍州。然《禹贡》有徐州、梁州,《职方氏》有并州、幽州,是两者不同之处。《禹贡》《职方氏》所列各州虽有不同,然土地分类、作物情况已经包含所有地域。
据《禹贡》可知,战国时期已经把土壤分为壤、埴垆、坟、涂泥、黎等,依据的是土壤质地;又配以黑、白、赤、青、黄等不同颜色区分,依据的是颜色辨别[3](P121)。从大的地域范围来看,《禹贡》对各州土壤的认识基本是正确的。然各州地域范围广大,包含不同地理单元,部分州的划分是存在问题的。如梁州,包含今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四川盆地等广大地区,土地为青黎当然是不符合的,所谓青黎主要存于成都平原。故《禹贡》所列各州土壤质地实为该州主要的代表性土壤,而非各州地域内的全部土壤。
《禹贡》在辨土地基础上进一步把九州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又分上、中、下,主要依据是战国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长江流域的扬州、荆州、梁州地区被列为下等而言,与当时长江流域地广人稀、水利基础薄弱、田地开垦利用不足有关。而其他各州的划分也多受经济发展影响,存在不实之处[4](P77-78)。总之,《禹贡》对当时田地分等非率意编排,但也不是依据地形、土地肥力,而是当时的农业发展水平,故各州田地等级的划分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5](P542-543)。
(二)据土壤改良与保养之法辨土地
战国时期文献已有土壤改良、保养方面的记载,与辨土地存在相互关系,是在辨土地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寻绎相关文献,大致可分为土化与耕作两种方式,俱见土壤分辨,亦是辨土地的内容。
1.土化之法
《周礼·土方氏》载土方氏“以辨土宜、土化之法”[2](P864),“宜”即辨别土地适宜种植的作物,“化”即改良土壤的方法。同时,《周礼·草人》在区分土壤性质、颜色基础上,强调用“土化”之法来改良土壤[2](P746),内容更为系统: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骍刚用牛,赤缇用羊,坟壤用麋,渴泽用鹿,咸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强鑒棠用蕡,轻爂用犬。
据郑玄注,骍刚,即赤色且坚硬的土壤;赤缇,即赤色而不坚硬的土壤;坟壤,即肥沃的土壤;渴泽,即干涸的泽地土壤;咸潟,即盐碱地;勃壤,即沙地;埴垆,即黑色硬土;强鑒棠,即坚硬成块的土地;轻爂,即轻脆易碎的土壤。《草人》煮各种兽骨汁用于浇灌土壤以起到土化之功,是当时人的认知,于今并无科学性可言。然综合相关注解可知,草人职责是掌管改造土壤、审视土地的方法,因地制宜地耕作以改良土地。
总之,《周礼·草人》所记各类土壤改良之法,既是当时土壤分类的一些基本认识与经验总结,也是综合了各类土壤土质、颜色两大辨别因素的辨土地之法。
2.耕作之法
《吕氏春秋》中的《辨土》《任地》篇在辨土地基础上有具体的土壤保养措施。《辨土》篇载:
凡耕之道,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靹,为其唯厚而及;缸食者。萁纤任之,坚者耕之,泽其靹而后之;上田则被其处,下田则尽其汙。
据孙诒让解诂,“厚”当为“后”。“靹”当为“偉纳”,《广雅·释诂》云:“偉纳,弱也。”《玉篇·韦部》云:“偉纳,偉纳耎也。”“泽”当为“释”。“盖垆为刚土,偉纳为耎土,‘必后其偉纳’与‘必始于垆’文正相对,谓先耕刚土,后耕耎土,故承之云‘释其偉纳而后之’,即谓舍其耎土而后耕之也。坚与偉纳,文亦正相对。”[1](P691-692)是言先耕刚硬且容易缺水的埴垆土地,再耕松散软弱的偉纳土。
《任地》篇载耕作五种方法,涉及土壤质地、肥力、软硬等:
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
其中,“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有关土壤结构与性质,是言黏重结块的土壤要使之松散,松散的要使之结实一些。“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有关土壤贫瘠与否,注云:“棘,羸瘠也。《诗》云:‘棘人之栾栾。’言羸瘠也。土亦有瘠土。”“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有关土地硬度,注云:“急者,谓强垆刚土也,故欲缓;缓者,谓沙堧弱土也,故欲急。”[1](P688)
《吕氏春秋》之《辨土》《任地》篇说明从耕作角度对土地的认识已经比较深刻,要注意土壤是否结块,贫瘠的土地施肥要适度、控制量的多少,土质硬度不同要注意耕作力度。
(三)据地形特征与作物辨土地
据地形特征及所决定的作物辨土地,是从小范围内土地特征进行辨析。
《周礼·大司徒》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九州,与《职方氏》相同,郑玄注:“九州,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也。”名物即十种土地名称及所生之物,郑玄注:“积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渎曰川,水钟曰泽,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坟,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湿曰隰。名物者,十等之名与所生之物。”[2](P702)土地主要依据所产之物、地形特征进行命名。《大司徒》辨土地,着眼于每州范围内进行更细致的分辨,与各类土地所产之物密切联系,较之《职方氏》与《禹贡》更为精细。
另《管子·山国轨》有“四壤”,亦与地形特征联系密切:“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柘之壤,有泛下渐泽之壤,有水潦鱼鳖之壤。今四壤之数君皆善官而守之,则籍于财物,不籍于人。”[6](P1282)这是将作物与土地结合进行分辨,四类土壤产出不同,征收赋税依据物产而非人头,官府亦需明辨土地。类似《山国轨》一类战国时人依托前人之名编写的著作,编撰思想明显与战国时代按田亩纳税背景有关,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情况。
二、战国时期的均田赋
战国授田制的目标之一是均田赋,即从农民年收成中征取比较合理平均的田赋,这是当时社会上通行的主张与做法。
(一)均田赋主张
经过春秋以来争霸战争,至战国早期逐渐在地域上形成局部统一,然各主要大国间激烈竞争又促进了授田制的实施。为在有限土地之内充分发展生产,壮大国家实力,合理均匀的授田成为当时普遍认知,在《周礼》和诸子著作中均有十分明显的均田赋主张。
《周礼》设计的职官中,大司徒、土均、司稼等的职事比较确切涉及均田赋。《周礼·大司徒》载其职责之一即:“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郑玄注:“均,平也。”[2](P702)具体而言,就是根据土地合理征取贡赋的原则,辨别五种土地、划分九种等级,以制定地税,使农民做好各自职务、贡献各种农作物,以便征取财物、赋税,使得以田赋为主要赋税的征收均平、整齐、划一。
《周礼·土均》记其职责为:“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贡。”其中,“掌平土地之政”,即使土地税平均。据郑玄注:“政,读为征。所平之税邦国都鄙也。地守,虞衡之属;地事,农圃之职。”[2](P746)又《周礼·司稼》记其职责为:“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2](P750)这段记载比较系统,在辨别各种作物适宜的土地基础上教民种植之法,同时根据收成折中收取赋税,即“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本质上与大司徒之职“以均齐天下之政”是一致的。
诸子著作中更是直接提出平均授田主张。《荀子·王霸》载:“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守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7](P252-253)从中可知,一夫所得百亩田地是授田基本数量,坚持“莫不平均,莫不治辨”的做法,讲究平均原则。
《管子·国蓄》载:“分地若一,强者能守……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计本量委则足矣。”[6](P1264)所谓“分地若一”,强调授田时统一、平等。据“人有若干步亩之数”,可知是授田数量相等,以此来保证口粮及赋税平均。又《尉缭子·原官》载:“均地分,节赋敛,取与之度也。”[8](P41)“均地分”指平均分地,“取”指征收田赋,“与”指授予农民田地。授田时“均地分”是“取与”的前提与尺度,要求从授田数量上保证平均。
(二)均田赋调控
公元前352年,商鞅在秦孝公十年发布变法命令有“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9](P2232),从法律角度打破旧田制来收取平均赋税,是战国均田理论的具体实践。总体上看,为了实施均田赋理论,使接受国家田地的农夫向国家提供的赋役平均合理,战国时期各国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保证农夫所分得土地的数量与质量的平均[2](P601)。也就是说,为了达到均田赋要求,授田时需从田亩数量与质量上进行调控。然在田亩质量影响下,还需从田赋征取数量方面进行调控。
1.授田数量调控
在授田制下,民众所得田地受国家政权调控,在数量、质量两方面基本是平均的。《周礼·遂人》载“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穑,以兴耝利甿,以时器劝甿,以强予任甿,以土均平政”[2](P740)。遂人职事“以田里安甿”及“以土宜教甿稼穑”,目的是实现“土均平政”。该篇下文有具体做法: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菜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二百亩,余夫亦如之。
农夫所得田地在野外,质量上划分为上、中、下三种,并通过菜地进行协调分配。具体而言,种植粮食作物之地,三种土地是平均的,通过在菜地上增加亩数调解三种田地质量上的差距。
又《吕氏春秋·乐成》载魏襄王时期史起言:“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1](P416)行田即授农夫田地,因土地质量好坏,而因地制宜地辨等分田,在魏国范围内标准是一百亩,然邺地土地贫瘠而授二百亩。也是根据田地质量而在数量上做出的必要调控。
总体上来看,战国时期授田数量调控是由质量决定的,国家授田时依据田地质量而在数量上进行差额授田。
2.换土方式调控
就耕作方式而言,战国时期存在换土易居情况。战国中期商鞅变法时曾有“废井田开阡陌”措施,然至汉代有商鞅“制辕田”之说。《汉书·地理志下》直言:“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注引张晏言:“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始割列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又引孟康言:“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侵废,商鞅相秦,复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在其田,不复易居也。《食货志》谓‘自爰其处而已’是也。辕、爰同。”[11](P1641-1642)
张晏、孟康所言周代因田地质量高低不同,故三年会换一次土地,而孟康所言更详细。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来看,在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中邑的长官需观察辖区内“立稼之状”,判断土地“美恶之所在”,目的就是为了“三岁而壹更赋田,十岁而民毕易田,令皆受地美恶□均之数也”[12](P36)。美、恶分别指田地肥沃、贫瘠。晁福林先生推测,从战国时期的情况来看,三年更换土地并非全部农户,而是其中三分之一,所以十年才能全部更换一遍[10](P596)。战国时期土地辨等已经很细致,目的就是为了平均征收田赋,一定范围内存在换土来达到平均田赋的做法是极有可能的。
3.田赋征取调控
战国时期田赋收取深受均田主张影响。《管子·山权数》记载:“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石,其余皆属诸荒田。地量百亩,一夫之力也。”校注言“高田,上腴之地”,“间田,中田也”,“庸田,下田也”[6](P1306-1307)。《山权数》 反映齐地亩产情况,田地好坏决定粮食赋税高低,且差距十分明显。以十亩为划分计量,上、中、下三等田地各收取粮税十石、五石、三石,如此征取差距,就是土地肥沃与贫瘠决定的,而授田时田亩数量则应是相等的。
银雀山汉墓竹简《田法》追述战国时期齐地赋税计算之法云:“岁收中田小亩亩廿斗,中岁也。上田亩廿七斗,下田亩十三斗。太上与太下相复以为率。”[12](P33)据此,战国齐地一带采取折中方法征收田赋(粮食)。具体做法是:以中等年岁收成为标准,中等田地每亩缴纳20小斗,上等田地每亩缴纳27斗,下等田地每亩缴纳13斗。然年收成受土地质量、气候影响较大。《周礼·司稼》“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巡野观稼”就是因为庄稼长势受土壤质量、气候影响。
总之,战国时期在具体的均田赋操作时,立足于辨土地基础上,以质量为核心,从田亩数量、换土易耕、田赋征取三方面进行调控,保证授田制下国家向农民征取的田赋公平合理,以实现均田赋主张。
三、结语
战国时期的辨土地是实施授田制的前提,目的是为了均匀合理征取田赋,壮大国家实力。各国为了保持争霸中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展农业生产以征取田赋,必然要对土地进行因地制宜地开发与利用,故有更为细致的辨土地要求,也进一步推动了均田赋主张的提出与实施。从土壤质地与颜色、土壤改良与保养之法、地形特征与作物等方面辨土地,既说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显著进步,农业科学水平已经较高,也是均匀合理征取田赋的保证。在战国时期辨土地与均田赋之间,必要的调控是因地制宜授田的具体措施,当时主要从授田数量、换土方式、田赋征取等方面进行调控,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均田赋主张,保证授田农民能够公平均匀地为国家提供田赋。
注释:
①主要参见陈恩凤《中国土壤地理》(详见第七章《古代土壤地理记载》之《禹贡所述之古代土壤》《禹贡所述土壤之解释》),商务印书馆1951年版;万国鼎《中国古代对于土壤种类及其分布的知识》,载《南京农学院学报》1956年第1期;邓植仪《有关中国上古时代农业生产的土壤鉴别和土壤利用法则的探讨》,载《土壤学报》1957年第4期;杨宽《战国史》(详见书中第二章《春秋战国间农业生产的发展》之“土壤的分辨和田地的等级”),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