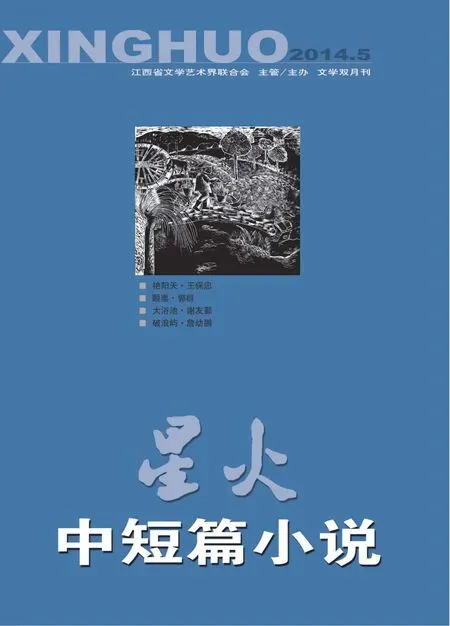旧屋记
○江榕
一
我对于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就是破败、晦暗,阳光束里四散的飞尘与刺鼻的樟脑丸气味,这或许与我父亲当年用来安置我的托儿所有很大关系。那时候他在军营,与我母亲两地分居—与许多上世纪六十年代生的农村有志青年一样,他们通过不同的方式跳出了祖辈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来到了无亲无故的城市,开始自己的寻梦之旅。在这段史诗般慷慨动人的创业史中,我这个孩子的存在未免有点尴尬。好在我父亲作为当时并不多见的军医人才,有资格在军营中拥有一间自己的小平房,也有资格将我送入大院幼儿园的托儿所,与那些父辈背景各异的孩子们同处一室。
这座托儿所曾经是某一座教堂的大厅,在那个年代,无数建筑都失去了它们原本的属性,而只剩下了遮风挡雨的作用。某一天,穿着开裆裤,和肉乎乎的孩子们一起满地摸爬滚打的我突然间意识觉醒,我睁着眼睛,看见透过彩色玻璃的斑驳夕阳涌入大厅,洒在周围那些正在骑木马玩皮球或者腰间围着代步车蹒跚前行的孩子们身上,那一刻阳光昏黄,纷杂的飞尘显得格外醒目而神秘。我呆呆坐在原地,大脑深刻地记录下了这一生中第一幕画面。
与托儿所相对应的,是父亲在军营中分得的那间平房,约莫建造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墙壁是红砖,屋顶却还是简陋的瓦片梁架结构。我记忆觉醒的那一刻恰好是这片平房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我只来得及记住那些藏在简陋的杉木门背后缝隙里时不时迟疑着爬出来的蟑螂、蚰蜒,和直接挂在屋梁上昏黄的白炽灯泡旁纱幔般的蛛网,记得每到夏夜就搬出屋子纳凉的竹床。我躺在竹床上,睁眼就看见漫天璀璨星斗。我盯着高远不知几何的星幕,看着看着眼皮就沉重起来,再睁开眼睛,眼前就变成了简单架在梁架上充作天花板的杉木条,和木条缝隙间漏下来的瓦片的影影幢幢。
我并不喜欢这座平房,或许哪怕在一个才会走路的孩子心里,就已经有了对环境的基本自觉。我更喜欢同在幼儿园的一个孩子的家。他是我在生命刚起步阶段交的第一个好朋友。起初我并不知道他的家世,而他总是拖着鼻涕带着鄙弃对我说幼儿园的这些玩具是如何如何的不好玩。有一天幼儿园放假,他约我去他家下棋,我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跟着一辆甲壳虫般乌黑发亮的小车驶上军营中的一座小山,又在中途折入藏在杉木林中的步行道,看见了一座藏在林中的两层独栋小楼。从外表看虽然是与我们家那座平房一致的砖瓦结构,但小楼周遭寂静的杉林和落叶让我本能地意识到此处与我的那间平房存在无法越过的沟堑。我的父亲在客厅与他的父亲闲谈,我和他来到二楼他的房间,看着他从自己的小床底下拉出一口巨大的塑料箱子,将箱子里的东西费力地倾倒在我面前。里面是我闻所未闻的东西,有可以变形的汽车,有附带轨道的子弹头火车,有可以发光唱歌自己前进拐弯的飞机,甚至还有一辆巨大的遥控汽车。那个下午,我坐在淡粉色的地毯上,看着他一边摆弄眼前的东西一边向我滔滔不绝地讲述它们的功能,其间他母亲进来给我们端来了一盘西瓜,告诉我父亲已经走了,晚上他们会用小车送我回家。
当我回到那座平房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木门上挂着暗青色的挂锁。我用力推拉,木门摇晃了一下,却并未向我打开。我望向左右邻居,有个面容已经模糊,但清楚记得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白背心的叔叔故作惊讶地对我说:“你没走吗?你爸爸已经走了,去南昌了!”
南昌是我母亲工作的地方,每隔一段时间,父亲都会用自行车带着我骑行两个小时去找她。后来或许是太辛苦,父亲给自行车装上了助力器,使它成为了一辆助动车,即便如此,我们也需要花许多时间在路上。那一刻,我骤然感到无言的恐惧抓紧了我的心,我哭喊着向模糊记忆中军营的出口奔去,一路跌跌撞撞,手掌摔得血肉模糊。当我跑到军营门口,看着大门两旁肃穆对视的哨兵,我一屁股跌坐在原地,说不出为什么,只顾哭。直到骑车外出兜风的父亲神人天降般出现在我面前,将我拎回住处,我才意识到这座墙皮斑驳、青草甚至蔓延进屋内的老平房,才能真正地给我微薄却必要的安全感。
当我意识逐渐觉醒,并打算将此处视为家时,这排平房却被一纸规划推平。新修起的两层宿舍中将有父亲的一席之地,但不是现在。于是我被父亲送到南昌,与母亲一起生活。
二
在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我跟随父亲生活多于母亲,是因为即便是一排摇摇欲坠的平房,也比母亲当时的居住条件好很多。
母亲在医院工作,住在集体宿舍楼的地下室,与另一个家庭共用一间房间。那栋楼还不是宿舍楼时,地下室曾经是用来存储尸体标本的仓库,曾经有人家在久未使用的橱柜中清理出住在福尔马林里的婴儿。活人与死人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共享同一处空间的潮湿和晦暗。每到雨季,雨水倒灌入地下室,约莫齐脚脖深,在室内也需以砖铺路。地下室阴森幽暗,走廊上的灯泡散发的微光仅仅只能抹亮灯泡周遭的墙壁,地面始终是漆黑的,不是积水便是积水携来的尘泥。因此,但凡稍有机会的人,都希望能将住处挪到地面上去透透光。
我随母亲,在地下室生活到小学二年级,终于有机会迁往地面。新住处是位于医院大院边缘一排三幢旧房子的中间一幢,两层,砖瓦结构,始建于1931年,曾经是民国一所医院的产业,据老人说,每一块砖头上都刻着“中正”二字。因为曾是病房,所以屋子的格局是再标准不过的“鸽子笼”,一条走廊两旁俱是蜂巢般的单间。一家人通常只能分得隔着走廊相对的两间,一间做厨房兼餐厅,另一间做客厅兼卧室。我母亲比较幸运,分得的是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她又用门板将走廊的最后一段一隔,就比别家多出了两间屋子,如此一来,母亲的居住条件一下子就超越了父亲的平房。搬进来的场景,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还记得那些二手乃至三手四手家具电器,是如何一点点填满屋子的。
然而,无论布置得如何温馨,这毕竟是修建逾六十余年的旧房子,寿命行将走到尽头。那几年南昌雨水丰沛,敲打在碧绿的臭椿和梧桐叶子上溅落于屋顶瓦片上的雨水,要不了多久就会渗入房间。我伴着盛接雨水的红色塑料桶度过了少年时夏天的若干雨夜。有一天雷暴甚于往日,母亲在医院加班,我一人在家,看着屋顶垂落入桶的水滴逐渐壮大为水柱,感到莫名恐惧,于是躲到用走廊终点隔出的客厅,蜷缩在弹簧刺出垫子的绿色人造革沙发上睡觉。睡到半夜,突然听见房中嘎吱作响,既而响起摧枯拉朽的轰隆声。我战战兢兢,不敢开里屋门一看究竟,不久母亲闻讯归来,打开门望向被整块垮塌砸落的天花板掩埋如废墟的里屋,全身发抖。
相比于在拆迁中率先倒下的另两幢旧房子,我们的住处即便出了这档子意外,依旧算得上是坚固且整洁。两座旧房子中的一幢,大厅屋顶常年缺损一个大口子,就像耄耋老者的牙齿,直到最后被拆迁也没有填补起来。站在一楼大厅,能够透过杉木条的断茬从空洞望见天空。旧房子的走廊没有灯,中午时分,光线射入空洞,整座屋子能够短暂地亮上许多,其余时间便是死气沉沉的晦暗,令我不时想起那排活人与死人同居的地下室。小伙伴们传说,当年打仗时,一枚炮弹击中了屋顶,也有说是两枚的,其中一枚至今未爆。我们始终深信不疑,在拆迁它时,我们每天都要“盯梢”许久,想要亲眼看一看那枚未爆的炮弹如何被抬出来。
我们最终只看见在废墟上蹒跚弯腰,寻找较为完整砖块的婆婆们,以及她们挑出来垒在一旁如小山般的“中正”青砖。这些在灰浆和尘土中封存了六十余年的砖块,在从作为房屋的整体属性中分离出来后不久,就迅速蒙上了一层细密的青苔。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能看见那些婆婆,在废墟间来来去去,用泥刀敲打砖头上的水泥灰浆。整个夏天,泥刀的铿铿声不绝于耳,又突然在某个时刻,一下子消失不见。
那时我并不能理解婆婆们的这一行为,只是感到新奇。有时候和伙伴们恶作剧,故意从整齐码放的砖堆中抢出一两块品相完好的砖块,以至于撞倒整座砖堆,然后拖着婆婆们尖利的叫骂声满大院跑。而当有一天,我逐步分辨清楚每一块残砖上不同的“中正”字样所代表的修筑时间,两侧的旧房子都已被推平,那些砖也被驶入大院的卡车成堆拉走,朋友们如浮萍飘散。铲车所向,接着就是我随母亲居住了五六年的旧房子。
三
在我的老家,余干县周边的一个乡村里,父亲的爷爷留下了一幢祖屋。父亲参军之前,与爷爷生活于此。我仅去过两次。第一次年纪还小,爷爷去世,我是长房长孙,随父亲扶棺回乡,将沉重的棺木停放在老屋大堂,将爷爷的黑白遗相摆在大厅彩泥已旧的雕花神龛上。那是一个光线灼热、草木媚绿的夏天,我随父亲摆好爷爷的遗像,向棺木磕完头,在穿透老屋残缺瓦片的光线中站了一会儿。依旧有尘埃在光束里飞舞,在大堂木板墙上节疤的衬映下,我突然意识到爷爷这才算是回家了,这才是他的家,而不是那个他退休后居住了十余年的敬老院里独门独户的小院落。
第二次回祖屋,是几年前的清明。隔了近十年,奶奶也躺在了爷爷身旁。拜祭之后,我们回祖屋敬香鞠躬。这里已经许久无人居住,但依旧打理得干净,草木在院中空地折转蔓延,却并未登堂入室。旁侧的几个厢房封了起来,唯一能打开的只有空空荡荡的大堂,香案神龛依旧彩泥灰暗,头顶光线依旧穿透屋瓦,石砖上浮凸的花纹还没有磨平,仿佛在这里,时间是无效的,近十年的时光并未在这里留下什么痕迹。
我们向爷爷奶奶鞠躬,然后退出大堂。父亲与留守老家的叔伯兄弟讨论转让祖屋所有权的事情,我坐在大堂门槛前发呆。
老家,近几年我回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在这个连大洋彼岸都可以在一日一夜抵达的时代,我花了近十年时间才回来一次。从我生活的城市,到这座大堂,短短一百多公里的路途,时间是凝滞的。
父亲告诉我,老屋附近还有一处鱼塘,时隔多年,鱼塘早已干涸,但如果修葺一下,还是能养养鱼,种点花草。至于老屋,一个叔叔占有一半的产权,父亲只有一间房。乡土势力和如今算是半个外乡人的父亲拉扯着老屋的两根梁柱。如果可以,他想将整间屋子拿下来,或者干脆把所有的产权让出去。无论怎样,应该都可以保全老屋的完整,不至于久不修葺,坐看老屋衰败垮塌。
而我却突然想起若干年前,爷爷在的时候,在他所栖身的院子里,他从一只仔细保管的红色木匣子里取出一本线装的手抄家谱端给我看。他指着纸张残缺的第一页对我说,我们江家,祖上最早可以追溯到颛顼,颛顼之后有孙子伯益,后来册封江国,姓氏就这样流传了下来。他让我仔细记住这一脉的源流,并指着家谱上逐渐繁多分散呈放射状的氏系路线告诉我,以后有人问起,你就告诉他是这么一条路线。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以后做人就不会虚。
爷爷放回家谱之后,搬出躺椅,在院子里坐下纳凉。我跑上有两间房间的二楼,这房间原先是给他的儿女们来探望时预留的,我有记忆之前,堵上了一间做储藏室,我有记忆后又堵上了一间。从二楼阳台可以望见远处的一座湖泊,那时候我刚知道鄱阳湖,所以有人问我就说可以看见鄱阳湖,其实如果不计较隔着几条连接的水系,它应该也是鄱阳湖的一部分。老家就在鄱阳湖边,因此,我面前的湖泊也能直接通向爷爷老家所在,但我那时不知道这些,我只是趴在爷爷的阳台上直到日落。
四
今年端午,我带着女儿和妻子,与父母一起回老家看龙舟。
划龙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项目,在老家,赛龙舟曾经因为赛出了火气赛成了群殴而禁绝了一段时间,近些年开了禁,也需要依照周边几个村子共同商定的条款进行。爷爷家没有太过宽阔的河湾,而隔着十几公里,外公的家门口,则正对着长年以来的传统龙舟赛道。
我们就在这里看龙舟。
外公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去世,那时我仅有模糊的记忆,记得他是乡里极有威信的人。出殡时,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几乎都来了,跟在浩荡的出殡队伍之后,棺椁已经上了坟山,队伍的末尾还没出村过河。一路上,大串大串的鞭炮隔着几百步,放了一阵又一阵。每一次鸣放,我们这些孝子贤孙就像稻穗被风吹倒在地,让棺材从头顶抬过,然后再起身追赶,在下一次鞭炮鸣响之后,再次匍匐,一直到将外公送上故乡最高的那座坟山。同样的场景,数年后,在外婆的出殡仪式上重现了一次。相比于外公的威信遍布左近,外婆的善良和贤惠也征服了同样多的村人。他们最终都留在了二十世纪,而我们跨入了新的千年。
据母亲和几个舅舅说,外公好酒,脾气暴躁,在世时常与外婆和几个子女磕磕碰碰。为此,在他走后,外婆甚至嘱咐说,以后不要与他同穴。事实上最终他们也的确没有同穴,只是住进同一座巨大的坟茔,分睡入两间墓室,共同居高临下,俯视着我们这些子孙,在他们的脚下继续生活。
我回外公家的次数也不多,但远超回爷爷家。记忆里第一次,是跟着父亲,从上百公里外搭乘一辆运货卡车,在车斗的篷布下靠着装满货物的桶或箱,一路摇摇晃晃直到天黑。下车之后,四周一片漆黑死寂,唯有一处有星点灯火,有人声隔着水面隐隐传来。那是我外公家。
外公家曾经是附近一带村落的最高点,也是从小山脚下湖边码头一路向上那条路的终点。形制与爷爷家的老屋相仿,中堂大屋,左右各有一间厢房,只是还多出了厢房侧边的厨房和隔着小路的平顶柴房。外婆在的时候,我睡在厢房里那张在乡村极为罕见的雕花架子床上,似乎这张床便能证明我外公耕读大家的身份。盛夏酷热难耐,就和舅舅和表哥到老屋前方柴房屋顶打地铺,远眺鄱阳湖面的渔火闪烁,我们在星幕下缠着大人讲故事,或者数星星。那年我恰好看了一本关于星座天文的书,便向在老家生活的表哥表姐弟弟妹妹们卖弄,然而他们对于星空的形状并不感兴趣,他们谈论各家的八卦和挣钱的门路多过其他。外公去世的那几天,我在架子床上睡不着,走到堂屋,看见几个表哥睡在堂屋的长凳上,鼾声一片,外婆和阿姨在煤油灯下用药碾子和铡刀处理药材,一边低声说些什么,昏暗的煤油灯把她们的影子拖在木墙上,那里贴着由几十张剧照和剧情注释组合而成的电影海报,字迹和图像被时间抹成淡蓝色。
后来,外婆走后,我回老家的次数骤然减少,数年仅一次。
此次回来,老屋已经由舅舅继承,在一侧又另起了一幢三层洋楼。老屋不再是村庄的制高点。而即便如此,自家修建的老屋,哪怕已经过了上百年时光,依旧稳固结实,梁柱从中间裂开,又被摩挲得包浆光滑发亮。我牵着女儿,四处游览了一遍。她保持着对陌生世界本能的谨慎,而我希望打开她的谨慎,让她与我的血脉源头链接。
然后我们去鄱阳湖边看赛龙舟。舅舅是本村龙舟的舵手,在鄱阳湖面上,带着其他七艘龙舟,仿佛雁阵回旋。
龙舟赛结束之后,早已过午睡时间,女儿依旧精神奕奕,我们驱车回家,她突然说却:“要去很小很小的乡下,还要看龙船。”
我再一次想起在爷爷那座并非故园的院子里翻看家谱的那个下午,夕阳西下,眼前湖面上的一抹丹色,将一幢幢旧房子,隔着几代人的时空,轻轻重重地盖进了我的身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