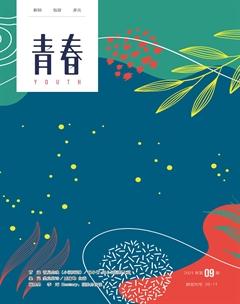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何同彬
墙上的挂钟还是那个样子
低沉的声音从里面发出
不知受着怎样一种忧郁的折磨
时间也变得空虚
像冬日的薄雾
——柏桦《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
循着逃逸线,我们将无法再见到我们逃离的一切……
——德勒兹《逃逸的文学》
差异
收录在这本中短篇小说集里的青年作家的五篇作品,构建出一种充满活力、自信的风格以及主题的差异性和多元化。《狂想一九九三》经由一种成熟、稳健、扎实的青春性、日常化的成长叙事,再现了一个特殊时代的诚与真、暧昧与悱恻、喜悦与忧伤。《木兰舟》在一片神秘的雨林和沼泽的氤氲中若隐若现,地方性、民间、民族性和神秘主义交织生成诸如生命、自然、死亡、信仰等复杂的主题;朴素、细腻、直观的写实能力,以及洞察当代家庭伦理困局的网状形态的特殊嗅觉,催生了《心梗》那种舒缓的节奏和感伤的风格;《花朝鲁》在一个貌似简单的青春爱情、侦探悬疑的故事框架里,独具匠心地铺展出关联丰富、洞幽烛微的一系列丰富的主题;《镜中人,镜中人》更像是拉康的镜像理论和三界说(象征界、想象界、实在界)的一次叙事演练,在一个颇具象征主义戏剧的恰切的氛围中,作者展现出丰沛的叙事野心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然而这些差异和多元化又显然呼应着某些当代文学的风格传统,比如青春小说、成长写作、寻根、新写实、先锋……如果把这五位作者的年龄、代际与这种呼应联系在一起,我们就难免对他们作品的外在的差异性产生疑惑。
怀旧/经验
五位作者,四位90后、一位00后,有共同的、相似的学院背景,以及与此相关的知识的、阅读的、审美经验的积累,但他们处理的题材基本上都是在他们自身的代际经验以外,从生活经验和审美经验看都带有显豁的“怀旧”性。当然,能够为文本选择的风格去构建相应的“经验”,这是当下的青年作家们具备的某种杰出的文学能力,比如一个自己未曾经历过的1990年代的氛围和精神气质,中年男女的情感、欲望和困境,充满巫性的人格的精神世界……他们都能通过自己受到的学院文学教育和相应的文学教养,构筑出让人信服的叙事的生活性和现实性,这无论如何都是让人惊讶和羡慕的。
然而,他们自己的青春和时代在哪里?为什么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消失了?他们是如何在继承已有的文学传统的同时失去了构筑自己代际传统的那种野心、蛮力,乃至莽撞、失败?这是双向选择的结果,评委们按照自身的熟悉的文学传统和审美期待选择他们认可的文本,所以才有可能把一位00后出生的作者“狂想”1990年代的作品选为头奖;青年写作者们选择了他们所受的文学教育推崇和认可的那种方式去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这显然是屈从了某种权力和规训,当然也屈从了自身的美学惯性和代际设定。选择里面充满了秩序感和区隔、削减,也许那些拥有着更属于青年人的成长经验、更属于这个时代芜杂的时代精神的文本,因其不够成熟、不够精确、不够符合传统,而被选择的机制抛弃了,同时,前一两个代际的青年作家们那些醒目而动人的“缺陷”、厌倦感和虚无色彩、反叛的幼稚情绪和革命的姿态等,也没能在这些更年轻的作家们那里得到呼应。我们看到的是比他们的前辈更老成持重的一代写作者,他们也许过早地把自身安顿于一个安全的体系之内了。
逃逸
是否“唯有旧日子带给我们幸福”?青年写作者该如何成为“这一代人”?如何从他们命定的代际秩序和文学乡愁中逃离呢?借用《狂想一九九三》的题目,他们该如何缔造属于“2021”的狂想呢?
“逃离一切,我们怎样避免重构我们的故乡和权力组织、我们的麻醉剂、精神分析以及我们的爸爸媽妈?”“逃逸线中总会有背弃。这不是奸计,不是像一个有条理的人在规划自己的未来,而是背弃,是一个简单的人不再拥有过去和未来。我们背弃的是试图拖住我们的固化权力、大地上已然确立的权力。”(德勒兹《逃逸的文学》)
这是一个陈旧而恒久的渴望,一再失落又一再被唤醒。事实证明,我们与其希望年轻人从“辖域化”的秩序中逃逸,还不如期待在一种跨越代际的共同体努力中,以一种艺术的勇气终止自身的“再辖域化”。
作者简介
《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南京市第一期“青春文学人才计划”签约作家。
责任编辑 孙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