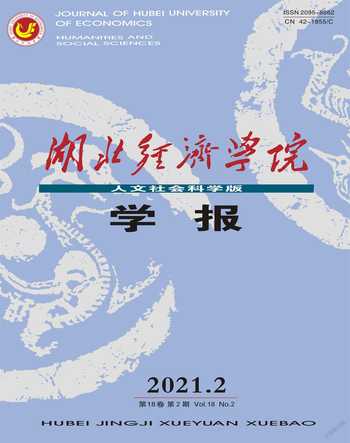医疗服务供给主体声誉机制研究进展与评述
周小梅 田小丽
摘 要:面对医患间较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医疗服务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降低医疗服务市场上的信息成本以激励和约束医疗服务供给主体行为。梳理不同制度安排对医疗服务供给主体声誉机制形成的影响。部分学者强调通过市场竞争促进医疗服务信息的传播,借助市场声誉机制激励与约束医疗服务供给行为。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可通过政府管制机构获取信息以控制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不少学者指出市场声誉和政府管制都是激励和约束医疗服务供给行为的制度安排,两者间存在交互作用,但过度管制会“挤出”市场声誉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会影响声誉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在梳理和评述文献的基础上对该领域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医疗服务;供给主体;声誉机制;市场竞争;管制
近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出促进公立医疗机构产权改革,引入民间资本及管制体系改革等政策。目前医改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医疗服务信息传播慢,市场声誉机制在短期内较难发挥作用促使政府强化管制,但政府管制导致医疗服务领域缺乏竞争,信息传播受阻,抑制了市场自发秩序形成的声誉机制有效配置医疗服务资源的功能。因此,亟需研究政府放松进入和价格管制后,在竞争环境下,如何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信息传播效率,借助市场自发秩序形成的声誉机制,实现在抑制医疗费用上涨趋势的同时提升医疗服务质量的目标,并需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发挥声誉机制功能的管制机制改革等问题。由于医疗服务领域较严重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导致交易的复杂性,大量文献基于信息经济理论研究医疗服务业治理模式。
一、信息经济理论在医疗服务领域应用的研究
与一般产品或服务不同,医疗服务是由医疗机构及从业人员(医务人员)提供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异质性的服务。Nelson(1970)根据消费者在购买前后拥有信息不同将产品和服务分为搜寻品、经验品和信用品[1]。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对患者而言,医院等级规模等属于搜寻品(就医前就了解),医生服务态度等属于经验品(就医后才了解),而诊疗方案等属于信用品(就医后也很难了解)。由于医疗服务供给有较强专业性,医疗服务存在较严重信息不对称,即部分医疗服务信息表现为信用品属性。这一特征也使得信息经济理论广泛运用于医疗服务领域的研究。医疗市场与其他市场间的差异在于医疗服务的不确定性,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提供者与保险公司(或政府)间普遍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国内学者也认识到医疗市场上存在广泛信息不对称,冯邦彦和李建国(2007)对医疗服务领域中信息不对称进行细分,即主要是医疗机构与政府部门、医生与患者、医生与医院以及医保机构与医疗其他相关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2]。
由于供求双方是医疗服务交易的核心环节,部分学者就医院、医生与患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展开研究。医患间信息不对称主要是作为代理人的医生拥有绝对多的医疗专业技术信息,而作为委托人的患者往往对医疗信息极其匮乏。医疗服务领域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在公费医疗制度下,患者存在过度医疗需求;另一方面是医生和医院为提高收入,利用信息优势向患者提供不必要的诊疗服务,如开大处方、大检查和延长住院时间等(吕国营,2004)[3]。根据卢洪友等(2011)的测算,医患双方凭借各自掌握信息程度议价最终形成交易价格高出相对公正基准价格26%[4]。另外,由于缺乏真实医疗信息且搜寻信息成本高,患者可能直接去相对规范的大医院,而不选择最便利、最有效且节省成本的小医院,这导致医疗资源配置低效率(范超和沈丹平,2015)[5]。
学界对医疗服务交易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基本达成共识。因此,医疗服务业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降低医疗服务市场上的信息成本。而降低信息成本,一是在市场竞争环境下医疗服务需求方传播信息,借助市场声誉机制激励与约束医疗服务供给行为;二是通过政府管制机构获取信息以控制医疗服务供给方的道德风险。部分文献从这两方面展开研究。
二、市场声誉机制激励与约束医疗服务供给主体研究
(一)市场声誉激励机制及其对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影响
Fama(1980)提出声誉激励的思想,认为在竞争性代理人市场上,代理人市场价值取决于市场期望,而这种市场期望由观测到的过去业绩水平决定。声誉激励下代理人会自觉地付出努力,改进代理人市场上的声誉评价,以提高长期收益[6]。Holmstrom(1999)建立声誉模型,进一步证明声誉隐性激励机制的存在[7]。
部分学者采用信息经济理论研究市场声誉机制与产品服务质量间的关系。Akerlof(1970)对劣质产品市场问题的经典分析证明,建立品牌声誉为消费者提供质量担保可解决信息不对称,克服“次品”问题。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市场声誉机制可调节产品质量,产品售价反映其质量,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声誉良好企业的产品,企业声誉是产品质量隐性特征,企业声誉越好,买者对其产品质量认可度越强[8]。因此,市场声誉是一种隐性契约,具有资产属性,且有信号显示效应和溢价效应,产品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时,良好声誉能使产品溢价,而溢价又促使经济主体长期维护良好声誉,声誉机制作用下不需政府对产品质量进行干预(Davies et al.,2004)[9]。就信用品属性产品质量而言,消费者根据卖方声誉判断产品质量,而消费者重复购买可提升企业声誉,提供足够产品和服务质量信息,声誉机制在信用品市场起作用,关键是如何建立可靠的声誉机制(Goldsmith,2001)[10]。Clay(1997)提出可设立中介组织(如商会、行业协会等)维系声誉传递,促进交易进行[11]。
国内学者中,张维迎(2002)指出重复博弈、市场主体机会主义行为能被及时发现且受到足够惩罚,以及经济主体要有足够耐心和长远预期是市场声誉起作用的条件[12]。而声誉惩罚机制的启动需要跨越信息鸿沟,促进质量信息流动,解决信息不对称、不完备问题(吴元元,2012)[13]。张耀辉(2006)认为市场声誉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内在机制在于消费者重复购买给企业带来额外利润即质量酬金,声誉是质量酬金的一部分,声誉机制越发达,越抑制低质量[14]。值得注意的是,竞争市场下的价格包含质量信息,购买时消费者通过品牌声誉对产品质量進行鉴别从而做出消费选择(周燕,2016)[15]。通过与法律和管制等机制进行比较,杨居正等(2008)强调声誉机制是一种作用范围广泛且成本更低的机制。中国缺乏高声誉品牌的原因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和市场竞争不充分[16]。蔡洪滨等(2006)则从动态角度考察重复博弈均衡,发现低信任与低质量相互作用使得中国企业信誉陷入低效率陷阱,但长期看,中国市场经济会经历从低效率均衡向高效率均衡演变,但演变时间长短与初始信念、信息清晰度、信誉溢价、提升产品质量的相对成本及政府改革力度有关[17]。
近年来,伴随网络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网络交易平台市场声誉与产品和服务质量间的关系。声誉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对网络平台的信任(曾小春,2007)[18],消费者愿意为信用度高、声誉好的商家支付较高价格,且进行多次交易,而卖家个人声誉可增加商品销量并获得声誉“溢价”(李维安等,2007)[19]。在网络交易环境下,声誉通过口碑表现,而口碑即消费者在电子商务交易平台信用评价系统的反馈评分,信用評价系统汇集商家声誉、卖方商品售价及销量等方面数据,消费者查看评价以了解商家声誉(Dellarocas,2003)[20]。为维护声誉,网络交易平台通过第三方支付、信用评价、商盟制度和消费者保障等建立信任机制(王小宁和李琪,2009)[21]。特别是网络交易平台大数据使商品销售进入全渠道信息传播时代,网购是信息流转过程,消费者可浏览、搜索、分析及传播信息,消费者购物时首先在意电商平台的可靠性及网络信息真实性,消费者感知风险程度决定其购买决策(朱光婷,2014)[22]。网络平台信用评级决定信誉高低,从而决定市场优胜劣汰。政府监管部门可利用网络平台大数据形成的信用评级促进声誉激励约束机制的运行。因此,网络交易平台信任机制的私人秩序对效率低下的公共秩序有一定的替代作用(章向东,2014)[23]。
综上,声誉机制的隐性契约性质有助于降低具有信用品属性产品和服务的交易成本。声誉机制不仅可引导消费者的购买选择,还可激励企业提供具有良好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诚然,市场声誉机制的有效运作取决于相关制度设计。值得关注的是,网络交易平台上建立的第三方支付、商家信用评价、商盟制度和消费者保障等制度为市场声誉机制的运作提供了有效的支撑,而互联网大数据信息传播效率提升对于发挥市场声誉机制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显然,网络交易平台设计的相关制度是市场自发秩序形成声誉机制的关键。
(二)医疗服务市场竞争环境下的声誉激励机制
关于市场竞争环境下声誉机制是否有助于激励与约束医疗服务供给行为方面存在争议。争议核心在于医疗服务市场与一般产品服务市场的差异。理论及经验分析证实了这种分歧。理论的复杂性主要产生于医疗服务市场的不完备性(Arrow,1963)[24]。面对医疗服务市场的不完备性,为降低医疗服务供给方道德风险,医疗服务市场由非营利性医院占主导地位(Gaynor & Haas-Wilson,1998)[25]。“非营利性”向市场传播一种信息,即医院提供医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以此获取患者信任。然而,关于哪种产权性质在经济上更有效率,研究结论存在冲突。部分研究发现营利性医院运营成本更低(Rundall & Lambert,1984)[26],但也有研究结论认为营利性医院成本更高(Ettner,2001)[27]。还有部分研究发现,非营利性和营利性医院成本没有差异(Sloan et al.,2001)[28]。许多研究考察了医院产权对患者健康结果的影响。其中,部分研究发现营利性医院提供更低质量服务(Hartz et al.,1989)[29],而更多研究却发现,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医院间,医疗服务质量没有差异(Budetti et al.,2002)[30]。综合这些研究发现,“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向市场传播的声誉信息对相应医院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存在争议。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向医疗服务领域不断引入民营医疗机构。但伴随民营医疗机构发展,争论始终未停止。基于医疗服务市场的特殊性,部分学者认为,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未必能带来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强调医疗服务应以非营利性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运营模式。而部分学者认为,民营医疗机构参与市场竞争,市场声誉的激励和约束可提高医疗服务供给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因此政府应制定政策鼓励民营医疗机构和公立医疗机构在相同环境下平等竞争。李文中(2008)提出,为控制医方道德风险,可通过引入市场竞争以及发挥声誉机制的激励和约束作用[31]。而建立声誉机制的关键在于信息有效传播,应由政府相关部门建立专门医疗服务信息平台,搜集并处理各家医院医疗服务价格和质量信息,并向社会公众公布(孙洛平,2008)[32]。鉴于此,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第三方医疗质量评估中介,对医疗机构进行声誉评价,为公众选择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参考。面对医患间存在严重谈判权不对称问题,唐要家和王广凤(2008)强调政府管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谈判权不对称分布带来的医生机会主义行为,医患合约设计的核心应当是形成有效的医生声誉激励机制[33]。而医疗服务需求的不确定性导致缺少重复消费以淘汰不合格医院或医生,促使医疗机构行为趋于短期化而不是着眼于长期声誉的维护(周小梅,2009)[34]。事实上,私立医疗机构一旦建立起声誉机制,能够逐渐获得市场认可(王箐和魏建,2012)[35]。在我国医院声誉社会评价缺失情况下,高山和石建伟(2011)提出建立以患者参与为基础的“自下而上”声誉评价体系,除了对以医疗服务为核心的医疗技术评价外,还对医院内部管理、外部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未来发展创新等进行综合评价,以期评价反馈最终回归于为患者就医提供客观有效的信息[36]。针对目前我国政府主导医院声誉评价的现实,周小梅和刘建玲(2018)认为政府应鼓励发展第三方医院声誉评价机构,从而使公众拥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做出最优的就医选择[37]。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部分学者对互联网与传统医疗服务业的结合展开研究。研究发现,搜索引擎是最主要互联网健康信息获取工具,“互联网+医疗”正通过变革就诊流程、医院协同模式、健康管理方式、药品服务形式等重构医疗生态,但公众对来自网络的医疗信息不能进行有效鉴定,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孔维琛,2015)[38]。张浩辰(2016)指出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智慧医疗体系将通过两个机制解决现行医疗模式缺陷:一是通过引入网络声誉评价体系,最大程度降低医患间信息不对称;二是推动医疗信息资源共享共用,优化医疗资源配置[39]。基于三家医疗机构实地调研,王安其和郑雪倩(2016)发现移动互联网技术运用于医疗服务已基本成熟,能够显著降低医疗成本,提升医疗服务效率,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40]。
现有研究成果证明,市场声誉机制在一般产品和服务市场上对引导资源有效配置起到很好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尽管医疗服务信息不完备和不确定性问题较为突出,但长期看,通过向医疗服务领域引入民营医疗机构,促进竞争,可有效提高信息传播效率,让市场声誉机制在激励和约束医疗服务供给主体行为方面发挥应有的功能。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医疗的出现和发展,提高了医疗服务信息传播效率,降低了就医者获取信息的成本,这有助于市场声誉机制在医疗服务领域发挥作用。尽管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市场声誉机制在引导医疗服务资源配置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全面系统研究放松管制等医改政策推进过程中,如何通过促进医疗服务领域的竞争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并借此发挥市场声誉机制在配置医疗服务资源方面作用的研究尚显欠缺。
三、医疗服务政府管制、放松管制与市场声誉间关系研究
多数学者认同政府管制是为克服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不完备性,但对于政府管制内容也存在争议。对管制机制设计问题上,Kumaranayake(1997)认为管制制度不完善会导致管制失灵。因此,管制制度的设计和管制能力提升是关键。且这种政府干预将随着不同制度以及管制能力的变化而调整[41]。Justin Waring et al.(2010)以英国医疗服务管制体系为研究对象,分析英国在对医疗服务业进行市场化和公共管理改革过程中,行业自律管制不断削弱,而政府管制得到强化。改变了控制和引导医生行为和绩效的机制,同时也重构了医疗行业、政府、公众和患者间的关系[42]。发达国家医改实践说明,在通过市场声誉激励和约束医疗服务供给主体行为的同时,实施相应管制约束,对医疗服务业有序发展产生一定引导作用。然而,由于管制不同程度上会限制医院发展,且管制过程本身也会发生相应交易成本。管制导致医疗服务出现短缺。因此,对医院进行管制的方法在许多国家已开始遭到质疑,出现了从管制约束方法转向以市场激励为基础的改革。在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医疗服务业管制效果不断减弱,最终导致放松管制。根据Robin Allen & Paul Gertler(1991)的研究结论,多年管制实践说明,在医院生产能力和医疗服务费率管制背后存在着使医院成本快速膨胀的驱动力。费率管制对医疗服务支出没有很大影响[43]。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施管制后,医院成本膨胀与通货膨胀间的缺口没有太大变化。这是因为,医疗服务业管制存在着与其他被管制产业一样的激励问题。为此,美国开始向医疗服务市场引入竞争以加强医院的成本意识。竞争性进入迫使低效率医院改变运营模式、出售或关闭。鉴于政府管制失灵,不少发达国家政府在医疗服务领域开始实施放松管制政策。
面对医疗费用和服务质量控制等问题,我国部分学者就管制内容和手段等展开研究。鉴于医疗服务支付体系的特殊性,谢子远等(2005)通过分析医疗服务产品的异质性、不可逆转性及服务过程中严重信息不对称,认为医疗服务市场需引入“第三方购买”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44]。而李永强和朱宏(2014)指出信息不对称下个体消费者处于弱势,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价格管制有其必要性[45]。为避免管制失灵,刘颖和杨健(2016)从监管合法性和民主性角度提出政府监管机构必须与医疗机构实现“管办分离”,才能保证监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保持独立性,防止“管制俘获”[46]。而基于医疗服务领域各方利益主体间的关系主要借助契约进行约束,费太安(2013)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作为分析框架,提出针对契约不完全程度分领域分层次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47]。
观察管制政策实施效果发现,尽管政府对医疗服务业实施管制是为矫正市场失灵,但多年来“看病难,看病贵”等医疗领域的突出问题让部分学者开始反思政府管制必要性和科学性,提出医疗服务业应实施放松管制政策。
研究发现,市场声誉和管制都是维持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手段,两者间存在交互作用。但过多管制会“挤出”市场声誉发挥作用的空间,甚至会影响声誉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杨居正等,2008)[16]。李鹏飞等(2006)的分析表明,当存在医疗服务价格管制时,若管制机构无法完全约束医生收取其他相关费用,则必定会导致“以药养医”等规避价格管制行为[48]。因此,“以药养医”体制改革需同时放松对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角度,龚秀全(2010)提出医疗服务领域中只有政府与市场合作协调,才能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效率的基础上尽可能減少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但促进政府与市场合作协调需要相应的机制保障[49]。朱恒鹏(2010)强调我国要走出“看病贵”困境,应实施放松管制政策,取消价格管制、消除公立医疗机构垄断以实现医疗服务市场的充分竞争[50]。就政府各种控制医疗费用失效的事实,姚宇(2014)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医疗服务提供方和费用支付方都没有控费的动力和压力,应构建以患者为主体的有效控费机制,在向医疗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情况下,政府相关部门不再对医院控制医疗费用水平提出无效要求[51]。薛大东(2015)认为在政府主导的医疗服务供给体制中,医疗机构声誉并非市场自发秩序形成,这在很大程度上会阻碍声誉机制的激励约束功能。为更好地发挥市场声誉机制,必须重构医疗服务供给体制[52]。
近年来,互联网医疗发展成为政府管制“真空”地带。诚然,互联网医疗一方面反映新技术突破政府进入管制壁垒,为医疗服务供求方创造市场机会,但另一方面互联网医疗对政府管制提出挑战,为维护平台声誉尚需行业自律管制和政府干预的协同作用(Bruce Merlin Fried et al.,2000)[53]。David & Atul(2000)分析互联网对医疗质量信息传播的积极作用,认为互联网提供了低成本、标准化平台,打破了收集有用质量信息并向患者及相关群体传播的壁垒[54]。但医疗服务质量信息的复杂性及互联网突破地域限制,对医疗服务质量管制提出新的挑战。目前互联网医疗管制机制尚未建立,患者面临一定风险(赵大仁等,2016)[55]。张山、马骋宇、郑云珩(2019)提出,互联网医疗平台对患者就医起到引导作用,为确保线上医疗信息的真实性,政府应加强在线医疗服务信息管制[56]。
部分研究表明,我国医疗服务业仍存在政府过度干预,医疗服务供给垄断性限制了患者选择;医疗服务价格管制抑制了供给方追求长期收益的动力;“管办不分”的政府管制机制阻碍信息高效传播,抑制市场声誉机制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我国医改实践表明,直接经济管制未从根本上改变医疗供给方激励机制。这一方面导致管制低效率,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市场声誉机制。因此,研究如何通过放松管制,优化我国现有医疗服务管制机制,在提高管制效率的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声誉机制对医疗供给方的激励和约束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四、研究评述
综上分析,尽管国内外大量成果围绕医改及医疗服务市场声誉和管制机制展开研究,但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领域。
其一,国外学者主要从医疗机构产权性质、市场竞争及管制机制的激励作用等角度研究医改问题。从研究结论看,医疗服务交易的复杂性导致部分研究结论存在分歧。这反映医改研究具有一定挑战性。国内学者就医改政策也不乏各種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医疗服务业是否适合引入民营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业引入竞争是否有助于控制医疗费用及改善服务质量?政府是否需对医疗服务实施管制?如果管制机制是维护医疗服务供给主体声誉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如何优化管制机制?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为我国医改方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诚然,发达国家医改经验值得借鉴,但对转型期我国医疗服务业而言,有其特殊的制度和政策背景。因此,研究我国医改政策取向可为深化医改提供参考。
其二,声誉机制功能发挥需要相关信息的有效传播,且声誉机制在一般产品和服务市场中对供给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和约束作用。鉴于医疗服务业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等特征,较多成果认同政府对医疗服务业实施管制可弥补市场失灵。然而,国内外医改实践证明,医疗服务管制一定程度降低了相关信息传播效率,抑制了市场声誉机制本应发挥的功能。且受资源及政府执政能力约束导致管制效率低下。鉴于此,研究放松管制下声誉机制对医疗服务供给主体的激励和约束尤为重要。国外不少学者对市场声誉机制的激励和约束功能有较深入研究,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较长,在较成熟市场环境下,供给主体较注重良好声誉的建立和维护。但就医疗服务市场自发秩序形成声誉机制与管制机制间互补和替代关系的研究尚较少。从国内研究现状看,较多成果研究引入市场竞争对医疗服务业效率和质量提升的积极作用,但就医改背景下政府放松管制对医疗服务信息传播效率的影响,以及信息传播如何促进市场声誉机制功能的发挥,继而激励和约束医疗服务供给主体,目前尚缺乏系统研究。
其三,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互联网医疗发展趋势,并提出这种跨区域医疗服务提供方式一方面改变了医疗服务组织形式,另一方面可能给政府管制带来新课题。结合互联网医疗信息传播对声誉机制功能发挥的作用,研究互联网医疗声誉机制形成机理以及相应管制机制改革是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
其四,从国内研究现状看,虽有学者以省(自治区)或市的医疗服务业为研究对象,跟踪研究医疗服务业改革。但针对不同市场和管制制度环境研究医疗服务供给主体声誉机制尚不多见。
综上,国内外学者关于公立与私立医疗机构、竞争与管制等医改政策效果的研究均有丰富成果,但研究结论尚有争议。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政府管制主导下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尚不成熟,地域差异大,且医改历时短。在此背景下,研究激励和约束医疗服务供给主体声誉机制更具复杂性和探索性。
参考文献:
[1] Nelson, Phillip. Information and Consumer Behavio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0,78(2):311-329.
[2] 冯邦彦,李建国.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医疗改革价格问题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7,(1):42-45.
[3] 吕国营.个人声誉、集体声誉与医生道德风险[J].理论月刊,2004,(3):126-128.
[4] 卢洪友,连玉君,卢盛峰.中国医疗服务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测算[J].经济研究,2011,(4):94-106.
[5] 范超,沈丹平.信息不对称对医患关系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中国市场,2015,(35):142-143.
[6] Fama,E.F. Agency Problems and The Theory of the Firm[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0,88(2):288-307.
[7] Holmstrom,B. Managerial Incentive Problem-A Dynamic Perspective[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9,66(1):169-182.
[8] Akerlof, G. The Market for“Lemon”: Quality Uncertainty and the Market Mechanism[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70,84(3):488-500.
[9] Davies G et al. A Corporate Character Scale to Assess Employee and Customer Views of Organization Reputation[J].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2004,7(2):125-146.
[10] Goldsmith R E. The 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Perceived Corporate Credibility[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01,52(3):235-247.
[11] Clay, K. Trade Without Law: Private-order Institutions in Mexican California[J].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s,1997,13(1):202-231.
[12] 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J].经济研究,2002,(1):3-13.
[13] 吴元元.信息基础、声誉机制与执法优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视野[J].中国社会科学,2012,(6):115-133.
[14] 张耀辉.产业组织与规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15] 周燕.政府监管与市场监管孰优孰劣[J].学术研究,2016,(3):89-99.
[16] 杨居正,张维迎,周黎安.信誉与管制的互补与替代——基于网上交易数據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7):18-26.
[17] 蔡洪滨,张琥,严旭阳.中国企业信誉缺失的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2006,(9):85-93.
[18] 曾小春,王曼.电子商务的信任机制研究—针对不同模式的比较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7,(2):57-63.
[19] 李维安,吴德胜,徐皓.网上交易的声誉机制—来自淘宝网的数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7,(5):36-46.
[20] Dellarocas,C. The Digitization of Word of Mouth:Promise and Challenges of Online Feedback Mechanisms[J].Management Science,2003,49(10):1407-1424.
[21] 王小宁,李琪.声誉与保障机制对网上交易的影响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09,(6):106-112.
[22] 朱光婷.大数据环境下网络消费者行为研究[J].经济与决策,2014,(23):59-61.
[23] 章向东.大数据时代我国信用评级业重构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6):95-100.
[24] Arrow K.J. Uncertainty and the Welfare Economics of Medical Car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3,53(5):941-973.
[25] Gaynor M., HASS-WIlSON D. Change, Consolid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Health Care Markets[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9,13(1):141-164.
[26] Rundall, T.G., LAMBERT W.K. The Private Management of Public Hospitals[J].Health Services Research,1984,19(4):519-544.
[27] Ettner,SL. The Setting of Psychiatric Care for Medicare Recipients in General Hospitals with Specialty Units[J].Psychiatric Services,2001,52(2):237-239.
[28] Sloan, F.A. et al. Hospital Ownership and Cost and Quality of Care: Is There a Dimes Worth of Difference? [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2001,20(1):1-21.
[29] Hartz et al. How Physicians Use the Stress Test for the Management of Angina[J].Medical Decision Making,1989, 9(3):157-161.
[30] Budetti, P.P. et al. Physician and Health System Integration[J].Health Affairs,2002,21(1):203-210.
[31] 李文中.医疗服务市场的道德风险和声誉机制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08, (10):23-26.
[32] 孙洛平.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性分析[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177-182.
[33] 唐要家,王广凤.“过度医疗”的制度根源与医生声誉激励机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4):43-48.
[34] 周小梅.提升医疗服务业绩效的制度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5] 王箐,魏建.我国医院市场的竞争效果——基于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科学,2012,(2):115-125.
[36] 高山,石建伟.公立医院“自下而上”的声誉评价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J].经济经纬,2011,(2):107-112.
[37] 周小梅,刘建玲.我国医疗服务业改革进展、问题与展望[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8,(5):5-11.
[38] 孔维琛.互联网:重构医疗生态[J].中国经济信息,2015,(15):30-33.
[39] 张浩辰.互联网与中国医疗模式变革研究[J].中国物价,2016,(4):62-65.
[40] 王安其,郑雪倩.我国互联网医疗运行现状—基于3家医院的调查分析[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1):69-73.
[41] Kumaranayake, L. The Role of Regulate: Influencing Private Sector Activity Within Health Sector Reform[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7,9(4):641-649.
[42] Justin Waring et al. Modernizing Medical Regulation: Where Are We Now?[J].Journal of Health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2010,24(6):540-55.
[43] Robin Allen, Paul Gertler. Regulation and the Provision of Quality to Heterogenous Consumers: The Case of Prospective Pricing of Medical Services[J].Journal of Regulatory Economics,1991,3(4):361-375.
[44] 谢子远,鞠芳辉,郑长娟.“第三方购买”:医疗服务市场化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经济学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5,(11):51-58.
[45] 李永强,朱宏.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价格的政府管制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14,(8):28-30.
[46] 刘颖,杨健.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领域政府监管责任若干问题研究[J].岭南学刊,2016,(3):88-94.
[47] 费太安.我国医疗服务提供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理论与实践走向[J].财政研究,2013,(7):52-56.
[48] 李鹏飞,汪德华,郑江淮.医疗服务价格管制与“以药养医”[J].南方经济,2006,(8):68-76.
[49] 龔秀全.医疗服务生产中的保障机制:基于政府与市场分工[J].改革,2010,(6):135-140.
[50] 朱恒鹏.还医生以体面:医疗服务走向市场定价[J].财贸经济,2010,(3):123-129.
[51] 姚宇.控费机制与我国公立医院的运行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4,(12):60-80.
[52] 薛大东.建立医疗服务市场声誉机制与转变政府职能[J].理论导刊,2015,(4):17-18,30.
[53] Bruce Merlin Fried et al. E-health: Technologic Revolution Meets Regulatory Constraint[J].Health Affairs,2000,19(6):124-131.
[54] David,W. Bates, Atul, A. Gawande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Quality Measurement[J].Health Affairs, 2000,19(6):104-114.
[55] 赵大仁,等.我国“互联网+医疗”的实施现状与思考[J].卫生经济研究,2016,(7):14-17.
[56] 张山,马骋宇,郑云珩.互联网医疗健康平台医院声誉排名有效性比较[J].中国医院,2019,(9):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