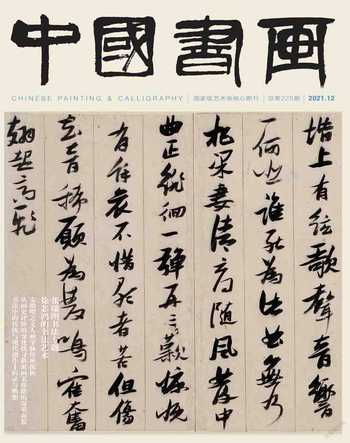“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笔谈两札
陈履生 曹庆晖


陈履生致曹庆晖札
庆晖教授,您好!
非常高兴看到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您的《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中国美术》《走进学院的中国画》两本专著。
感谢您的馈赠。两本专著反映了您近年的学术方向和学术成果,确实不一般。作为中年学者,您在近现代美术史个案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基于自己从教的中央美术学院而展开的多方面的研究,让人刮目相看。毫无疑问,关于近现代美术史的研究,这几年已经改变了过去“冷”的状况,显得非常“热”,但是,像您这样深入细致地做个案研究的依然是稀缺。对于近现代美术研究,现在有很多问题,可能表现在很多方面,但缺少对美术史论的感觉,缺少对美术史论的兴趣,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方面。很多年轻的学者是为了学位而进入这个专业之中,一切都非常勉强。
对于当下美术史的研究,我们该如何进行?尽管现在人多势众,但是我们整体的学术水平不高、不深、不广、不专。面对如此状况,您的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个示范,它让我们看到了您所选择的“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中国美术”这样一个题目,并非完全是研究本体的意义,由此还可以引发对当代美术史研究的反思。“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中国美术”是要数十本书才能完成的一个专题,您起了一个很好的头,相信您的学生或者我们业内的同仁都可以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做深入的研究。因为20世纪初以来的美术教育的发展,对于20世纪中国美术的成就有着特别的关系。中央美术学院或其他艺术院校对于美术教育的发展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中央美术学院对于全国的辐射作用,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美术教育发展中应该是一个共识。基于此,中央美术学院不仅是培养了很多著名的画家、杰出的教授,而且其学生也分布于全国的美术院校之中,开枝散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和影响。那么这些影响何在?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而由此来看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美术之间的关系问题,其中的人和事,其中的教育规律和教育的本质,以及教育中出现的问题等,都是值得研究的。因此,在“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中国美术”这个题目之下,除了书中4个方面之外,应该还有其他很多方面,而在4个方面之内也还有能够丰富它的其他方面。毕竟您的大著只是一本文集。可以预料的是在您所提出的这个大题目下,未来还可以见到您更多的研究成果。
与之关联的“走进学院的中国画”,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题目。它可以看成是上一本书中的一个章节。您对“三位一体”的学院教育的发展过程的研究,我感觉下了很多的功夫,而且材料丰厚,论述精当。基于此的所有研究,我以为对于我们今天来认识“走进学院的中国画”,都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走进学院的中国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仅是关系到中国画自身,还关系到学院中国画与整个中国画发展的关系问题。这之中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对当代中国画发展的影响是什么?书中所揭示的能够说明问题的史料,都说明了过往历史中的一个过程,有些是无奈,却影响广泛而深远。
就具体而言,第三章所谈到的“三位一体”的形成追踪,其中的墨画、彩墨画和中国画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我细细地看了这一部分内容,对所提出来的“墨画”这个词,感觉有点突兀。我非常好奇您为什么用这个词?您在论述里没有交代清楚它的来源,只是有一个注释里面提到,但是不够详尽。因为这个词比较生涩。我们通常所说的是“水墨画”,而历史上对应的是“彩墨画”,您在文章中说过“墨画”的词源是“水墨画”,那么,“墨画”是否等同于“水墨画”,它们之间有没有差异?差异在哪里?而“走进学院的中国画”,与社会上的中国画,有没有异同?都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疑问。对于这样一个美术史的概念问题,我相信您能提出来自有其中的道理,但是应该给读者一个交代。不管怎么说,您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哪怕是所关联的历史研究中的方法问题,或者是其他,都是值得研究的。
以上是我大致翻了一下以后的读后感。我还要继续再读、再看、再研究这些问题。您的大著给予我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我相信也有很多读者和我一样,看到这两本很厚的专著之后都会有所得,都会沿着您的路线去思考这一方面的问题。
再次祝贺您的著作出版。谢谢。顺致
教安
陈履生
2021年10月25日于得心斋
曹庆晖复陈履生札
陈老师,您好!
没想到您这么快就回信,我知道您很忙,所以特别感谢您愿意花时间翻阅这两本书并及时分享您的看法。
说实话,在我把这两本书安排递出之前,并未奢望您真的能写点什么。没想到您会以笔谈的方式及时和我交流您的感受和意見,也没有想到这两本书会让您联系中国现代美术研究现状而有所感慨。您以“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中国美术”作为观察和评论的角度,去整体看待《美育一叶》《走进学院的中国画》这两本书的收获与进展,在科研方向和方法上给予的肯定与鼓励,令我感到温暖。特别是您提出“墨画”这个具体的问题向我质疑和求证,更令我感到师友同道间开诚布公交流的亲切。您的热情和敏锐促使我要把想和您讲的内容认真捋一捋,回一封信谈一谈。真的特别感谢您以写信笔谈这种传统方式,给予我能够与您写信交流请益的机会。
按照今天日新月异的成果出版速度来说,我的这两本书其实都已经不是新书了。这两本书中您置后评论的《走进学院的中国画》,较早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在2019年9月出版,主要讨论的是现代美术语境中的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教学体系形成史,是以学科变革观察中国现代美术变革的一次“解剖麻雀”的个案深入。而您先行评论的《美育一叶》,是一本由日常科研积累起来的书。如您所看重的那样,它从日常研究所归纳出的几个方面,以小见大,呈现了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这个课题。其中《艺专名单补遗》和《美术史论教研纪程》这两篇突出资料整理与分析的文章,是在编辑过程中出于内容需要而斟酌编写的。目前,学术期刊不会发表这种史料编研文章,但我觉得却是研究之必须,惠人之食粮,所以趁机收入,一体编辑,定名为《美育一叶—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中国美术》,交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C I P数据是2020年8月,但因疫情一度严重影响石家庄,一直耽搁到2021年8月底才印出来。书出即过期,这也是抗疫年代给我的一个特别的记忆。
如您所言,中央美术学院与近现代中国美术是一个大题目,在上述两本书里我虽然涉及一些方面,但也基本是个起步,值得再研究和再讨论,另外还有其他方面值得去开拓和挖掘。您的鼓励于我很重要,这让我更加明确要持续关注以学院、学科为中心的现代美育(美术)演变讨论,抓住重要選题的重要方面,力所能及地做些扎实的基础工作。我关注这方面并投入调查研究确实由来已久,目前还多聚焦于1918年以来的北京美术学校、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中央美术学院这条历史脉络上,但日常如有关联性的研究课题和条件,触角也努力向外蔓延,这方面的努力和进展在书中也有体现,比如梳理胡一川和讨论杨之光与中央美术学院的联系。您和美术界一些老前辈多有往来,私交甚笃,其中不少出身或任职于重要的美术高校,了解各时期前前后后的情况,今后如有问题和需要,还要请陈老师多加帮扶。
我之所以关注中央美术学院,主要还不是由校系史、学科史研究的需要出发,作为专工中国现代美术研究的美术史系教员,我更关注的其实还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发生和演进。但我深知获取材料的可能或便捷对于研究起步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对近现代中国美术研究而言,占有材料不充分,进入历史不深入,很容易被各种自以为是的揣测和流行理论的解释带跑偏了。同时我深知学院在中国美术现代演进与变革中发生的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不了解学院,不针对学院艺术史开展调查研究,其实很难理解中国现代美术中的种种问题。所以我应该感谢已有百年史的中央美术学院,是它让我知道可以从这扇窗观看中国现代美术江河的风景和浪潮。
具体到您质疑和求证的“墨画”一词,在我最初接触到时也感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从何而来。我们一般所知,进入1949年后,有关于“彩墨画”与“中国画”的不同命名与争论,但罕见大家议论过所谓“墨画”,但通过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学档案,可以非常清楚地获悉这个词汇。它与我们头脑中即刻反应的“水墨画”在词源上有关联,但在观念上有间离。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央美术学院推行普及教育时,它更多的意义是用于教学组织,但其中也夹杂着标示新画种的企图。像墨画科、墨画组这样的建制名称在当时的教学文件里俯拾皆是,其教学任务主要教勾勒,但又非传统的“十八描”,而是吸收了素描造型观念又要求骨法用笔的线描,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对接年连宣创作中的形象塑造。以后,虽然经过“彩墨画”“中国画”这样的名称演变,“墨画”一词在教学组织中逐渐不再使用,但对墨画的教学理解却已经完全渗透在中国画造型基础的教学里了,这方面从前到后的主导教授就是蒋兆和先生。以上是我《走进学院的中国画》第三章第一节“为了‘创作的‘墨画”的大略交代。我不知道我的答辩是否消除了您的疑惑,抑或是让您更疑惑了。但无论怎样,我觉得通过教学环节梳理和捕捉教学用词,具体讨论新中国画在教学中的形成和变革,马上就引起了您的注意,这说明这种方法和方法下的内容发现还是有效的。
暂就谈到这里,有机会遇见再向您当面请教。在微信朋友圈里常常看到您持续更新公众号里的评论文章,平常也总能得到您的各类成果。我就很纳闷,您这一天一天的时间到底是怎么规划的,怎么能做这么多事呢?多保重。
再次感谢您的来信。祝
秋安!
曹庆晖
2021年10月31日于海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