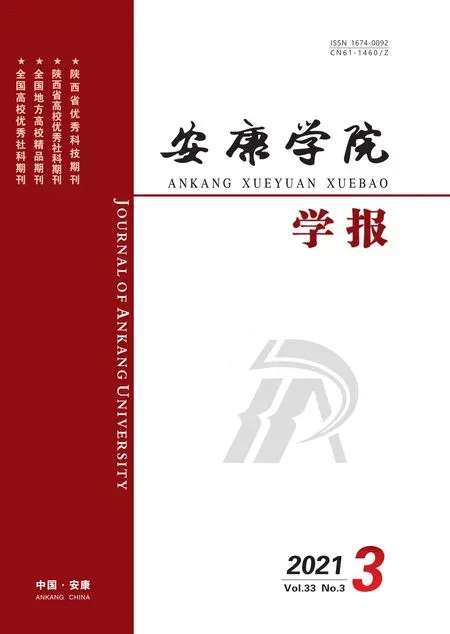明代张籍诗接受研究
——以唐诗选本为考察中心
谭春蓉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张籍(约766—约830),字文昌,和州乌江人,元和诗坛代表诗人,现存诗450余首。目前学界对张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考证及诗歌文本研究方面,对其接受研究仅见傅小林《张籍诗歌在中晚唐的传播与接受》[1]一文。张籍诗歌在明代的接受传播尚无专文研究。明代出现大量唐诗选本,众选本对元白诗派的评价普遍偏低,但对张籍的评论却相对颇高,其诗歌地位甚至远超白居易与元稹。鲁迅指出:“凡是对学术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展和流布自己的主张的手段,倒并不在于作文心、文则、诗品、诗话,而在出选本。”[2]本文通过考察明代唐诗选本对张籍的接受情况,试图对其地位远超元、白的原因作出揭示。
一、凌驾元白:张籍在明代唐诗选本中的接受程度
查清华《明代唐诗接受史》将明代唐诗接受分为三个时期:洪武元年到成化末年(1368—1487)为前期,弘治元年到隆庆末年(1487—1572)为中期,万历元年到崇祯末年(1572—1644) 为后期[3]。本文以此为据,列出明代前、中、后期具有代表性的14个选本选录张籍诗歌的情况,以考察张籍在明代不同时期的接受程度,并列举刘长卿、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的选诗数量,以便比较分析。众选本选诗数量如表1所示。

表1 明代唐诗选本选录张籍诗歌数量
明初120年,明人自编唐诗选本较少,多为元代的重刊本,其中影响较大的明选本有高棅《唐诗品汇》《唐诗拾遗》《唐诗正声》,以及康麟《雅音汇编》。高棅《唐诗品汇》编于明洪武甲子年(1384),完成于洪武癸酉年(1393),历时10年,选诗人620家、诗5769首。高棅“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4]14,选张籍诗歌72首,虽少于刘长卿167首,但同比高于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张籍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均被列为接武,符合张籍“中唐诗人”的身份,但其古诗被列入晚唐的“正变”之列。《唐诗拾遗》十卷为《唐诗品汇》的补充本,选诗人61家、诗954首,补编张籍诗歌13首,选诗亦是相对较多。《唐诗正声》是精选《唐诗品汇》“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5]编纂而成,选140人、诗931首。此时期髙棅宗盛唐观念进一步明显,对元白诗派持排斥态度,白居易诗歌一首未选,但仍选录张籍诗歌15首。康麟《雅音会编》成书于天顺七年(1463),共12卷,选诗3800余首,明人王钝指出:“其为后学启蒙者多矣”[6],该选本选张籍诗35首,仍多于白居易等人。
“弘治时……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7]7348,明中期崇盛唐思想进一步盛行,诗坛普遍对中唐诗歌持排斥态度。其间影响较大的选本有李攀龙《唐诗删》《唐诗选》,孙琴安评价:“李氏一选,声誉鹊起,身价百倍,批注者蜂拥而起。《三体唐诗》《唐诗鼓吹》《瀛奎律髓》等一批名重一时的唐诗选本,均被打入冷宫”[8]。李攀龙推崇盛唐诗歌,排斥中晚唐诗歌,故两个选本张籍诗歌均仅选入1首,张籍诗歌的接受跌入低谷。此外,著名选本还有邵天和《重选唐音大成》,该书编成于嘉靖五年(1526),共15卷、选诗1565首,分为始音、正音、余音,张籍诗歌被列为“正音”,选入18首,略低于王建21首,却也远多于白居易5首、元稹3首。胡缵宗《唐雅》编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全书共8卷,选诗1263首,其选诗推崇雅正,张籍诗歌选入25首。
明代后期,文学观逐渐走向多元,唐汝询《唐诗解》50卷,选诗人200家,诗1546首,该书以《唐诗正声》《唐诗选》为宗,选诗仍推盛唐,张籍诗选入18首,多于王建12首、元稹3首、白居易8首。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成书于崇祯三年(1630),选435人、诗2413首。该选本延续明中期宗盛唐思想,选录张籍诗歌30首。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选诗审美主清空疏淡、含蓄蕴藉,录诗人291位、诗2252首,选张籍诗歌41首,仅次于刘长卿50首,列为中唐第二。选诗出现变化发生在崇祯年间,陆时雍《唐诗镜》选诗人307位、诗3158首,录中唐诗1259首,占总选诗量40%,盛唐诗1114首,占比35%,其选诗打破独尊盛唐的局面,所选中唐诗歌甚至超过盛唐。陆时雍选白居易诗204首,位列中唐第一,超过刘长卿63首;张籍选诗35首,相比前期选诗数量变化不大,但其诗歌地位已经远低于白居易、元稹等人。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为明代后期一部大型选本,《石仓唐诗选》为其中的唐代部分,选诗100卷,拾遗10卷,录诗人1043位、诗10977首,该选本也对中晚唐诗歌予以重新重视,选白居易206首,位列中唐第一,选张籍诗歌148首,王建158首,元稹104首。张籍虽然诗歌选入数量增多,但地位稍显下降,次于白居易、王建等人。
从唐诗选本来看,受明代崇盛唐的复古思潮影响,张籍在选本中的接受经历了前、中期下降,晚期稍有回升的过程。明前、中期200余年间,元白诗派的接受度整体偏低,但张籍诗歌选诗量均高于白居易、元稹等人,为元白诗派接受度最高者。崇祯年间,白居易诗被重新选为中唐第一,张籍诗歌的选录数量仍然保持相对稳定,但诗歌地位稍有下降。
二、重视七古七绝、排斥律诗的选诗特点
辨体是明人的核心诗学观念,如李东阳认为:“古诗与律诗不同体,必各用其体乃为合格”[9]6。对各诗体进行细致的区分,其目的在于树立不同诗体的学习典范,即古诗学习汉魏六朝,近体学习盛唐。在辨体意识下,明人对张籍各诗体的接受度存在差异。兹将明代前、中、后期各3个选本对张籍诗体的选录情况罗列如表2所示。
张籍古诗早在唐宋时期便颇受推崇,南唐张洎《张司业诗集序》称:“公为古风最善,自李杜之后,风雅道丧,继其美者,唯公一人”[10]。宋周紫芝《竹坡诗话》称:“唐人作乐府者甚多,当以张文昌为第一。”[11]通过表2分析发现,明人对张籍七言古诗、七言绝句的选录最多。首先,在所选张籍诗歌中,七古和七绝的占比最大,律诗的选录均相对较少。前期《唐诗品汇》选张籍诗72首,七古选入29首,占张籍总选诗的40%,其七绝选入23首,占比32%;而五言、七言律诗共选入11首,仅占15%。中期李攀龙《唐诗选》仅选1首,为其七绝《凉州词》,其余诗体则全弃不录;后期《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选张籍诗歌30首,七古选诗12首,占张籍总选诗的40%,七绝选诗8首,占比26%;《唐诗镜》录张籍诗歌35首,其七古选入21首,占比更是高达60%。

表2 明代唐诗选本选录张籍诗体情况
其次,在中唐诗人群体中,张籍七古和七绝的选录往往也名列前茅。髙棅《唐诗品汇》选张籍、王建、韩愈的七古各29首,并列为中唐第一;中唐七绝选诗最多者为刘禹锡28首,张籍七绝选诗23首,排名第二。对于张籍的近体,髙棅则评价为“无足多取者”[4]620,评价不高,选诗仅10首。其后《唐诗正声》选录张籍七绝6首,仅次于刘禹锡9首,与刘长卿6首并列为中唐第二。胡缵宗《唐雅》选入张籍乐府诗9首,仅次于王建14首,位列中唐第二。唐汝询《唐诗解》选张籍七绝8首,为中唐第二,选诗仅次于刘禹锡13首。周珽《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选张籍七古12首,为中唐诗人中七言古诗选入最多者。
此外,选本评点与明代诗话对张籍的古诗和七绝评价最高,对其律诗则多持批评态度。髙棅《唐诗品汇》评价张籍古诗“大历已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4]169,认为在中唐中仅有张籍、王建二人的古诗,尚存古意。受明代复古思潮的影响,“古”是一个评价极高的词语。钟惺评价张籍古诗:“法紧气宽,古诗至此,不得以中唐限之。”[12]188陆时雍认为其古诗“稍存雅道”“语近真际”“有古趣”[13]992。髙棅对张籍的七绝也予以较高评价,认为“自贞元以来,若李益、刘禹锡,张籍、王建、王涯五人,其格力各自成家,篇什亦盛”[4]429。而白居易等人则根本不被提及,胡应麟亦称张籍七绝“有可观处”[14]120。徐献忠认为:“水部长于乐府古辞,能以冷语发其含义,一唱三叹,使人不忍释手。……其近律专事平净,固乐天之流也。”[15]明人不喜白居易诗歌平易冗长,格调不高,张籍近体被评为乐天之流,评价显然不高。其后陆时雍对张籍律诗的评价也是“大历以后,五七言律诗流于委靡,元和诸公群起而力振之,贾岛、王建、乐天创作新奇,遂为大变,而张籍亦入小偏”[13]246,将其归属为“变体”之列,明人崇正斥变,其评价也不高。
辨体意识之下,明人对张籍诗歌的接受主要在于古诗而不是律诗,其七言古诗被认为“尚存古意”更接近魏晋古风而备受推崇,而律诗则被认为流于白居易一脉的“变体”,无可多取,遭到排斥。
三、明代诗学观念对张籍诗歌地位的影响
纵观明前、中、后期,张籍诗歌的接受虽有起伏,但其七古、七绝一直最受推崇,其诗歌地位也多高于白居易、元稹等人;仅在崇祯年间,白居易诗歌重选为中唐第一,张籍的诗歌地位才稍有下降。张籍诗歌地位的起伏变化,是明代崇盛唐的时代风气、“正变”诗学意识、崇尚含蓄蕴藉的审美观念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崇盛唐”观念下对张籍诗歌的排斥
明前期,朱元璋主张恢复传统文化,重建盛世,明初大儒方孝孺称:“上方稽古,以兴一代耳目,正彝伦,复衣冠,制礼乐,立学校,凡先王之典多讲之”[16]。受政治、文化环境影响,不少唐诗集重刊,唐诗选本也风行起来,明初文坛已经“透露出一股拟古和崇尚唐音的风气”[17]。高棅《唐诗品汇》诗分四唐,认为“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4]6,主张学习盛唐诗歌。至明中期,以李东阳、李攀龙为代表的前、后七子将宗盛唐的思想推向顶峰,提倡“诗必盛唐”“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7]7307,李攀龙《唐诗选》更是仅选张籍七言绝句1首,张籍诗歌的接受在明代中期陷入低谷。究其原因,缘于明人推崇盛唐并以时代论诗,认为“体以代变”“格以代降”[14]1,故评诗每先依据时代划分,然后再评价其优劣,诗人诗才再好,都不能脱离其所属时代的限制。明、前中期推崇盛唐而贬斥中晚唐,故张籍同白居易、元稹等中唐诗人均属于“吐弃”之列,故选诗较少。
万历以后,社会腐败,国力衰微,士人试图恢复汉唐“盛世”的理想幻灭。同时,社会出现一股反传统、张扬个性的思潮。自嘉靖年间王阳明心学兴起,“其说风靡天下”[18],渐开思想多元趋势。其后李贽“童心说”及汤显祖等人推举“真情”“浅俗”,提倡人性本然之真,有力推动了重个性、重情感文学思潮的形成。《明史·儒林传》载:“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7]7222公安派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不再沿袭“诗必盛唐”的观念,中、晚唐诗歌逐渐受到重视。在此背景下,明代后期,白居易、元稹等大家重受关注,张籍的诗歌数量选录较中期也有所增多,但诗歌地位却有所下降,已位列白居易之后。
(二)“正变”观念下对张籍诗歌的批评
诗之正变是明代重要的诗学观念,“学者审其源流,识其正变,始可以言诗矣”[19]433基本是明代论诗的共识。元代杨士宏《唐音》以正变论唐诗,大力推崇盛唐,《唐音》选诗1314首,分为“始音”“正音”“遗响”。张籍在《唐音》中,尚被列为“正音”,选诗57首,而同时代的元稹、白居易则被列为遗响之列。到明代,崇盛唐观念进一步增强,明人认为《唐音》仍太过于注重中晚唐,故髙棅等人对《唐诗品汇》予以修正,崇盛唐之“正”而斥中、晚唐之“变”,其诗学观念影响了有明一代。《唐诗品汇》明确提出诗分四唐,并将诗歌细分为“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变”“余响”“旁流”九格。在《唐音》中可与王维等人并列为“正音”的张籍在《唐诗品汇》中已属中唐的“接武”,历代评价较高的古诗也沦为晚唐的“正变”之流,其前后变化,可见张籍在明代地位明显下降。但髙棅指出张籍古诗为“抑亦唐世流风之变,而得其正也欤”[4]169,认为张籍古诗已属变体,但仍是变中之“正”者,故对其古诗选录仍然较多。此外,如许学夷《诗源辨体》等诗话称“元和间,贾岛、张籍、王建始变常调”[19]268,也将张籍归类为“变体”之列,评价不高。
诗之“变”会遭受排斥,源于传统认为诗之正变与时世有极大联系。《礼记》:“声音之道,与政治通矣。”毛诗称:“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正音寓意着国家兴盛,变音则是衰世的象征。明万冀《和唐诗正音后序》认为:“诗之于世,虽曰道性情,发心志,然其兴废邪正,实关乎气运之盛衰,治道之隆替。”[20]明前期,朱元璋提倡文学“和而正”,文坛莫不“鸣国家之盛”,至明朝中期也多鸣盛世之音。在此影响下,诗歌莫不尊正斥变,如李梦阳论诗与政治的关系:“常则正,迁则变;正则典,变则激;典则和,激则愤……而其变也,讽刺忧惧之音作,而来仪率舞之奏亡矣”[21]。提倡“典雅”“中和”之诗而排斥“讽刺忧惧之音”,对诗之变持排斥态度。许学夷《诗源辨体》评价元和之际:“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矣。亦犹异端曲学,必起于衰世也。”[19]248张籍诗歌被认为是“讽刺忧惧”“衰世”之变音,不符合“雅正”的典范与盛世之音的期待,故属于排斥之列。
(三)“含蓄蕴藉”审美观念下对张籍诗歌的欣赏
张籍身为中唐诗人而受排斥,却在长达200余年间为元白诗派中接受度最高者,缘于明人对诗歌“含蓄蕴藉”审美风格的追求。明代复古派推崇“诗必盛唐”,在诗歌审美上推崇盛唐诗歌“高古宛亮”“含蓄蕴藉”的风格,认为中唐则是“才力既薄,风气复散,其气象风格宜衰,而意主于清空流畅,则气格益不能振矣”[19]235。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歌则被评价为“浅近冗长”,在明代前、中期遭受排斥。而刘长卿生于盛唐,因其诗歌符合含蓄蕴藉的审美风格而最受推崇,多次被选为中唐第一。张籍诗歌的风格具有多样性,明人认为张籍诗歌具有“俚俗”的一面,对其予以批评,李东阳称“张籍善用俚语”[9]85,陆时雍评价“张籍小人之诗也,俚而佻”[13]13。与明人批评否定元白等人诗歌的观点一致,均因其诗歌“俚俗”“言尽”而多受批评。
但同时明人也意识到张籍诗歌与元、白诸人的不同,髙棅意识到张籍的古诗具有“古意”“古淡”的一面,胡震亨也称张籍“变风犹未失古”[22]。钟惺、谭元春《唐诗归》认为:“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思绪清密,读之无深苦之迹,在中唐最为蕴藉”[12]188。指出张籍诗歌有“含蓄蕴藉”的一面。张籍、王建诗歌选录数量不相上下,但张籍往往居于王建之上,许学夷《诗源辨体》指出:“二公乐府,意多恳切,语多痛快,正元合体也。然析而论之,张语造古淡,较王稍为婉曲,王则语话痛快矣。且王诗多,而入录者少,故知其去张实远也”[19]267。其评价的核心仍在于主张诗歌“含蓄蕴藉”,且注意到了张籍诗歌的风格具有质朴古淡、婉曲蕴藉的一面,故张籍诗歌选录较王建多。也正是因张籍诗歌较元白含蓄蕴藉,故成为元白诗派中接受度最高者。
受复古思潮推崇盛唐诗歌的审美倾向影响,张籍诗歌被批评浅俗;明人正变诗学观念下,张籍诗歌被归入变体之列,与衰世之音联系,故被排斥。但另一方面明人又认识到张籍不同于元、白等人,认为其古诗“古淡”“含蓄蕴藉”,故形成了张籍在明代的接受稍有起伏,但相较元、白等人接受度最高的面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明代对于张籍、白居易等人的诗歌的接受呈现明显的时代化特征,明前、中期带有普遍化、极端化的诗学观念之下,明人对张籍、白居易等人的批评更多指向的是其时代风格,只有明人具体到诗人个体之时,才能发现张籍“蕴藉”而有别于元、白诸人的特点。